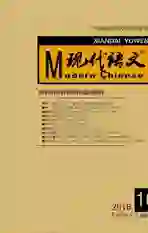《红高粱》战争描写的人性视角
2016-05-30胥岩妍
胥岩妍
摘 要:传统战争小说注重揭示战争的残酷和破坏性,从而表达人们对战争的厌恶之情,以及对安定与和平的渴望,对来之不易幸福生活的珍惜。而战争造成的流血和死亡被挂上英雄的勋章,荣誉成为了疗伤的灵药,崇高的光环掩饰了战争带来的创伤。莫言的描写直面血淋淋的战争场景,并从战争对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的影响入手,通过人性的角度来解读战争。
关键词:《红高粱》 战争 人性
传统战争小说通常以惨烈的战争场景震撼人心,让人的记忆停留在血肉横飞的战争记录中。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往往从国家安危、民族大义的高度出发,被塑造成一种高大英勇、不畏牺牲、勇当大任的光辉形象。荣誉的光环笼罩着战场英雄,鲜血与死亡是忠诚与英勇最好的证据。模式化的英雄人物和战争描写充斥着传统的战争文学,莫言的《红高粱》以一种新的视角,站在人性的角度去更好的解读战争,让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战争,以一种新的视角去观察战争。
《红高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片黑色土地上的红色故事。在墨水河边打死鬼子少将的著名战斗,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大背景。这个背景就像是盛着高粱酒的大酒坛,这片高粱地上的人和事仿如那千千万万的高粱,这人与事的交织仿如那酿成了的高粱酒,这个酒坛装满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这个酒坛承载了那一代人的生存状态,“我奶奶”一生的传奇沉淀在了这个酒坛中,“我爷爷”一生的豪气被这个酒坛记录着,“我”那罗汉大爷的悲惨终结沉入了酒坛深处,“我”家的大黑骡与罗汉大爷相伴着栖息在了酒坛中,“我”的那些乡亲们、同“我爷爷”战斗的那些弟兄们,都一同地在这酒坛中实现了永远的团聚。战争这个大酒坛,让人们彼此的故事有了牵连,让人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酿造香醇来填充它。
莫言一改传统战争描写的宏大叙事模式,不重战争过程和战争结果,而是以战争作为背景和线索,将人的故事作为重点,填充战争的骨架,从“人性”视角入手,去观察战争状态下人的最本真的状态,以及战争对人性的影响,从而引发人们对战争破坏性的深层次思考。就如莫言所说的“小说家写战争,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我们就是要从战争所揭示的人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入手,在战争所造成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之外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
一、人性的赤诚状态
罗汉大爷可以算作是“奶奶”家的忠仆,这样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却遭受了世上最残酷的死亡方式。罗汉大爷为了保住“奶奶”家的骡子,惹恼了鬼子,头皮被锋利的刀刃开了口子。骡子被迫牵到工地后,罗汉大爷还不忘叮嘱工人“你珍贵着使唤,这两头骡子,是俺东家的”,罗汉大爷满心都是自己的东家,还有东家珍贵的骡子,一时间他忘了自己头上的钝痛,也不在乎自己的话是否会惹恼鬼子。罗汉大爷遇到了一个绝好的逃跑机会,本已经离开的他却因为东家骡子的一声嘶叫折了回去,就此错过了唯一的一个机会。然而黑骡却认不出遍体鳞伤的罗汉大爷,拒绝离开。本是要救骡子离开的罗汉大爷,不能容忍自家的骡子变成吃里扒外、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用铁锹向骡子发泄愤怒。因为骡子错失离开良机的罗汉大爷,最终落得一个被生割活剥的结局。
罗汉大爷是这黑土地上的小老百姓,在“奶奶”家安安稳稳地做着长工。但是他忠于这个家的一切,必要的时候不惜付出血的代价。他为了东家的骡子,不惜再次身陷险境,这个朴实农民用自己的鲜血,在这片黑色的土地上书写绚丽的忠诚。但是面对不识自己、里通外国的黑骡,刘罗汉发自内心深处的愤怒让他忘记了处境,忘记了恐惧,哪怕丢了性命也要处置忘恩负义的叛徒。没有人教导过刘罗汉家国大义,源自他灵魂深处的自觉让他忠于自己的家自己的国。他不为留名千古,只为忠于内心的选择。面对生与死的抉择,人性方显其真面目。战争以检测者的角色,以最严格的标准,检验着生活在东北乡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让他们以最为赤裸的状态呈现自己。
二、人性的本真状态
“我奶奶”为了给惨死的罗汉大爷报仇,邀请冷支队长和余司令来商量。“奶奶”说道:“后日一起把鬼子汽车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1]并毫不含糊地像男子一样,咕咚咕咚地喝了掺着罗汉老爷血的高粱酒。将罗汉大爷视为亲人的“奶奶”张罗报仇一事展现了她直爽、率性、英气的一面。而奶奶自然朴实的语言,流露出她心中的大义:“买卖不成仁义在么,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2]这是一种自觉的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不需要刻意的灌输和提醒,在遭受侵犯时这种意识会主动地觉醒,充斥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灵魂,这就是在战争状态下观察到的深度灵魂状态。它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这就是新式战争小说以战争视角解读人性,从人性角度反思战争的意义所在。
胆小、迟钝的王文义在余司令打鬼子的队伍里就像一个笑话,但是王文义进入游击队的理由却是严肃地直戳人的心窝。王文义的三个儿子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成了碎块,不分左右、胆小怕死的他被妻子送到游击队的队伍里。丧子之痛、血海深仇——这就是王文义当游击队员的原因,纵使他害怕死亡,自己不是當兵的料,也要留在队伍里,见证一个鬼子的死亡,便是对他死去儿子的一份祭奠,这是慰藉他们在天之灵的唯一方式。之后亲眼目睹妻子惨死的王文义,跳出保护屏障,将自己暴露在鬼子的视线中,高喊着“孩子他娘”死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面对妻子的死亡,王文义的心也死了,他心中的爱与恨混杂交织,心痛、绝望与仇恨一齐涌上心头,冲昏了他的理智。在战争与死亡面前,人的心灵与精神状态被赤裸裸地披露,残酷的现实衬托了人性的真实。
在这片高粱地里,杀人越货的那一批人,同时也是精忠报国的那一批人。在战争面前,土匪和英雄的本色,在同一批人身上彰显。“我爷爷”余占鳌司令杀过人抢过亲,实在算不上什么正道人,被称作土匪头子一点儿都不为过,但是官职、地位、好名声都收买不了他。“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3],这便是横在“我爷爷”心中的一把尺子。余占鳌强劲有力的话语,揭示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人们不管自己处在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来赋予他们任何使命。他们为了自己心中的爱恨情仇在高粱地里穿梭,这样的生命状态,不禁让现在的人汗颜。这种自发的斗志,无形中嘲笑着推脱的不肖子孙。历史车轮的前进,并未必然地带来物种的进化,这是战争揭露的事实为我们引发的又一思考。
三、人性的扭曲状态
孙五在鬼子的威逼下用杀猪刀零割活剥了罗汉大爷,这段惨绝人寰的酷刑在作品中的刻画让人不忍卒读,而孙五却是亲手行刑人。他将作为屠夫的一身本领施展在了自己的同胞身上,在此之后精神错乱,再之后便口歪眼斜,鼻涕口水淋淋漓漓,话也说不清了。在生与死面前,善与恶的抉择就变得分外艰难。我们无法评判孙五在面对死亡时做出的选择,我们只能说他的结局是他得到的应有的报应,而孙五作为战争的牺牲品,也只是一个可怜人,这就是战争造成的人性的扭曲。战争以一种绝对的权威来施展自己的魔爪,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直面死亡,所以难逃魔爪的人其内心在不同程度上都会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就如高粱地里弥漫的浓烈的腥甜味,它不仅浸透了人的感官,更是浸透了人的灵魂,它在残忍的岁月里伴随了“我父亲”一生——终其一生,他无法摆脱。
战争带来的伤害从来不只限于肉体,心灵上的伤痕更为刻骨。人性有时便在战争的逼迫下走入歧途,被扭曲的面目全非。
四、人性的丑陋状态
冷支队长满口答应帮罗汉老爷报仇,并向“我爷爷”放出了鬼子汽车路过的情报。“我爷爷”带着那支连瘸带拐、连伤带病不到四十人的队伍埋伏在河堤里。这样的一支队伍,兵力不足、装备简陋,然而士气高亢,战斗顽强。“爷爷”喊一声打,响应者寥寥无几,最后打到了这个地步,每一個死去的人都是铁打的英雄,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钢筑的好汉,他们用生命守卫着脚下的土地,用鲜血染红了挚爱的家园。这场仗打得异常惨烈,队伍里的人死得不剩几个,鬼子也元气大伤,这时冷支队长带的兵才出来收拾残局。冷支队长大模大样,假情假意,面对余司令惨死的兄弟作秀似地鞠了一躬。面对共同的敌人,冷支队长将私心放到第一位,看两方相斗,坐收渔利,而同胞的性命只是他谋权得利的筹码。什么是英雄,什么是正义,冷支队长打着保家救国的旗号,干着残害同胞的行当。在战争中,有些人的本性发生了彻底的变异,人面对流血和死亡可以无动于衷麻木不仁,那些丑陋的真相被无情地揭露,冲击着人的道德和良知。
五、人性的张扬状态
整个故事是在战争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战争场景的刻画描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奶奶”和“爷爷”相识相伴的传奇故事穿插在紧张、血腥的情节中,他们为我们还原了一种人性的原始的张扬状态,让我们被这种人在残酷的环境中对于自我、对于爱情、对于生命的意义的追求所震撼。“我奶奶”十六岁时被迫嫁给了麻风病人单扁郎,但“奶奶”盼着自己能有一个“识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热”的好女婿,不愿自己的一生就这样荒废在这样一个了无生气、毫无希望的家,“奶奶”抱着一颗毋宁死,不苟活的心,“上马金下马银”的日子也动摇不了“奶奶”的坚定决心。在“奶奶”看来,作为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追随自己的心,勇敢地爱,勇敢地活,舒适的生活完全撼动不了“奶奶”坚守的心。所以“奶奶”才能不惧世俗地同“爷爷”在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以高粱般火红的热情燃烧自己、释放自己,寻求心灵真正的归属。就如奶奶濒死的质询:“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4]这段是奶奶一生情感的释放,奶奶热爱生命,渴望幸福,在追求幸福的路上,她不怕采取离经叛道的方式,只要幸福肯来眷顾,罪与罚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在“奶奶”身上,闪耀着追求自我,渴望自由的光芒,在一个旧的时代,她身先士卒地树立了典范,以超越的精神做出“新”的表率。莫言在一次讲座中提到“我想,作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首先是一部感情的历史。人性很难用经济和政治的方法来分析,只能用感情的方法分析……进行一种人性化的表述”[5]。红高粱这段历史,就是莫言笔下的一部感情的历史,他以一种剥离的方式来写战争中的人,通过人在战争中的表现,来进行对人性层面的深层次的解读。
与“奶奶”相对的便是“我爷爷”,“爷爷”原本是个优秀的轿夫,但自从不小心看到“奶奶”玲珑的小脚后,他心中的情感便泛滥的一发不可收拾,他灵魂深处的野性与狂放由此被唤醒,自此这片黑土地上便多了一个匪气十足的英雄人物。“奶奶”激活了“爷爷”向往新生活的热情,“爷爷”便从杀人越货开始走向了通往新生的路,“爷爷”的命运是由“奶奶”改变的,“奶奶”唤醒了他沉睡着的种种本性,造就了一个出入在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中的英雄人物,这个英雄在守护自己所爱的人的同时,也让这片红高粱的土地上又多了一个守护者。“爷爷”的感情自遇到“奶奶”才有释放的机会,而他性情的真正面目才得以彰显,并在艰苦的奋斗和艰难的挣扎中延续了下来。
“奶奶”是个知恩图报、有情义的女子,她为了给罗汉大爷报仇牺牲在了战争上,她柔嫩肩膀上深深的紫印是她光荣抗争的标志。“奶奶”生命走到尽头之时,她只是遗憾自己的一生没有活够,但并未抱怨自己生命意外的终结。在不舍与豁达的情感相对比时,方显“奶奶”本性中的纯净与美好,这便是人性最美的港湾。而“爷爷”只是一介草莽之人,不懂大义,但在情与理面前还是站在了理的一边,因为他要为了自己的那支队伍负责。血性之人本应更重情义,但是为了大局他要杀了养育自己的亲叔。在恩情和法理的对决面前,方显“爷爷”本性中的顾全大局和重情重义,这便是人性赤诚的所在。就像一些作家在创作中奉行的“第一是‘人写得好不好的问题,人写好了一切大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我的创作目标,就是无限利用‘人和‘人性的分量,无限夸张‘人和‘人性力量,打开人生与心灵世界的皱折,轻轻拂去皱折上的灰尘,看清人性自身的面目,来营造一个小说世界”。[6]这便是战争小说中以“战争中的人”的视角切入的重要性,人性的状态是对战争最有力的批判和控诉。
人性在战争面前的不同状态被赤裸裸地揭示出来,真实的人性直击我们的灵魂,它的冲击力不亚于血淋淋的事实。莫言对于战后场景的描写是直接的,还原了战后惨状,他以图景式的描写,用最大的力量,冲击着人的内心。“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头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地浸泡成稀泥。”[7]越是这么直接地直面鲜血和死亡,越是能解释那种迸发自内心深处的爱恨情仇。雷达说自己在读《红高粱》时,“我体验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怵和惊异:震怵于流溢全篇的淋漓的鲜血,那一直渗沥到筋骨里的感觉;惊异于作者莫言想象力的奇诡丰赡,在他笔下战栗着、号叫着的半个世纪前的中华儿女,不仅是活脱脱的生灵,而且是不灭的魂灵”[8]。雷达从残酷现实的描写走进真实内心的描写,从战争实况走向人性原貌,在双重的震撼力下感受战争的别样写法。
“战争文学如果不单独描写战争过程,而能通过这一过程写出其对人的命运、生存状态、精神走向等的深刻影响,让我们从中听到人性的阐述,看到灵魂的历险,它便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人的文学。优秀的战争文学,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9]《红高粱》借以高粱的形象揭示了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走向:火红的高粱地象征着蓬勃向上的生命。“一颗高粱头颅落地”,便象征了生命的终结。这毫无准备的一幕,展现了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王文义“司令——我没有头啦——”的惨叫,揭示了人们面对无常命运的恐惧。“鲜嫩的高粱在铁蹄下断裂、倒伏,倒伏断裂的高粱又被带棱槽的碌碡和不带棱槽的石滚子反复倾轧。”[10]高粱被倾轧的惨状象征了惨遭蹂躏的人们,战争让人的肉体流血,让人的心千疮百孔。在战争面前,再绚烂的生命也感动不了无情的战争。生命的终结彷如高粱穗坠地那般随意,越是看似不经意的描写越能触动人的内心。在战争的大背景下,人们在火红的高粱地演绎着生命的传奇故事,穿插的每个情节都在揭示人的状态上独具内涵,我们在聆听人性的阐述中,体味着灵魂的历险记。
注释:
[1]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25页。
[2][3]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24页。
[4]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64页。
[5]莫言:《我的文学经验:历史与语言》,名作欣赏,2011年,第10期。
[6]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褶皱——苏童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第2期。
[7]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4页。
[8]雷达:《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文艺学习,1986年,第1期。
[9]黄修己:《对“战争文学”的反思》,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10]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