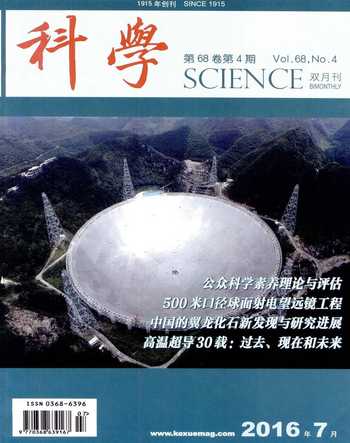守望医学入文桥头堡
2016-05-30方益防
方益防
百年妇产学科的发展表明,每当生命科学新技术面世,首先遭遇医学伦理挑战的学科,就是妇产科,但直接体现生命科学人文素质的,也是妇产科。
自人类先祖萌发生、死概念,生殖意识和生殖器崇拜随之产生。新石器时代,婴幼儿尸体瓮棺葬并在陶器上凿孔,是先民期盼生灵回归,生命繁衍,将生育概念与社会进程原始对接的证据。当人口增长和生产力水平矛盾时,华夏文化中的性别选择和溺婴现象,本质是生育、接产等妇婴技术的成熟体现,却与原始部落生存状况和日常习俗发生首次冲突。学术上,此类文化现象不属妇产科社会角色研究的领域。本文苇点讨论1835年以后,现代西医来华后形成的建制化妇产学科发展与社会进程交集案例。
目前,我国注重妇产科人文价值和社会担当的领军学者,当属协和医科大学郎景和院士。2013年,他出版的《一个医生的非医学词典》,是近年医学人文领域不可多得的专业文本。2015年,他又推出《一个医生的故事》,记录“150个有温度、有笑有泪、真实无比的医院生活”故事。基于学科的特殊性,妇产科界的白‘年医学人文气氛,始终领先医学同仁。协和医院向阳教授等集体为中国妇女出版社编撰妇女健康系列;上海交大医学院狄文教授团队着重妇产科史的学术整理;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打造多媒体“段涛医生”;曾任上海红房子妇产科医院院长的邬惊雷教授,直接负责上海医学伦理学会,将相关工作融入医疗行政管理宏观决策。
妇产专家直接介入社会事务,显示医学人文关怀的拐点出现。每当生命科学新技术面世,首先遭遇医学伦理挑战的学科就是妇产科,全方位直接体现医学人文素质的也是妇产科。既要应对前卫技术冲击下的敏感社会伦理,还要充当生命学科与社会冲突的平衡角色。因此,视妇产科为医学伦理冲突桥头堡,这个新生概念是基于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概括,更是现代医学与社会发展直接碰撞后,星火四溅和伦理调适所需的缓冲抉择。
晚清西医建制化中。
女性医师对妇幼事业的贡献
1920年代,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将女性留学的处女行定格于1914年的庚款赴美,大大低估了清末女性踊跃留洋,学习、从事妇幼医学的史实与规模。1885年,宁波籍妇产科医生金韵梅在纽约获医学学位,稍后留学美国的有福州籍妇产科医生许金訇,以及九江籍医生石美玉和康爱德等。她们是各地教会资助下的早期首批医学女专家,学成海归后在国内培训了一大批巾帼专业人员,使之成为从事医疗服务的先驱团队。海内外培训出来的女性医务人员主要活跃在妇产科和儿科界,她们是中国医学史上妇女独立行医的开拓者。
比1914年旅美更早的女留学生,还包括首位哈佛博士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1913年,23岁的大龄单身女性杨小姐获得留学日本机会,独自艰难地完成6年制严格医学专科培训。回北京后,杨步伟设森仁医院,兼任妇产和小儿专科大夫,其专业女性的特征,赵元任爱慕至极。
在世俗的适婚年龄,杨步伟没有首选相夫教子,却远赴海外求学,独立生活与工作能力兼具的现代女性新形象,成为时代风景。以笔者家族的私人档案为例,清末民初,女性留学风潮甚至影响到了浙东沿海的小城镇。一些富裕且开明的家庭,支持女性后裔留学日本习医,归国后服务家乡父老。当地民众普遍接受新式妇产科服务,展现民风渐开的时代改革特征。
除留学海外,清末国内各大城市,也在教会支持下,纷纷开设自己的西医培训机构,其中以广州教会学校培养的女性妇产科医生最多。1879年,广州著名的博济医院附属博济医学堂开始招收女生,这批实习医生成为学堂教授妇产学科的主要对象。全国先后成立的还有广州夏葛女子医学校(1901年),北京协和女子医学校(1908年),广州赫盖脱女子医学专门学校(1909年)等,培养了大批妇幼诊治和保健护理人才。这些教育机构既顺应潮流,呼应了当时世界各地掀起的女权运动,也为知识女性争取了职业权利。女性妇产科医生的批量执业,契合华夏文化中的性禁忌,也符合人类古老文化中,女性身体尤其私处,不得暴露于男性的传统观念,一定程度催生了女性妇产科医生群体性崛起。
值得归功于妇产科医生的关键社会贡献是,西医逐年东进带来的理念更新,促使中国社会开始对产婆、消毒、育儿乃至独身等社会模式严肃思考。每次医学新概念的引进,旧式家庭与传统社会必将经历从意识形态冲击,到事实认可的进步轨迹。医学女性的历史贡献,实质上大大超出医学范畴。
比如,金韵梅大夫在女性着装的改良方面,引领时尚生活,精神风貌独树一帜,其职业妇女的特殊影响力进入了妇女的日常领域。许金訇大夫则直接介入政治生活,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国际会议。盛誉许大夫为近代女性政治先驱,似也名符其实。许多女性大夫和医护人员洁身自好,自愿选择独身方式,以便最大限度服务社会,这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女性独立精神的表达。种种细节表明,在晚清时节的沿海中国,前卫知识女性的集体行动与世界女权运动,没有完全脱节。
晚清西医东渐中,
男性医师从事妇产科临床实践
1886年,孙逸仙刚满20岁,香港中央书院尚未正式毕业。经他的美籍受洗牧师喜嘉里(C.R.Hager,又译哈格)介绍,转学广州博济医学堂专攻西医。自1835年耶鲁大学医学博士伯驾(P.Parker,又译派克)设立博济医院的前身博济医局起,半个世纪以后,博济管理方积累珍贵的西学东渐经验,懂得洋技艺也必须融汇中国本土文化。所以,他们在教学中严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规矩,禁止男生进入产房学习婴儿接生和妇产科疑难杂症。为此,孙逸仙对同学中的四位女生很羡慕,他向时任院长嘉约翰(J.G.Kerr.又译克尔)建议,“学生毕业后行医救人,遇有产科病症也要诊治。为了使学生获得医学技术,将来能对病者负责,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规定”。
毕业于费城杰克逊医学院的嘉约翰头脑开明,其实他内心也主张按当时西方医学院标准,系统培训学生技能。于是,嘉约翰顺水推舟,允许男生参加所有妇产科的教学活动。尽管一年后,孙逸仙转学香港西医大学堂(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但博济医学堂经过孙逸仙的呼吁,催生了清末首批妇产科男性精英,他们可称作中国最早的男性妇产科学员,即最早的男性妇产科实习医生。
孙逸仙呼吁医学院男生从事妇产科,首先是思想解放的体现,认同男女平等观念。另一方面,他了解社会底层,深知仅依靠传统的产婆等民间习俗,无法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生育危机。1892年7月25日,香港中国邮报(China Mail)载登香港西医大学堂康德黎(Dr.Sir J.Cantlie)院长的毕业祝词,从中可以看出前辈医者对孙逸仙等首批男性医科生从事妇产科的鼓励和推动。“经过五年的辛劳,现在我们毫无保留地把我们的劳动成果无私地奉献给伟大的中国,因为在目前的中国,科学还鲜为人知,也没人懂西医;外科手术亦没人尝试过去做,只有巫师神婆横行,谎称能治病救人,害得成千上万的产妇枉死,婴儿夭折”。
1892—1894年间,毕业后的孙逸仙全职行医澳门2年。史料表明,期间他对妇产科相当关注,孙逸仙懂得利用媒体做宣传,他在葡萄牙文的《澳门回声》上刊登为外籍女性处理难产,大功告成的医案,广告自己从事妇产科的宣传资料。据此,称孙逸仙为良医,而且为中国男性妇产科执业先驱,所论有据可依。
从伯驾西来,到逸仙行医,西医在华发展了一个甲子,形成了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现代医学试验田,现代医学中国化考察理应以此为起点。1842年,博济医院的首例产科手术,由伯驾为中弹负伤的孕妇操刀,其门生关韬,又名关亚杜(Guan Yadu或Kuan Ato)现场辅助。
1857年,与容闳、黄胜一起留学美国高中的黄宽,辗转英国,最终成为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回国后先后任职广州惠爱医院、私家诊所和博济医院。在西医分科笼统的早始阶段,有“好望角以东最佳医生”之称的黄大夫,处理难产和女性疾患,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
博济医局早期雇佣著名画师关乔昌,又名林官(Lan Qua),记录了大量广州地区女性特殊病例的写实画作,这是其侄子关韬和老师一起从事妇女病研究医治的直接证据。笔者期待更多新史料面世,不断考证中国男性妇产科第一人,将实证依据推向更早、更扎实。此项医学人文追踪,是发掘国人破旧立新、反抗世俗,华夏拥有创新基因和开拓勇气的新证据。
近年来,个别娱乐媒体推出以窥视男性妇产科医牛为卖点的商品。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主创人员在性别与医学认知上趣味低下,其人格、视野比100年前还要落伍。此类商品仅为迎合大众对妇产科男性的好奇与调侃,格调不高,没有正能量。避孕技术的“蝴蝶翅膀”,引发女性意识苏醒
大多数生命科学的创新都与妇产科领域发生或多或少的关联。特别是,当人类社会纠结于生育还是不育、怀孕还是流产、性交还是性病,解决上述两难选择的技术发明成功后,随之而来的冲突,往往首先表现在与宗教团体的格格不入。性,或者基于性的私人化家庭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与宗教约束、社会习俗发生正面冲突,妇产科专业技术问题立即衍生为社会公共问题。
17世纪中叶,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御医康德姆(J.Condom),发明了鱼鳔阴茎套,史称“愉快的发明”,用于防止怀孕,缓解了主观性爱享乐与客观生育难题的冲突。几个世纪下来,在妇产科等生殖领域专家的共同努力下,随着避孕套概念、选用材料与制造技术不断革新、拓展,避孕套事实上已大大超越防止怀孕的原始初衷。在解决公共卫生和社会危机中,这层轻巧的薄膜起了决定性作用,有效阻止了从梅毒到HIV病毒的传播,降低了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带来的家庭破坏和社会崩溃。当下学界将避孕套更名安全套,不是简单的修饰调整,更是蕴涵了科学、医学和社会学的与时俱进理念与价值判断。
1879年,纽约出生的山额夫人(M.Sanger),年少时目睹母亲怀孕18次,生产了11个弟妹,毅然决定参加护士培训班,幻想发明“神奇药丸”,解救不停怀孕的妇女。她发起节育运动,积极伸张女权,普及妇女避孕主张和技术。
适逢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山额的节育呼吁成为大家庭容易接受的舆论支撑,人们私下直接挑战教会,不许堕胎的传统禁令威力减弱。山额说服生殖生理学家平卡斯(G.Pincus),研究利用荷尔蒙帮助怀孕或协助避孕的技术。这项与当时的美同法律直接冲突的秘密研究,直到1960年5月9日才获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临床应用。口服避孕药异炔诺酮上市标志着妇产科与宗教权威,以及世俗伦理的冲突,再一次交战,又一次获胜。
相比而言,伴随妇产学科发展起来的性学,自出世之日起,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冲击力,比避孕概念及其产品推广来得更为猛烈。19世纪末起,两方冠以性学之名的著作通过与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的交叉、整合而不断涌现,于1939年公布的震惊世界的《金赛性学报告》,其社会冲击力一时抵达顶峰,其本质原因是男女平等的号召力。
1791年,法国大革命妇女领袖德古热(O.de Gouges)发表《女性与女性公民权宣言》,“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如果说,此话仅仅揭开了女权运动的理论序幕,而上述避孕科技和性学知识,则为女权信奉者提供了实质性武器。自此,大批新式女性从床帏和厨房中被解放出来,进一步诱发和壮大了女权革命规模。女权意识从边缘进入主流,补充了完整的人权含义。女权运动从个人和局部抗争,渐渐转变为大规模有组织的社会抗议,女性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妇产科具体落实的控制生育、性病诊治,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社会进程,保障了女性人权。与妇产科相关的医药开发、临床医学和尖端研究,不是简单的技术性活动,而是重新从社会生活中,争回女性的社会地位。
中国近代的性知识传播,最早可追溯到民国初期的张竟生和稍晚的潘光旦。1949年后,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性学科普读物,要数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1955年首版的《性的知识》。截止1981年,正版发行总数达560万册,堪称出版界奇迹,也折射出几十年的性压抑影响之广。其中,王文彬就是协和医院妇产科医师,几位作者不仅是突破社会禁区的性学大师,更是指导千万生灵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最后一丝人性的活菩萨。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科学画报》重新提倡性科学,当年第一期刊登了郎景和医师的《新婚性卫生》,标志着“文革”后再次打破一道舆论禁区。仅靠一位妇产科专业新人,就造福千万对懵懂“新人”。
完善伦理约定,为细胞克隆和生物合成定规矩
“你关心医术,我在乎人性”是笔者近年演讲的主旨,我们正处于妇产学科与现代尖端技术再次发生伦理冲突的时代。
1951年,在避孕药研究中大有斩获的平卡斯,通过体外授精,从培养皿中成功获得实验兔胚胎。这项先驱性的生命科学成果的萌芽,在“上帝创造一切”的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无疑是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即使一贯主张自由精神的哈佛大学,也迫使平卡斯离职,以暂时平息各界的争议。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人工体外授精技术的成功,导致科学共同体在器官移植(包括体内人工受精)技术之后,再次意识到《纽伦堡宣言》和《赫尔辛基宣言》等指导原则的重要性。受到上述医学伦理规范的生命科学,其范畴涵盖从生殖到死亡,从药品到食品,学科分支极广。但妇产科涉及的技术路径,基本上伴随着辅助生育、遗传性疾病诊断、干细胞技术、克隆技术和近年的基因编辑技术等,临床研究且行且调适,妇产科学的发展无法置身事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遗传学逐步成熟、DNA学说建立。这些基础理论的突破为此后的优生优育、试管婴儿、产前诊断,直到21世纪发展起来的体外受精联合胚胎移植技术(IVF)、胚胎干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iPS)、无性生殖或孤雌繁殖、体细胞克隆、代孕母亲、定制婴儿、基因编辑改良人种、计算机辅助设计合成生命体等等奠定了基础。这些技术逐一在临床上获得成功,或者在实验室预告即将面世,人类社会确实到了需要严谨规范生命科学研究的理性阶段。这种科学共同体盟约,初衷在于适应人类社会伦理,并非全面叫停有关的生命科学探索,更不能成为利益集团玩弄科学政治的堂皇借口。
21世纪生命科学技术的研发不再是一个小组、几个专家的封闭探索,大型课题多层次协作已成为主流模式。产业资本与政治决策参与其中,使得20世纪制定的医学研究伦理基本原则,或者在这些原则上修补起来的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HUGO)等一系列声明,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都显得不堪重负。
笔者跟踪研究的2005年震惊中外的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干细胞克隆事件,则代表了前所未有的伦理冲突新动向。表面上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冲突,实际上是东西方政治经济综合势力的一场利益博弈。西方科学共同体揭露黄禹锡实验室违规操作,不当使用研究团队女性成员卵子,违背四大基本原则开始,使代表东方干细胞研究水平与产业能力的韩国的业已启动的生命产业研发工程轰然塌陷。而短短两年后,美国、日本等类似研究团队,先后在黄禹锡工作的线索上宣布跨时代的iPS细胞获取路径,人类可以规避适应了几百万年的生殖细胞模式,让生命再次循环。原本距离韩国一步之遥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花落他家一去不返。直到10年之后的2014年1月,英国《自然》姗姗来迟,回顾、总结了这项生命科学与国家利益博弈的新世纪较量,宣称“黄禹锡再度辉煌回归”,尽管硕果累累,但今非昔比。
未来几十年,借用科学家预测的2045年为界线,合成生物与人类寿命大限将破。但交叉学科领域的技术与理念即使有创新,涉及生命的手段再花哨,也终究离不开生殖器官和内分泌系统等女性医学,妇产科难以独善其身,还会继续代表医学,成为介入社会运转的先驱,不断与来自资本、政府、法律、家庭、伦理、舆论等多方利益集团周旋,任重道远。
或许,正是因为历史青睐妇产学科,赋予它哲学探索的时空机遇。妇产科的学术进步一方面辅助了人类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种群优势,另一方面在医学伦理规范和社会伦理调适的桥头堡上,成为终极守望的先头部队。但是,担当这项历史性社会责任,不仅仅只有妇产科挺身参与,而应该延伸、定位到医学人文和医生整体,当下社会需要更加明确清晰、层次立体的三级医生构成。
首先,心怀生命敬畏,按程序规范接诊、循证,规避过度诊治的,就是雪中送炭的好医生。他们是构成医学匠人层面的绝大多数,是托底社会基础医疗的仁术网络。他们与芸芸众生休戚相关,是拥有悲天悯人菩萨心肠的悬壶济世者,承担救死扶伤、安抚心灵的总体需求。
其次,在这批日夜忙碌于治病救人的医学人中,从来不乏精力旺盛,在执业间隙挤时间寻求精益求精新医术,悉心探索医学前沿的研究者。世俗社会不能刻意要求每位医者都额外付出,成为攻克疑难杂症的学术奉献者或科学志愿者。但是,在传染病、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现实中,近几十年发病率下降、死亡率下降、生存质量提升,确实归功于这批医学精英的悉心研究。全社会理应从上到下,从舆论到法律,鼓励患者及其尊重信赖医务人员,而不是以行商贩贾对待之,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共识。
最终,我们务必理解,能够同时兼具人文情怀与哲学素养的医学精英,实际上少之又少。到达医学认知顶层,不仅需要医生个人的悟性和厚实的跨学科知识储备,更需要优厚的工作条件和各种不期而遇的人生契机。在以论文数量、病床周转、甚至微笑程度作为制度设计的当下医疗体制中,只有超脱了杂务羁绊的医学精英,才有可能最终升华到宏观豁达、技术与人文和谐交融的艺术境界。唯有身心自由解放,才是科学研究带动学术创新的前提,中国医学界大师级精英,才有可能源源不断脱颖而出。
鼓励执业医生跳出医学看社会,重视医学人文思考的可敬之处在于,他们往往主动奉献了大量时间精力,却挣不到所谓的学术评估“影响因子”。当下民众常常将现代医学误会成包治百病,平常的医学常识难入千家万户,与孜孜不倦写作大众阅读文本的医学大帅少之又少,不得不说是关键原因之一。而只有打通了学术与人文沟通密码的医学精英,才会深刻理解医学与社会、伦理、人文和情商的内在联系,才会深深融入其执业灵魂。
必须承认,世俗社会中权威的影响力是客观存在的。假如正牌专家不主导医学科普舆论,事实上就是为胡说八道的蛊惑之言提供生存的时间和空间。在伞民医保的宏观设计中,医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有必要改善修订目前的医学考核标准,从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开始,医改成功方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