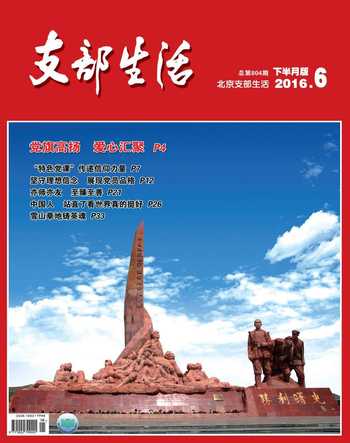雪山草地铸英魂
2016-05-30郑京湘谭梦齐士英王砚文余琦景陈艾迪
郑京湘 谭梦 齐士英 王砚文 余琦景 陈艾迪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带着胜利夺取泸定桥的豪迈,开启了长征中艰苦卓绝的一段征程。
四川省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念碑直冲云霄,在阳光下披着金辉。金碑顶端,立着一座雕像:身穿羊皮背心、手握步枪和鲜花的红军战士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铜像下的三角立柱上镌刻着巨大的红五星。这颗曾镶嵌在红军战士八角帽上的红星,铭记了工农红军留下的闪光足迹,更昭示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长征精神之魂。正如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志所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千古江山,英雄辈出,惟万里长征举世无双……”
川西北高原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雪山连绵、草地无垠。1935年至1936年,红军曾在这里数度翻越雪山、跨过草地,举行过重要会议,进行过激烈战斗。“长征苦,最苦是雪山草地。”采访中,每一位经历过雪山草地的人都用了一个“苦”字。81年前,红色大军的雪山草地之行,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一次行军。
向北,雪山那边是战友
春日,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仍被皑皑白雪覆盖,蜿蜒于雪山之间的公路亦是冰封难行。报道组一行翻越这座被称为“神仙山”的大雪山,重峦叠嶂、云海翻腾、雪粒打面,在高原反应、头晕气喘中感受着81年前那支红色队伍不惧艰险、攀爬雪山之巅的惊世壮举。
1935年5月的最后一天,红军夺取泸定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泸定县城内召开。此时,踏着摇摇晃晃的铁索奋勇冲到大渡河对岸的红军将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与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会合。
从泸定向北有三条路可选:西面,一条马帮走的小路通往川北的阿坝,但路程较长;东面,一条大路,沿途是人口稠密的城镇,虽可直通成都,但路上敌人重兵把守;还有一条路,就在东西两条路之间,需要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人迹罕至,连马帮也很少走。中央红军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条路。
此前,国民党企图凭借无法逾越的大雪山来阻挡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而翻越夹金山,是毛泽东又一出其不意的果断决策。
其实,中央红军此刻并不知道红四方面军的准确位置。但事后证明,这条路恰恰是两军会合的最近距离。
1935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的会合,开展新局面”。两个“一切”足见迫切之情。几天后,博古也在《前进报》用《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的文章标题,表达了与红四方面军战友会合的热望。
在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迅速北上,袭占天全,继占芦山,向着北方的夹金山而来。
翻越夹金山夺取懋功的任务交给了红一军团。在宝兴县城的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县委宣传部干部张镜海向我们介绍:“夹金山被称作‘鬼门关,终年积雪,主峰海拔4950米,山上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山高寒冷,红军衣着单薄,又多是南方人,根本不知道高海拔意味着什么,很多人甚至连雪都没见过。”
对于刚刚突破两道天堑的中央红军而言,翻越雪山甚至难于一场战斗。《长征组歌》的作者萧华清晰地记得,一个从福建参军的小红军问他:“雪是什么样子的?”萧华说:“和面粉差不多,但是比面粉还白。”藏族村寨的百姓知道红军要翻越夹金山,一再劝阻:“要过夹金山,性命交给天……”然而,英勇无畏的红军还是在6月12日这天,带着干粮和御寒的辣椒、烧酒,拄着竹竿、树枝,踏上了翻越夹金山的征途。
虽是夏季,但一进入雪山,温度骤降。战士们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狂风和雪花如刀割般打在他们身上。越往上走雪越深,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路陡湿滑,稍有不慎,就会掉进深不见底的冰谷雪窟中。
翻越雪山,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员。担架员不愿丢下负伤的战友直至被累死;炊事员不想让战友们饿肚子而违反轻装命令,体能消耗殆尽,长眠于雪山。
快到山顶时,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站在高坡上喊:“同志们,老乡都说雪山是神仙山,鸟飞不过,人烟绝迹,只有神仙能过,如今我们上来了。岂不成了神仙!”“同志们,胜利在前!”
鼓舞之下,红军战士加快了脚步。快下到山脚时,一条深沟挡在路上。此时,沟口方向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四团团长黄开湘从望远镜中发现前面村庄周围有部队,但分不出敌我。
在杨成武的记忆中,这段历史很让他兴奋:“忽然,山风前来了一阵很微弱的呼声,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我们是红军!”
真的是战友?杨成武半信半疑时,一个侦察员飞奔回来,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
8个月征战,万余里行程,前有高山大河,后有围追堵截,啃草根、卧冰雪,尝尽人间苦难,战友牺牲无数……
这一天,在夹金山北麓达维小镇以南这个叫木城沟的藏族村寨,红四方面军的战友终于出现眼前。两支部队发出震天的欢呼,喜悦的泪水从这些钢铁汉子的眼中夺眶而出。当天夜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致电中央,代表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軍”。
继红四团翻越夹金山后,中央红军后续部队也陆续翻越大雪山。6月14日,毛泽东喝下一碗热乎乎的辣椒汤,拄着木棍翻越夹金山。他望着皑皑雪山,说:“蒋介石认为红军不能从雪山上爬过去,咱们今天就是要创造出个奇迹来。”
夹金山之后,梦笔山、达古山、亚克夏山、昌德山等大雪山也相继被红军征服。在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前的“雪山丰碑”的雕塑上,镌刻着这样的诗句:
震古烁今,三次翻越夹金山;
感天动地,六月飘舞瑞雪花。
主席让马而军心稳,
周公鼓劲而士气增。
解饥渴,壮士和雪餐云霞;
驱寒冻,英雄踏天磨枪刺。
雪山滴泪,
悲几多红军之牺牲;
雪山开颜,
喜两方红军之会合。
雪山汉白玉,三嵌红军足迹;
雪山杜鹃崖,长镌红军身影。
雪山化江河,
岁岁年年流传红军故事;
雪山映日月,
朝朝暮暮彪炳红军精神。
于此,
仰望雪山而拜,
缅怀红军而歌。
巍巍雪山,红军丰碑!
向北,那里是红军发展壮大的沃土
懋功以北60多公里的两河口,因从西北的梦笔山和东北的邛崃山流过的两条溪流交汇于此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两河口会议”。
走进两河口会议会址纪念馆,40岁的曾天迎了上来。这位朴实的嘉绒藏族汉子,是这座纪念馆唯一的守护者。他对红军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年我三奶奶就是一名红军战士。纪念馆修建时,我还捐出了珍藏多年的红军用过的铜壶。”
1935年6月中旬,中央领导抵达懋功,住在县城内的一座天主教堂里。担负接应任务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当晚即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教堂的东厢房见了面。此时,毛泽东的心中正酝酿着一个关乎全局的大问题——会师后的战略方针。
岷、嘉地区物产丰富、人烟稠密,部队给养和兵源容易补充。从战略地位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回旋余地大。李先念的介绍与毛泽东心中所想不谋而合。两支队伍会师后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无疑是上策。地图上,毛泽东大手一扬,把红军的根据地移到了500多公里以北的甘南地区。
6月25日这天,刚刚抵达两河口不久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步行3里路,去迎接从茂县赶来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
其实,在此之前,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人已出现分歧。6月16日毛泽东曾致电张国焘,提出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则在岷江以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张国焘在回电中同意向川陕甘发展,却不同意“目前计划”。凭着四方面军八万之众的部队和优于中央红军的装备,张国焘认为眼前应向南进攻。
毛泽东主张向北,张国焘选择向南。面对争论,只有通过会议来统一思想。第二天上午,在一座关帝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提出向北进发,在岷山山脉以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与会人员都明白,红军要想从已经占领的茂县、理县、懋功等岷江西岸地区向甘南推进,唯有攻占松潘,打开北上通道。然而,张国焘却坚持认为向南打成都,尔后在川康边界建立根据地更有利。
激烈的讨论持续到中午,毛泽东站起来稳定局面,他主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胡宗南的防线北上。最终会议决定,两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根据这次会议,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确定一、四方面军兵分三路,攻打松潘。
松潘,古名松州,历史上著名的边陲重镇。唐朝时,这里是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地方,汉藏修睦的历史让古城愈显厚重。红军为什么把北进的入口选在这里?松潘县史志办主任陈来述解释道:“红军最初并没有过草地的打算,而是从马尔康、黑水、毛儿盖一直向北,经松潘直接取道南坪北上。从这条线来看,松潘成了红军经川西进入甘肃的咽喉要道,得之全盘皆活,失之则生死未卜。”
离开两河口后,中央红军继续翻越梦笔山、长板山等大雪山,一路北上,到达黑水县,为攻打松潘进行积极准备。然而,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并没有急着命令部队向松潘进发,而是提出了“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陈来述介绍,早在红军制定松潘战役计划时,国民党军在松潘城内驻军并不多,常驻部队只有一个加强营。胡宗南并不想与红军交战,一来当时他的部队尚未完全集结,二来他知道红军能吃苦、肯拼命,真打起来,他的部队很可能凶多吉少。而蒋介石却信心满满——只要北堵南追,红军在劫难逃。
松潘以西50多公里的毛儿盖,两座东西相对而望的大山中间夹着一条小河。胡宗南清楚毛儿盖的战略地位。守住毛儿盖,有利于镇守松潘,也就能扼住川甘咽喉,陷红军于重围之中。于是,在到达松潘的第二天,他就把一个加强营驻扎在毛儿盖的索花寺内,并命令营长李日基“搜索、警戒和打游击”,企图堵住红军的去路。
关于毛儿盖战斗打响的时间,史料记载不一。阿坝州志《红军长征在阿坝》一书这样记述了那场战斗:“7月中旬,红军击毙李营守寺院大门的副营长和一连长后,李营乘夜率部向寺院东北方突围。红军追击,俘李营近百人。一军团侦察连和三十军二六八团两个连围李营残部于腊子山以西25公里处,除李日基率少数人逃脱,全部被殲。”
丢掉毛儿盖的胡宗南坚信红军会进攻松潘。因为,红军若不走松潘,就只能进入人迹罕至的大草地,他认为,数万红军无论如何也不会选择那条绝路。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为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辞去了红军总政委职务。中央决定这一职务由张国焘来担任,成为“军委的总负责者”。之后,张国焘才下令红四方面军向北推进。
俗话说:兵贵神速。就在张国焘与中央产生意见分歧期间,在松潘恃险固守的胡宗南部已是深沟壁垒、严阵以待。在松潘古城附近驻扎了装备先进的部队3万人。如此重兵把守,远非当时红军实力可敌。
但是,红四方面军还是发起了一次试探性进攻。两个多小时的激战中,作战勇猛的红军击毙了400多国民党军。但是,红军也有上百人阵亡,终究敌众我寡,又缺乏增援,部队只好后撤。
张国焘的动摇,使部队北进行动受到延宕,攻打松潘已错过战机,中革军委只好放弃夺取松潘的作战计划。
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8月初到达沙窝的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春天的沙窝村,山上还覆盖着积雪,小村里零散分布着具有藏式建筑风格的小木楼,顺着一座小楼窄而陡的楼梯爬上二层,是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1935年8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间昏暗的小屋里召开。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两河口会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同时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
为了执行8月3日中革军委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中央决定两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分两路继续北上。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及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过草地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由红军总部的朱德、张国焘率领,在卓克基等地集结,北出阿坝,在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南进军。而此时,张国焘却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并率左路军开向阿坝地区。
至此,新的分歧再次产生,毛泽东心中有种挥之不去的忧虑。仅仅14天后,中央又在毛儿盖上八寨乡索花喇嘛庙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这次会议,张国焘并没有参加。会上,毛泽东指出“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再次号召全体党员和指战员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为实现赤化川陕甘,为苏维埃中国而战。
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向着茫茫草地进发。蒋介石认为,几十万国民党军将红军追击了大半年,马上就要修成正果了。可是,他又一次打错了算盘。
向北,从荒无人烟的水草地上踏出一条胜利通道
川西北高原的若尔盖草原,放眼望去,纵横数百里,不见山丘树木,渺无际涯。当年,红军两万五千里的足迹,在中国的广褒大地上踏出了一条红色飘带,而最曲折的一个结,就在这片草地上。报道组从松潘出发,一路向北。虽已是春天,草原上依旧罡风凛冽。
“草地气候恶劣,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每年的5月到9月是草地的雨季。当年,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跨越草地的。”陪同采访的若尔盖县史志办主任徐绍勇指着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地说。
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的战士们每人带着千方百计筹来的几斤青稞面和一点御寒的辣椒,从毛儿盖向草地深处挺进。出发前,藏民劝告红军,如果不穿毛袜子和羊皮衣,一定会被冻死。而实际上,红军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些衣物,他们大多是穿着单衣走进草地的。
草地中遍是沼泽泥潭,人和骡马必须踏着草甸走,或是拄着棍子探深浅,三五人搀扶而行。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越挣扎,越会深陷;二怕下雨,草甸本就难走,再一下雨,脚下又软又滑,一个不慎就会摔进泥沼;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河宽流急,战士们身体虚弱,经不住刺骨的河水。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战士倒下。如此惨状,黄克诚大将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最大的困难还是吃。草地过了不到一半,战士们准备的干粮就吃完了。剩下的路程只能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走在前面的部队还能找到些野菜、树皮,后面的连这些也吃不上,战士们就把皮带、皮鞋,甚至马鞍煮着吃,实在饿极了,只好挑出粪便里残留的粮粒洗了再煮着吃。再后来,首长们的坐骑也成了战士们的食物。
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是殿后部队,准备的干粮少,能吃的野菜更少。部队即将断炊,他只好让饲养员杀掉仅有的6头牲口吃肉,其中包括驮着他翻过大雪山的那头大黑骡子。枪声响起,彭德怀向着斜倒下去的大黑骡子摘下了军帽。这天晚上,草地的篝火旁才多了些生机。
在“七根火柴”的雕塑下,徐绍勇说:“若尔盖是红军三过草地的地方,也是小说《七根火柴》的故事发生地,是真人真事。”
在杨成武将军的回忆文章《向草地进军》中,记者找到了这名红军战士:“在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把四根柴禾藏在贴身处的小宣传队员郑金煜。”
进入草地的第四天,因为严重缺氧,呼吸困难,郑金煜病倒了。临终时,他对杨成武说:“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路线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
7天后,川甘边境的一个小村庄——班佑村,终于出现在红军战士的眼前。
茫茫草地,吞噬了许许多多年轻的红色生命。我们肃立在若尔盖草原的标志性建筑——“胜利曙光”群雕前,静默,深深鞠躬,向那些为中国革命胜利献出生命的红军战士致敬……
得到杨成武率先遣团到达班佑的消息时,胡宗南慌了,急忙电令伍诚仁第四十九师的一个团星夜兼程,火速赶往包座增援,与驻守包座的军队共同阻截红军。
上、下包座相距20公里,群山环抱,包座河纵横其间,山高路险、森林密布。胡宗南部在险山密林中修碉堡、筑工事,并在包座南北的达戒寺、求吉寺屯积了大批粮食、弹药和武器,据险防守。
班佑东北的求吉乡嘎哇村内,一座藏族寺院——求吉寺历经几百年风吹雨打,已是断壁残垣,只剩下几面厚重的院墙。包座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1935年8月29日黄昏,寺院西面山头上的晚霞刚刚退去,接到攻打包座任务的红四军军长许世友率十师官兵迅速抵近求吉寺,向敌军进攻。拿下外围几个据点后,部队乘势突入寺院。在寺内防守的胡宗南补充第一旅第一团团长康庄指挥着机枪向冲过来的红军疯狂扫射。一批战士倒下了,又一批战士冲上去,寺院顿时血流成河。后来,康庄亲自率领敢死队趁红军喘息之时发动了反击。
仗打到这个程度,许世友焦急万分。这时,十师师长王友钧从一名战士手中夺过一挺机枪,冲上战场,向敌人扫射。然后,又从身后拔出大刀,吼了一声“交通队,跟我上”,便与敌人展开了肉搏。交通队是十师的一张王牌,官兵们人手一支德国造20响驳壳枪,外加一柄锋利的大刀。驳壳枪一阵响,敌人倒下一片。之后,大刀便朝着敌人挥去。刚刚结束了草地的煎熬,一个个面黄肌瘦、肚皮紧贴着脊梁骨的红军指战员,喊杀声依旧洪亮,作战依旧勇猛。
冲进寺院后,战士们沿着台阶一层层往上打,打到最高一层时,敌人的一个机枪火力点封锁了红军的冲击路线。王友钧把机枪架在战士的肩膀上射击,硬是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王友钧的头部,他倒在寺院的台阶上,24岁的红军师长壮烈牺牲。
8月29日至31日,凭着顽强的战斗意志,红军夺取了包座战役的全线胜利,歼灭了伍诚仁第四十九师的5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了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
1935年9月,当听到红军穿越草地胜利北进后,心情沮丧的蒋介石不禁长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走过沟沟坎坎,满怀崇敬,我们拜谒了求吉寺烈士墓。求吉乡党委书记张建荣动情地说:“当年这里都是战场。整个山谷流淌着红军战士的鲜血,山上有无数红军与敌人肉搏后留下的遗体,老百姓把红军遗体往山下搬的时候,并不费力,因为每一具都是骨瘦如柴……”就是在这样的身躯里,却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惊天地泣鬼神的不屈精神!
包座战役的胜利,打开了红军北进的通道。怀着期盼的心情,毛泽东立即致电张国焘,再次要求左路军向东靠拢,以便共同北进。可是,刚刚下令部队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的张国焘,却以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为由致电中央,掉头返回了阿坝。
为此,9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了非正式会议,并致电张国焘:“目前红军行动处在最严重的关头,须要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第二天,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却得到了他坚持南下的回复。当即,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五位政治局委员在班佑寺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巴西会议”。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红一军团靠拢,一起向甘南前进。
求吉乡苟均寨旁的求吉河上,有一座清代建造的风雨桥。红军长征时,共和国十大元帅中的7位都曾从这里走过,由此得名“元帅桥”。1935年9月10日,一个万籁俱寂的凌晨,毛泽东率领红三军团和红军大学从这座风雨桥上走过,出川北上,向着甘肅迭部县俄界方向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