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金场
2016-05-26王连学
王连学
不知是哪年哪月的事了。
龙王山下,一个被称之为石窝的地方,有一位孤独的老人,整天在石窝滩里的那些乱石中穿行驻足,躬着本来就不能再躬的躯体,用一根拄的棍子敲敲这儿,又打打那儿,仿佛寻觅一件遗失其间的宝物。
其实,这个老人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干散人。只是他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乱石滩里寻寻觅觅,使他的背也在不知不觉中驼了起来。人们似乎早已忘记了他的姓名,或者压根儿就不知道他是还有名字的。
——人们只因他是招赘来的,所以实在的称他为“招货”。
招货年轻的时候,年年跟人走金场,春天去,秋天来,吃尽了苦,受够了累,可一家三口人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不见起色。所以这一年,儿子长得也有一鞭杆那么高了,招货就跟媳妇好说歹说,最后领着自己未成年的儿子又上了金场。他想,如果老天开眼,一年下来,有了儿子的那一份辛苦钱,一家人的日子就会好起来的。
天可怜见,那一回,招货和他的儿子真的奇迹般的得到了一块重达四十六斤的金子。
俗话说,钱多了累人,金子也一样。走到半路,招货就在一个儿子不认老子的叫做塔拉的破地方,把自己生病的儿子当做累赘“遗弃”在一个山洞里,自己走出了金场。然而,招货没有想到,自己还是没福消受那块金子。尽管他为此吃尽了苦头,甚至搭上了儿子的性命。
招货提着心吊着胆,丧魂落魄地翻过了日月山,方才沉重地松了一口气。然而,这一口气松下来,招货浑身的劲儿刹那间便被抽走了,两腿像灌了铅,一步也挪不动了。
走了大半辈子的金场,这一回,招货却像走了整整一辈子,生生把人都走老了。
招货再回头看了看自己来时的路,浑浊的眼里立刻涌满了辛酸的泪水。他想起了儿子,想起了儿子那张憨墩墩的脸,那双清澈而又水汪汪的眼睛。他幻想着儿子还和以往一样,在家里,他压根儿就没有带着儿子到金场里去。儿子会在他回家的时候被他的妈妈牵着小手迎出了村口。他看着他们母子笑了笑,然后叫着儿子的名字,紧走几步,然后蹲在地上张开双臂等着儿子扑进他的怀里。儿子也张开着小臂膀,扑的太猛了,把他扑了个狗坐墩,父子俩就笑着滚倒在路边的草丛里。他的媳妇麻嘹儿也笑着走上来,拉起儿子,又把他从地上拉起来,捡起了他装满金子的沉沉的包裹,跟着抱起儿子的他,在儿子回家了,回家了的吆喝声里,风光无限地走进村子,走进家门……
招货的幻想就像日月山上的云彩,一忽儿工夫便被一阵突来的风吹得踪影全无。残酷的事实再一次活生生地呈现在了他的眼前——不远的地方有一顶帐篷,这使他想起几个月前和儿子一块儿过日月山的情景。那天,晴空里突然来了一场风雪。为了躲避,他领着儿子就钻进了这家牧民的帐篷。五十多岁的女主人非常热情,用香甜的奶茶招待了他们。又听说他要领着儿子去星宿海挖金子,就一叠连声地念着佛,还为他们父子诵了一段平安经文。那时候他有使不完的劲儿,过河还是儿子走不动了,他就把儿子背在背上,两个人有说有笑的,脸上写满了幸福,也写满了憧憬和希望。可是,几个月后的今天,从金场出来,那顶牧民的帐篷依然还在那里,可是自己的儿子呢?儿子真的没有了吗?不错,自己的怀里是如愿以偿地揣满了金子,但形影相吊,死气沉沉,再也没有儿子的身影……
儿子,我的儿子!招货又哭了起来。
招货不知道自己已经哭过多少回了。一路上,他强迫自己不去想儿子。儿子的影子一冒出他的脑袋,他就从怀里取出那一疙瘩金子,放在面前,看罢了就哭,哭罢了再摸,摸罢了又揣进怀里。可是今天,他看着眼前的金子,再也赶不走儿子的影子了。儿子就是儿子,金子就是金子。金子再多,也替代不了儿子啊。
招货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声嘶力竭地嚎了起来。嚎着嚎着,他看着一路上当做自己的儿子支撑他走出金场的那一疙瘩金子,突然变成了一个吞吃了他儿子的魔鬼,张牙舞爪地向他扑上来。招货恨死了,狠狠地一脚踢了出去。魔鬼没有了,金子被他踢出了老远,在地上滚了两下也不动了。
日月山的天气又变了,变得阴沉沉的,像要下雪的样子。招货像一堆懒婆娘解下的裹脚带。他已经没有力气嚎了,只剩了无声的呜咽。
招货把心里的委曲和辛酸哭完了,再哭出一点儿力气的时候,天已近黄昏,也顺便飘下来几片雪花。招货抬眼望望西山的那一抹光亮,就去捡拾被自己踢在一边的金子。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金子被一只残破的靴子踩着。招货两手走了空,心就有点不踏实地跳,慢慢而又惶惑地抬眼看去,却是他甩了一路终究还是没有甩掉的阴影似的那个白板皮袄的搭帮。
看啥,不认得了?白板皮袄的搭帮冷笑一声,一脚就把招货踹了个仰绊,然后从容地捡起那一疙瘩金子,狂笑着在衣襟上擦了擦揣进自己的怀里。临了,白板皮袄的搭帮嘲讽地对招货说,你连儿子都不要了,还要金子做啥?说完就走,没走两步又回转身来,从怀里摸出一个装了十几块银洋的麝皮袋子,扔给了招货。
你连儿子也不要了,还要金子做啥?
白板皮袄的搭帮的话如一记闷雷击在了招货的头顶。我要金子做啥,我要金子做啥?招货喃喃地念叨着,眼睁睁地看着白板皮袄的搭帮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他的白色顶子了,这才像被人抽了脊梁骨似的堆在了地上。
招货连眼泪也没有了,哪里还能哭得动。
后来,白板皮袄的搭帮把那块金子辗转献给了马步芳,换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做。马步芳以为祥瑞之兆,为其做琉璃罩,当神物供奉于“馨庐”,炫耀于人,以示其德政。
招货用自己亲生儿子的性命换回了十几块银洋,同时,也换回了半生的凄凉、冷清、潦倒和孤独。从此以后,他再也没上过金场,甚至没离开过石窝一步。
传说招货的媳妇长得很美,瓜子的模样儿,说有多俊就有多俊。只是脸上有几点因生育而留下的淡淡的雀斑,却越发地衬托出她的妩媚多情。她是一个唱“花儿”的能手。优美嘹亮的歌声在她樱桃似的小嘴里缠缠绵绵地吐出来,听得蜂儿迷了本性,蝶儿找不到家了,就追逐嘻戏在她的头顶。人们给她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麻嘹儿(百灵鸟)。其实,最美的还是她那副窈窕的身段,被一双纤纤小脚载着,走路的时候仿佛一只蝴蝶,翩跹蹈之,风情万种,动人心魄。
那一年,招货一回到家里,麻嘹儿见不到自己的儿子就哭上了。她如泣如诉的哭声仿佛一首失传了几千年后又被突然发掘出来的古老而新奇的歌谣。感动得那年的老天爷下了整整四十天的连绵泪雨,使长在地里来不及收割的庄稼的穗果上萌生出黄绿的嫰芽。
不久,麻嘹儿失了踪。人们再也没见过她如花的面容,窈窕婀娜的身姿,也没听到过她如潺潺流水般的歌谣……
直到招货死的那一年,人们忽然传说,见过麻嘹儿领着一个半大不小的女孩儿,在石窝滩里走过。还说那女孩儿就是她的女儿(还有人说是孙女)。可是人们只把它当成一个传说,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谁也没有相信。
这一天,招货终于从石窝滩里溯着泉水的源头滚雪球似的滚下一个浑圆的石头,并沿着村巷一路滚过去。那一刻恰是娃娃们放学的时候,他的后面就跟了一群背着书包的孩童,仿佛追逐嬉戏着一个从远古走来,尚未完全直立起来的人猿。
招货,你滚石头干啥?
不会是石包金吧,把它给我吧!
啊……不、不……
招货滚着这个浑圆的石头,经过十字路儿上的“广人台”时,人们看着他汗流浃背、慌张失措的样子,不禁有些奇怪,于是半开玩笑地问他。谁知这一问,却把招货吓得几乎就要伏在那块石头上,生怕被人抢走了他的宝贝似的,满脸的惊恐和不安堆撮成一个刚出笼的青稞面包子,颤微微怯生生地望了一眼跟他开玩笑的人们。
招货,你的石头里有金子吗?
招货,原来你是在石窝滩里寻金子啊,我说嘛!哇哈哈哈……
招货,我看见麻嘹儿了。那天在石窝滩里,她是来看你的吗?你看见她了吗?
招货,你儿子呢?他还活着吗……
招货,你连儿子都不要了,你还要金子干啥?
……
我要金子干啥,我要金子干啥……
招货自言自语着,没完没了地自言自语着,惊恐、不安和惶惑写满了他的脸。尤其是人们那种变幻莫测、抑扬顿挫的笑,在招货听来无异于魔鬼索命的叫声,足以让他失魂落魄。如果用落荒而逃这个成语来形容招货滚着石头逃离广人台时的样子,显然是不确切的。但来形容他此时此刻急于逃走的心情是再好不过的了。
从此以后,石窝的人们再也没见过在石窝滩的那些乱石岗子上寻寻觅觅的那个驼背的影子。
招货把石头滚到家里,喘着粗气,用驼背靠着门板就瘫坐在地上。然后“噗——”地吁了一口气。招货这口气还没有吁完,一个女人的声音就劈头盖脸地向他砸了过来。
我的儿子呢?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
招货知道这声音是他的媳妇麻嘹儿的。他太熟悉这声音了。但是,他还是被吓得愣怔怔打了个激灵——他已经有几十年没听到过这声音了。招货摇了摇头,使劲地闭上了眼睛。因为,他不仅听到了声音,仿佛还看见了什么。他以为也是自己的媳妇。他太爱她了。爱她的美,爱她的歌声,甚至爱她的风骚。他走了十几年的金场,每一次他都幻想着掐上一疙瘩金子,回来的时候在西宁城里给媳妇买一对翠绿的吊耳坠儿。他想他的媳妇的脸形再配上这么一对儿耳坠儿,就会显得更加美丽、更加迷人的。这种想法在他招赘过来的那一年走金场路过西宁的时候就有了。也就是那一回他在一个卖首饰的铺子里面看到了那一对绿耳坠儿的,那是一种多么可爱的绿啊。每一年进场的时候他都要去看一眼那一对绿耳坠儿。十几年来,招货已经跑了十几趟了,那家铺子的主人也好似认识了他,把那一对绿耳坠儿一直给他留着。可是,每一次从星宿海出来,捏捏羞涩的行囊,招货再也抬不起脚走进那间铺子……
招货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的不是他的媳妇麻嘹儿,而是在落日的余晖里,一个戴着半截绿玉镯的半大孩子欢快地向他跑来……
大……招货仿佛听见了儿子的叫声。
儿子?我的儿子?!
招货含糊且欣喜地叫着,一阵喜悦涌上他的心头。他情不自禁地张开了双臂,等待儿子投入到他的怀抱。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等到。他的眼前却不仅仅是他的儿子,反而多了一对绿茵茵滚动的灯笼,接着又是一对、两对……渐渐的变成了灯笼的洪水,闪烁着寒人的光芒,向他的戴着半截绿玉镯的儿子漫过来、漫过来。招货不知道眼前的情景到底是什么,一道闪光——确切地说是一道忽喇喇划过天空、照亮了夜晚的星宿海的流星告诉了他答案——那是狼。一只灰黄色的瘸腿母狼,不,是一群,像拖着长长的影子,数也数不清……
啊——
招货抱着头,声嘶力竭地大喊了一声,接着浑身都像筛筛子似的抖起来。尿也禁不住如冰水般一滴滴挤出来,洇湿了他脏迹斑驳的大腰裤子,洇湿了他家门口的那一块黄土地。
不、不会是这样的,不会的……
招货“呜呜呜”地哭起来。他从来也没有相信他的儿子会死掉。他只是把儿子放在了那个山洞里。而且,那个山洞里先前曾有人住过,他放下儿子的时候铺在地上的草还是温热着的。他会把他的儿子接回来的。只要以前跟随过的那个掌柜再来叫他,他一定会再去星宿海把儿子接回来,不管掐上掐不上一疙瘩金子……
招货的思绪(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回顾他的往事)如梦般的飘浮不定……
掌柜的还活着,没有被绿茵茵的灯笼的洪水淹没,又来叫他……
招货看见自己又回到了星宿海。他找到了寄放儿子的那个山洞,他看见儿子高兴地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他甚至于感觉到了儿子的体温……
儿子在他怀里的蠕动惊醒了睡梦中的招货——在即将来临的暮色里,招货的眼前却是一片灰色。而且,他在这灰色的寒光里清晰地感觉到有一股清新的腥膻。他明白那是人肉的味儿,而不是儿子的味儿。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没有死,没有被狼吃掉。他不再觉得怕了。怕对他来说已是很遥远的事了……
恼人的是招货看见儿子痴痴的、呆呆的,嘴里不停地叫着“狼、狼”,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儿。而且他还看见儿子向一个沙娃们栖身的洞子走过去……
招货正为儿子担心,这种担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上……
招货听见儿子咤嘛古怪的叫喊声,穿越了时空、穿越了山川草地,掼进他的耳里。同时他也看见他的儿子返身就跑,没跑几步就跌了一跤……
在招货的感觉里儿子跌倒了再也没爬起来。因为儿子的身后滚出了那对绿茵茵的可怕的灯笼一样的眼睛——那只灰黄色瘸腿的吊着两行奶子的母狼……
接着那狼又变成了一个人,那人穿着破旧的白板皮袄。招货看清了那是他的掌柜的搭帮。那刺眼而又破旧的白板皮袄以及他头上的白色顶子,就像鬼一样附着了他的躯体、他的灵魂、他的命运……
狼吃了人,却留下了所有人的金子……
一想到金子,招货的眼里就有了光亮,思维也变得清晰起来。
……白板皮袄的搭帮收敛了满脸的惊骇。他看了看眼前的招货父子,眼睛里露出难以捉摸的笑影。他也忘记了感谢他的主再次保佑和赐于了他第二次生命,就急急忙忙地翻遍了每一块撕碎的血淋淋的衣衫,翻遍了每一根死人的骨头。一时三刻,黄澄澄的金子就装满了他满是污垢的白色顶子。白板皮袄的搭帮踢开了自己翻捡过的最后一块骨头,看了一眼木然地望着自己的招货就拉下了脸。
猪日的,你看毬。你捡了一条命就够便宜了,还不快去给老子做饭。白板皮袄的搭帮呵斥道,那语气仿佛招货的命就像他捡起来还给了似的。
金子的光泽照亮了白板皮袄的搭帮的眼睛,滋润了他吓成土黄色的脸,同时也薰黑了他的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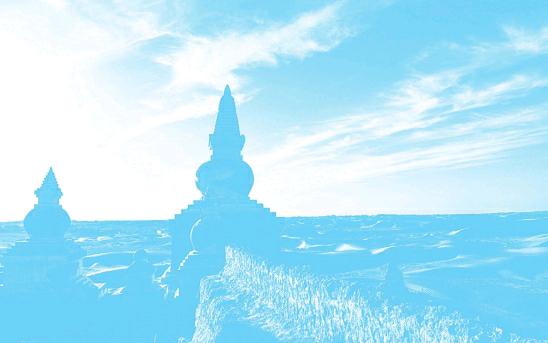
招货眼巴巴地看着白板皮袄的搭帮怀里揣满了黄澄澄的金子,然后嘴里喊着烂摊子,舒舒服服地躺在阳凹里晒着太阳。招货恨不得过去宰了他,最少也该踢他两脚。但是他不敢。他只好极不情愿地喊来吓得傻乎乎的儿子,帮自己在那三块被熏黑的石头上支锅做饭。
吃了饭,白板皮袄的搭帮又命招货烙了一个礼拜的干粮。然后就说出一个铁板钉钉的字眼——走!而且叮嘱招货砸烂那口锅。他要面对着西方的圣土发愿——再也不会到这个猪日的鬼地方来了。星宿海再也没有他扯心的了。
招货并没有砸那口锅。他想把它背回家去。因为家里的那口锅早已烂得没办法钉了。那怕向白板皮袄的搭帮下下情也可以。他想,看在这一回“生死之交”的份上,小小的一口锅,搭帮一定会答应他的。
然而,白板皮袄的搭帮虔诚地发完了愿,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回头发现那口锅不仅没砸烂,反而叫招货给背上了,他就来了气,照定招货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两脚,恶毒的骂道,猪日的,没有出息。千里的路,你当是耍的,背一口破锅。说着,从招货的背上扯下行李,照定那三块做过饭被熏得黑不溜秋的石头就摔了下去,然后扬长而去。
招货没来由挨了白板皮袄的搭帮几脚,心里说不出的冤枉。又看那锅早已烂了,气就有点儿不顺,又不敢撒向白板皮袄的搭帮,就抬起那三块熏黑的石头,先后向那顶还没完全烂碎的铁锅砸了去。
只因这一砸,招货的眼前便晃过一道金色的光亮。几乎于同时,他的两腿便如抽掉骨头似的软软地跪了下去。而且,浑身的血液顷刻间涌上心头,使他的全身止不住的哆嗦起来。
金子!招货轻轻地叫了一声拉毛佛,虔诚地伏下地去。
招货爬在地上,费了好大劲才把自己镇定下来。他从裤裆里看见白板皮袄的搭帮还没走远,自己又不敢在地上爬的时间太长,就颤巍巍的捋下裤子,把自己的身子转过来,蹲在那三块石头的边上,装成了拉屎的样子,一边眼盯着白板皮袄的搭帮,看他在高低不平的草地上走路的样子,像一个舞蹈的魔鬼。
白板皮袄的搭帮回头看了看招货,不禁皱起了眉头,“呸”了一声,自言自语地骂道,这猪日的……
招货眼巴巴地看着白板皮袄的搭帮只剩下一个头影儿,在远处的地平线上闪动,方才像剥煮熟的鸡蛋似的把那个石头里的“蛋黄”取出来。他不敢站起来,依然蹲着,慢慢地把那块金子裹好,然后小心翼翼地要往自己的怀里揣。
正当招货做这一切的时候,他那个丢了魂的儿子却推着自己的影子悄然无声地向他走过来。
儿子的影子慢慢地笼罩了招货,也笼罩了他的心。招货的心里一悚,两只抱着包了金子的包裹的手触了电似地立刻僵住了。——他以为是那个该死的搭帮又回来了。
招货慢慢地抬起头。当他看清刚才的那个影子不是白板皮袄的搭帮,而是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他的心里就蹿起了火。招货把金子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边,提着裤子一个蹦子就跳起来,照准儿子稚嫰的脸就煽了一巴掌。
狗日的,吓死老子了。
招货打过之后就后悔莫及,但儿子已经在哭了。招货摸了一把儿子的眼泪,又摸摸他的脸,嘴里说着不哭不哭,我的儿不哭,都是大的不是。大对不起你。招货心里一痛,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而且打儿子的那只手也麻酥酥的,一整天也不得劲儿。要知道儿子长这么大了,招货连一个指头也没有动过。但今天这是怎么了啊,手这么贱。
招货心里愧疚着,在儿子的哭声里把包裹揣进了自己的怀里,试着走了几步,觉得不行。肚子太凸,一看就知道怀里揣着一疙瘩金子。招货想了一想,又把它褊在裤腰里,用裤带勒紧了,方才放了心。可是没走几步,那金子就要掉进裤裆里一般。招货就像直肠里夹着一坨稀屎似的连忙解了裤带蹲在了地上,只差了没把裤子扒拉下来。招货没别的办法,只得小心翼翼地把那劳什子解下来,然后跪在地上,系好了裤带,又把金子揣进了怀里。这回他再也顾不了许多,站起身来抡起自己的行李斜挎在肩上,一把牵了儿子的手,望着白板皮袄的搭帮那顶日日晃晃的白色顶子撵了去。
在沟沟坎坎的草地上望着蓝茵茵的鄂陵湖走了一天,招货觉着仿佛是一年。那块四十六斤重的金子像一座山一样压着他的躯体,也压着他的心。使得他那早已麻木的脑袋,也不得不跟随他的双腿不停地运转起来。他知道要把那块金子瞒着这个精得猴似的穿白板皮袄的搭帮,那要比登天还难。但是,自己又不甘心把金子乖乖的交给他,交给这个狗日的东西(招货心里这样骂),因为这毕竟是他十几年的梦啊。这里面有他的汗水、有他的运气,也有他的未来。还有,还有他的妻子麻嘹儿美丽的笑脸和那对在那个小首饰铺子里静静地躺了十几年的翠绿的吊耳坠儿。对,金子是上天可怜他而赐予的,无论如何也要把它带出去,带到家里。还有,要让媳妇看看金子的样子。男人挖了十几年的金子,但他的媳妇却没见过金子,叫人听了笑话。可又怎么带出去呢?这是招货想了一天也没有想好的问题。他想了一千种办法,但一千种都不行,都被他没走几步就否定了。眼目时下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是跟在白板皮袄的搭帮的后面,诚惶诚恐的躲着他的眼睛,避免跟那个白色顶子底下的面孔照面。因为招货害怕自己那怕是瞬间的表情也会不经意地把自己给出卖掉。可是,不行,特别是在打尖做饭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在白板皮袄的搭帮面前晃来晃去,就像是一个玻璃人儿,啥也遮不住,特别担心那块金子就要从怀里跳出来,再在阳光下划一道灿烂的弧线,然后掉落到地上,顺便也把他的脚给砸一下。
这不是个办法,不是长久之计,怎么办呢?
夜,已经很深了。阿尼玛卿雪山像一条伏在地上静待猎物的蟒蛇,时时准备着要蹿出去一般。几声狼在远处的嚎叫和不远处两只鼠兔肆无忌惮地调情的声音,更增加了夜的静谧和恐怖。
招货辗转反侧,久久地不能入睡。尽管天依然很冷,风又一阵阵“呜儿呜儿”地吹,而且还吹进洞子里来,针似的刺骨。但是,招货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冷。倒是他看见儿子蜷缩着瘦弱的躯体,不住地咳嗽着。他尽量紧紧地抱紧儿子,想把自己的破皮袄盖在儿子的身上。可是不能,因为破皮袄穿在自己的身上,怀里还揣着金子。招货感触到了儿子在冷的发颤,但他只能盼望着天快些亮起来,暖洋洋的日头快些升起来。那样的话,儿子就不再挨冻了。儿子的脸庞上又可以有灿烂如阳光般的笑了……
大,你掐了那么一大疙瘩金子,就用皮袄裹着它,可把我快冻死了。儿子的呓语虽然迷迷糊糊地听不清,却不亚于惊雷一般,把招货从梦中惊醒过来,吓得他脊背发凉,冷汗直冒。
招货赶紧捂住儿子的嘴,再看白板皮袄的搭帮依旧酣睡如故,这才吁了一口气。儿子的话提醒了招货,他想,这一路走出去,就是儿子不说,自己也难免不露出马脚。那时,不说是金子,恐怕连命保住保不住也说不定的……
招货越想越怕,越怕就越想,心里就越乱。等到天亮了,他也没想出法子。
这一天,招货走得更加艰难。他的神经系统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不仅因为他的不可告人的心事,更要命的是他的儿子又发起高烧了。
对,儿子又开始发高烧了。招货把儿子用皮褂裹好了抱起来往下庄里的先生家跑,麻嘹儿在后面撵着说你不要裹得太紧,儿子已经烧得很厉害了。招货说,你知道啥?不裹紧点,儿子受了风,病就会越重的。一路上招货看儿子的小嘴干巴巴的,媳妇是小脚走不快,隔得远,他就只好用唾液濡儿子的嘴。他一口气跑到先生家,“卟嗵”一声就跪在地上,先生爷,快救救我的儿子吧!先生一边喝着茶,一边慢条斯理地瞅了他一眼,算是问询。他赶紧说,我儿子烧得快要点着了,您老看看。先生用手摸了摸他的儿子的头,说,裹得太紧了,你想把儿子捂死啊。先生把招货的儿子接了过去,放在旁边的床上,然后揭开裹着的皮褂,又看了招货一眼说,还戳着干啥,去寻两个石头。招货正不知该寻两个多大的石头,他媳妇麻嘹儿也像一只蝴蝶似的进了先生家的门,手里正拿着两个拳头大小的卵石。这时候,先生已将他们的儿子剥得只剩了一个钻钻(棉背心,只能钻着穿,故名)。麻嘹儿给先生行了礼,然后把石头用衣服包好了,夹在儿子的腋窝里。招货看了大惑,说了声你干啥,就想把儿子抢过来抱在自己的怀里。先生发话了说,你媳妇做得对,照你的样子看儿子,当真会把儿子看没的。去那个碾槽里碾药去,等你把药碾细了,你儿子的烧也退下去了。招货听了先生的话,只得去碾药,一边看着媳妇把儿子抱在怀里,解开自己的衣扣,用大襟子把儿子草草地裹了些,再把那个白白的奶子拉出来给儿子喂奶……
招货一会儿背着,一会儿搀扶着他的发着高烧的儿子在白板皮袄的搭帮的怨声和骂声里,走一阵又歇一阵。
就这样走着走着,招货的心里倒渐渐地有了主意。他索性磨蹭起来。他想着要使白板皮袄的搭帮撂下自己和儿子,独自一个人走了就好了。可是,那个狗日的好像明白他的心事一样,尽管怨声载道、骂骂咧咧,就是没有独自要走的迹象。招货又恨又急,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在不到宿头的地方,黑夜总算又姗姗来临,招货的心里又松了一口气。白板皮袄的搭帮看招货的儿子病成这个样子,虽然不痛快,但也不好硬说什么。在这荒山野岭,有个同伴总比没有的好。何况是一个由自己任意摆布的“务拉子”。幸好,一路上有的是沙娃们进出时留宿的洞子,所以也不难找到歇宿的地方。于是三个人吃了点干粮,就睡下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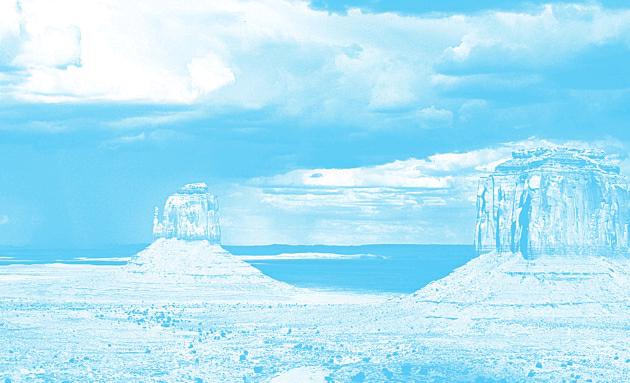
招货拥抱着儿子,满腹的心思,眼巴巴望着洞子外面天边上的几颗星星。儿子的病和怀里的那块金子像两个秤砣,压得招货这杆秤都快要断了。招货又累又乏,可是一点儿睡意也没有。睡不着的招货脑袋里一会儿像翻涌的浆糊,一会儿又像一滩死水,他又不敢随意地翻动自己的身子,小心翼翼的样子就像搂着一块豆腐在睡觉似的,说不出的难怅。
招货好不容易耐到半夜的时候,方才听见白板皮袄搭帮的呼噜声,看来已经睡得很香了。这时候就是宰了这个狗日的,他也会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哩,招货想。于是,招货便把半条破毡给儿子盖好了,自己就悄悄地往外挪。他要找一个地方把那块金子藏起来。他实在受不了儿子的病和金子的双重压力。他要想办法减少这种压力。儿子是重要的,是他的心头肉。同样,金子也是重要的。虽是身外之物,却也是用血汗换来的。不仅如此,它里面还包含了自己走了十几年金场的梦想。如果硬让他在儿子和金子之间作出选择,这不仅愚蠢,而且荒唐——他不会那样做的。他可以把金子暂时藏起来,因为它不会跑掉的……而儿子也能藏起来吗?!答案是否定的。不能,肯定不能,怎么能这样想呢……
你做啥?想抢我的金子吗?嗯嗯,谅你也你不敢,我知道。白板皮袄的搭帮迷迷糊糊地说着,转了个身又呼呼地睡去了。
招货那敢动弹,吓得连气也不敢出。又等了一盏茶的工夫,坚信白板皮袄的搭帮不是有意说他,而是在做梦时,这才小心翼翼地溜出洞来。
招货站在洞外,犹自觉得自己的双腿还在发抖。不远处,一只猫头鹰的叫,阴森森地尤其觉得吓人。招货长出了一口气,然后从怀里取出金子看了一眼,又揣进怀里。招货有些得意,腰一猫就钻进夜色里。
招货猫着腰,借着星光一路小跑,去他在傍晚的时候看好的一个地方。
招货藏好了金子,也藏好了自己的心思,感到浑身的轻爽和来劲。这时候,他听猫头鹰的叫声也仿佛夜莺的歌唱。尤其是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儿吹得他晕乎乎、轻飘飘如腾云驾雾的一般。他昂着头,背着手,竟然在心里唱了个少年——
铁青的马驹儿银笼头,
红丝线绾下的绣球。
尕妹妹你跟上哥哥了走,
好日子就在个后头……
招货在这种自我的陶醉中醒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找不到那个有他的儿子和讨厌的白板皮袄的搭帮的洞子了。招货想借着刚刚升起的月牙儿昏暗的光亮,寻觅自己来时的足迹。可他转身之间,自己刚刚留在沙地上的足迹,也被风儿刮得无影无踪。那个洞子到底在哪儿呢,我的儿子又在哪里?招货心头一热,他感觉到自己的魂魄沿着脊梁窜上顶门,仿佛一个久病的人突然预感到死神的来临似的无可奈何。——儿子,我的儿子,我怎么把个家的儿子给撂掉了。招货在心里说,他晕头转向,心急如焚,老泪伴着嚎哭纵横流淌。
曙色微现,天很快就亮了,接着太阳也升起来,又有一竿子高了。招货始终没有找到那个洞子。到现在他甚至于弄不清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难道这真是天意吗?在儿子和金子之间,自己必须有所选择。而且在不经意间,却选择了金子?天哪!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呀?!我真的选择了金子吗?可我把自己的儿子丢掉了。儿子是自己的骨肉啊,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是命根子啊,是连着心的,是屎一把尿一把地拉扯大的。没有了儿子,自己回去怎么跟媳妇交代?——因为儿子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他也是媳妇麻嘹儿的儿子呀……
没有了儿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最后,招货想到了死,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啥也不扯牵了。可在这个处处透着死亡气息的地方一时之间却找不到死的方法。想抹脖子,没有刀;想上吊,没有树;想淹死,没有水。没有打死人的石头,没有吃死人的药,没有碰死人的墙壁……
本来对于星宿海,招货已经走了十几年了,自信闭上眼睛也能走得出去。可是今天怎么了?招货瞪直了眼睛看那山、看那远处的黄河、看那大地,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但一切仿佛要旋转起来。他感觉到自己正在一个磨死转儿(陀螺)的边上,东西南北在顷刻之间变幻八方。他又感到自己的头好大好大,“嗡嗡嗡”地响个不停。他抱着头闭上了眼睛蹲在了地上,想静一会儿,可是儿子的影子立刻跃居他的脑际。他无法把自己镇定下来。
大,你在哪儿呀,你不要我了吗?你快来救我呀!大,大……
招贷仿佛听见了儿子的叫声。同时,他也看见了儿子正被那个灰黄色瘸腿的吊着两行奶子的母狼叼走,又在一处低洼的草地上就像它的狼娃似的嗅着、舔着。而后,那狼一声悲鸣,就张开了它的血盆大口……招货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睁开眼睛看时,那天那地也如一张血淋淋的大嘴,要吃人似的。招货在自己的脑袋上重重地捶了两下,又摇了摇头,再看时那天依旧,那地也依旧。远处的地平线上一个白色的顶子一现一没,渐渐地成了一个人影。那人影身上的白板皮袄虽很破旧,却格外的刺人眼目。招货下意识地爬在凹蜗里,眯眼瞅着那人影渐渐地近了,又渐渐地远去,最后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之中。
招货瞅着白板皮袄的搭帮消失的背影,从心里笑了。他不会去问他的儿子在哪里?因为他知道儿子就在白板皮袄的搭帮来时的路上,那个洞子就在那里。只是昨晚上自己急昏了头,白白在荒草滩里忙活了一夜,差一点把自己给吓死。如今好了,不仅轻而易举地知道了儿子藏身的方向,而且也轻而易举地摆脱了那个讨厌的白板皮袄的搭帮。
招货在暗暗地庆幸。
摆脱了白板皮袄的搭帮,招货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同时也捡回了自信。真是有福的人儿不再忙。如今自己有了金子,连老天爷也来溜尻顺情哩。招货这时倒觉得昨夜的折腾着实有些可笑和不值,便挪腾好身子,瞅好了方位,这才取出烟瓶,打燃了火镰从容不迫地抽起烟来。不想招货这一抽烟,心劲儿一松,竟然睡了过去。
招货在睡梦里回到家里,他媳妇麻嘹儿给他做好了饭食端上来。招货正吃得津津有味,突然,麻嘹儿问他说,我的儿子呢?招货到这时方才恍然大悟,觉得浑身燥热,一骨碌就翻下炕来……
招货醒了。醒过来的招货吓得三魂早去了二魄。望着只有一人高的太阳,他在自己的头上狠狠地打了两拳。然后觅了白板皮袄的搭帮来时的路,飞也似地跑出去。
招货风急火燎地跑到他认为该到了那个洞子的时候,天早已黑麻了。只有满天的星斗眨巴着眼睛,似在嘲笑招货的愚蠢和无奈。招货的眼睛里急得喷出了火焰。他叫喊着儿子的小名,像一个病猪,不停地在野地里乱蹿。
招货不知道自己找儿子找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自己找了多少地方,但在无意中又到了他藏金子的地方。招货没有忘记把那块埋在地里的金子取出来。
天哪!你……
招货欲哭无泪,当他把金子再次揣进怀里的时候,望着远处闪着白光的阿尼玛卿雪山,心里泛起的只是辛酸。他爬在地上,几乎嘶哑着嗓子喊出了这几个字,却不知怎样诅咒这个暗无天日的世界。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招货才静下心来。他又想想昨夜来时的路,哪儿是坎,哪儿是沟,自己又是如何走的。一路想,一路抱了最后的希望喊喊叫叫地寻过去。
可惜的是招货还没找到儿子,他的喊叫声却引来了一只狼。
哀,莫大于心死。对于狼的出现招货也没感到多少恐怖和威胁。或者说,人到了这种时候,躯体和思想早已背道而驰了。招货的心里老是在寻找自己的儿子。而且这种目的的重要性早已使他的思想忽略了恐怖和威胁的存在。然而,他的躯体则说了不。它要保持自己的完整,它要设法使自己不成为狼的口中之物。这样的两种目的在一个人的身上显现出来,意识里就会相互矛盾、相互背叛、相互对抗;表现在招货的身上,则使他的思维变得恍恍惚惚,行为变得盲目而无所适从……
天很快又亮了。
微曦中当招货看清跟自己周旋了大半夜的狼就是那只凶残无比的灰黄色瘸腿的吊着两行奶子的母狼时,招货的思想和躯体完整地统一了。他再也无法想象他的儿子还会活在这个世上。他再看看四周,天啊,鬼使神差,自己竟然已经踏上了归途。星宿海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他的身后。
畜牲,我日了你的妈妈!
招货声嘶力竭地大吼一声,不顾一切地向母狼扑了过去。灰黄色瘸腿的吊着两行奶子的母狼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跳到一边,迷惑不解地望着眼前这个两条腿的异类。
招货扑了个空。但是,他的悲愤发泄不到狼的身上,就不是说不再发泄了——他需要发泄出来。他的躯体为了自己的背叛勇敢地向思想做出了悔过自新的表现。而他的思想也为自己的软弱和无可奈何找到一些补救的方法,以维持心理的平衡和踏实。于是,招货仰天大喊了一声,就跪在地上对着狼嚎哭起来。
也许,招货嚎哭的声音比狼的嚎叫更阴森恐怖了十倍。
那只灰黄色瘸腿的母狼看着招货的样子,听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它仿佛预感到末日的到来似的,诚惶诚恐地退了几步,突然掉转身子,夹起尾巴,一跳一拐一溜烟地跑了,转眼之间就跑的无影无踪……
招货的思绪被不远处一声脆亮的响鞭声惊醒。他不禁打了个冷颤。看看天,圆润的月儿早已升起来了。该又到八月十五了,他想。难怪孩子们又开始打响鞭了。如果自己没有去挖金子,如果儿子还在身边,那么自己的孙子也该到了打响鞭过八月十五的岁数了。那么……那么他的麻嘹儿也不会扔下他离家出走……
招货越想越不是滋味。他恨透了白板皮袄的搭帮,恨透了那只灰黄色的瘸腿母狼,恨透了星宿海,同时也恨透了自己,还有那块自己没福消受的金子。
招货把满腔的愤怒和仇恨都放在眼前的那个浑圆的石头上。他使尽吃奶的力气把那块浑圆的石头举起来,举过自己的头顶,然后朝另一个石头上摔下去……
招货不知道那个石头到底摔碎了没有。但是,他感觉到自己满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头,而且“ 嗡”地一声就在脑子里炸开了。这当儿,他的脑海里很快闪过他跟麻嘹儿从结婚到儿子的出生以及长大的每一个片断,这些片断前后颠倒,次序混乱,最后化成了一根线,一根魄的线,而且这线很快就一截一截地断开……
最后,招货的眼前一黑,就栽倒在地上……
几天后,招货的邻居家的孩子在玩耍的时候,好几次从门缝里看见招货总是保持着一个姿势,心里便觉得蹊跷,才告诉了自己的家人。后来,人们翻墙进去,看见招货把自己的头放进自己的裆里,像一个倒置的腐朽透了的树根似的坐着,早已死去多时了。他的前面那个从山上滚下来的浑圆的大石头已经烂成了几半。
邻居叫人上前,想把招货扳直了,使他舒舒服服地躺下来,可是谁也不肯动手。人们只是厌恶地看了看他的脸——他的凝固着最后的愤怒的脸,就像一疙瘩烧红的生铁被突然扔进水里,而后水干了,上面又落满了尘埃。
日他的,死得着了,还忘不了金子。有人忿忿地说。
于是,人们将招货原封不动地埋进石窝的沙土里。那块被他自己砸烂的稍大些的半块石头,有幸象征性地做了他坟头的石桌子。说是象征性,是因为那半块石头上,除了掩埋他的那天有人奠过一泡尿之外,二三十年来形同虚设,再也没放过任何祭品。甚至连尿也不曾奠过。只有发绿的苔迹和发红的石锈,偶尔也有发白的雀鸟的屎迹。
(作品系西宁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生活与法》节目特约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