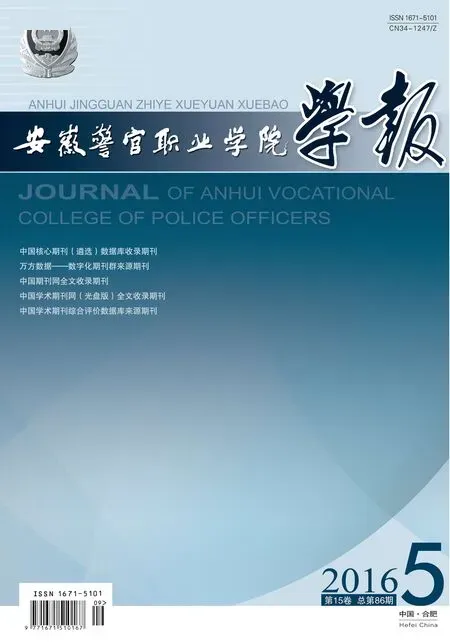公众视角下我国警察执法合法性来源研究
2016-05-23凌志
凌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公众视角下我国警察执法合法性来源研究
凌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合法性是指实定法规范的符合性以及社会公众理性判断的统一,涵盖了合法律性和合理性的内涵。基于对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探究,明晰我国警察执法合法性来源于基本法律层面的权力授予和公众基于事实层面对执法活动作出的价值判断。公众的理性价值判断标准具体包括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程序规范和警察执法活动的功能属性两方面。公安机关应通过对警察执法的程序和功能属性进行合法性建构,从而获得公众的价值认同。
合法性;公众;警察执法;来源
长久以来,人们谈及警察执法的合法性仅仅是从执法者角度进行专业的法律层面的考量,而忽略了社会公众基于事实层面的价值判断。这就导致在现实的执法实践中,社会公众往往会对警察执法行为产生合法性怀疑,不利于警务工作的开展。视角的差异其本质上是合法性判断依据的不同,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究于是对权力合法性来源的理解偏差。故本文拟在对合法性概念辨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梳理、分析,进而探究社会公众视角下警察执法合法性认知及其来源。
一、警察执法合法性概念及其一般性问题
(一)合法性概念
合法性最初是政治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概念。“合法”一词并非人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与“非法”相对应的概念,把合法性简单地理解成是理论法学中的主体行为符合法律规范的想法是不准确的。
关于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 《经济与社会》一书中作出了详细概述。韦伯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现象出发,指出了合法性(Legitimacy)与合法律性(Legality)之间所存在的分野:“今天,流传最广的合法性形式是对合法律性的信仰,换句话说,接受那些形式上正确的、按照与法律的一致性所构建的规则。”[1]换言之,韦伯认为合法律性是政治系统实现统治秩序或权力合法化的必要前提。政治系统首先通过法律程序即合法律性来确立自身统治,进而运用统治手段来获得社会成员的信仰与忠诚,实现统治秩序或权力的合法化。但哈贝马斯对韦伯的这种经验性阐释提出了批判。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只注重政治统治在法律层面的合法性,而忽视了社会公众对统治秩序或权力的理性思考,即合理性原则。韦伯的合法性认知更多的是基于统治系统的统治目的而言,强调的是统治阶层自上而下的“统治——服从”。
笔者在对韦伯、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比较分析中发现,他们的理论认知其实质都是围绕着合法律性与合理性两个概念进行探究的。因此要对合法性理论作出正确的建构,就必须要明晰合法性与合法律性、合理性概念间的区别与联系。
“合法律性”中的“法”指的是实定法①实定法是指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法律,即国家制定颁行的法律。意义上的法,具体内涵是指行为主体要符合法律规范,依法作为。合法律性强调的是法律的现实存在以及行为者对法律的服从与遵守,因此也有学者将其称为狭义的合法性。这点与韦伯的合法性理论有所不同。韦伯所述的“合法性”概念中的“法”是一种自然法①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法学理论和道德理论。意义上的“法”,其基本特征是对法律或统治秩序的二元观念:不仅突出实定法规范的符合性,还注重对法律或统治秩序的检验与批判。所以在韦伯看来,政治统治只要获得法律形式上的确立后,就可以利用其他手段(包括道德、宗教、习惯、惯例等)向公众灌输其统治的合法性,让公众对其政治系统或统治秩序产生“合法信仰”。
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理性判断与现代行政法学领域中的“合理性”一词概念内涵并不一致。行政法学领域的“合理性”主要适用在自由裁量权领域,是指行政执法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因而针对的对象是执法主体。而哈贝马斯的合理性原则指的是社会公众依据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对政治系统的理性判断,这强调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价值认同,因此所指的对象是社会公众。
通过对合法律性、合理性的概念辨析后,笔者认为合法性涵盖了合法律性和合理性的内涵,合法性强调的是实定法规范的符合性以及社会公众理性判断的统一。
(二)警察执法合法性
执法合法性是建构在对合法性内涵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上述对合法性概念的分析,笔者认为所谓的执法合法性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执法主体依据法律的规定,在法定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对特定主体或事务所采取的执法行为(强调的是“合法律性”);另一方面是指社会公众根据公平、正义、秩序、安全等价值追求对执法主体的执法活动作出的理性判断(强调的是“合理性”)。执法合法性的具体内涵如下图所示:

具体到警察执法,警察作为特定的执法主体,其执法合法性是指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行政与社会公众对警察执法活动理性价值判断的有效统一。
二、警察执法合法性来源的理论探究
(一)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分析
警察执法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行政权,谈及警察执法合法性来源就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国家权力或统治秩序的合法性来源。
现在普遍认为卢梭最早提出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其在《社会契约论》开篇即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2]但对于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卢梭并不清楚,其在文中主要阐述论证“是什么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legitimate)”。在卢梭看来,社会合法秩序的形成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如果仅依靠强力来获得“服从”的合法性,那么这种合法联系是脆弱的;一旦当人们有能力打破身上的桎梏,这种强制获得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即使统治者通过强力形成“权利”,将服从转化为所谓的“义务”,这种荒谬的“权利义务”依旧会果随因变,伴随着强力的终止而结束。因此,卢梭认为权力或统治秩序的来源在于社会契约。
此后,对合法性来源问题作出开拓性探讨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对合法性问题坚持的是法律多元主义理念,即“法律”并非国家所特有。换句话说,对韦伯而言,凡设有强制机构的社会团体皆有其法律,家有家法,帮有帮规,党有党章,家族、行会、帮会……皆有其自己的规矩(法律)。[3]鉴于此,韦伯指出合法性的来源同样是多源的:即合法性的建构不是简单的法律层面的一致性规则,而是由道德、宗教、习惯、惯例等构成的多维建构规则。在此基础上,韦伯依据合法性来源将合法统治分为传统型、法理型和个人魅力型三种类型。韦伯认为传统型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传统的神圣性;法理型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法律制度;魅力型统治的合法性则来源于统治者个人的非凡魅力。[4]
之后,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对合法性来源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李普塞特提倡统治或社会控制的主体要使公众对其构建的的政治系统、制度甚至统治本身产生合法化的信仰并且坚持这种信仰的能力(这与韦伯的观点类似)。李普塞特创造性地从有效性②有效性是指公众对政用基本功能的期待以及政治系统满足这种功能期待的程度。入手来探究政治生活中的合法性来源问题。李普塞特认为有效性的长期持续会赋予统治以合法性或增强其合法性,反之,有效性的削弱或长期丧失则会危及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但他并不认为有效性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李普塞特视角下政野的合法性离不开有效性,但又不限于有效性。李普塞特从功用角度出发,同样论证了合法性来源的多源性。
而哈贝马斯则基于对韦伯合法化概念的逻辑论证,指出法律形式具有“伪装”功能,即使是违法统治也会通过法律程序主义即外在的法律形式本身来获得统治或权力的合法性。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如果纯粹的正当性想被视为合法性的一种标志,那么,这个统治系统就必须在整体上被合法化。”[5]换言之,哈贝马斯认为要使统治系统合法化,就必须脱离法律的技巧形式,寻求法律形式以外的合法性来源——公众对于统治或权力的理性价值判断。
笔者在对权力或统治秩序的合法性来源梳理后认为:卢梭所指出的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公约。公众通过对权利或自由的让与形成的社会公约,其本质上正是法律。卢梭仍然将合法性的来源局限于法律本身,忽略了即使是违法的统治系统也会通过法律形式来获得统治的可能性。韦伯虽然论证了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多样性,但由于韦伯坚持的“法律”多元性与现代法治国家所要求的合法性存在一定的分野,即使是韦伯声称的法理型统治仍然未脱离法律层面的羁束,强调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服从;李普塞特的有效性理论同样论证了权力来源的多样性,但其仍局限在韦伯的认知理论中,是政治系统通过法律形式确立以后、为让社会成员对其统治产生信仰与认同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忽视了社会公众的合理性判断,其本质仍然是为法律形式获得长久的承认所做的努力。笔者比较赞同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种观点全面揭示了合法性的实质,将基于统治秩序的自上而下的法律形式与基于社会公众的自下而上的价值判断有效的结合起来,考虑到了社会层面对合法性的认知。这与前文所述的合法性内涵完全一致。
综上,笔者认为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包括法律形式层面的明文规定和公众层面的价值判断两个方面。
(二)我国警察执法合法性来源
警察执法其实是警察权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警察从其诞生之初,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国家统治的工具。从最初的奴隶制国家到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伴随着国家历史阶段的不断变迁,警察权的职能属性也由专制化、封建化向今天的法治化、规范化演进。但从政治系统或国家层面而言,警察权作为国家统治权力的本质属性是未曾改变的。
因此,此处的警察权与笔者在前文所述的国家或政治系统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中的“权力”在内涵实质上是完全契合的。所以,上述权力合法性来源分析的结论同样适用于警察执法。因而,我国警察执法合法性来源也必然离不开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基本法律层面的权力授予;二是公众对执法活动的价值判断。
由于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公众视角下警察执法的合法性来源,因此笔者对于法律层面的合法性来源只作简单的阐释,并不赘述。基本法律层面的权力授予意味着警察执法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和法定的构成要件,要依法行为。换言之,我国警察执法法律层面的合法性必然来源于现实颁行的法律。首先,警察执法从其权力设置、运行规定、价值追求等角度而言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其次,《人民警察法》作为我国警察法律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基本的、主要的职责作出了概括性规定。此外,《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则详细列明了警察权在具体执法中的运用及依据。这都为公安机关实践执法活动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因而,在法律层面我国警察执法合法性的来源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根本性授权、以《人民警察法》为概括性授权和以 《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指导性法律①此处的指导性法律是指具体涉及警察行政的法律,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为具体性授权的多层次建构体系。
三、公众视角下我国警察执法合法性来源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不可能作为孤立的个体存在,必然与其他社会个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警察机关作为现代公民秩序的维护者和国家行政职能的重要承担者,也必然会与社会公众发生特定性联系。由于公众并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素养,不能从法律层面上来判断警察执法行为的合法性。但其作为警务活动的参与者(直接的或间接的),对警察执法活动本身有着最直观、最真实的感知。他们对合法性认知往往并不出于法律层面的考量,更多的建构在警察执法事实层面。从警察执法的程序规范,到警察行为的功能属性都影响着公众的合法性判断。所以,公众对警察执法活动的合法性认知主要建构以下两个事实层面:
(一)公众对合法性认知来源于警察执法的程序规范
在警察执法过程中,应注重程序的规范性。如果说实体正义重在结果正义的话,那么程序规范酝酿和生成的正义就是过程正义。王名扬先生曾论述过程序规范的价值:“从抽象的观点来说,实体法是基础,处于首要地位。程序法是执行,处于次要地位。然而从实际的观点来说,程序法的重要性超过实体法,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6]在警察执法实践中,程序规范蕴涵着公平、正义、公开、平等等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正是社会公众基于自身利益和发展所寻求的,是公众合法性认知的理性判断标准,因此程序规范是公众对警察执法合法性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
程序规范主要强调警察执法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告知程序等因素。故而公众对警察执法合法性的认知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警察执法过程中的信息公开。信息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资源。源于警察机制设置、警察执法的结构性等因素,警务信息传播模式是一种以警察为主导的单向的信息传播方式。警察作为警务活动的行为主体,自然比作为信息接收方的社会公众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由于信息拥有量的不足,公众无法清楚了解警察权力运行中的事实情况,社会监督也就成了一纸空谈。这种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对等正是公众对警察执法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依据。而信息公开能有效缩减这种信息不对称差距,使公众能够掌握更多的执法信息,从而对警察执法的合法性作出理性价值判断。
2.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社会参与。一是特定的公众,主要指利害相关人。利害相关人参与警察执法办案既是法律设定的基本方式,同时也蕴含着其对执法活动的认知和判断。通过参与方式,利害相关人可以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表达自己的合法诉求。二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有些可能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案件,如食品药品案件,在执法过程中可以邀请社会公众参与。这样不仅可以接受公众监督,也彰显了执法的价值追求。
3.警察执法过程中的告知程序。通常情况下,公安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作出对执法对象合法权益不利的决定时,要说明相关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其享有的权利。告知程序是警察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承载着维护公众尊严和自尊的价值。告知程序会使公众感受到自己处在一个公正、公开的权力运行过程中,能有效缓解公众对警察权的抵触。
这些举措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公众感受到警察执法办案所彰显的公平正义,进而对警察执法产生理性的价值判断。因此,我国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执法实践中,应严格贯彻落实程序规范的基本要求,要让群众感受到合法性价值。
(二)公众对警察执法合法性认知来源于其功能属性
警察执法的功能属性是指警察执法活动对社会公众所产生的效用。作为理性的社会人,我们都寻求一种能够维护自身发展的公共秩序。这种需要强力维持和建构的社会秩序,正是警察行政的功能效用体现。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由于社会控制机制的转换落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等,将不可避免的产生社会失范等诸多问题。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更离不开警察职能的作用发挥。结合上文分析,社会群体中的大多数并不能从专业的法律层面来对警察执法活动的合法性作出判断,但他们对于这种能维护自身发展的社会公共秩序的共有理念和价值追求与警察执法功能所产生的客观效用是相吻合的。所以,公众往往将合法性认知与警察执法的功能属性相联系。
警察执法的功能通常包括打击犯罪功能、维护治安功能、行政管理功能和服务社会功能。因此具体而言,公众对警察执法合法性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
1.公众对警察执法合法性认知来源于打击犯罪功能。打击犯罪功能实际上强调的是警察权在刑事司法领域的运用。从犯罪的实质看,无论是针对社会个体的人身、财产权益的侵犯,还是对社会公共利益抑或是公序良俗的破坏,都会对合法建构的社会秩序产生侵害。公安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重要构成部分,从其制度设计或历史背景而言,就是围绕着控制和预防犯罪而展开的。其次,从警察执法实践中具体运用的职权而言,无论是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采取的侦查权、预审权,还是对与犯罪相关财产、文件所采取的查封、扣押权等;无论是公开的侦查措施,还是秘密的侦查措施,都具有打击犯罪的功能。最后,从公安机关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的设置而言,也是以打击犯罪为主要需求依据的。公安机关对犯罪的打击,不仅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也是对社会个体成员所注重的归属、安全、规范等需求的保障。
2.公众对警察执法合法性认知来源于维护治安功能。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是社会及其成员的基本需求。从社会个体而言,人们都寄希望寻求一种有序、安全的社会生活模式,这样的生活模式与自身的权益需求相适应,有利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从国家和社会统治层面而言,稳定的秩序模式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因而这也是社会本身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维护社会治安是警察执法的重要功能,是指公安机关依据治安规范对各种涉及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所施行的管理和规范。公安机关维护治安功能作用的发挥能有效维护社会安定、为社会公众创造有序的生活环境。这种功能所体现的有益性正是社会公众对警察执法的合法性认知来源。
3.公众对警察执法合法性认知来源于行政管理功能。公安机关的行政管理事项涉及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户籍、身份证的办理,大到危险物品、特种行业的管控,都切实关系着公民的切身利益。在具体的行政管理过程中,警察执法办事的方式、态度、效率等因素都切实影响着公众的合法性判断。
4.公众对警察执法合法性认知来源于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是警察执法为民的体现。长久以来,我国公安机关一直将人民利益作为警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例如我国推行的社区警务模式就是警察服务功能的体现。此外,公安机关的各项管理工作其实都是和服务相关的,警察执法功能也蕴含着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保障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为人民创造安定、有序的生活模式,就是对人民最好的服务。美国学者迈耶和泰勒甚至认为“民众报警更多的是为了服务,而不是为了执行法律。”[7]所以,如果警察的公共执法服务功做得好,能让公众满意,公众就会对警察执法活动产生价值认同,从而对其合法性作出正面评价。
四、结语
公众视角下警察执法合法性在于执法活动本身。警察执法过程中程序规范性、执法功能的有益性都与社会公众个体或集体意识层面的价值追求相同,是公众合法性认知的理性判断标准。因而,在对警察执法合法性建构的过程中,不能仅从法律层面进行考量,而偏废了公众视角的合法性建构。只有均衡化法律层面的权力授予与公众层面的价值判断,警察执法活动才会真正得到社会公众的信仰与认同。
[1][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7,241.
[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
[3]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
[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31.
[6]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41.
[7][美]罗伯特·兰沃西,劳伦斯·特拉维斯.什么是警察——美国的经验[M].尤小文,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332.
Study on the Sources of Legitimacy of Law Enforc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Ling Zhi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38)
Legitimacy refers to the compliance with the law,as well as the unity of rational judgment to the public,including legality and rationality.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power sources,clarify the legitimacy of law enforcement comes from the law and the public value judgments based on the fact of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To the public,the criteria of value judgments includes the procedure in the course of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police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Public security organs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procedure and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thus obtain the public value judgments.
legitimacy;public;police law enforcement;sources
D631
A
1671-5101(2016)05-0018-05
(责任编辑:王泓)
2016-05-17
凌志(1990-),男,安徽合肥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4级治安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治安学、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