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生命共享希望
2016-05-14王怡波
王怡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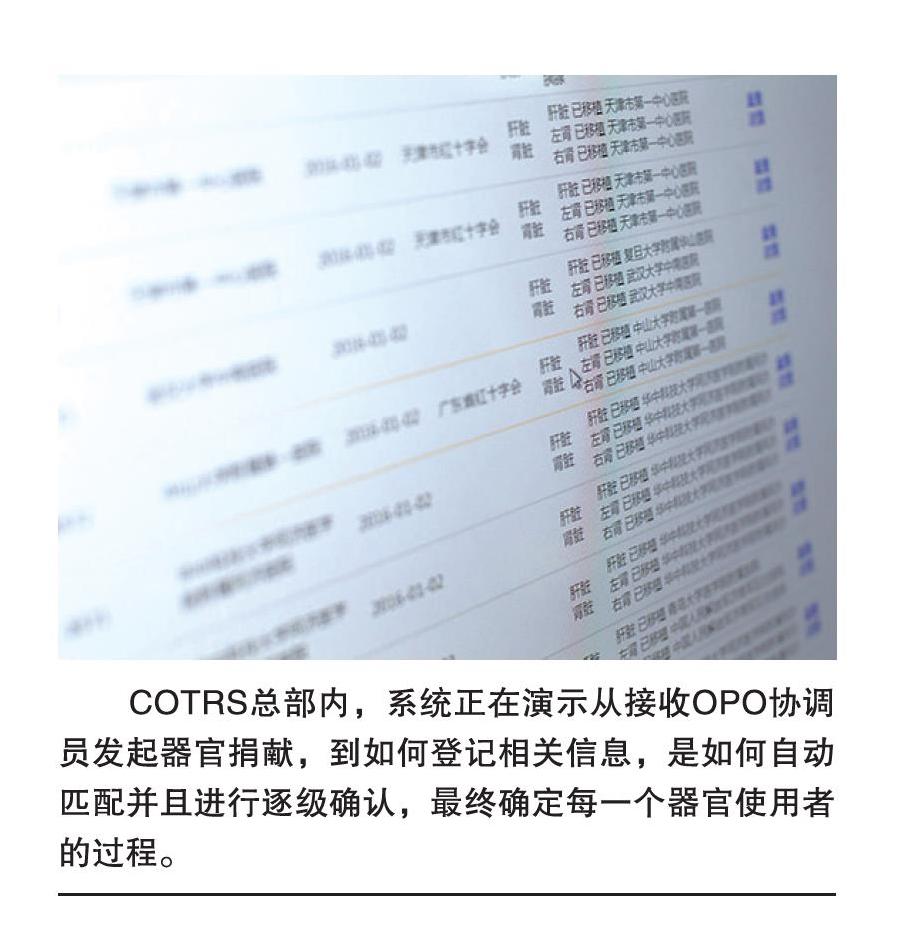
人体器官是稀缺资源,解决好“怎么分配”,是涉及整个捐献移植体系能否赢得老百姓信任的基石。
人体器官分配是信任基石
器官是稀缺资源,但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稀缺资源。
2010年,当在香港长期从事器官移植科学注册系统研究的王海波团队接受任务,研究器官分配政策时,对于器官捐献的社会信任度就处在令人堪忧的状态中。
“器官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也不是生产出来的,是老百姓捐出来的。”王海波说,任何捐献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用”,器官捐献中,如果讲不清这个问题,那就失去了社会的信任。
王海波认为,实际上,如何保证老百姓对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信任,才是一切工作的基石。“只有说明白是如何使用的,才会有人捐献。器官捐献的基石实际上并不是医疗技术,而是社会信任。”
在系统全面铺开之前,有网友曾在网络上质疑,器官的分配是不是就以两个标准来衡量:钱和权。
王海波说,要获得公众支持来稳定整个信任体系的根基,器官分配的透明和器官的可溯源性就要保证,“要清楚地记录它怎么来,根据什么原则,去到哪里?如果这些能够做到公开透明的话,就能确保公众信任体系的建立。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器官这个稀缺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王海波说,医学需要是唯一的排序标准,而不是权力,不是财富。
是政策决定如何分配,不是计算机
2013年8月,国家卫计委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实行)》,首次明确严格使用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TRS系统)实施器官分配。王海波团队设计的系统开始成为器官捐献后分配的唯一通道。
“分配器官就是分配生命。”王海波说,如何搭建完善的分配体系,最根本的是先有清晰的分配政策,这些复杂的政策最终掌握和“分配生命”的大权,其最终目的,是使器官最安全、最高效地匹配给最需要的人。“COTRS系统只是从技术手段上,承载了这些政策。”王海波说,有人会误认为,现在的分配机制是由计算机决定的,“其实不对,计算机系统只是执行者,负责分配的是政策。”
在综合评定原则中,排在首位的是病情危重原则。“第一个目标是要降低等待名单的死亡率。”王海波解释,就是从医学需要出发,使在等待名单上的人,死亡率降下来,“这样是最佳的匹配”。
经过一套严密的评分系统测算,每一名在COTRS系统里排队等待移植的患者都会生成一个分数,而一旦发生器官捐献案例,经过区域优先原则筛选后,这个分数的排序将成为器官分配顺序的最重要依据。“如果一个病人不接受移植,死亡的可能性是90%,另外一个病人是10%,当然要先救那个90%的病人。”王海波说。
复杂的政策仍在不断进化中
COTRS系统的使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器官分配的各种人为干预的问题,甚至一些伦理难题。例如,器官捐献者能否指定将器官捐献给亲人?如果在传统意识中,这应该是可以的。但在严密的分配政策中,答案是否定的。
王海波便曾经接触过一个这样的案例。2011年起,一名29岁的患者黄某患慢性肾功能衰竭,在上海一家医院等待肾移植;2013年8月20日,他的父亲因交通意外,被送往医院救治无效,脑死亡,家属决定捐献器官。但他的器官只能进入系统分配,而不能指定捐献对象。后来,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系统破例,允许他捐一个肾脏给儿子,但最终因为血型等医学原因,这个肾脏没能用在儿子身上,还是进入系统分配。
“但是分配政策中设计有专门针对器官捐献者直系亲属的优先原则。”王海波说,黄某因为父亲捐献在排队系统中获得了加分,在其父亲过世大概一个月后,便通过分配系统获得右肾,成功进行了肾移植手术。
这只是捐献器官分配中可能碰到的极端情形的一种,分配政策需要考虑到各种复杂的情况。“排队最简单原则就是四个字:先到先得。但是,全国世界器官分配的政策都是从等待时间开始,很快演化为纷繁复杂的分配政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要避免人为干预,尽可能保持公正公平。”王海波说。
为了保证能应对各种情况,这套本已十分复杂的系统,仍在不断地完善进化中。但是,政策的改变要通过一个公平公正的过程,不能是某个人说的算,而是专家委员会定下来,然后还要评估政策改变会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复杂的业务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