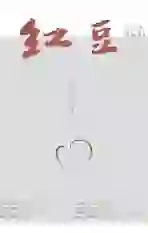感谢生活
2016-05-14高维生
高维生,满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出版有《浪漫沈从文》《点燃记忆》等十几部散文集。作品入选《21世纪年度散文选·2001散文年选》《1979-2008中国优秀儿童文学典藏》《2002中国散文年选》《2003中国散文年选》《百年中国性灵散文》等多种选本。
这些琐碎的小事
丰子恺离开故居一段时间后,每次归家,他都要坐到南窗下的书桌旁,感受思念的滋味。
阳光从窗口投映进来,光线落在桌上,驱散没有主人的寂寞。初冬的风清冷,窗外的太阳不那么毒辣。丰子恺的椅子靠在窗边上,他坐在里面背对窗子,阳光投在身上,晒得暖洋洋的。排除一切杂念,捧一本书读,这是他所追求的状态。
多年养成的习惯,早饭后清理书房,擦一擦写字台,书摆在案头,按读的秩序摞好。要精心,有纪律,养成的规矩不能乱,读书不能没有头绪地抓一本就读。
案头摆放着一摞新书,等待盖上藏书章。书中有朋友的作品,有的是新买的书。人坐在书山中,书中的文字汇聚一起,形成巨大的河流。坐在案前是一种享受。书房弥漫书香味,一些重要的文章,都是在那里完成。
家是温馨的地方,身心全部放松,在书房中尽情地挥洒想象,不会有人破坏心情。丰子恺带着一身疲惫回家,当他坐在桌前,捧起一本书读,思绪变得自由,在时间中奔跑。
我掩卷冥想:我吃惊于自己的感觉,为什么忽然这样变了?前日之所恶变成了今日之所欢;前日之所弃变成了今日之所求;前日之仇变成了今日之恩。张眼望见了弃置在高阁上的扇子,又吃一惊。前日之所欢变成了今日之所恶;前日之所求变成了今日之所弃;前日之恩变成了今日之仇。忽又自笑:“夏日可畏,冬日可爱”,以及“团扇弃捐”,乃古之名言,夫人皆知,又何足吃惊?于是我的理智屈服了。但是我的感觉仍不屈服,觉得当此炎凉递变的交代期上,自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足以使我吃惊。这仿佛是太阳已经落山而天还没有全黑的傍晚时光:我们还可以感到昼,同时已可以感到夜。又好比一脚已跨上船而一脚尚在岸上的登舟时光:我们还可以感到陆,同时已可以感到水。我们在夜里固皆知道有昼,在船上固皆知道有陆,但只是“知道”而已,不是“实感”。(丰子恺:《初冬浴日漫感》)
丰子恺很久不这样恣意,一个人不被打扰,坐在南窗下,被初冬的日光笼罩,身上竟然发出细汗。
我看到丰子恺回到家,不需要掩饰什么,卸下在社会上应酬的面具,他索性将书搁在桌上,整个身子躺在藤椅里。人的身体方向改变,看物的视觉发生变化。视角的不同,再瞅屋子里的东西,觉得与以往不一样。夏天空气闷热,凝固在室内空间散不出去,人宁可待在外面,嫌屋里小不愿进。即使敞开所有的窗子,打开屋门都不够。现在天气转凉,刮来的风阴冷,屋子里被阴气充满。突然觉得空间太大,有一点热气,马上被冷气吸收。丰子恺泡了一壶茶,案上的热水壶,夏天摆在面前,嫌它散发热能,都将它放在远处。现在博得人们的喜爱,伸出两手抱一下,暖暖凉手。棉被变成人们的爱物,夏季它挂在天井的绳子上,暴晒在阳光下,从布的纤维中散发的热量,无人愿意抚摸。季节一转换,现在重新回到床上,人们感受暄软,嗅布质的清香味。
人的心态不是一成不变,天气的阴晴,空气的湿度,控制人的情绪。季节的更替,人变得不可思议。
沙发椅子曾经想卖掉,现在幸而没有人买去。从前曾经想替黑猫脱下皮袍子,现在却羡慕它了。反之,有的东西变坏了,像风,从前人遇到了它都称“快哉”!欢迎它进来。现在渐渐拒绝它,不久要像防贼一样严防它入室了。又如竹榻,以前曾为众人所宝,极一时之荣。现在已无人问津,形容枯槁,毫无生气了。壁上一张汽水广告画。角上画着一大瓶汽水,和一只泛溢着白泡沫的玻璃杯,下面画着海水浴图。以前望见汽水图口角生津,看了海水浴图恨不得自己做了画中人,现在这幅画几乎使人打寒噤了。(丰子恺:《初冬浴日漫感》)
注视窗口的小书架上,裸体的洋囝囝,原封不动地坐在那里。不是视觉转换的因素,“以前觉得它太写意,现在看它可怜起来。”阳光的暖意,使身子松弛下来。丰子恺对身边的东西,一一观察。
丰子恺对于事物观察敏感,捕捉细微之处,从中发现人生的道理。四季不止一个,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在外面见的人与事多,对待事物与以往不同,对世界的看法不断变化。
回到老家躺在藤椅里,听着窗外后河的流水声,不需要考虑时间,静心是最好的状态。丰子恺离开大城市,突然一下清静,思想比往日更清楚,想的事情反而多了。“其实,物何尝变相?是我自己的感觉变叛了。感觉何以能变叛?”这个反问,埋藏很多的缘由,一个人对自己梳理不清是危险的。只有不断地追问,残酷无情地审视自己,人才能一步步成熟。
窗外建筑工地的轰鸣声,带着撕裂的尖锐,钻进我的书房里。我看到丰子恺躺在藤椅里,在深思人生的大问题。他的每一个文字里,灌注对生命的体验。
感谢生活
船老大将船调头,稳稳地靠在岸上。不远处有一家小杂货店,旁边的绿草地上,搁着剃头担子。
在船上时,丰子恺透过窗子,观看岸上情景,视觉中心落在剃头担子上。职业的敏感,促使他打量挑担人一举一动的神态。丰子恺观察剃头师傅的言行,他坐在凳上抽烟,有顾客来后,将座位让给另一个人,从担子里拿出工具,给新来的人剃头。丰子恺有很多写实的漫画,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寻找特定的人物,故意典型化,作为描绘对象。丰子恺喜欢常态生活,在普通人身上,发现有趣味的画面进入作品。
船在水中走,船窗变作画框,从中移动出现实的立体画。“这图中的人物位置时时在变动,有时会变出极好的构图来,疏密匀称姿势集中,宛如一幅写实派的西洋画。”并不是两岸的自然风光,将丰子恺吸引住,剃头师傅的表现,使他有了创作的冲动。他在活动的画框中,寻找最佳的画面,人未到岸,画面构思成熟。
2007年,我编《滨州广播电视报》副刊,刊发师专学生写的《清河镇年画》。从那时开始,我记住了有着600年历史的年画,还有传人王圣亮。有一次他来到编辑部,带着一沓年画,并送了我一幅门神。我从东北来到滨州,一晃二十多年,对它的文化了解才刚开始。清河镇年画,拨开时间的浓雾,浓烈的乡土气息,感染人的情绪。
2010年12月3日,第一次去清河镇在丁庄下车,王圣亮说穿过十字路口,向南走不很远的路。我按照声音地图的指引,横穿十字路口,一直向路南走去。阴历二十八,正是丁家大集,走出不远,碰到理发的老手艺。白土布搭成的帐篷,理发师傅戴着蓝布帽子,穿着蓝中山装,脚上是手工做的棉布鞋,他在给顾客理发,地上丢弃剪落的头发。帐篷的边上,挂着长方形的红幌子,写有“惠民理发”的字样。我久未看到露天理发,举起相机,被理发的老人扯着嗓子喊住,他不高兴地拒绝拍照。
意外碰到的露天理发铺,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我读丰子恺的《野外理发处》,画面的上方,留有一片空白,师傅正在给顾客理发,几条粗线,流畅地勾勒出轮廓。看似简单的画面,传达出鲜活的人情味和当地的风俗文化。丰子恺受佛家影响,爱是他思想的骨骼,支撑创作的根基。丰子恺画出大量的乡土风俗漫画,文字中也写出家乡人的真实,他们的善良和对生活的自信。
船在水中有一些小摆动。丰子恺向岸上眺望,小杂货店,一块绿草地,剃头担子构成的画面,影响丰子恺的情绪。他注视剃头师傅,这是一个鲜活的情景,浓重的生活气息,一拨拨地扑来。丰子恺看到被剃者,身不由己,只能任人摆弄,平时高贵的头变得温顺。剃头师傅敬业,耐心地给顾客清洗,“不管耳、目、口、鼻,处处给他抹上水,涂上肥皂,弄得他淋漓满头;拨他的下巴,他只得仰起头来;拉他的耳朵,他只得旋转头去。”船驶向岸边,将剃头的情景拉近。发现被剃头的顾客,身体结实,在剃头师傅的手下十分听话。小凳子勉强支撑住他的身子,屁股有一小半悬在空中。丰子恺从中看出滋味,感受到另外一种东西,“人在被剃头的时候,暂时失却了人生的自由,而做了被人玩弄的傀儡。”
此外,丰子恺漫画注重写神气,讲求“气韵生动”,这与西洋画注重写实截然不同,他非常推崇王维“画中有诗”。这些。实际上正是他的一种美学追求。丰子恺漫画不以直接社会功利为创作目的,而以题材的小中见大,是否有内涵,是否有诗意作为审美尺度。三是丰子恺漫画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生哲理。丰子恺从小深受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他的世界观,儒释道并存,兼蓄老庄。丰子恺的社会风俗题材画,常以旧社会底层劳动群众为主人公。这种艺术视角的选择,和儒家哲学“仁”即“爱人”密切相关和佛教普度众生教义也不无关系。(刘飞飞著:《都市文化视野中的丰子恺漫画》)
1934年6月10日,丰子恺想将船窗中的画面速写在纸上。他取出速写簿,拿起铅笔,眼睛在审视。他的笔触在纸上,情感凝聚笔尖,等待暴发出的线条。丰子恺酝酿成熟,画出野外理发处,摆在船中的小桌子上。他仔细地端详,“这被剃头者全身蒙着白布,肢体不分,好似一个雪菩萨。幸而白布下端的左边露出凳子的脚,调剂了这一大块空白的寂寞。”丰子恺觉得缺点什么,又在凳脚的下端,“擅自”添加一笔浓墨,表现被剃头的顾客露出黑裤的一部分。
船终于靠岸,船主人随丰子恺下船,顺便给小杂货店十个铜板,买新采的一篮豌豆。店主看见丰子恺在修补画,便放下盘子来看。
“啊,画了一副剃头担!”他说,“像在那里挖耳朵呢。小杂货店后面的街上有许多花样:捉牙虫的、测字的、旋糖的,还有打拳头卖膏药的……我刚才去采豆时从篱笆间望见,花样很多,明天去画!”我未及回答,在我背后的小洞门中探头出来看画的船主妇接着说:“先生,我们明天开到南浔去,那里有许多花园,去描花园景致!”她这话使我想起船舱里挂着一张照相:那照相里所摄取的,是一株盘曲离奇的大树,树下的栏杆上靠着一个姿态闲雅而装束楚楚的女子,好像一位贵妇人;但从相貌上可以辨明她是我们的船主妇。大概这就是她所爱好的花园景致,所以她把自己盛妆了加入在里头,拍这一张照来挂在船舱里的。
丰子恺抬起头,新出锅的豌豆散发香气,他并没有马上吃。看着店主对比中的赞美,有一些讨好他的意思,同时肯定他画的像。在店主的身上,丰子恺发现朴素的美,不是人工所能创造的。
吃着豌豆,和船家夫妇俩扯了一些闲话,又得到一幅画作,心情格外好。
一次不快乐的旅行
1934年8月15日,丰子恺在杭州招贤寺回忆一次难忘的出行。那一天的清晨,不过六点多钟,温度计上的数字爬升很高。丰子恺为了赶路,走得有些匆忙,他胳膊上搭着夏布长衫,拎着行囊,在晨光的映照下,来到河埠上船。
船事前早已订好,舱中有路途上的用具,“备着茶壶、茶杯、西瓜、薄荷糕、蒲扇和凉枕。”为了这次写生,他做好一切准备,本应是愉快的旅行,丰子恺踏上晃动的船,并没有往日的兴奋。坐在舱里面对熟悉的茶壶,身上浮出细密的汗水,丰子恺抹掉脸上的汗水,鼻孔钻满水湿气。船老大看到雇主坐稳,扯了嗓子问,一切情况正常,船离开岸边,驶向河中心。
船在河水中行,流动的河水声使丰子恺的心安静。他望着两岸的青山,古老的村庄,偶尔有一声鸡啼传来。船老大穿着对襟短褂,露出结实的肌肉,一层汗水浮出,被阳光照耀,焕出另一种色调。天气闷热,无一点风动,连续的高温,人陷入焦灼的包围。天气这么早,太阳憋足劲,阳光照在船棚底上。路途还长,丰子恺转移注意力,调整心情,从行囊中找出《论语》,封面题有李笠翁的话。“说道人应该在秋、冬、春三季中做事而以夏季中休息,这话好像在那里讥笑我。”丰子恺读后,觉得李老先生的话针对他。这样的热天,躲在家中最好,泡一壶茶,摇动芭蕉扇,躺在藤椅上,读一本喜欢的书。丰子恺这一天必须出门,他有事情要办,不是以前坐“写生画船”。那是美好的季节,暮春天气,丰子恺雇一只船,搬上书籍、被褥、器物,摆进船舱中,坐在其间,如同在家中一样。一条大河宽又宽,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听凭船主人摇到哪个市镇靠夜,便上岸去自由写生,大有‘听其所止而休焉的气概。”丰子恺不是写生,是有时间限制,赶十一点钟的火车。心中有事,人坐在船上,什么都不顺眼。丰子恺透过船窗向外张望,劳动的情景冲进眼帘。
从家石门湾到崇德的距离,水路不过十八里,沿运河的两岸,排列数不清的水车。农人穿着一条短裤,光裸上身,伏在水车上,一下下地踏水。
船老大在运河上来往,每天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他是久闯江湖的人,善于察言观色,掌握人的心理活动。他看到丰子恺对水车感兴趣,便得意地说:“前天有人数过,两岸的水车共计七百五十六架。连日大晴大热,今天水车架数恐又增加了。”丰子恺听后,感到非常惊讶,佩服有心人的耐力。丰子恺望着旋转的水车,将水排起,转送到大地中,灌溉干渴的田苗。“设想从天中望下来,这一段运河大约像一条蜈蚣,数百只脚都在那里动。”
船到达目的地,丰子恺走下船,心情沉重提不起精神。离开船上岸,人一下子扑进阳光中,行囊变得沉甸甸的,每走一步都感到艰难。
他时常对时间、空间、人生进行思考,深感人生的无常,并欲在佛理中寻求答案。但是佛、道两家的影响使他具有了达观、超脱的人生态度,能够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能够以距离审美关照身边的琐事、杂事、不平事。同时佛家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以及儒家的入世“仁义”的思想,使他不能视人与社会的苦难而不见,悲天悯人,扬善抑恶,执着地追求真、善、美。一只脚立于现实,一只脚迈向理想,这也就是他儒道释兼容的思想以及“出世”“入世”合二为一的最好印证。(林秀明著:《丰子恺散文创作论》)
船老大说,只是个大概的数字,远不止这些,运河有多少架水车,谁也说不清。如果这样连续大旱,“田里、浜里、小河里,都已干燥见底;只有这条运河里还有些水。”现在运河的水浅,遇到会船的时候,听见触碰河底的声音。农人靠天依水吃饭,没有其他的水源供应庄稼的需求,农人就把水从运河车送到小河,小河边上的水车,再将水收集到浜里,浜上的水车输送进田里。古老的水车,看似那么简单,送水经过复杂的工序,才能完成最后的一送。
在逃难路上,有过生死患难的章桂,在后来的回忆中,记得一段亲身经历,他在《怀念敬爱的老师丰子恺先生》中说:
大约是1934年吧,我们故乡特遇百年难逢的大旱灾。灾情严重,古运河河底朝天。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束手无策,听凭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大旱之望云霓》这张画,是先生对当时劳苦农民日夜车水、艰苦挣扎的情景,发自内心的深表同情之作。此画作后,悬挂在缘缘堂楼下西书房内门后。就是那年,我国驻瑞士公使戴葆流先生夫妇,专程由沪来石湾访问先生,而先生却适去莫干山看望他的姐姐去了。因戴先生要求得到先生一点作品留作纪念,是我做主,将此画初稿赠给了戴先生。现在不知有否保留。(丰一吟著:《缘缘堂的夏天》)
一阵锣声响起,清脆的声音,在水面上滚动,被河水卷进水中。一声号令,农人停下劳动,带着一身汗水,找到庇荫处,坐着休息一会儿。有人摘下挂在桑树上的篮子,拿出从家带来的吃食。他们吃了早饭,出门车水时,带了一篮蚕豆。饿时吃几口蚕豆充饥,马拉松似的活,不是车一阵子完事,必须车到半夜,才能回家去睡觉。嘡嘡嘡的锣声响起,农人离开乘凉休息的地方,又蹬上水车。“无数赤裸裸的肉腿并排着,合着一致的拍子而交互动作,演成一种带模样。”丰子恺看到这样的情景,旅行充满太多的痛苦,找不出快乐。
住在都会的繁华世界里的人最容易想象,他们这几天晚上不是常在舞场里、银幕上看见舞女的肉腿的活动的带模样么?踏水的农人的肉腿的带模样正和这相似,不过线条较硬些,色彩较黑些。近来农人踏水每天到夜半方休。舞场里、银幕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正是运河岸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
人与自然的残酷搏斗,他看到农人劳动的景象,毒辣的阳光下,没有任何遮挡之物。太阳燃烧大地,痛快淋漓地狂吸土地里的水分,运河水变浅。离丰子恺不远处,有几架水车运转,农人的两条腿,不停地踩踏。他们在和太阳战斗,凭自己的力量,争夺救命的水。丰子恺坐在火车里,不快无法排除。
责任编辑 卢悦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