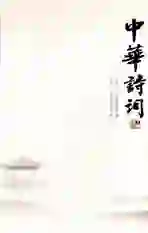“诗避重字说”辨析
2016-05-14李旦初
李旦初
所谓“诗避重字”,是指一首诗内不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的字。此说的唯一依据,大概是毛泽东为他1935年所作的七律《长征》后来修改时加的一条白注:“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长征》诗原作中的两个“浪”字,指“金沙浪拍云崖暖”和“五岭逶迤腾细浪”两句中的“浪”字。我倒觉得不改完全可以,改了还不如不改好。因为“浪拍”之“浪”是实指,“腾细浪”之“浪”是喻指,这两个浪字字义并不相同,而“浪拍”显然比“水拍”更有声有色、更有气势,形象更美。何况这样一改,虽然没有了两个浪字,却又有了两水字,即“金沙水拍云崖暖”和“万水千山只等闲”两句中的“水”字,而这两个水字都是实指,字义完全相同。而且,这一篇内还有两个“军”字、两个“千”字、两个“山”字,为什么都没有改呢?由此可见,以《长征》诗这条作者自注作为“诗避重字说”的立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重字现象在历代诗词中屡见不鲜,普遍存在。张若虚的名作《春江花月夜》,一篇内用了15个“月”字,被闻一多誉为“诗中的诗,顶峰的顶峰”。元代丁复的《月湾钓者歌》共47句,用了43个“月”字,创造了引人人胜的奇妙意境。此类古风大概不在“避重字”之例,姑且不论。
重字在律诗、绝句和词中出现的频率并不亚于古风。如白居易用“东”韵的七绝34首,一篇内有重字者多达22首。其中《暮江吟》一篇内就8个重字。我推测他作诗不但不避重字,有时还刻意追求重字,以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他有一篇区区小令《长相思》,用了15个重字,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把情意缠绵的思绪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诗词的重字不仅是一种正常现象,而且还是多样而巧妙的艺术表现手法。这是因为,诗词创作使用某些富于表现力的修辞手法和富于美感的特殊句式,不可避免地要出现重字。或者说,由于艺术表现的需要,要求作者在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中善于创造性地使用重字。
诗词重字大体可分八类,现分别举例说明。
(一)叠字。这在诗和词中都十分常见。叠字的作用在于增强绘声绘色的描写力度,并以铿锵的韵律营造抒情氛围。例如:“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维《渭城曲》),“青山隐隐水迢迢”(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平林漠漠烟如织”(李白《菩萨蛮》),“帘外雨潺潺”(李煜《浪淘沙》),“斜晖脉脉水悠悠”(温庭筠《梦江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声声慢》)。
(二)叠句。某些词牌在规定的位置必须用叠句或叠韵。如《如梦令》的第五、六句,《调笑令》上、下片的首二句,《相思令》上、下片的首二句等。例如:“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李勖《如梦令》),“团扇,团扇,美人并来掩面”(王建《调笑令》),“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同上),“花似伊,柳似伊,花柳春来人别离”(欧阳修《长相思》),“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林逋《长相思》)。
(三)顶真。顶真修辞法的两种格式在诗词中都不乏其例。第一种是在同一首诗词中“用前一句的结尾来做后一句的起头,使邻近的句子头尾蝉联而有上递下接趣味”(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例如:“相府潮阳俱梦中,梦中菏泽市穷通”(自居易《寄潮州杨继之》),“一渠东注芳华苑,苑锁池塘百岁空”(杜牧《甘棠馆御沟》),“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白居易《长相思》),“芰荷香喷连云阁,阁上清声檐下铎”(潘阆《酒泉子》),“千万恨,恨极在天涯”(温庭筠《梦江南》)。
第二种是在同题组诗中用前一首的结句来做最后一首的起句。如王安石《忆金陵三首》(皆七绝),用第一首的结句“烟云渺渺水茫茫”做第二首的起句,第二首的结句“追思往事故难忘”则做第三首起句,使三首浑然一体,极具回环婉转的韵味。
(四)连动。一句之中的重字相连(但非叠字),分别用作谓语和主语,表示前后发生、连续进行的动作。这种诗句读起来顺口,别有风味。例如:“眼见客愁愁不醒”(杜甫《绝句漫兴》),“使君何在在江东”(白居易《宿窦使君庄水亭》),“花园应去去应迟”(白居易《杏园花落时招钱员外同醉》),“手把红旗旗不湿”(潘阆《酒泉子》),“泪眼问花花不语”(欧阳修《蝶恋花》)。
(五)连环。一句之中重字相间,分别描写两种并列或对立的事物或情景,连环相扣,读来朗朗上口,意韵流畅。例如:“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半入江风半人云”(杜甫《绝句漫兴》),“半江瑟瑟半江红”(白居易《暮江吟》),“露似珍珠月似弓”(同上),“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白居易《王昭君》),“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苏轼《蝶恋花》)。
(六)对仗。诗的对仗上句的重字与下句的重字相对。但不允许同字相对,还必须平仄相对。重字对有叠字对、流水对、连环对、成语对等多种形式。例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杜甫《曲江》),“不明不灭胧胧月,非暖非寒慢慢风”(白居易《嘉陵夜有怀》),“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风力渐添帆力健,橹声常杂雁声悲”(陆游《望江道中》)。
词的对仗比较灵活自由。对仗位置按词牌规定或按惯例,有些地方可用可不用。允许同字相对,也不一定都要平仄相对。例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蜂也销魂,蝶也销魂”(张炎《一剪梅》),“春到一分,花瘦一分”(吴文英《一剪梅-赋处静以梅花见赠》),“风又飘飘,雨又潇潇”(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
(七)反复。为了突出某种事物或情景,有意用同一语句加以反复强调,以表达强烈的情思。例如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此诗历来为人称道之处,在于“期”两见,“巴山夜雨”重出。两个“期”字一问一答。问者与答者南北相隔千里。两个“巴山夜雨”一虚一实,前者实写此时此地羁旅之苦;后者想像他日还乡之乐。此时此地的“巴山夜雨”却成了与亲人剪烛夜谈的有趣话题。构思之精巧,意境之独创,感情表达之深刻,皆得力于别出心裁的反复。
又如李白《忆秦娥》,上片的“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桥伤别”,下片的“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如此回环反复,使伤别情绪表达得十分强烈。
(八)呼应。即诗词作品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使之章法严谨、脉络贯通。呼应手法有明暗之分,明法直接从字面上加以照应,前后出现重字是很自然的。例如杜甫的《对雪》:“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这首五律是安史之乱期间杜甫身陷长安时写的。通篇抒发战乱造成的种种愁苦,故以“愁吟”起,以“愁坐”结,前后呼应,首尾圆合,历来为人们所称赞。其中“愁坐”句早已被一百年前出版的《辞源》引用作为解释“书空”的经典例证。然而,现在却有人认为前后出现两个“愁”字是此诗的“微疵”,为避重字,可将“愁坐”改为“面壁”。这显然是持“诗避重字说”者的一种偏见。
又如辛弃疾的《西江月·遣兴》,上片开头为“醉里且贪欢笑”,下片首句为“昨夜松边醉倒”,前后出现两个“醉”字,呼应之法与杜甫的《对雪》如出一辙;这又如何“避重字”呢?更有趣的是下片:“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日去!”不仅又多了一个“醉”字,而且每句有一个“松”字。正是写醉倒后与松交谈,以“问松”、“疑松”、“推松”,写出了活灵活现的醉态,写出了妙趣横生的戏剧性场面。难道三个“醉”字和四个“松”字还能改吗?
以上分类列举了诗词重字的若干例句,足以证明“诗避重字说”既无理论依据又无事实依据,无须多举全篇例证。有人说“重字也是违律”,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试读白居易的《采莲曲》:“菱叶萦波荷飚水,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这首意境优美、极富情趣的绝句,用了两个“荷”字、两个“水”字、两个“头”字,违律了吗?没有。苏东坡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用了两个“月”字、两个“天”字、三个“有”字、三个“不”字、三个“何”字、三个“人”字,违律了吗?也没有。如果要说重字违律,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诗词韵脚重字(某些词牌规定用叠句或叠韵者例外),二是诗的对仗上句与下句重字相对。这两种重字一般是必须避的。此外,如果字义完全相同、语意完全重复,也要力避重字。除此之外,再无重字可避。
诗词重字是一种技巧、一种艺术。我们必须从“诗避重字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造性的去追求重字艺术的审美趣味,而不要作茧自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