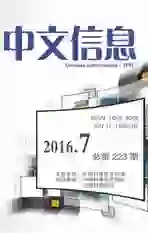自由即奴役
2016-05-14钟文
钟文
摘 要: 《饥饿艺术家》作于1922年春,为卡夫卡本人所珍惜的六个短篇之一。笔者拟从“寓言性”、“矛盾性”入手来观照卡夫卡的所建构的文学世界以及其所投射出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卡夫卡 饥饿艺术家 双重思想 寓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7-0390-01
木心将尼采、托尔斯泰、拜伦均列入飞出的伊卡洛斯。笔者认为卡夫卡亦可归入此类,定要飞出迷楼,靠艺术的翅膀。
一、现实与寓言的交织
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是一个构建在无数寓言故事之上的荒谬寓言性世界。在这里,人类荒谬、动物荒谬,连空气似乎也是荒谬的。卡夫卡诉诸寓言,重新解构现代人类的生存现状。
身着“黑色紧身服、脸色苍白、瘦骨嶙峋”的饥饿艺术家可以说是现实世界的闯入者“任何人对他都变得不复存在,连笼子里那对他至关重要的钟表发出的响声也充耳不闻”,他排斥现实世界,同时,也被现实世界所排斥。
笔者注意到,饥饿艺术家的表演是以四十天为周期,而耶稣禁食也是四十天。《圣经》记载,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一如饥饿艺术家反抗马戏团经理、反抗看守者、反抗观众、反抗世界,他的这种抗争,被卡夫卡作品的译介者叶廷芳认为是西绪福斯式的悲剧精神,沉默地、日复一日地却也是无望的。他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这种同“愚昧的世界抗争是徒劳的”,但却也依旧殉道式的在这条认定道路上向前,“知其不可而为之”,靠的是其强大的内心世界,那种穷尽一生为达到自己渴求的境界,他可以舍弃无用的驱壳,甚至于对他来说,这驱壳只是累赘。
结尾处,饥饿艺术家终于道出了一直挨饿的原因——“找不到适合我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我不会招人参观,若人显眼,并像你,像大伙一样,吃得饱饱的。”
这之中所透出的冰冷的孤立与隔绝感,正是卡夫卡本人内心投影。殉道的艺术家正是作者自况,据说,卡夫卡病中在榻上艰难地校对完此篇后,留下了悲伤的泪水,一个月后,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饥饿艺术家以生命为代价追寻的艺术的自由,没有欣赏的观众。饥饿艺术家自己心里最清楚,只有他自己“才算得上是对自己的饥饿表演最为满意的观众。”
有人评价毕加索“是一个故意的扭曲者”,卡夫卡说:“我不这么认为。他只不过是将尚未进入我们意识中的畸形记录下来。艺术是一面镜子,它有时像一个走得快的钟,走在前面。”这一评语也十分贴切地形容了卡夫卡自己的文学艺术特征和价值。卡夫卡的作品和毕加索的画有着同样的超前指涉与现实意义。
就像叶廷芳阐述的那样,某些文学艺术往往要以“怪物”形象在人们的记忆里潜藏一段时间,直到这一时代的审美意识在人类中普遍觉醒。
卡夫卡在他所处的时代没有找到同类,这也是他最疼痛的部分——他在注定孤独的路上孤独到底,一个人,没有同类。
二、自由即奴役的矛盾
悖谬“是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公式,是卡夫卡揭示世界荒诞性、存在的悲剧性的重要手段”。这里简要分两个部分阐述:
首先是取代饥饿艺术家的一头年轻的美洲豹,它似乎“什么也不缺”,“而且连自由好像也带在身边”。比起饥饿艺术家,观赏者们更愿意为美洲豹驻足,“看到这只野兽在闲置长久的笼子里活蹦乱跳”即使他们很难享受到轻松,可是依旧“挤在笼子周围,丝毫不肯离去”。
这矛盾恰反应了“非人化”的开始。二十世纪继“上帝死了”之后,失去精神家园的人类,是矛盾的、荒诞的、异化的,人性开始于兽性沦为一体。
于此,将观赏者和美洲豹归为一类,他们同处于“悖谬”中而无法自知。套用奥威尔的在《1984》中英社“双重思想”中的“自由即奴役”来解读——他们均认为自己处于自由状态,实则是被奴役的客体,自囚于笼中。这种双重思想也是贯穿于他的所有小说中。
其次是饥饿艺术家本身,其“精神追求的无限性”与“人类生理矛盾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想要达到形而上的境界,就必须舍弃形而下的外壳,即选择死亡。
卡夫卡眼中的世界荒谬矛盾。他认为孤独重要,然而孤独却又是卡夫卡苦痛的源头。他“狂热地把孤独当作一种追求,实际上是渴望得到一种摆脱了上述种种困扰的自由。”[]这种矛盾投射到饥饿艺术家身上就成了——他一方面希望外人赞赏自己的表演,一方面又认为他们不应赞赏自己。
这种矛盾贯穿于卡夫卡所有小说甚至是他的一生中。在卡夫卡看来,世界是荒谬的,人必须忍耐一切,以至于对一切荒谬形成习惯的态度,人的存在才能达到自由。他不接受世界,世界也不接受他,他渴望自由,却又被自由所束缚。从存在主义者的角度来观照,以饥饿艺术家为代表的人,实际上就是“荒诞的人”,同样也是“充分的自由人(哲学意义)”。
加缪在谈到存在主义时提到:“人生活在一个与自己对立的、失望的世界之中,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确定的。绝对自由的人也是烦恼和无所依靠的孤独者。人虽然有选择的自由,但他面对的未来的生活却是混沌而没有目标的。他只是盲目地走向未来,他只知道人生的真实的终结就是死亡。”
回到开头,众所周之伊卡洛斯渴望自由,于是飞高,飞出迷楼,结局是摔死。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在于,世界是迷楼,生命本身也是迷楼,我们实则无法逃遁。据此层面来看,自由在某种程度是也是奴役。即奥威尔提到的将“自由即奴役”颠倒为“奴役即自由”——“一个人在自由的时候总是要被打败的”“是因为人都必须死,这是最大的失败”。我们永远被奴役,死,才是归宿。
如此看来,我们终无法跳出生命本身。是奴役,亦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