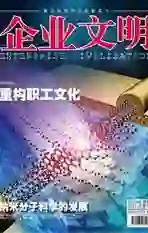要重视新工人的文化生活
2016-05-14吕途
吕途
“新工人”是伴随着农村集体化的解体和城市产业的集中发展而产生的,他们从农村到城市谋生和生活。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将近3亿的打工者却面临“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的没有出路的境地。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认清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提供日常文化服务两个角度去着手。
新工人群体的整体状况
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该《意见》中对这个群体进行了定位,定义这个群体是“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并且“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工人”是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本文中,新工人、打工者和农民工是可以互换的概念。
使用“新工人”这个概念有下面几层含义:
一是用于区分过去的老工人。今天我们新工人争取的很多东西是过去老工人曾经得到过然后又正在失去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李静君(Ching Kwan Lee)写了一本书在国外很有影响,书名是《违法/依法》(“Against the Law”),书中对比了国企工人和新工人的不同。她称呼老工业区为“生锈带”(rustbelt),称新兴工业区为“阳光带”(sunbelt)。她认为在生锈带,老工人所拥有的是一种“社会契约”,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找单位、政府和国家;而移民工所拥有的是一种“法律契约”,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我同意這样一种观察,不过我们不能忘了,法制并不是孤立的,现在保护工人的法律一一出台而且正在完善,但是损害打工者权益的事件却层出不穷,而且打工者维权也是步履艰难。可见新工人要依靠法制,但是社会的进步又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健全。我访问过一位过去的纺织厂的老工人,她告诉我:“我们那个时候都特别听领导的号召,领导只要下达任务,我们起早翻大门进厂赶任务,工资也不多拿,就是那样一种热情。后来厂子被承包了,厂长给我们这些固定工人放假,去雇佣那些从农村来的临时工,一切都变了。”在这简短的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问题:(1)工人不是工厂的主人,因为工厂承包给私人没有经过工人的同意;(2)工人当时的工作热情不是靠收入调动起来的:(3)当时社会上还存在很大的社会差异,有固定工作的工人处于经济、社会的优势地位,而且有“世袭”的味道,正因为这样的地位不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得来的,因此也就轻易被剥夺了。
二是“工人”和“打工的”这两个词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工人”这个词从历史上讲还是被赋予了一定的主体性的含义,它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而“打工的”更多的是指自己是个被雇佣的劳动者。
三是“新工人”是我们的一种诉求,它不仅包含我们对工人和所有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
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16年4月28日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全国打工者的数量为27 747万人。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也是一个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这近3亿打工者中,8 6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我们穿的、用的都是他们制造的;5 8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铁路都是他们建设的;2 000万人从事家政工作,他们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见不到自己的亲人。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 102.55万,全国有农村流动儿童达3 581万,在农村他们见不到父母,在城市他们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权利。
打工群体的状况不容乐观,我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概括: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
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们的工作很不稳定,平均一到两年换一次工作,换了工作之后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一部分人支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甚至借钱在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子,或者在村里盖起了房子,但是,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家”,因为必须在城市打工才能维持生活;打工者结婚了并且有了子女,但是他们的子女很多不能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入学,很多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抚养照顾,有一些干脆长年学习和生活在寄宿学校里,城市和企业急功近利使用了廉价劳动力,但是拒绝支付社会成本,社会把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无偿地转嫁到留守老人的身上;那些有幸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在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从名称上看就好像他们要重复父母的命运。
新工人群体文化生活的现状
迷失是新工人的整体精神状态。新工人群体现在最突出的文化状态是“迷失”。新工人最大的迷失是,明明农村和乡镇是回不去的,因为农业生产根本无法维持生计,而且乡镇也少有就业机会,但是很多打工者花掉自己毕生的心血,甚至预支自己未来的收入在田间地头盖起了小楼,在镇上买了公寓房。2010年9月3日我在四川省邻水县斑竹村进行调研,当我在稻田边一座四层小楼里访谈一位81岁的孤独老婆婆,同时看到外面墙上“新农村建设”的标语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滑稽的概念:建设的是“新农村养老院”。再往下想,如果这些房子将来能够成为养老院还好,但是我不认为在外打工20年、30年以后打工者会回到几十年以前在田间地头建设的房子里。也就是说这“养老院”也只是一种臆想。这种把“不可能”作为未来和寄托,把“臆想”当成现实的现状是让人非常痛心和悲哀的,这也是我说的“迷失”的表现。这种迷失状态让我们不能拥有现在,更不能创造未来。
打工者的“过客心态”。“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迷失的最显著的特征。打工者生活在南方的工厂宿舍和北方的打工者聚居区,生活条件都非常差,但是,因为大家都以为打工生活只是暂时的,所以就可以将就和忍受。在生活中的过客心态,会让他们不去争取很多的现实需求,比如:对居住权的要求,对居住条件和环境的要求,对子女在城市义务教育权的要求。在工作中的过客心态,会让他们不去争取工人应得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过客心态让打工群体没有任何抗争的动力和谈判的合力,最后只能被各种势力和利益群体牵着鼻子走。事实上,从居住地的稳定性来说,打工者倾向于在一个地方落脚的趋势是明显的。我在北京皮村的调查就发现,在皮村居住了5年以上的工友并不在少数,很多在深圳和广州打工的工友也已经在那里“暂住”10多年,甚至20多年了。打工者的“过客心态”看似是一种无奈选择,其实却正是资本霸权的胜利,资本本来就是“过客”,它的目标永远指向最廉价的劳动力,而打工者的过客心态完全符合资本的逻辑,迎合和支持了资本的扩张和逃离。
没有业余时间。很多工友上班时间长、加班多,所以几乎没有业余活动的时间。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打工者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5.2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7个小时。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占39.1%,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85%。2009年的监测报告中,还有下列统计数字:制造业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58.2小时,建筑业59.4小时,服务业58.5小时,住宿餐饮业61.3小时,批发零售业59.6小时。
下面是2009年笔者主持的《打工者居住状况与未来发展调查报告》的调研结果:
·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居住的打工者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北京皮村,很多工友自己开店,为了多些收入,每天工作12~18个小时,而且没有休息日;一些工友打零工,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都不固定;还有一些工友在厂子里上班,皮村一般都是几十人的小厂,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比打零工相对固定,但是工作时间也很长,每天平均工作时间是9.6小时,每个月平均休息两天半。
·從每天的工作时间上来说,家政工平均每天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平均15.2小时。大多数都是每周休息一天,也有根据需要而定的,也有个别的没有休息日的。
·在苏州和深圳的打工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差不多。苏州工作状况是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为9.8小时,每月平均休息的天数是4.9天。深圳的工作情况是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为9.4小时,每月休息的天数是5天。
上文详细描述了打工者几乎没有业余生活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由于对绝大多数打工者来讲,打工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不打工就无法谋生,打工者在工作中所从事的事情往往不是自己主动喜欢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打工者不仅在经济上贫穷,而且在幸福感上也很贫穷。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是拥有最多财富的人,而是拥有最多可以由自己来支配时间的人。当一个人可以拥有很多时间来做自己喜欢和愿意做的事情,这个人一定是很幸福的人。还有,也是更重要的,“没有时间”也意味着一个人失去了选择如何生活的权利,因为没有时间思考也没有时间和机会进行选择。
业余生活单调。即使工友有了一些业余时间,也会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而没有丰富的业余生活,这些限制因素包括:(1)没有合适的业余活动场所;(2)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承担娱乐消费;(3)休息时间不固定,就算有了业余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打发。
一份贵州省的打工者业余生活调查显示,在工友的业余生活内容中,“看电视”排第一,“睡觉”排第二。在2012年“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座谈会上,共青团贵州省委发布了对该省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的结果。数据显示,逾七成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的业余生活内容“不太丰富”或“很单调”。其中79.12%的受访者在工作之余选择看电视或睡大觉,而“业余时间学习或参加培训”的只有17%,去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或纪念馆的不到5%,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主要集中在打扑克、上网等简单的娱乐活动上,主动参与学习型活动的较少。
新工人积极文化的展望
打工者的工作体验是作为劳动者的体验;打工者的生活体验是作为底层民众的体验,这些体验是这个群体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那么,代表劳动者的基于劳动者生活和工作体验的积极文化就是我所说的“新工人文化”。下面我讲一下工友小叶的思想意识。小叶1990年出生,是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他2006年初中毕业后出来打工,在东莞打工了5年,2010年来苏州打工。2011年6月1日我访谈了在苏州打工的小叶,我们讨论对“自由”这个概念的理解。他给我讲了他的工作现状和认识:“我现在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上班、下班、洗漱、吃饭,时间就没有了,然后就是睡觉。我不上班的时间都是在为上班做准备。我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时间。我没有自己的时间就等于不拥有自己的生命,生命都不属于自己,我哪里谈得上自由。”小叶通过自己的工作体验和认识很好地诠释了对生命和自由的最朴素的理解。这就是我说的新工人文化的基本元素。
用打工者聚居区北京皮村的案例来说明新工人文化建设的可能性。北京工友之家从2005年来到皮村,长期开展社区活动,探索社区工作和工人文化的方向和意义。皮村是一个典型的城边村,本地人口大约1 000多人,外地人口2万人左右。我们对皮村列表简单总结了他们所开展的活动。这些活动充分反映了他们的文化状态和文化诉求。
新工人个体和群体的思想和认识决定了自身和群体的命运,也决定着中国的未来。新工人应该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主动承担起发展和壮大劳动文化的责任,否则,我们就看不到这样一个文化形成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陈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