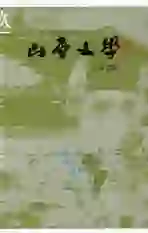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2016-05-14姜红伟祁智
姜红伟 祁智
访问者:姜红伟
受访人:祁 智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至少,那个时代过去之后的三十多年,这样的盛世没有重现。大家思想活跃,心地单纯,热情高涨,废寝忘食。无数的人写了无数的诗歌,无数的诗歌让无数的人心有所安。那么多年轻人,年轻的大学生,投身于诗歌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你身在大学,如果不读诗、不写诗,不参加诗歌活动,简直不可思议。
我说“这样的盛世没有重现”,其实是想说,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但不能缺少理想、激情,甚至不能缺少不可或缺的忧郁与悲愤。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答:我16岁上大学,79级。宿舍里有一学兄叫赵幼明。他中学同学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定期给他寄油印的《未名湖》《启明星》。他收到油印本,都是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那些诗歌有别于“老诗人”的作品,句子、语法都是新鲜的,与“我”距离很近,读后热血沸腾。我在长江边古老的城市扬州,在一个传统文化符号里,像在黑夜里遥望北斗一样对北大心驰神往。
我很幸运,我有一个78级的学长曹剑、一个77级的学长王慧骐。入学不久的一个晚上,曹剑找到我。之前我们素不相识。他说他知道我喜欢诗歌,要带我去见一个人。我们走四五里地,到了扬州农学院教工宿舍,见到了王慧骐。王慧骐当时已经是著名诗人,我激动万分,崇拜至极。那晚,主要是他们两人交谈,我认真听。聊天结束,王慧骐摸着我的头说,这小兄弟不错。
之后的一天,我接到曹剑的通知,让我参加诗社成立大会。我去了。我记得,都是77、78级的学长,79级只我一个。我在诗社里认识了我的老乡苏徐。苏徐对我说,大家都看重你,好好写。
我当时除了激动就是惶恐。我惶恐,是因为我当时没有什么作品,他们却很看重我。当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看重我。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答:我觉得我的大学四年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踢足球,一件是写诗。我当时睡上铺,站在板凳上趴在我的床上写诗;上课的时候,我喜欢坐最后一排,开小差是日常生活,精神集中的时候是在稿纸上写诗。有时候睡到半夜,爬起来到盥洗室写诗。每隔三五天就要向外投稿,当然,都是退稿——那时候时兴退稿。看到邮递员向我走来,我就知道退稿又有了。
问:大学时期,您曾经在哪些文学报刊上发表诗歌作品?
答:大学里,我在《飞天》《青春》《青年诗人》《新疆文学》等刊物发表过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班级、年级和学校的影响很大,在江苏高校内也有了名气。如果说,最初大家喜欢诗歌,毫无发表的功利,但后来,让自己的诗歌变成铅字,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让更多的人知晓,至少是我和周围的诗友的梦想。曹剑在《飞天》“大学生诗苑”上发表诗歌,收到刊物的当晚,激动万分喊我去王慧骐家一起分享。
问:您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飞天》在当时是大学生诗歌圣地,仿佛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革命圣地延安。一个写诗的大学生,没给《飞天》“大学生诗苑”投过稿,就像一个朝圣的人没到过麦加。能否谈谈您在《飞天》发表诗作的经过以及“大学生诗苑”栏目责任编辑张书绅先生对您的帮助?
答:1981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们对阵扬州教育学院教工足球队。
“我们”是扬州师范学院学生足球队,打遍扬州高校学生队无敌手,只得寻教工队打。我是守门员,门前无战事,对方半场拥挤不堪,风声鹤唳。班上负责取信的同学,从门后给我一个长信封。这封信是甘肃《飞天》杂志寄来的。
作为初学者,我在学长王慧骐(77级)、曹剑(78级)那里,知道了《飞天》杂志,因为这家杂志专门开辟了“大学生诗苑”栏目。
一天晚上,我把三首诗装进信封,贴足邮票,丢进学校门口的邮箱。《飞天》“大学生诗苑”收到投稿的诗歌不会少,而每期杂志版面有限,我未必会有发表的幸运。但我是想试试。我听说责任编辑张书绅老师,有稿必复。我不指望作品能发表,能得到编辑老师指点一二也好。另外,我觉得,一个写诗的大学生,没给《飞天》“大学生诗苑”投过稿,就像一个朝圣的人没到过麦加。
同学从门后塞给我的信封厚厚的,我以为是退稿。但我敏锐地感觉到,信封的厚度与我寄出的略有不同。我不禁内心一荡。我疑疑惑惑、急急匆匆地撕开信封口,一行流畅老练的铅笔字写在我的稿件上:
留用一首《写在那一张日历上》,发明年第四期。
张书绅
我寄了三首诗,退回了两首,一首留用。留用通知,没有写在信笺上,而是写在退给我的诗稿上。
这是我的诗歌第一次被杂志说“留用”。我激动万分。这时候,队友见我闲着,从中场回传一个球给我。我迎上去接了,边慢慢向前推进,边指挥队友向前扑。我在推进中发现,对方只注意盯防我的队友,对我放松了警惕。我立刻快速启动,狂呼着后卫“赶紧回去防守——”,从中场带球连过数人,一直把球带进对方门里,手里还抓着张书绅老师给我的信。
这个球赢得全场轰动。后来,我多次试图如法炮制,都没有成功。这不奇怪,奇迹的发生,得有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就像李广不可能两次把箭射进石头。
我开始漫长的等待,等待“明年第四期”。《飞天》杂志,每期都提前在《光明日报》上登广告,只是提前的日期不定。我每天到图书馆一楼大厅的阅报栏看《光明日报》。三月底的一天,我看到了第四期《飞天》目录,我看到了我的名字。我趁人不注意,撕下了豆腐大的《飞天》广告。
后来,我给张书绅老师投过几次稿,都是几首一起投。有的留用,有的退回。无论是退回还是留用,他都是用铅笔在退回的诗稿上写字。有时候就四个字:常人所想。
我是1983年7月大学毕业。6月中旬,我收到一封寄自《飞天》的信。信封很薄。我觉得奇怪,因为我快告别大学了,没有给张书绅老师寄过诗稿。我拆开信封,读到了张书绅老师给我写的一封短信。这封信,写在信笺上:
祁智:
你的诗歌里有比较强的叙事成分,不要拘泥于写诗,不妨写小说试试。
张书绅
我在此之前没写过小说。张书绅老师的提醒,让我忽然明白,在我心底里其实藏着一颗顽强的种子。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和伙伴们没有什么书看,就想做一个讲故事的人。写小说的人,就是讲故事的人。这颗种子,被张书绅老师催发了。我开始在纸上写小说。
我至今没见过张书绅老师,甚至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我一直感激他,经常会想起他,也经常会提到他。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啊?
答: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点文墨的人都在写诗,大学生诗歌尤甚。小组有诗社,班上有诗社,年级有诗社,系有诗社,校有诗社。有的诗社,还跨宿舍、年级、系科,甚至跨院校。诗人像杂草,诗社像草丛。
我在大学里参加了学校的“萤火虫”诗社。最初,诗社除我是79级的以外,其余都是77级、78级的学长,济济一堂。我记得我们年级4个班级,3、4班合成一个中班,我是3班的,同教室的4班办了一个“峣岹”诗社,诗社成员把诗歌贴到墙上。好多人不认识“峣岹”,但这不影响大家读诗。77级很快就毕业了,王慧骐成了影子领袖,诗社由78级的曹剑操持。曹剑毕业后,似乎是我主持。但曹剑后期,诗社成员分化,活动已经不多;轮到我,除了小范围的交流之外,稍大一点的活动少到几乎没有。
79级发展到后来,大概就剩下三个人还写诗了。一个是我,一个是戚华海,一个是郁斌。毕业之后,戚华海还坚持在扬州张罗活动,他现在身在官场,但还在写诗。
问: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王慧琪、曹剑等学长创办了“萤火虫”诗社。我参加创办,但我只是参加。学长们个个风华正茂、挥斥方遒、诗情横溢,16岁的我只有仰视。但他们会顾及到我。往往是这样,他们说到激烈之处,王慧骐就会笑眯眯地说:“小老弟,你看呢?”大家就友好地看着我,而我不知道说什么。
诗社编印了刊物《萤》。让我没想到的是,77、78级学长,一致将我的一首小诗,放在创刊号的开篇——
追求
云低
风冷
天空中一张网
静悄悄捕捉
草尖的绿
枝顶的春
光着脚
我追赶
冲出网的雁阵
这是我的诗第一次变成印刷体。我在学长们面前诚惶诚恐,其实我内心激动死了。
就在学长们筹备《萤》第二期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个冬天的下午,诗社成员到系主任办公室旁边的小教室集中。系里的书记说,系里是支持同学们结社的,但现在“上面”情况有些变化。
书记指着《萤》创刊号对我说,有些人喜欢上纲上线,搞“莫须有”,“我追赶冲出网的雁阵”,一是说我们这里没有春天,二是说,你跟着雁阵走,走到哪里去?向南走,就是台湾、香港。
大家面面相觑。但书记和善地说,我们不搞莫须有。
这次见面的结果是平和的:我们放弃结社,放弃《萤》;“上面”没有追究我们。
问: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啊?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答:见面不易,书信来往很多。我收到过不少信件,地址是张书绅老师“透露”的。他在发表我们诗歌的时候,会标明作者的学校和年级,比如“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79级”。这就等于把地址公开了。
那时候的通信很单纯,都是谈诗歌,即使说到感情,也极为含蓄,含蓄到你如果当真或许就是自作多情。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我印象深的大学生诗人有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潘洗尘、许德民、徐芳、李其纲、王家新、叶延滨、程宝林,还有张小波、宋渠、宋炜、宋琳。当然还有王慧骐、曹剑。
我和张小波见面是198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雨后,闷热。当时我刚到南京工作,他还没从华东师大毕业。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单位的电话,把电话打到单位门房,我骑车赶到新街口。他和宋琳在巷子里的水饺店等我,我请他们吃了水饺。巧的是,25年之后,我和张小波同事了一年半;在此期间,又遇到了找他的宋琳。
曹剑和张小波是同乡,如皋人。曹剑的《江北大汉》写得轰轰烈烈。他们的老家紧邻我的老家。我老家是靖江西来,与如皋隔了一条不宽的界河。
我记得这些诗人的名字。我还要提到两位先生,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谢冕,一位是《飞天》“大学生诗苑”责任编辑张书绅。谢冕老师一直为诗歌鼓与呼,张书绅老师则是为大学生诗人做嫁衣。
张书绅老师处理诗歌来稿非常人性化。比如,有些大学生诗人一直投稿,一直没被录用。但临近毕业了,他会尽量争取让你登一首诗,让你的大学生涯甚至文学生涯有一个记忆。
张书绅老师知道我要毕业了,又发表了我的一首诗,有“壮行”的意思。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我在大学里发表诗歌不多,影响也不大。但这段生活,让我受益匪浅、享用一生。
大学毕业后,我到南京做中学教师。南京有很多诗人,专业的,业余的。鸡鸣寺那里,还有“诗人角”。我一开始还写诗歌。我记得在诗歌上帮助我的老师:马绪英、吴野、沈双兰。他们是《青春》杂志的诗歌编辑。当然,杂志之外,还有冯亦同等老师。
非常巧的是,我班上有一个学生,父亲叫陈玉田,是《青春》杂志的小说编辑,后来做小说组长、副主编。我学着写小说。第一篇小说《黄金》写了7万字,交给陈老师。后来没有消息,再后来河南《莽原》杂志来信,说录用了。我把这一消息告诉陈老师,陈老师说我的小说太长,不适合《青春》月刊发表,给了双月刊的《莽原》。
这之后,我就写小说了。我参加《钟山》 《青年文学》 笔会,等等。我在 《人民文学》 《钟山》《收获》《莽原》《十月》《青年文学》《雨花》《上海文学》等很多重要刊物,发表过“头条”小说,被一些朋友戏称为“祁头条”。我的作品也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家争鸣》等转载,也有作品被翻译到国外,被拍成电视剧,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冯牧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现在虽然不写诗,但我读诗。我一直订着《诗刊》。看到诗行,我仍然激情难抑。于是又写一些分行的文字——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诗。
姜红伟,1966年生,黑龙江海伦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倡导者,曾创办《中学生校园诗报》。系中国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历史研究者,八十年代民间诗歌、校园诗歌报刊收藏者。
祁智,著名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呼吸》《芝麻开门》,中短篇小说集《反面角色》,长篇童话《迈克行动》等。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