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课堂关系,呈现学习本质
2016-05-10李淑慧
李淑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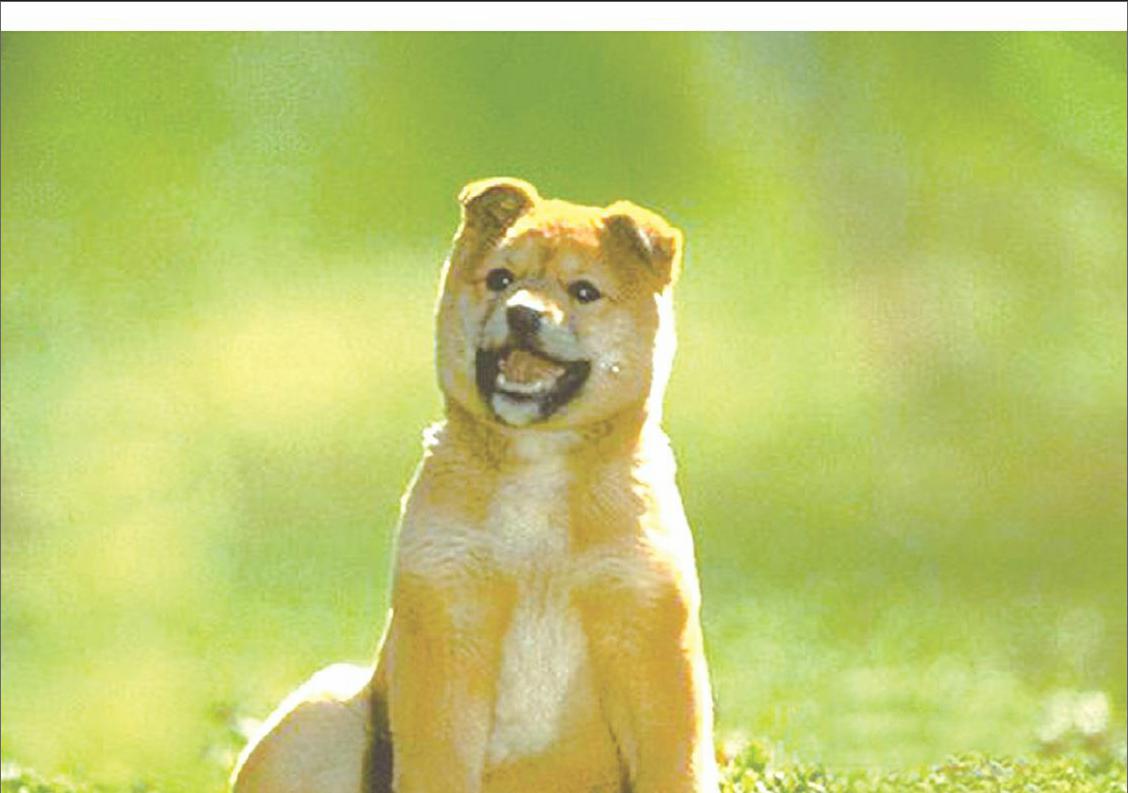

教师、学生和文本是课堂教学的三个基本要素,阅读教学就是教师、学生和文本之间互相对话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三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不同,课堂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但不管我们怎样处理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学习的本质即信息的接受、理解和内化都不会发生改变。那么,课堂三要素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教师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推进学生阅读能力的发展,使学生获得最大程度的收益呢?本文以《小狗包弟》的三个课例做一对比分析,试图探索课堂三要素之间的合理关系。
当代散文家黄裳曾这样评价过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作者写的也不过是一些‘身边琐事,不过由于作者生活的时代是不平凡的时代,因此,‘身边琐事也就有了更深广的内涵。”《小狗包弟》作为《随想录》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便以对比的手法以小见大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时代。一条可爱的小狗,一个被戕害的生命,折射出一个疯狂的年代,凸显了一颗高贵的灵魂。教学《小狗包弟》,怎样引导学生通过这条小狗去解读那个时代从而理解作品“更深广的内涵”便成了本文教学的一个重点。
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而且距离学生已很遥远,阅读背景的缺失会使学生产生很多困惑。因此,虽然《小狗包弟》篇幅短小,情节简单,要让学生真正地理解作品中那个特定的时代也仍有一定的困难,这个内容也是学生阅读的难点。
针对这一教学难点,三位执教教师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展现了课堂三要素之间的不同关系,下面逐一呈现。
资料展示的时代:教师带着文本走向学生,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
第一位老师借助导入环节补充相关资料,期望学生在了解背景的基础上阅读。
上课伊始,教师首先通过大屏幕出示一组图片——刘少奇、陈毅和彭德怀被揪斗,老舍、傅雷和吴晗被迫害致死,故宫改名血泪宫,清华校门被毁坏等等。然后打出秦牧描述“文革”的一段文字,而后利用图片进行总结。继而大屏幕打出下面这段文字,教师学生齐读: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那是一个缺少理性的年代!
那是一个人人难以自保的年代!
那是一个不堪回首、令人痛心的年代!
那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深刻反省的时代!
然后,老师正式导入新课: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文革”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我们通过学习《小狗包弟》来了解这段历史。
这个导入很自然,选择的图片也很震撼,通过这些图片的确可以使学生对这段历史有一些感性的认识,这对于那些对这个时代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学生来说也不失为一种了解历史的方法。但这种认识是老师通过大屏幕打出来的,是通过视觉轰炸的形式强加给学生的,不是学生通过文本阅读理解的。如此处理,极有可能对学生产生一种误导:既然时代是这样的,那些伟人都受到那样不公正的待遇,那么一条小狗又算得了什么呢?包弟的厄运就很正常了。所以在后面的学习中就出现这样的对话:
师:为什么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
生:因为“文革”。
师:为什么抄“四旧”就要打小狗?
生:因为“文革”。
用资料展示的时代,学生接受了固定的观点,在后面的阅读中学生便以贴标签的形式来对待和使用相关资料。“知识先行”的教学制约了学生对文本本身的理解和挖掘,使学生的认识停留在概念上,他们难以深入到文本的内部,理解文本那朴实的文字中传递出来的那种震撼人心的悲哀,体会到那种求人而不得的无助、不愿做却必须做的无奈以及这种矛盾纠结所带给人的内心的无尽的痛楚。
教师阐释的时代:教师带着学生走向文本,学生是知识的理解者。
第二位教师这样设计了核心教学环节:
1.粗读课文,理清思路。
2.细读课文,深入理解文章内容:
(1)阅读3~5段,概括包弟的形象特点。
(2)联系前后文说说包弟变成“包袱”的原因。
(3)第十段中“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解剖”一词该怎样理解?本段中哪个词语指出了作者在“文革”中的生活状态?
不难看出,第二个小问题的讨论涉及时代问题,师生之间产生了这样的对话:
师:聪明可爱的包弟为什么会成为作者的“包袱”?
生:因为抄“四旧”,杀小狗。
生:因为这是一条日本种的小狗,会被诬陷卖国。
生:因为小狗曾经有一个瑞典的主人,所以新主人可能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生:因为小狗的叫声会把抄“四旧”的人引来,这样会给作者带来麻烦。
课堂上学生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但学生活动时间不充分,讨论也并不深入。老师只好越俎代庖地进行了这样的总结:
包弟是一条可爱的小狗,文章通过叙述小狗包弟的故事,以及自己的情感体验,反映出在“文革”那个动乱的年代,连狗都难以幸免,任何生灵都可能遭受不测。表现了作者呼唤人性、提倡人道主义的态度以及可贵的严于自我解剖的精神。
实际上,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已经触及了问题的关键,但教师未能帮助学生走向深入。如果老师再追问一下:养一条日本种的小狗就是卖国吗?小狗有一个瑞典的旧主人,小狗的新主人就一定“里通外国”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在那个时代,养狗本身就会被认为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于是抄“四旧”的人会明目张胆地杀小狗,更何况巴金先生养的是这样一条历史复杂的小狗呢?所以,才害怕包弟的叫声会把抄“四旧”的人引来,从而使已经“半靠边”的自己以及家人受到连累,于是包弟就成了一个“包袱”,最终只有被送到解剖台。明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竟这样被荒唐地牵扯到一起,于是包弟的悲剧就产生了,伴随而来的就是作者痛苦的自责。这样几个追问之后,思维路线贯通起来,那个时代的荒唐性、疯狂性就不言自明了,而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没有理性的时代产生小狗包弟的悲剧就很正常了。endprint
这个教学过程是老师带着学生一起走向文本的过程,学生对文本有了一定的认识,思维方向也是正确的,但由于缺少必要的等待,缺少充分的对话,师生、生生之间思想的碰撞不够激烈,导致理解流于肤浅和程式化。
学生领悟的时代:学生带着文本走向教师,学生是知识的探索者。
因为有了这样的两节课的体验,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个文本时,发现这样教学对文本的挖掘远远不够。于是重新研读这个文本,发现第一段和第十一段,作为引出小狗包弟和从包弟的故事中回到现实中的段落,其意义绝不仅仅是在文章结构上的作用,更有小狗形象的深远意义。
艺术家和狗的故事,本身就与小狗包弟的故事形成对比,前一个是狗的忠诚,而后一个则是人的背叛,这也是巴金先生深深自责的。而这故事本身,同样以鲜明的对比来揭示一种时代特征。生活在另一个城市的艺术家无端被诬陷为“里通外国”,被痛打,头破血流,打断腿,游街示众,满身血污。认识的人看见他都掉开头去,可他曾经款待过的一只小狗却扑到他跟前,闻他,舔他,用爪子抚摸他,最后也被专政队打断了腿。对比狗,人性泯灭到什么程度?随意践踏生命,于是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地为求自保而泯灭良知。而这样的结果就是第十一段,当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之后,留下来满园的荒败和满心的创伤。这一段也暗含着一个对比,从前的园子绿草如茵,花开灿烂,一个拔草的人,一只可爱的小狗,其乐融融,何其美好!而现在,满园衰草,少了花,多了树,葡萄藤被挖走,竹篱笆变成无缝的砖墙,一个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何其凄凉!第一段的另一个城市的狗使包弟的悲剧具有了普遍性,第十一段包弟的悲剧又向外辐射为更多事物的悲剧,于是包弟的悲剧就有了代表性。
这样的分析后,第三位教师在学生理解小狗包弟的悲剧后设计了这样的问题:
包弟的厄运仅仅是包弟的悲剧吗?
包弟的厄运仅仅是狗的悲剧吗?
巴金先生是为了写小狗而写小狗吗?
带着这样的问题继续研读课文,重点是第一段和第十一段,师生之间便有了下面的讨论:
生:包弟的悲剧当然不是它自己的,附近的孩子时常大喊大叫杀小狗,所有的狗都在被杀之列,都属于被破的“四旧”。
生:第一段中,在另一个城市的狗也被打死。可见不仅仅小狗包弟因为走投无路被送到解剖台,其他的小狗也不能幸免。它们仅仅是被杀的方式不同,但死的结局是一样的。
生:老师,是不是连花都不能养?
师:为什么?
生:你看第十一段中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好像不让种花,但可以种树。
师:你阅读真仔细,对,因为种花和养狗一样,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生:养花和种树在本质上有区别吗?怎么就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呢?这不是很荒唐吗?
生:哦,那就是说,花也是包弟,草也是包弟,葡萄架和葡萄藤也是包弟,连巴金先生也成了包弟。
生:“自己也终于变成了包弟”,也就是像包弟一样,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这是什么意思呢?
师:(资料补充)作者想用舍弃小狗包弟来避免抄家的危险,但是他的愿望很快便化为泡影。1968年8月,巴金被监禁;9月,被抄家,并经受各种形式的批判;1970年春节后到上海郊区劳动改造;1972年8月,妻子萧珊病逝,巴金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
生:太不可思议了。不许养花,不许养狗,但可以随便打人,抄家,诬陷人?艺术家也是包弟,大家都是包弟。这是什么世道?
师:是啊,就是这样的世道,所以巴金先生才害怕包弟这样一条历史复杂的小狗把那些人引来,忍痛把它送上了解剖台。从此他备受良心的谴责长达十几年,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心灵上千疮百孔。这样的命运同样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就算那些认识艺术家的人,他们不敢同情他帮助他,也同样要经受良心的谴责。
生:如此说来,写包弟就不是为了写包弟,而是为了表现那个荒唐的不正常的变态的时代。
师:是啊,生命无辜被摧残,人性无奈遭扭曲,尊严无端受践踏,这就是那个没有理性的时代,异化了人性,酿成了灾难。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革”,就是十年浩劫。所幸我们没有生在那样的时代,所幸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作为这个时代的受害者的巴金先生在这个时代过去之后,没有抱怨,而是勇敢地通过小狗包弟反思自己在这场浩劫中的责任,让人心痛,更让人敬佩。
一朵花里有世界,一滴水中见太阳,一条小狗,便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而我们的阅读,正是透过这只小狗去了解那个时代,也通过那个文本去感知“一个最无责任者对自己责任的拷问”,从而接近那个高贵的灵魂。
对比三个课堂教学的片段,不难看出,教师、学生和文本之间不同的关系。资料展示的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文革”,对学生来说是接受一个概念;老师阐释的是老师传递给学生的“文革”,学生尚没有形成自己对那个时代的完整印象;学生通过文本领悟的是他们自己感受到的“文革”,也许学生的认识还不是很全面,还流于稚嫩和肤浅,但这是他们自己的理解,带着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温度,所以才最有可能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凝结成他们自己成长的智慧。
教学过程中师生的内在关系是教学过程创造主体之间的交往(对话、合作、沟通)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文本得以展开和实现的。在《小狗包弟》的课例对比中,随着教师行为的一次次弱化,讲授——对话——引导,学生的学习本质一步步突显,接受——理解——领悟,这恐怕就是语文课堂教学一点点深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行为看似弱化了,但其引领作用实际上增强了。
课堂应该只是传授学生知识的场所,更应该是探究知识的场所。根据学生的智慧特点和认识特征将知识点转化为待探究的问题,让学生的思维在对问题的探究中得到发展。这要求教师在先于学生与文本对话的过程中找到一条最适合学生进入文本的途径,拉近教师、学生、文本三者之间的关系,把握师生之间的对话主题,营造师生平等的对话氛围,疏通学生与文本的对话渠道,构建师生、生生以及生本的对话平台,在师生以文本为中介的阅读活动过程中,共同走向文本,同时也让文本走向师生,于是教师、学生和文本产生共鸣, 实现文本价值的最大化,从而启迪学生的智慧。就像这篇《小狗包弟》,在老师一次次的改进中,在学生一遍遍的阅读中,那个时代便从字里行间浮现出来,让人震惊,更让人警醒。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