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优雅遇上蛊魅——阿毛的《波斯猫》
2016-05-03林喜杰
■林喜杰
当优雅遇上蛊魅——阿毛的《波斯猫》
■林喜杰
2008年以前阿毛的诗歌创作已趋成熟的态势,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女人辞典》、《午夜的诗人》、《爱情教育诗》、《当哥哥有了外遇》、《献诗》、《红尘三拍》、《诗朗诵》(组诗)、《单身女人的春天》等,尤其是2004年阿毛参加了诗刊社的第二十届青春诗会以后,她承认诗风由“惊涛骇浪”转变为“静水流深”。“静水流深”是要达到的另一种创作境界,把诗歌的创作重点由陌生的语感或形式感的创新转向与熟悉而自然的契合,潜入生活的细处与底部,自然舒缓地写出日常生活中的朴素与平实。《波斯猫》写于2008年,这不仅是我们了解这首诗,也是理解一个诗人走向成熟的重要背景。
《波斯猫》是阿毛诗歌中不带有元诗写作因素或者女性经验的诗歌之一。《波斯猫》具体地说是“我”经过楼梯扶手邂逅一只邻居家的波斯猫的过程,由对猫的欣赏到抵挡侵略,进而转向人生经验中的自我关注。这个事件是否是诗人的一段亲身经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诗中发挥了怎样的结构功能。
邻居家的波斯猫在楼梯扶手上坐着,
两只眼睛望着我,
事件中的主语是“波斯猫”,而不是“我”。起句如果改成“我看见邻居家的波斯猫在楼梯扶手上坐着”会造成不必要的延宕感,削弱语境的紧迫性和情感压力。猫“坐着”、“望着我”所突出的正是语境的紧迫感和情感压力,笔锋一点,一下子把“波斯猫”推到读者面前:仿佛是在和诗人一起看猫。诗人把笔墨集中在猫的眼睛上,那是人们渴望看到的眼睛颜色和亮度“冰蓝”、“宝石蓝”、“孔雀蓝”、“色谱中找不到的一种绿。”人忘情地欣赏那样一种沁人心脾的颜色和光芒,这样至真至深的热爱,女性与猫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相似特性。“这些被我从衣服上爱到诗歌里的颜色”,如此优雅华丽的女性颜色,精致到无与伦比的珍贵,但是这种珍奇却不是为我所有,“邻居家的”距离的近抵也不过心理上的“别人家的”远,也为下行的人猫之间“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作了伏笔。
“喵——喵……”
两粒可爱的钻石陈列在橱窗里……
这两句诗的标点使用恰到好处,“喵——喵……”破折号表明猫独有拉长的音调,双引号如同戏剧的独白,强调声音的爆发力,省略号蕴含着攻击将要来临的危险。“两粒可爱的钻石陈列在橱窗里……”诗人用这样一句眩晕在猫眼光芒的内心独白,表现了女性在独有的想象意识世界不能自拔。这里的省略号与上一句的省略号代表了一个人猫共处的空间想象和活动。当两个虚实的影像互相注视,试图看清自认为真实的对方时,内心影像的差异集中到一个尖锐的瞬间。这最后一个省略号里还包括那恼羞成怒的凌厉的一个迎面而来的抓扑。紧接着,诗人横空抛出辩解,人对猫没有利害冲突的“俯身”、强取豪夺式的“摘取”和温柔的“购买”。人猫大战拉开大幕,而且是美女与猫大战。坤包是美女的“猫眼”,脸和头发都是美女的利器。最后一节,宕开一笔,正是“优雅,或一脸的道德感,∕使我们疏于防范。”回转神来,冷静地为自己解嘲战争的起因,借此烘托看不见的内心波动的惊险。
诗人通过这种动物讲述一种古老的、蛊魅的命运。在世界每一个的转弯场景处,我们都可能遇到“一只张着利爪抓过来的波斯猫。”。猫是一种表面上与人世亲密的、将自我隐藏得很深的、神秘幽居的生灵。猫的隐秘和孤傲也具有明显的童话气质。我们对于宠物的态度习惯上是把它当成人一样,但是它毕竟是另一个种族的生物。四目相投却不是眼神交流。猫的一种特性就是老对着一些地方发呆。它在想什么呢?它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它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生物学家解决的问题被诗人一语道破。“它需要∕绝对的静,以积攒力量,消除∕内心的恐慌,面对暴力和死亡吐露∕生存的全部秘密∕和残忍(周瓒《此刻,给爱猫》)”。
这首诗是一个不断生成、同时自足的语言实体,不是“让局部说话”(布罗斯基)。作为一个时尚女性诗歌写作者的“我”和攻击性强的、蛊魅可疑、有着宝石般夺目的眼睛、利爪的波斯猫搭建了一个私密空间框架。这首诗在语调层次、思理肌质方面,更具诗歌戏剧化、意象的童话气质、内敛的抒情以及对生命体验的表达,可以说,这首诗歌是来自诗人的“灵魂深处”,坦然而又意义深远。
英国诗人W.B .叶芝曾经说过,虽然每一位诗人“总是在描写自己的生活”,但他“从不直截了当”,“他的诗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也不像人们用早餐时一席漫不经心的胡话, 而是一种再生的思想,有其预期的目的,有其完整的意义”。
日常生活场景的写作虽然并不是阿毛经常采用的结构,但是这类诗歌将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场景转换成文本的场景,包含了诗人的知识、激情、经验、观察和想象,一方面出于诗人独立而自我的存在经验与对话意识的从容呈现,另一方面诗人始终是冷峭地面对这种现实“蛊魅”的“攻击”,抒发出诗歌想象的批判力量。比如《当哥哥有了外遇》、《爱情教育诗》、《速写午间小区》等诗作刻画世相、描摹人心,展示在世界面前的生活场景的含混和尴尬。她以独特的女性经验来言说,反而可能是她的优长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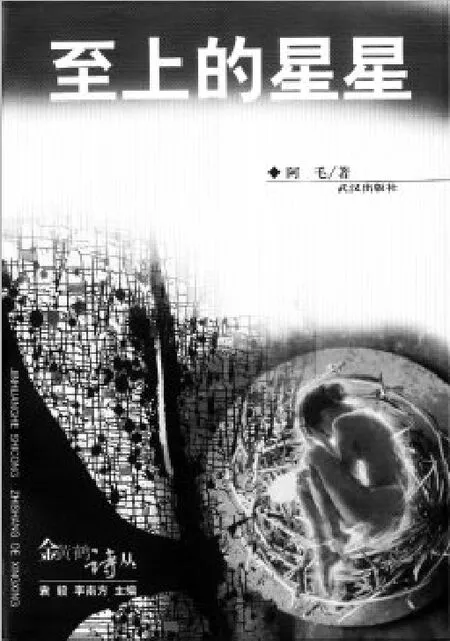
《至上的星星》
诗人作为一个独特的诗歌经验的享有者,陈静而内在,对当代的“历史场景”颇为忧心。有论者认为杰出的女性写作需要的是“以女性的经验去展开想象,结构一种普遍的、人民和民族的经验,既再现了沉埋已久的女性经验,又使普遍的经验获得具体深度。”阿毛动人而诚恳的诗风,使作品即使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也能发现其内在意义。因为唯有如此,她的忧心才能被人们具体、深切地体会。
阿毛对生活有一种极为优雅、机智的热情,但常常倾向于以克制陈述来造成微妙的距离感。在她身上似乎也有一种神秘、孤傲的猫女气质。她曾自称“最喜欢睡眠,等待一场又一场梦的降临,它是我创作的另一源泉;我常常带着构思的由头入眠,结果是穿过一片又一片云山梦海醒来。如果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做梦的职业,我最愿意从事这种职业。”阿毛诗歌无论是题材、主题,还是视角、修辞技艺都富于变化。但总的来说,阿毛诗中幻想和哲理错综交融,那些不断挠着读者神经的微小的、巧妙的因子,似乎高蹈于现实之上,但又跃动在其最深的隐秘处。在近作中,阿毛从容地道出了当优雅遇到蛊魅之后,岁月在内心中如何蜕变的秘密。
猫在石质经卷上
卧眠
鼾声
成为她曼舞的鼓点
——《树阴下的舞蹈》(2014年)
作者简介:(林喜杰,黑龙江讷河人,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所科研员。研究方向:新诗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