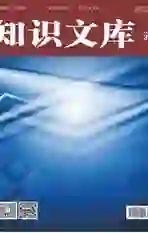“多心之人”和“诚心之人”
2016-04-29王燕
在《长亭送别》中,王实甫塑造了“多心之人”崔莺莺。以及“诚心之人”张生和老夫人。崔莺莺的“多心”和张生的“诚心”统一于“痴情”,为使崔张二人形象更为鲜明生动,作者还采用了传神的动作描写以及心理描写。从而使得作者笔下的人物更贴近生活,具有现实性。
《长亭送别》是《西厢记》中戏剧矛盾弱化的一节,可崔张二人情感也从此开始经受更为现实的考验。因此戏剧人物之间虽没有了之前情节中的直接冲突,可从心态上讲,张生也在无形中也站到了老夫人一边。一个短暂的长亭饯别,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没有剧烈的矛盾冲突,但作者在这近乎平实的场面中却塑造了“多心之人”和“志诚”之人这两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一、多心之人
崔莺莺是《西厢记》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人物,长亭送别之前,因为和张生的爱情得不到老夫人的认可,所以她的行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表现出口不对心,狡黠多变的特点。
但在《长亭送别》这一本时,她和张生不仅获得了情欲上的满足,而且也在红娘的帮助迫使老夫人妥协退步,有条件地答应她们的亲事,她和老夫人的矛盾已经不像前边那么紧张。但是崔莺莺的心理并没有松懈而“放心”,反而更多地表现出“多心”的特征。
去长亭的路上,崔莺莺以内心独白的形式表达了对张生的依恋和对分别的不忍。“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因情设景,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了离别带来的痛苦。“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煎煎熬熬的气……久以后书儿信儿、索与我栖栖惶惶的寄”更是从早上备车出行叙起,甚至设想到久别之后,抒发她愁苦而又无奈的心情。
长亭离别宴席上,崔莺莺更是长吁短叹,怨此恨彼。一方面做无力地自我排解,“虽然久后成佳配,奈时间怎不悲啼”,另一方面又对分别不满,对前途有着深重的担忧,“年少呵轻远别,情薄呵易弃掷。全不想腿儿相挨、脸儿相偎、手儿相携。”
封建时代的政治联姻是非常普遍的,朝中大员需要培植新的力量,新进人员又要寻找靠山,联姻就成了最普遍直接的方式,所以书生高中后停妻另娶屡见不鲜,崔莺莺并不以功名利禄为念,在她看来为了虚名微利,却迫使夫妻分离。最怕的便是张生高中,停妻另娶。所以从这点来讲,张生高中对他们的爱情婚姻反而有一种潜在的威胁。崔莺莺更看中的夫妻厮守,渴望夫妻的尽早团聚。
除了愁和忧之外,还有怨。怨张生不解风情,为何一味去迎合母亲,进京赶考“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怨老夫人:“若不是酒席间母子们当回避,有心待与他举案齐眉。虽然是厮守得一时半刻,也合着俺夫妻共桌而食。眼底空留意,寻思其就里,险化作望夫石”;怨老天:“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她怨天尤人,愁肠百结。
在这些心理活动描写中,崔莺莺没有任何的羞涩和掩饰,完全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悲苦、不满及对张生的依恋和对前途的担忧。
当老夫人和和尚先离开,留给崔莺莺和张生一点单独话别的时间,崔莺莺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但张生却回答“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张生的回答完全和她的希望背道而驰。所以崔莺莺便口占一绝:“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她担心张生移情别恋,用爱她的心去爱别人。在临别之时对张生细细叮嘱,牵肠挂肚:
【五煞】到京师服水土,趁程途节饮食,顺时自保揣身体。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最要扶持。
当张生据鞍上马,即将离去的时候,崔莺莺才尽情地表达了自己的内心:
【二煞】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你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担忧被抛弃,害怕张生杳无音信,强调“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尤其是要求张生对自己坚贞不渝。
可见,长亭送别中的崔莺莺,她的心理和言行延续了和张生交往中呈现出的“多心”特征,而这也正是这个人物逼真,可爱的地方。
虽然老夫人的拘禁已经解除(“张生,你向前来,是自家亲眷,不要回避”),但作为一个少女,一个初尝爱情甜蜜的少女,羞涩、矜持、以及浪漫的天性却表现得分外强烈。
因此在内心里她肆意地表达自己的痛苦,毫无忌惮地表达自己对张生的爱意,但在言行上因为羞涩,因为身份却呈现出自矜的姿态,只有在屡次不经意间的“长吁气”中才流露出真实的情感。爱情本来就是一件浪漫的事,它需要甜言蜜语来包裹,少女尤其对它抱有更多的憧憬和幻想。她所追求的纯粹是浪漫的爱情,所以她埋怨张生:“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但张生却多次显得不解风情,所以崔莺莺才假意试探,怕张生抛弃自己,以此求得张生的一个承诺。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一个承诺不具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但是爱情正是一件不需要理性的事,需要的是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因此,张生的不解风情正是崔莺莺的言不对心的原因。
直到临别在即,她才顾不得羞涩和矜持,把自己的心思统统倒了出来。
长亭送别的人物中间,崔莺莺的心思是最多的,而这些心思却完全出自于对张生的痴情。作者通过这些“多心”的描写,把一个深处爱情之中的少女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诚心之人
在长亭送别这一本,张生无形中是和老夫人站在一边的,他们都表现出“志诚”的特征。
老夫人虽然着墨最少,但她的形象却和主角崔莺莺一样鲜明。长亭送别之前,因为怕崔莺莺和张生私下结合之事,有辱门风,所以她才在红娘的“礼义大防”的心理攻势下答应了崔张二人的婚事,可她要求张生必须摆脱白衣的身份,考取状元。所以在酒席上,她叮嘱张生:“俺今日将莺莺与你,到京师休辱末了俺孩儿,挣揣一个状元回来者”,所强调的无非是状元,无非是她们家的名声,无非是崔张婚姻的门当户对。就在离别之时,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的老和尚尚且叮嘱张生:“先生在意,鞍马上保重者!”而老夫人只有一句:“辆起车儿,俺先回去,小姐随后和红娘来”,对张生没有任何的关怀之意。这个“诚心”的丈母娘对女婿显得如此冷漠无情,其原因主要在于她对家族利益、功名的“志诚”,而这些世俗利益令她忽略了人情。
张生本是个风流倜傥,聪慧过人之人。他与莺莺爱情的阻碍主要是老夫人,但在长亭送别时,他却无形间和老夫人站在了一起。
崔莺莺对他留恋不已,对老夫人拆散他们怨恨不尽。在老夫人要求张生“挣揣个状元回来者”的时候,张生踌躇满志地回答:“小生托夫人余荫,凭着胸中之才,视官如拾芥耳。”将考中状元当做囊中之物,唾手可得。在莺莺要他及早便回来的时候,他却态度坚决地回答“金榜无名誓不归”,崔莺莺对他留恋无尽的时候,他却急着据鞍上马,并问“有甚语言嘱咐小生咱?”他急于进京,立志夺取状元,这些均和老夫人保持了一致,令崔莺莺怨恨不已,只好生出种种心意试探于他。
张生表现出的不解人意,愣头愣脑也正是因为他的“诚心”,对爱情的志诚,不同于崔莺莺的浪漫和幻想,他把考状元当做实现他们爱情理想的出路,所以他才忽略了崔莺莺的感受,执意去考取功名。
张生对莺莺的“背叛”和对老夫人的“皈依”,一方面衬托了崔莺莺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正表现出他对崔莺莺的“痴情”。
三、现实性的人物特征与传神的动作描写
作为一出爱情剧作,《西厢记》表现出了强烈的反礼教的意义,崔张二人也成为大胆追求爱情的青年人的典型。从主题意义角度上来讲,《西厢记》比不上《牡丹亭》反封建礼教,宣扬自由情感强烈;从人物的反叛性格角度来讲,《西厢记》比不上《墙头马上》中人物强烈。但就人物形象本身来讲,《西厢记》的人物塑造却比这两者更真实,更具有现实性。
《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表现出泼辣大胆,无拘无束,敢作敢为,无所畏惧的性格特征。她可以抛弃父母,随一个自己喜欢的素昧平生的书生私奔,她可以无名无分,在后院生儿育女,她可以为了维护自尊割舍儿女,放弃情感。这个形象虽然让人觉得痛快豪爽,但她却距离现实生活较远,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成分。“在作者理想化的婚爱观和女性观中 , 李千金的身份与性格则原本是一致的 , 实为作者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和生活理想所塑造的一个 “完美 ”。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可以因情而死,为情而生,为维护爱情和父亲据理力争。连花神,鬼王都可以被她感动,她的形象体现的是汤显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论”思想。但这个人物却是脱离现实的,是人们美好愿望的化身,具有的是浪漫主义幻想。
而崔莺莺的形象却具有活生生的人的特征,她有对爱的执着追求,她有着对失去爱情的恐惧,她也有着少女的羞涩与矜持。她有着对爱情,对张生的一片赤诚,也有着虚情假意,对张生的刁难试探;她身上有着礼教挥之不去的阴影的笼罩,也有着对爱情的浪漫的憧憬和幻想。
没有了现实的,具体的矛盾冲突,为了凸显人物性格,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同时用传神的动作描写用以表现人物心理,使得人物活灵活现,也增强了戏剧的舞台表现效果。
如“【小梁州】我见他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见了把头低,长吁气,推整素罗衣。”
崔莺莺内心愁苦交加,但在众人面前又不好表露,所以忍悲含泪。只能偷眼相看张生,偶尔碰上张生的目光,四目交对,本来是含情脉脉,但又怕这脉脉深情为他人、为张生所见,所以下意识地低头,又情不自禁地吁气。为了掩饰这种羞乱,只装作整理衣服。这样一个动作描写,使一个含情少女的娇羞之态跃然纸上,神情毕现,可爱可亲。
而“【朝天子】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一个这壁,一个那避,一递一声长吁气。”则将心里描写和动作描写相结合。表现出崔张二人愁绪满腹,而又碍于老夫人在场而无法倾诉,愁肠百结时在下意识地叹息憾恨,心有所应,不由自主叹息的神态。
心理描写如同大笔泼墨,动作描写如同工笔细描,一个写态,一个描神,两者结合,神态兼备。同时动作描写使得舞台表达效果非常强烈,同时也使人物性格更为鲜明突出。
崔莺莺身上的这些相互矛盾的特征也正是这个形象的动人之处,她既不脱离现实,又承载着人们浪漫的理想。在长亭送别这样一个没有明显对立的矛盾冲突的情节中,用平实的写法,塑造出了神情毕现的统一于“痴情”特征的主要人物形象,既表现出崔莺莺的“多心”,也表现出张生和老夫人的“诚心”,可见王实甫神乎其技的写人艺术。
(作者单位: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