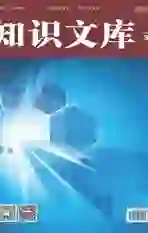宗法社会下的“歇斯底里”
2016-04-29毕琳
张爱玲的小说时常会写出一些由于受到宗法社会压抑而灵魂扭曲的女性形象,《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本文以曹七巧为例,并联系《金瓶梅》古中的潘金莲形象,旨在就由宗法社会对女性的禁锢所造成的“歇斯底里”做一些初步的探究。
张爱玲笔下最令读者关注的,无疑是一些“性冷淡和受挫的女人,老处女,受骗的妻子,以及那些因残暴,独裁,生活空虚的女人”(波伏娃《第二性》),其中,以《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夏志清先生对曹七巧做出过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评价,即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枷锁里的女人,不给自己快乐,也不给别人快乐”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于《金锁记》的艺术成就,笔者在此无需赘述,而是更多地将关注点置于这种现象的背后,并找到《金锁记》与《金瓶梅》一类小说的共同之处。
曹七巧的遭遇与她所处的环境有关,感情上,尤其是“性”的缺失使得她的心灵一直处在被压抑的状态之下,这种被压抑的情绪一旦爆发,那么,便“对一切活着的东西抱怨,不满和怀有敌意” (波伏娃《第二性》),尤其是在爱情方面,子女的爱情与她的进行对照,无疑会使其产生一种混有嫉妒和愤怒的情绪,并在摧毁这样的爱情中获取报复的快感,即弗洛伊德所谓的“利比多”能量,而这种破坏性的能量在《金瓶梅》中也充分地体现出来:潘金莲在性的压抑下,先是鸠杀武大,之后又在斥责,毒打下人的行动中,宣泄着自身性欲得不到满足的苦闷;另外,在《初刻拍案惊奇—西山观设辇度亡魂》中,寡妇吴氏恼怒于与道士的奸情受到儿子的干扰,不惜预谋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此类文本除了宣示伦理道德以外,我们同时可以发现造成此类所谓“荡妇”的生存状态的原因——除了表面上的“性”的匮乏,更重要的,是男权统治下的宗法社会所导致的女性的生存困境。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统治权掌握在男性的手中,男性以伦理道德,礼仪规范为手段,以经济地位为基础对女性进行掌控,使女性始终处于附属地位,甚至在精神层面上,也诱使女性成为男性自身的附庸,这使得女性一直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焦虑之中,女性的人格消耗殆尽,逐渐失去了自我意识和独立性:
“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 还会飞出来, 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一泡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 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 羽毛暗了/ 霉了, 给虫蛀了, 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茉莉香片》
“她睁著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土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一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 鲜艳而凄怆”——《金锁记》
张爱玲以这样意味深长的象征手法向我们昭示了彼时女性受压抑,凌辱的命运,这种遭遇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经济上的封锁。《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对于范柳原一再采取委顺的态度,其原因便在于失去经济地位的恐惧和无奈,与此相对,掌握着一定经济实力的女性便会在处境上大不相同,《金锁记》中,曹七巧正是由于继承了丈夫遗留下的财产才得以在接机兄长的同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也得以拥有吸引小叔姜季泽的筹码。
男权社会长久以来得以对女性进行压制的另一凭借便是女性对于“性”的需要,在性行为的过程中,男性一直处于一种“给予者”的地位,同时,男性治下的宗法社会又对女性的性需求做出严密的控制,颂扬贞节烈女,严惩荡妇淫女,这使得女性的性的主动权完全被男性掌握: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
曹七巧明知姜季泽只是贪图她名下的财产,但仍旧对其抱有一丝丝幻想,潘金莲即使受到西门庆的百般凌辱,依然千方百计将他留在身边,均体现出男性在控制了女性感情和性的需要后完全扮演了“统治者”的地位,这不仅摧毁了女性本该拥有平等地位的权利,并且直接导致了女性“自我雄化”的行为。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往往具备双重身份,既是主体(如婆婆、母亲),又是客体(如妻子、女儿);或反过来,既是从属客体(如妻子、佣人、女儿等),却又含有主体自我的意涵(如女性家长、疯女等)。因此,张爱玲笔下众多丰富的女性人物,实际上面对着双重的压抑,不单只受到父权直接的压抑,同时也受到父权间接的压抑。前者的压迫者是男性,而后者的(压迫)代理者则是女性。这些女性人物往往因而扮演着双重矛盾的角色,甚至是自我分裂的双重身份:是被压抑者,同时也是压抑自我(同性)的施虐者;是父权的反抗者,同时也是父权的寄生者” (林幸谦 《张爱玲—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的文本》)。林幸谦先生所提出的“双重身份”概念,直指张爱玲笔下女性人物的实质,在《金锁记》中,曹七巧的身份便具有这种“二重性”,年轻的时候,无论是面对姜家还是曹家,她无疑处在一种被动和附属的地位(对于曹家,她是妹妹,女儿,对于姜家,她是儿媳,妻子),到了晚年,她便成为了曹家的女性家长,面对自己的儿女,她时时刻刻展现着自己封建家长的权威。在此,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曹七巧对于对于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女儿长安,曹七巧破坏了她的婚姻,幸福,这其中隐然含有一种敌意,而对于儿子,她采取了尽力拉拢的方式,而将儿媳排斥在外,这其中,便暗含了对存在于身边的潜在替代者(年轻女性)的敏感;《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同样具有这种“双重身份”,在西门庆面前,她是妾,是玩物,甚至不具有一个女人本应具有的身份和待遇,但是在外人面前,尤其是在下人面前,她却将自己的权威发挥到了极致,这一切,都源于在其他人眼中,潘金莲是作为西门庆的替身而存在着,她的一切均是以西门庆为代表的父系社会所赋予的,她自身也表现出对于这种“家国同构的封建宗法文化极其制约下的封建性别文化”(谭邦和 《明清小说史》)认同。而这种父系宗法制的绝对权威,正是将女性的“女性身份”异化为“双重身份”的主要原因。
抛开两部小说的说教意义不谈,单就曹七巧与潘金莲而言,二者同样是宗法社会下异化变形的产物,同样是扭曲为“歇斯底里”式的“恶之花”,另一方面,她们却也试图改变她们的处境,然而她们却将她们的希望寄托在(纨绔子弟姜季泽和浪荡子西门庆),这向读者表明,在彼时社会,宗法制如同天幕一般笼罩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金瓶梅》虽是世俗小说,但是却反映出社会的全景),令人无处逃遁,挣脱不得,无疑将小说的悲剧性深化了一层。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