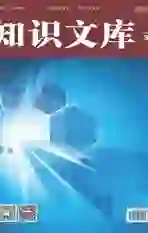残雪《最后的情人》的思考
2016-04-29刘亚利
残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她的创作以现代的手法,独特的感悟,结合自己的创作观念和体会,没有笨拙的模仿和故作姿态的卖弄,眼于人物深层的精神世界,深入人物内心,并深挖细究,独辟蹊径,通过作品传达自己的真性情,具有鲜明创造风格和个性化特征,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残雪于2005年花城出版社出版《最后的情人》,就她本人自己来说“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许这是一部有些奇异的小说——无视常规、放荡不羁而又过分空灵。就连作者我,在刚写完这部小说之后,心里也是充满了重重迷雾的。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部小说在开辟空间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最后的情人》确实是一部奇异的小说,可以说,整部小说没有跌宕起伏、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没有生动鲜活、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没有开合有度、浑然一体的结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部小说排斥人和水平面的描写,以及通常那种情节逻辑的操纵。在同类小说中,它在这方面或许是最为走极端的。”在这部奇异的小说里,最吸引读者眼球的地方,首先是空灵的构思,就如作者如上说的一样,是个无视常规的空灵的存在,小说在情节之外、人物之外、结构之外寻找着创作的自由,完全挣脱了传统小说注重人物塑造、注重结构完整的创作模式,在文学创作的精神层面、客观的层面上作出了大胆的、另类的努力,作者似乎是以最理性的最客观的姿态审视着作品中似乎甚至与常人不同的人物们,在奋力摆脱着眼前的迷雾,寻找着出路,所进行的非常人所能为的努力。小说中,作者的精神旅程大开大合、大起大落,任意游走,无所牵绊,或进或退,从地下瞬间至到空中,从遥远瞬间至眼前,人物的精神活动完全失去了常理,作者不是在塑造形象而是在人物超越常规的思维的牵引下前行着,下一步是什么,无法预料,这种叙事空缺的存在这似乎就是小说最具魅力的所在,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留给读者的仅是无果地推理的困扰。
即便如此,小说中每个人物彼此独立又彼此联系,他们之间不存在前因后果却保持着高度的紧凑,没有亲疏远近却互相完成塑造,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精神追求,乔爱看书以至于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跟老板或主顾谈生意时也不忘看小说、里根热衷于自己庄园的扩张、埃达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马丽亚眼看着丈夫乔对书籍的爱好吞噬了一切,毁掉了他们的夫妻生活,面对丈夫无时无刻的“游走”,给马丽亚自己带来了突变,也像丈夫一样陷入了“神游”的圈套,首先是倾其所有来买各式各样的首饰,将买来的首饰不是用来佩戴而是装进首饰盒,然后就是不厌其烦地编织挂毯,乔和马丽亚的儿子不专心读书一心想当个花匠,等等。这些带有魔幻甚至是荒诞色彩的描写读来超出常人预料。作者在《最后的情人》序中说“我写的小说都可称之为垂直的小说”,“将每一处的描述都扎进地心深处”,“深入,再深入,这就是我的创作姿态。”这似乎是这部小说另一个吸引读者眼球的所在。为什么是垂直的小说,换句话说,就是直接用文字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深层次地挖掘人物在“本我”状态中的所作所为,以更深刻地揭示人的本质。在弗洛伊德看来,失语和口误都是“本我”状态的表现。而在残雪的小说当中,人物的梦境状态似乎是口误和失语的扩大化,以此充分暴露“本我”,这种方式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但这种所谓的“垂直”似乎真是一针见血地刺中了人物的要害位置。在小说中,人物的独特行为没有矫揉造作,而是在一个小小的背景下的产生而为此延续下去,如埃达,泥石流毁灭了她的家,她奋力逃出,流浪于人间。作者写道“也许我的作品同那些有过毁灭性的经历的读者更为亲近,她(他)们会更理解作品中的决绝:那种在吞没一切的虚幻感中的坚持,那重即是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的气概。今天离我写完小说已经3个月了,我终于明白了埃达追求、寻觅的到底是什么——她要重返已经消失了的过去,因为那时她的精神支柱。”就如同马丽亚因了丈夫对书的痴迷使自己也有了突变一样,埃达因为自己失去了家园才使她在世俗的爱面前流连,既不安又难以割舍,这让她很痛苦,但为了两全,她又无法抛弃这痛苦,只能忍受着痛苦,在痛苦中继续爱。小说将人物的痛苦和追求直接深入到人物的无意识状态中,马丽亚因困惑而疯狂的买首饰或是编织挂毯以至于到了痴迷的程度,不厌其烦地编织着蝎子形状的挂毯,似乎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的无边的困惑物化,比起痛苦、困惑等来的更加直接,更让人难以琢磨;而埃达的不断寻找,这种非正常的状态,都是对现状不满的异化表现。
总之,在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个性化的行动轨迹,丹尼尔的执着于成为一名花匠,文森特的找寻、里根的寻根,都以一种魔幻色彩的形式表露出来,是非常人所能为的,如作者本人所说“我所开辟的小说的空间里有一种隐秘的机制,大概所有的人或物都受到那种机制的操纵……也因为那种机制,人和人之间的对话永远是猜谜,有时候并不是相互猜谜,而是共同猜一个不解之谜,猜到死。”在序的结尾处,作者自己也在追问“最后的情人是谁呢?我想将这个谜留给读者去猜,我觉得,这是值得一猜的。”试着猜想,单就情人来讲,对需要的人来说,她是一个充满诱惑、欲望的的载体,在当下一大批有权有势的人们,会为实现诱惑和欲望而付出昂贵的代价去争取,于是她便成为了一个虚幻的欲望的代名词,现实社会当中的人在追求着,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着不可企及的欲望,为了得到而不断付出努力。《最后的情人》当中的主人公也在追求着,对自己现状不满了就需要新鲜生活的陶冶,就需要去寻找,欲望是无止尽的,追求的路途是漫长的,追求的道路是艰辛的,就像小说中人物所经历的种种的复杂一样,最终却有被异化的可能。但他们走的很坚决,没有放弃。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梳理痛苦的过程,用她自己的话说“在我看来,几乎每一位有精神追求的读者,他的内心都会有一个终生解不开的情感死结。” “我的空间里的人们在某些方面看似外星人,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将那些最具普遍性的人类欲望赤裸裸地加以发挥罢了。”乔最后到了东方,埃达在绕了一大圈之后回到了农场,文森特来到了五龙塔,马丽亚去履行了,等等。每个人物都满足了自己的欲望都得到了自己的“情人”。但是,欲望的“情人”是无止境的,也就没有所为的“最后”,最后的也只是一个新欲望的起点罢了。试着猜测,如果就《最后的情人》这种魔幻的形式写下去,作者仍还能写出如此厚度的长篇吧,因为人的欲望无止境,人的想象也就没有尽头。
如此看来,对于《最后的情人》的欣赏阅读也可以非常规性的进行了,在小说的序中,她谈到“我所追求的,是一种‘元小说’的境界,我要将文学的本质准确地表达出来,最好是丝毫不偏离。” “我就如同小说中的那位乔一样,怀着一种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我要将陈腐不堪的表面事物通通消灭,创造一个独立不倚、全新的世界,一个我随时可以进入的、广阔的场所。”就此来讲,作者残雪是努力了,但是文学作品要有它的欣赏性才能实现它存在的价值。根据罗兰巴特把文学的文本分为可读的和可写的两种形态来分析一下。在他看来,传统的写作是“及物”的,而现代写作则是“不及物的”。前者把读者引入一个仿真的世界,而后者则把写作作为自身的目的。这就导致了两种文本的出现,传统的文学作品是“可读的文本”,读者与作者分离,读者被动地被作者引入作品;相反,现代小说则是“可写的文本”特征是读者发挥想象力去补充文本,使自己从一个被动者成为一个主动者。实际上就是从“作者之死”到“读者诞生”。《最后的情人》即可称之为可写文本了,读者阅读获得的并不是愉悦和消遣,而是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完备作品,是一个付出劳力的过程。所以说“我的小说不会给人以抚慰,它是一种对痛苦的分析,也是将矛盾层层深入地加以演绎”。作者的情感体验必须由读者的情感体验反射出来,这样作者作品的全部功能才会得到延续和理解,否则便不存在。也就是说,即是《最后的情人》有比较完备的结构,由十六个章节构成,似乎每个小标题都阐明了每节的主旨,但是,读起来,不去发挥读者的想象力是无法继续的,这是种痛苦、是一种煎熬,同时在这巨大的阅读阻力面前,也是一种勇气。
所以说作者残雪是特另独行的,《最后的情人》带给读者的阅读期待也是另类的。
(作者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