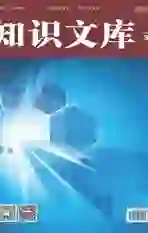浅析《颓败线的颤动》
2016-04-29苗文敬
鲁迅《颓败线的颤动》这首散文诗创作于1925年6月29日,于1925年7月13日首次发表在《语丝》周刊第35期上,后收入散文诗集《野草》中。《颓败线的颤动》不同于《野草》中其他描写梦的作品,它塑造了独特的“梦中梦”,共包含三个不同的场景:母爱的崇高与无私、巨大牺牲反遭儿女怨恨遗弃、极端绝望沉痛之下的复仇。作品通过母亲忍辱出卖肉体将女儿养大成人、年老反遭儿女怨恨背弃的故事,展示了牺牲者的悲剧性,揭示了先觉者鲁迅在现实中经历类似事件后遭受的沉痛心灵体验和巨大精神折磨。
一、创作目的
前人关于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创作目的诠释大致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一)表达鲁迅对周作人夫妇恩将仇报行为的悲怨;(二)通过“老妇人”这一形象展现旧中国妇女的苦难生活,表达对她们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与关怀,是一部揭露并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散文诗。(三)表达鲁迅对曾以心血关怀的某些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的青年们的义愤,对人伦中的丑恶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
我认为以上三种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作品中穷困无依的年轻母亲为了养活女儿忍辱出卖肉体,年老后却遭到子女怨恨、鄙夷、抛弃的故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遭际。然而,不论是鲁迅对以怨报德的青年们的批判,还是对胞弟恩将仇报行为的怨愤,都只是鲁迅创作《颓败线的颤动》的外在原因;该散文诗也绝非单纯的想要表达对旧中国妇女的同情与关怀。我们不应刻意的将鲁迅的生活遭际与作品中老妇人的境遇简单对应起来,导致对作品的认识趋于肤浅、片面,从而忽略了作品本身蕴含的复杂而深刻的意义内涵。
对于内心情感和矛盾意识的直视是先驱者精神特征的昭示,作为先驱者的鲁迅,其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处于痛苦难堪的自我审视之中。鲁迅借助《颓败线的颤动》中“老妇人”牺牲与复仇这一象征性意象,思考并探索先趋者与民众之间的隔膜,寄托着深沉复杂的人生关怀。
二、浅析“梦中梦”的三个梦境
厨川白村曾在《苦闷的象征》中指出,梦是人的意识和内在情绪的一种“改装”,而“改装是象征化”。《颓败线的颤动》是一首象征主义散文诗,鲁迅笔下“老妇人”的故事被赋予了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
(一)梦中第一个场景:生活所迫走向堕落
一个贫苦无告的小妇人为饥饿所迫,在一间“深夜中紧闭的小屋”,向一个“初不相识”的男人出卖肉体,赚取微博的收入供养两岁的女儿。这“瘦弱渺小的身躯,为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而颤动”,多么悲凉、凄苦的场景。母女两人难耐的饥饿迫使年轻妇人走向堕落,肉体被蹂躏的苦痛、对自己行为的惊异、出卖肉体产生的强烈羞耻感、有钱可以使女儿果腹的欣慰,种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内心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使她身体不自觉的颤动。一个卑微、孤苦无依的年轻母亲为了生存独自承受着巨大的屈辱,她牺牲的不仅仅是肉体更是做人的尊严。
“妈!我饿,肚子痛。我们今天能有什么吃的?”“我们今天有吃的了。等一会有卖烧饼的来,妈就买给你。”她“欣慰地更加紧捏着掌中的小银片,低微的声音悲凉的发抖”。能使女儿摆脱饥饿,这是小妇人在侮辱、痛苦、悲凉中获得的唯一一丝欣慰。她的尊严被践踏、身体被蹂躏,她的声音变得低微、悲凉、发抖,她的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还早哩,再睡一会罢”,“她说着,同时抬起眼睛,无可告诉地一看破旧的屋顶以上的天空”。“无可告诉地”苦痛,是这个孤困无依的小妇人对社会现实最痛苦最悲壮的无言的控诉,她迷茫的、眼神涣散的望向天空,痛定之后反而使人变得麻木、茫然。“空中突然另起了一个很大的波涛”,这个波涛是鲁迅对小妇人所遭受巨大侮辱和痛苦的同情、愤怒所产生的。它和小妇人的情感波涛“相撞击,回旋而成漩涡,将一切并我尽行淹没,口鼻都不能呼吸”,“我”和小妇人的情感波涛相呼应、混为一体,产生出巨大的使人窒息的压力。传达出这一巨大的牺牲和侮辱的作者本人,情不自禁的陷入巨大的哀痛之中,被这种悲苦、沉痛的情绪所淹没,心情极端沉重无法自拔,导致“呻吟着醒来”。
(二)梦中第二个场景:巨大牺牲后反被鄙夷怨弃
多年后,小妇人早已垂老为老妇人,女儿已结婚生子。屋内外已这样整齐,生活不再贫苦不堪,可老妇人的境遇反而更加悲惨:青年夫妻和一群小孩子都“怨恨鄙夷”地对着这个垂老的女人。女婿气愤地说“我们没脸见人,就只因为你”,“你还以为养大了她,其实正是害苦了她,倒不如小时候饿死的好!”,根深蒂固的旧道德观念使这个男人无情的说着荒谬残忍的话。“使我委屈一世的就是你!”女的说,“还要带累了我”男的说。“还要带累他们哩!”女的说,指着孩子们。老妇人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养育大的女儿,对母亲巨大的牺牲不仅没有丝毫的体恤反而充满怨恨、鄙夷,老妇人内心的沉痛、悲凉、怨愤之深可想而知。女儿女婿的话像一把利刃,一下又一下的剜着老妇人的心!老妇人和子女处于一种深刻对比和尖锐对立之中:一方面,老妇人无私的牺牲、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另一方面,忘恩负义的子女对老妇人巨大的牺牲奉献的不理解,把它当做扰乱他们正常生活秩序的罪魁祸首,予以敌意的冷骂与毒笑。受难者的悲剧命运不仅表现为不被理解,更表现为付出与牺牲的被扭曲被歪曲,当年忍受巨大侮辱和内心谴责的无私奉献如今却变成了自取其辱!老妇人“口角正在痉挛”,女儿女婿的言行使她极度愤怒、口角痉挛。小孩子的“杀!”使她“登时一怔”。因袭的虚伪残忍的道德观念使懵懂无知的孩子深受毒害,他们虽不懂父母口中虚伪的道德,却表现的比父母更加残忍无情!小孩子的反应令老妇人彻底绝望,她再也不会对子孙以及所谓的家庭抱有一丝希望。
愤怒过后一切归于“平静”,这是绝望的平静、心灰意冷的平静,哀莫大于心死。老妇人已清醒的看透人生,她不再具有任何利用价值,等待她的只剩怨恨鄙夷和无情的抛弃,对于这种忘恩负义的行迳似乎在她意料之中。鲁迅现实生活中经历过类似的情感体验,所以传达老妇人的感受才会如此深刻。“她冷静地,骨立的石像似的站起来了”,老妇人决绝的离开这个她为之付出一切却毫无温情的家。“她开开板门,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以怨报德的子女和狭隘刻薄的社会,人性深层的冷漠、残忍、无情一步步将老妇人推入绝望的深渊。老妇人处于沉痛、怨恨中无法自拔,混合着沉重的怜悯和决绝的反抗,复仇的情绪油然而生。作品中的“子女”在鲁迅的观念中已转化为一种由历史传统和现实关系所组成的强大的社会力量,与鲁迅所代表的先驱者形成鲜明对立的一种现实异己力量的象征性揭示。
(三)梦中第三个场景:沉痛绝望下的复仇
深夜中她走在无边的荒野上,裸露着颓败而颤动的身躯,她已丢弃所有的耻辱感,一个人踟蹰在荒野中。痛苦献身的过去与当下儿女的背叛、抛弃令她悲痛、绝望,她要诅咒、复仇!抽象离奇的意象、朦胧迷幻的境界使复仇成为全篇最富张力、最吸引人情感的地方。过往的一切于刹那间全部涌现在眼前,她禁不住的浑身发抖痉挛,哀莫大于心死,很快一切又归于平静。“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诅咒……”爱的眷恋、爱抚、养育、祝福,生成的却是决绝、复仇、歼除、诅咒,各种对立情绪并和在一起,她独自承载着痛苦和绝望。对老妇人的描写展示了鲁迅内心世界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激烈纠葛,这纠葛化为呻吟从老妇人口唇间流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在毒笑和谩骂声中,在被侮辱被放逐的痛苦回味中她开始决绝的挑战和复仇。她“举两手尽量向天”,“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并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老妇人的姿势既是一个无助的“天问者”的姿势,也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反抗与控诉的姿态。这姿态既包含了人对于自身命运的深刻绝望,又表达了伴随绝望而来的极度愤怒情绪的宣泄。此处的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澎湃于无边的荒野。”鲁迅对颤动变形的象征性描写,既是将老妇人无言的控诉和复仇精神状态的具体化,也是表达自己对历尽心血培养过的青年反掷来敌意与谩骂时内心强烈绝望、悲凉感受的表达,对以怨报德的丑恶伦理道德的复仇的强烈情绪。
鲁迅将做梦原因归结为“将手搁在胸脯上的缘故”,有意弱化梦产生的原因将其简单化,将有意识的梦弱化为无意识的梦,反而更加衬托出梦背后隐含的深刻精神意图。帮佣、乞讨的付出和牺牲远不够表达鲁迅体悟到的生存个体所忍受的极端的肉体及精神双重的苦痛,鲁迅现实境遇中牺牲而被弃的痛苦只能通过牺牲肉体终被弃的老妇人的形象得以表达。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