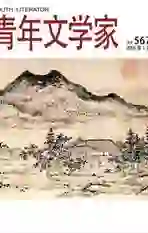且耕且耘定乾坤,红学更显精气神
2016-04-19吴广义
作者简介:吴广义(1947-),辽宁沈阳人。1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包头师专,包头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等职务,并兼任中国屈原学会理事,内蒙古社科联及包头社科联专家评委,包头师范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主要著作《解读道德经》(获内蒙社科政府二等奖)、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河北教育出版社),《大学语文》(远方出版社),《先秦文学论集》(远方出版社),《荀子评注》(崔文恒教授主编,我参与主编,远方出版社),并在省级、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几十篇。2010年评为包头首批三级教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4
由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崔文恒、崔晓耘著的《耕耘斋解读<红楼梦>》这部专题研究《红楼梦》显学专著在2014年7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部近45万字著作凝聚了崔文恒教授30多年的教学积累和学术智慧。它是集学术性、趣味性、知识性为一体的一部学术专著。它的出版给红学界一个沉甸甸的礼物。全书分为七个板块:一、简说《红楼梦》;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三、贾府的主子们;四、王夫人与金玉姻缘;五、贾宝玉和丫鬟们;六、红颜薄命;七、她们是掩饰封建罪恶的祭品。这七个部分看似彼此独立,其实又彼此勾连,洪然一体,无不体现出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缜密的逻辑。第一部分简说《红楼梦》是一综合性板块,既是全书的总论,最能体现作者对《红楼梦》的态度。
一、对《红楼梦》的主题定位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历来存在争议,鲁迅先生说过:“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对《红楼梦》的这部小说的主题定性问题上,是研究者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作者没有回避。作者没有迷信权威,也没有妄加揣测,而是以大量无可辩驳事实明确指出《红楼梦》是一部世情小说。开篇在引言部分(《<红楼梦>就是一部世情小说》),作者就明确指出:有不少人只要看见“红楼梦”三个字,马上就联想到爱情、婚姻,甚至三角恋爱等字眼儿,他们非常狭隘地把《红楼梦》看成是一部爱情小说,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言情小说。最典型的例子是高鹗的续书,他所写的调包计就是把《红楼梦》拉到婚姻的轨道上去的,因此没了《红楼梦》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即使是其他艺术形式的再创作,也是以爱情故事为主体,淡化了小说更为重要的思想内容,越剧《红楼梦》的情节演绎就是如此。上世纪民间还流传过这样的俗话:“看了红楼梦,害上相思病。”可见其被扭曲之一斑了。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在宣传《婚姻法》的活动中,也有人拿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来说事儿,这些现象的产生与存在,充分验证了人们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误解之深。不错,《红楼梦》是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也准备写或者已经写了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姻,还写了其他许多人的爱情或婚姻故事,甚至还有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和同性恋情节,但是,这只是《红楼梦》小说内容的一部分,并不是它的全部。……事实上,《红楼梦》几乎是全方位地描述了封建社会的婚姻问题:从皇宫的“选秀”纳妃嫔以及替皇室子弟指婚的制度,到贵族家庭之间的政治联姻;从贵族、富人的纳妾制度,到男子聘娶“填房”的续弦制度;从女子从一而终的礼教杀人,到歧视女子改嫁的社会流俗;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制度,到主人决定女奴命运的收房制度与指婚制度。这些等级不同的婚姻关系,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本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触及了封建社会各种制度的本质以及它们的不合理性和腐败性、野蛮性,其中包括继承制度、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土地制度、蓄奴制度等等。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红楼梦》看成是一部爱情小说或言情小说,……当然,它也不是胡适所说的“自叙传”小说,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虚构的文学形象,事件也都是虚构的故事情节,它们是曹雪芹从各类生活原型中提炼出来、并且予以千锤百炼而熔铸在一起的文学形象与故事情节。虽然看起来有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因素与成分,但它们同历史中的人物与事件不能一一比附,更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因此作者认为,对于《红楼梦》中所写的人物与事件,我们只能说是曹雪芹的文学创作,是他搜集、筛选、提炼、熔铸各种素材,并且是忠实于生活轨迹的文学虚构,并不是原原本本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把它说成“自叙传体小说”,既不符合江宁织造府的兴衰变迁,又不符合曹雪芹的生平经历;因此,江宁织造府只是《红楼梦》文学素材的一个来源,与小说中的宁国府、荣国府根本挂不上钩,请读者千万不要迷信考据派的固执己见,更不要被所谓的“探佚派”那些胡说八道所蒙蔽!俗话说,“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儿”,作者用这些掷地有声的证据指出《红楼梦》“应该是一部描写社会问题的世情小说”。材料之充分,逻辑之严密,言辞之犀利,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学者治学之严谨。
二、关于《红楼梦》的人物、情节、环境
关于《红楼梦》的人物。就人物而言,“文学是人学”,人物是小说故事的中心,是主角。在“《红楼梦》的人物设置”一节中,作者首先详尽地论证了作品中人物的独特构思。作者认为,曹雪芹为《红楼梦》设置的人物结构,就是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的关系。《红楼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各起各的文学作用、各尽各的文学使命的,无论其为主为次都是缺一不可的,缺了哪一个都会使故事情节索然无味。作者以鲁迅先生说过“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段话作为切入点。作者指出,在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代,深受几千年来“春秋笔法”的影响,在小说、戏曲里描写人物形象就成了传统的习惯,往往是写好人就不写他的缺点,写坏人就不写他的优点。曹雪芹完全突破了这个俗套,他从社会的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择取素材,从生活的深处与思想的高度提炼这些素材,然后塑造成几百个鲜活的形象。在《红楼梦》里写了众多女子,诚如王昆仑先生所说,《红楼梦》“是中国最能理解妇女悲剧性的书;也再没有谁能和这位作者一样,创造得出那么多的妇女典型”。在灿若星辰的女性形象里,仅金陵十二钗的正、副、又副,就该有三十六人;直接描写的只有十五个女子,未直接描写的远不止另外的那廿一个,若是老少合计起来不下二百多人。她们都是薄命司中的“千红一窟、万艳同杯”,都是封建末世的不同阶段、不同地位、不同经历、不同个性、不同类型的牺牲品,她们的悲剧命运完全一样。鲁迅先生曾说过:“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又有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接着作者又写到,作为小说的《红楼梦》,描写众多美女的苦难与死亡,最能唤起读者的同情,也最能唤醒读者的良知;而痛恨并揭露封建社会的非人本质,正是《红楼梦》的价值之所在。作者剖析之透彻,见解之独特,感悟之深刻,溢于言表。
关于《红楼梦》的环境。环境是人物活动的空间,离开了环境,人物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环境的设置和描写,主要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和交代人物命运的。没有环境,人物就成了抽象的存在。在《红楼梦》的环境安排一节中,作者指出,《红楼梦》的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的展开,都有极其广阔的空间及具体环境。从地域上看,它包括作者指代北京的“都中”或“长安”,以及实际存在着的金陵(南京,江宁)及毗陵驿、扬州、苏州等地。这些真实的地方都在京杭大运河沿线,作者从繁华的京师与富庶的江南提炼出小说的地域环境,再把江南的各类人物调动到北京(长安、都中)来,铺开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编织成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塑造出一个又一个个性独具的鲜活形象。此外,还有虚构的那个并不平安的平安州,那是贾赦获取灰色收入的一个矿井,更是他东窗事发的一个源地,也是薛蟠遇险获救并解怨的福地。这个平安州的设计,既是环境描写,又是暗示社会背景的写法,它与甄士隐遭火劫后不能安居于乡间一样:“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粮夺食,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这是民不聊生而形成的匪患,官兵又借剿捕之名骚扰百姓而构成了兵祸,兵匪一同危害着甄士隐以及广大民众的生存。作者用亦虚亦实的环境描写,揭示出小说中的封建末世大环境。关于《红楼梦》中的贾府,作者这样写道,《红楼梦》所写的贾府,既然是北京(都中,长安)城里的贵族,为什么不直呼北京而要叫作长安或都中呢?这是曹雪芹为了逃避文字狱的迫害而有意安排的结果。关于宁荣二府以及大观园,作者明确指出它们完全是曹雪芹的一个文学虚构。作者认为,大观园虽然是把荣国府旧花园的后半部分和宁国府的会芳园连在一起,却同宁荣街、宁荣二府一样都是虚构的;因为,明清两代的中国虽有许多宏伟的或优雅的建筑,却并没有一个如此集中的府第园林。曹雪芹凭借自己的见闻,集中了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等风格迥异的园林和北京等地的街道、衙署、府邸和民居,把它们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进行反复的萃取与熔铸,然后虚构出一条宁荣街与连绵数里的宁荣二府,尤其是虚构出一座引人入胜的大观园来。当我们走进《红楼梦》,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跟着众多人物的活动,也行进在宁荣街上、漫步在两府中间,特别是畅游在大观园里面的时候,千万不要做按图索骥的事情,非要找什么“京华何处大观园”,那是注定要误入歧途的。什么北京的恭王府、南京的随园等说法,都与大观园没有可以吻合的地方,它们只有被吸取素材的可能,这就是不容置疑的文学虚构。……所以,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在现实世界里根本找不到,它只是作者创造性地设计出来的一座理想乐园,是曹雪芹专门为贾宝玉和青少年女子们虚构的一个典型环境。从《红楼梦》的环境描写来看,大观园是宁荣二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处可供居处并游玩的园林建筑。从文学创作意识和审美意念来看,大观园是一座永恒的理想乐园,只要《红楼梦》在人世间存在,大观园就会在人们的头脑中永远存在。从文学的创作理念来看,大观园只是一个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而设置的文学环境,只能伴随文学形象在文学作品里存在,随着其文学使命的完成便会自然地消失。这些独特的见解,字里行间体现着作者厚实的学术积淀。
关于情节情节设计。情节是按因果逻辑关系组织起来一系列事件。是展现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命运、集中表现矛盾冲突的舞台,情节的设置决定着读者阅读心理,是吸引读者阅读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成功与否。作品的情节线索设置得好,便能够凸显各种矛盾,深刻地揭示主题思想。《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经典,人物众多,故事情节错综复杂,要理清其情节线索,并非易事。作者对此并未回避。在书中作者对《红楼梦》情节线索的梳理不仅有条有理、细致入微而且生动有趣,读起来趣味横生,让人流连忘返,拍案叫绝。作者在文中写道:指出《红楼梦》的情节编排和线索设置,却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它们有如巨型的七彩刺绣一样,存在着许多条线索,或并行不悖,或明暗相间,或互相交错,或前后照应,既有整体构思的大线索,也有具体情节的小线索。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节编排,如果不作仔细的梳理,必将导致卯榫失错,无论理解主题思想,还是欣赏艺术和审美,都会出现不少的窒碍。尤其要牢牢记住以下这一点,那就是不能单独地挑出某一条或两条线索来,进行简单的、肤浅的评论,甚至武断地下结论。例如,有人把《红楼梦》片面地说成是言情小说,他就会强调爱情主线这一说法,自然会造成阅读与思考时的狭隘性和肤浅性,在认识上乃至所作的结论上就会导致形形色色的错误,在文学欣赏和审美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歧义和弊病。这样的见解就把人们对《红楼梦》故事的误解根源很清楚的揭示出来,为正确阐释作品的主题指明了方向。故事情节的曲折紧张、起伏跌宕,不仅能够增加小说的趣味,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也会鲜活起来,鲜明的文学效果与强烈的审美趣味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作者指出,无论是作者自己的表述,还是脂砚斋评点系列的说法,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那就是作者构思的所有线索里,或者说小说的故事情节结构里,都应该有男女主仆的风月故事和金陵十二钗的悲剧故事;在某些特定的情节中,还会把风月故事同十二钗的悲剧故事交织在一起。而且,两府虽然都有风月故事,却是侧重描写宁国府的糜烂,而写金陵十二钗悲剧故事则侧重于荣国府,再加上贾宝玉同封建卫道士之间的矛盾冲突,封建贵族的兴衰际遇与日常生活,包括高雅的文化生活与低俗的性生活,乃至明争暗斗的大小事件,共同构成了《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关于金陵十二钗的故事,作者这样谈到,这是曹雪芹安排的十二条情节线索。这十二条情节线索或互为交织、或并行不悖、或相辅相成、或两相对比、或交相映衬,使它们或明或暗、或主或次、或详或略、或写或不写之写,从而构成头绪纷繁、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即使在每一个具体情节里,它的线索也有可能是伏脉于千里之外。作者指出,正册、副册、又副册中的金陵十二钗,共有三十六人,明写的只是十五个少女,暗写的远不止另外的廿一个。古人习惯于把青少年女子比作花,曹雪芹构思她们的故事,也是扣住千红、万艳、群芳、沁芳来写她们的悲剧。在对林黛玉的《葬花吟》的这一情节的分析中,作者不仅是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梳理的别有一番滋味,令人叫绝,最后总结也是恰到好处。
另外,对刘姥姥进贾府的分析也是独树一帜的。作者认为,小说的第六回和第三十九回至第四十二回,写刘姥姥的两进荣国府;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贫婆子打抽丰的故事,实际上却起了极其重要的文学作用。首先,她成了串联众多人物的线索,周瑞家的、王熙凤以及贾蓉,贾母、薛姨妈、王夫人、李纨,贾宝玉和宝钗、黛玉、湘云、迎春、探春、惜春,乃至平儿、鸳鸯等人,都被她串连起来而成为故事的组成部分。其次,她的到来引发了两宴大观园的故事,这既描写了游园与宴会的场面,又展开了故事情节,重温了大观园的环境,还进一步细腻地刻画了人物形象。刘姥姥出场本身就是一条线索,她又牵引出好多条线索,编织成如此丰富多彩的叠印画面;她甚至还留下了两条线索—贾惜春作画、贾巧姐获救而为村妇,真正完善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情节结构,给人造成目不暇接的美感,生出天衣无缝的文学效果。
一篇好的鉴赏文章不仅能够增加小说的趣味,更能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这里经过作者的一番探究不但读者对故事情节有了深刻的认识,作品中人物形象也会因此鲜活起来,这样的评论文章既有鲜明的文学效果又有强烈的审美趣味,这就体现出作者的功力和匠心独运。
三、关于《红楼梦》的女性
关于《红楼梦》的女性,作者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的谴责。曹雪芹在作品中写了十四则判词,为晴雯、袭人、香菱、薛宝钗、林黛玉、贾元春、贾探春、史湘云、妙玉、贾迎春、贾惜春、王熙凤、巧姐、李纨、秦可卿等十五人,作了品格的评论和命运的预言,同时还写了十四支“红楼梦曲子”,这不仅对《红楼梦》的创作宗旨和金陵十二正钗的命运作了明确的交代或隐讳的暗示,同时也是对她们不幸命运的集中展示。作者指出,曹雪芹创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地位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修养不同、性格不同、结局不同;但是,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抑或是奴隶,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她们全都是薄命的红颜,谁也逃不脱悲剧的命运为进一步证实自己论断的说服力,作者还引用了王昆仑先生的话说,“(《红楼梦》)是中国最能理解妇女悲剧性的书;也再没有谁能和这位作者一样,创造得出那么多的妇女典型”。作者在第六部分“红颜薄命”和第七部分“她们是掩饰封建罪恶的祭品”对她们一一进行了点评和深入的剖析,用大量的事实告诉读者,她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她们是掩饰封建罪恶的祭品。作者指出,曹雪芹在第五回里,为十五位女子设计了判词,其核心就是“薄命司”的“薄命”二字;而“红楼梦曲子”的前提,就是“群芳髓”“千红一窟”“万艳同杯”。其中的“芳、红、艳”,古代皆指女子,也就是另一说法的“红颜”;我们把“薄命司”和“红楼梦曲子”合在一起,这就是古话说的“红颜薄命”。有良知者只是在作无可奈何的伤感,他们慨叹红颜薄命,却掩饰薄命的根本原因;没有良知者就为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百般的辩护,从无半点儿悲天悯人之心。特别是那些伪道学者,他们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以为女子是可以任意摆布的私有财产,有的毫无人性地蹂躏、摧残女性,有的用猥亵的目光玩弄祭坛上的薄命红颜。以上这些评价,分析之透彻,语言之犀利,材料之丰富,没有厚积是不可能如此深刻的。美中不足的是全书第七部分,绝大多数内容与秦可卿有关,总体上来说应该是秦可卿的专论。作者对秦可卿相关问题的研究非常详实,论据充分,推理严密,如对秦可卿形象的定位,对秦可卿之死的推断,对脂砚斋批语的梳理,都凸显出作者独特研究视野,从研究篇幅、思想容量、学术价值上也应为秦可卿研究开辟一专栏,但是作者却没有把它独立出来,这似乎有点缺憾。
此外,作者关于《红楼梦》的创作与文化继承、关于《红楼梦》中的礼仪、关于《红楼梦》的版本问题等都有独到的论述,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总之,《耕耘斋解读<红楼梦>》这部大作思想性、艺术性极强,读后给人的感觉用《红楼梦》中的话来说,真有点“若说无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的禅悟!全书材料丰富,趣味丛生,同时又科学严谨,有理有据,见解独到,有继承又有创新,这是近年来在红学研究方面难得的一部好书,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著名作家宗璞先生在王蒙《红楼启示录》一书的序言中说:“《红楼梦》是一部挖掘不尽的书,随着时代的变迁,读者的更换,会产生新的内容,新的活力。它本身是无价之宝,又起着聚宝盆的作用,把种种的睿思,色色深情都聚在周围,发出耀目的光辉。”我相信读完该书也会让读者在《红楼梦》研究上有更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