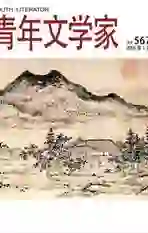沈从文思想探究
2016-04-19丁宇航
丁宇航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1
汪曾祺称“《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边城》是一部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心情的怀旧。”如果说痛惜的怀旧是因为出入都市文明的作者想要以回忆自己的童年的美好来逃避现实的污浊,并在这个理想化的纯美的世界里寄于自己的希望。汪曾祺先生只是说出了这个作品在现实中不存在,说出了边城在看似美丽与世无争的湘西世界的背后故事的悲剧色彩。悲剧感只是针对作品而不是针对作者自身的。笔者另有看法。真实的生活的理想化,沈从文般的大师级作家的刻意“藏着悲剧感,而痛惜的怀旧”,更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价值观念。
岳焕先生写作《边城》为代表的一类作品,首先,这是真实的。自小谙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土地,谙熟那绵延千里的沅水流域以及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的生活样式和吊脚楼淳朴的乡俗民风,因而形成对民间的、世俗的东西特殊敏感的审美情趣。先生14岁因循当地习俗入伍当兵,先后做过卫兵、班长、司书、文件收发员、书记,看多了湘兵的威武,以及各种迫害和杀戮的黑暗(在芷江的乡下四个月看杀人一千,在怀化镇一年多看杀人七百)。如此幼小的年龄承受巨大的心理炙烤,面对社会的残酷和周围生活的愚昧,这对于先生来说,无疑不是巨大的阅历伤痕,同样也产生了厚重的思想深度,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穷。其后,作者接触了“五四”新文化的影响,而渐次迈上文学的舞台。他带给我们的,是真实的血泪和悲欢,真实的淳朴和原生,真实的愤怒和怜惜。因而,说理想化,我倒认为,是我们读者,不能真正将自己融入那片土地,融入那山水之间的爱恨悲喜,所以造成我们今天解读沈从文的误区。世间万象,不可证其伪者,切莫言其真,也切莫言其伪。我认为,“边城”系列是真实的、改换了人物角色的作品。《边城》之中,隐晦的利益线索牵动着人物的命运,这是毋庸置疑的。一座碾坊造成了轩然大波,让所有人除了翠翠乱了手脚。顺顺是为了利益,天保、傩送为了爱情和亲情,老船夫为了翠翠。这合情合理没有丝毫逾矩之处,也是事态发展的必要元素,一步一步推动悲剧在合理的环境下产生不合理的结局。而暴风雨的死亡,则又是作者为了安排一个痛苦的成长,而必须做的情节需要和情理要求:老船夫必须会死,而翠翠一个人必须要成熟面对这个世界,无论这个过程多么辛酸多么痛苦。作者在这里仍然要表明,这样的血泪蜕变犹如文明的进程一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1933年的作者,早已经是数篇名作的发表人和《大公报》的主编,站在这样的高度看这个世界,我们更可以理解作者写作《边城》的时候,所怀有的悲悯情怀和普世价值观。
其次,作者的悲剧感从何而来。我认为没有根据。没有根据的事情,就如我们证伪之学般,不可轻言真伪。作者的悲剧,笔者认为,是一种手段和工具,用了这才能更好地表现作者的主旨。一部作品,必定有它要说的主旨,这个主旨要很多的要素去完成它的表达。沈从文同样如此,边城的主旨是揭示善良、淳朴的人性悲剧,这里的悲剧是为了揭示更为深刻的主旨:“这个民族过去的伟大处和目前的堕落处”。所以,没有哪个作者的写作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小心思小悲情而肆意将作品渲染和安排成悲剧,这是浅薄的揣测。如果作者自己都不能跳出作品,那么这样的作品定不是优秀的作品。沈从文写作《边城》,这部作品绝妙之处就在于它自然流畅又精工安排的悲剧结尾,这样的结尾才能发人深省,才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深刻的阐释作者本人的意图和立意:那就是“高等”文明的“入侵”对于原生态文明的摧残毁坏,这是不可否认的。窥一斑而可知全豹。翠翠最后的悲剧象征着原生态文明对抗“高等”文明的失败,这昭示着所谓的“高等”文明给原生态文明的伤害。这也是作者,出身于这样的原生态文明对于“高等”文明的批判和谴责。在其他的作品中,尤其是像《都市一妇人》、《三三》、《绅士的太太》以及到《八骏图》这类都市题材的小说,作者的意图愈加明显,所要表达的感情愈加明显,作者为自己的心立传的意味也更加明显。这就是作者想要的,揭露所谓的“高等”文明所作下的所隐藏的所滋生的恶欲。作者这里不是要表达自己的悲剧感,而是要表达自己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民生和民族未来的思考:文明应该如何组织来造福人类。
所谓怀旧,是暮年悲歌,是绝处低吟,是枯槁余声。沈从文作品,突出着人的欲望,在作者笔下,以性欲为着笔点,描绘原生态文明的强悍和初始。当然我们也很能理解,这种欲望根植于每个人而不可抗拒。作者描写性欲,不是在赤裸裸的色情描写,而是描写对待性欲的态度。作品《柏子》、《丈夫》,更是深刻的刻画出,作为乡村的他们,对待性欲是原生的需要,而不是罪恶的交易。但是当“高等”文明到来之后,便充斥着淫荡和无耻。柏子花尽用性命换来的金钱与妓女云雨其乐,即便是有一天有所悟了,还脱不离“自在状态”,这是“高等”文明对原生态文明的利用和掠夺,栢子最后成为一个对生命毫无感觉而麻木的行尸走肉;《丈夫》忍辱让妻子卖身,和后来感受到地位低下的痛楚,无一不是在“高等”文明的入侵下,罪恶滋生,民不聊生,丧尽人性卷入恶的洪流。这是作者非常痛惜的,这是反抗是呐喊,而不是怀旧,这没有怀旧的意味,面对这样的悲惨和灾难,作者要表达的不是怀旧而是抗拒,是解救,是寻求新生。他没有政治意思,只是叙述着事件,抒发着悲愤,点出令人心灵颤抖的故事,他的目标是那些历经磨难而又能倔强地生存下去的底层人民的本性和苦难。而道出这些苦难,是为了寻求解脱苦难的方法和关注。因而沈从文的作品,他是以大爱来书写文字,用文字筑就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