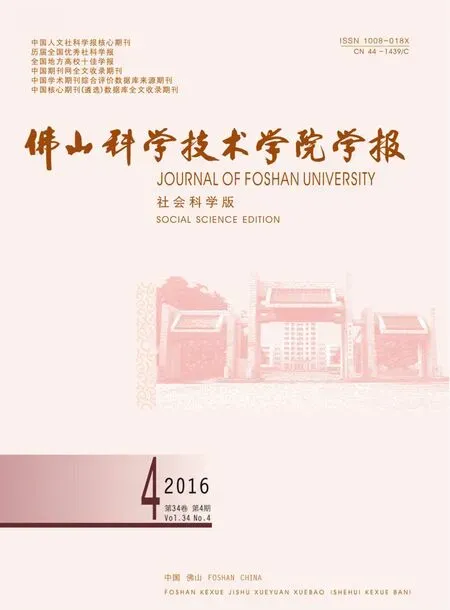《广州音说》音变现象探析
2016-04-17陈卫强蒋尊国
陈卫强,蒋尊国
(1.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院,广东广州510631;2.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广东佛山528000)
《广州音说》音变现象探析
陈卫强1,蒋尊国2
(1.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院,广东广州510631;2.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广东佛山528000)
《广州音说》是陈澧专门讨论广州话语音特点的一篇论文。从陈澧的生平经历可断定《广州音说》所据之“广州方音”正是当时的标准省城音,文章所讨论的语音特征,大致反映了19世纪初期至中期的广州话概貌。《广州音说》是陈澧在考证韵书切语过程中,以广州音为参照,“以隋唐韵书切语核之”,逐渐积累形成对广州音特点的认识而成文的,其成文时间应为《切韵考》之后,大致与《东塾初学编·音学》同期或稍后。通过比较考察《广州音说》所列举“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的五项语音特征,发现广州话存在浊上变去的发展趋势。在共同语的影响下,广州话原读阳上调的浊上字先出现文读音,形成阳去阳上文白两读共存的过渡阶段,然后阳去调文读音逐渐覆盖阳上调白读音,完成浊上变去的变化。
粤方言;广州话;《广州音说》;语音演变
一、《广州音说》所据之“广州方音”和成文时间
陈澧(1810-1882)祖籍江宁,祖父陈善从南京到广州投靠舅舅韩公,其父陈大经虽有文才,却因未入籍广东而无缘科举,延至陈澧一代始入籍番禺。陈澧生于广州城南木排头,幼年入读书塾,后就读于粤秀书院、学海堂等处。陈澧自幼聪敏,9岁时已能够写诗作文。青年时期的陈澧学业优秀,是学海堂的高才生,与卢同柏、桂文耀、杨荣绪被誉为“四俊”。自道光十三年至咸丰二年(1833~1852)陈澧先后六次上京赴进士试,然均未及第。道光二十年(1840年),被聘为“学海堂”学长。陈澧在四十二岁应试失败之后,绝意科举,潜心问学。同治六年(1867年),广东官运使方子箴与中丞蒋香泉,将粤秀山西偏之“长春仙馆”改建为“菊坡精舍”,陈澧被聘任“山长”。陈澧后半生在广州著书立说,培养后学,开创了“东塾学派”。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二日(1882年3月11日),陈澧于广州病逝,享年73岁。除几次上京应试、赴任河源县训导二月余以及两次因战乱避居城郊之外(一次到萝岗,一次到横沙),陈澧足迹基本不离广州城,居住地大致在广州城南木排头附近。[1]陈澧祖父已迁居广州,他自己一生也基本在广州度过,对广州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可以说是地道的广州人,陈澧亦自云“余广州人也”。纵观陈澧的生平经历,可断定陈澧的母语当为广州话,《广州音说》[2]所据之“广州方音”正是陈澧所熟稔的标准省城音,文章所讨论的“广州方音”语音特征,反映了19世纪初期至中期的广州话概貌。
《广州音说》是陈澧专门讨论广州语音特点的一篇论文,不过早在写作《切韵考》[3]时,陈澧就已经注意到广州音的特点了。《切韵考》中列举了一些粤音的例证,如《切韵考外篇卷三·后论》:“疑,吾怡切。疑母之字多误读者,粤音吾字不误,故今用之为切。”“《广韵》切语上字四十类,字母家分并为三十六,有得有失。明微二母当分者也,切语上字不分者乃古音之遗,今音则分别甚明,不必泥古也。粤音则不分,微读如眉,无读如谟,与古音同。”在《东塾初学编·音学》中[4],陈澧更常引粤音为例,如讨论“四声清浊”,强调“读此当用粤音”,讨论“双声”,注明“此一类字粤音皆讹,当以官话而字为定,余皆以而字推之。”又说“第一条即第二条之清,第二条即第一条之浊,后皆仿此,每两条并读之,读此勿用粤音。”列举“明微”母时,特别指出“此二母粤音不能分。”
《广州音说》的一些观点在《切韵考》和《东塾初学编·音学》中也已述及。如谈及的第一项特点“广音平上去入四声各有一清一浊,截然不混,他方之音多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浊”,就见于《切韵考卷二·声类考》:“今人于平声清浊,皆能辨之;上去入声之清浊,则多囿于方音而不能辨。”以及《切韵考卷六·通论》:“上去入之清浊,不能辨者甚多,不独方民为然。”《东塾初学编·音学》中也曾提到,如讨论“四声清浊”时列举了“医怡倚以意异忆翼,腰遥夭鷕要耀约药”等字例,强调“读此当用粤音,他处音但能辨平声清浊,多不能辨上、去、入清浊也。”此外《广州音说》谈及的第五项特点“广音则明微二母不分”在《切韵考》和《东塾初学编·音学》中也已有定论(例见上文)。
陈澧在《广州音说》文末已经明言:“余考古韵书切语有年而知广州方音之善,故特举而论之”,可见《广州音说》是陈澧在考证韵书切语过程中,因时常以广州音为参照,不自觉地“以隋唐韵书切语核之”,逐渐积累形成对广州音特点的认识而成文的。由此我们推测,《广州音说》的成文时间应为《切韵考》之后,大致与《东塾初学编·音学》同期或稍后。
二、《广州音说》述及的音变现象
《广州音说》论述“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的五项语音特征,其中第一、二条讨论声调,第三、四条讨论韵母,第五条讨论声母。
第一,“平上去入四声各有一清一浊,他方之音多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浊……而广音四声皆分清浊,截然不混,其善一也。”列举例字有平声“邕、容”,上声“拥、勇”,去声“雍、用”,入声“郁、育”。广州话今音“邕,於容切jung1(阴平)”、“容,余封切jung4(阳平)”、“拥,於陇切jung2(阴上)”、“勇,余陇切jung5(阳上)”、“雍,於用切jung3(阴去)”、“用,余颂切jung6(阳去)”、“郁,於六切juk7(阴入)”、“育,余六切juk9(阳入)”(音标据《广州话正音字典》[5],下文简称《字典》)。广州话声调有平、上、去、入四类,而且四声阴阳分调正好与古音清浊对应,因此陈澧说“广音四声皆分清浊,截然不混”。“雍”字陈澧作注言明“雍州之雍,於用切”。《广韵》[6]“雍”收平声於容切和去声於用切两个读音,去声注为“‘雍’九州名,於用切。”贾谊《过秦论》“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的“雍州”即九州之一,“雍”为去声。因《广韵》“雍”有两读,故此陈澧在“雍”后加注强调去声。“雍”广州话今音只有阴平一读,《广州话正音字典》只收jung1[翁]平声,未收去声。《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中“雍”也都只收平声。因此若以今音比对《广州音说》所列之“雍”,会觉得此例欠妥。
《广州音说》入声只列“郁、育”两字来说明入声清浊之别,不过陈澧在《东塾初学编·音学》中谈到四声清浊时注明“粤音入声有两清一浊,如必,清;鳖亦清;别,浊”是也。如“忆”即“必”之类,“约”即“鳖”之类也。当知入声亦一清一浊,其歧出者,乃粤音之未善耳。”可见当时广州话阴入调已然两分,如此算来十九世纪广州话已有九调,与今音一致。不过早期的《分韵撮要》把“鳖”归入“必”字头之下,表明“必”、“鳖”同音[7]。《十级大成》采用发圈标记调类,高入声与中入声不分,如“急kapɔ”与“甲kápɔ”为同一调类[8]。据此推测早期广州话阴入调可能尚未分化为上阴入和下阴入两类。
第二,“上声之浊音他方多误读为去声,唯广音不误。”例字有“棒paang5、似tsi5、市si5、恃tsi5、佇tsy5、墅soey5、拒koey5、柱tsy5、倍pui5、殆toi5、怠toi5、旱hon5、践tsin5、抱pou5、妇fu5、舅kau5、敛lim5”等,这些字《广州正音字典》皆标为阳上调。此外陈澧又指出“弟”、“重”二字有上、去之分,“又如孝弟之弟去声,兄弟之弟上声浊音;郑重之重去声,轻重之重上声浊音。他方则兄弟之弟、轻重之重亦皆去声,无所分别,唯广音不混,其善二也。”广州话“重”今音两读,“郑重dzung6”,“轻重tsung5”,与陈澧所举字例相符。“弟”在《广韵》中有徒礼切和特计切两读,陈澧所示读音与《广韵》一致,并附记李登《书文音义便考私编》“弟子之弟上声,孝弟之弟去声;轻重之重上声,郑重之重去声。愚积疑有年,遇四方之人甚夥矣,曾有呼弟重等字为上声者乎?未有也”。案语云:“李登盖未遇广州之人而审其音耳。”说明当时广州话“弟”确有上声和去声两读。反观“弟”今读只有去声,无论“孝弟”或“兄弟”均读为去声。《广州话正音字典》只收dai6[隶],无上声读音。如今广州话未发现“兄弟”之“弟”有上声一读。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粤语文献中[9],我们也未发现“弟”有上声读音,如《分韵撮要》将“弟”列于第二韵“威伟畏”去声,词例为“兄弟”。《粤语速成》[10]收“兄弟⊂hingtai⊇”,《十级大成》收“贤弟⊆intai⊇”、“兄弟⊂hingtai⊇”、“孝弟hau⊃tai⊇”,“弟”皆为阳去调。不过20世纪40年代的《粤音韵汇》[11]“弟”收阳上和阳去两读。罗伟豪(2003)提到旧时书信署名“弟某”之“弟”为阳上调[12]。传统中国农业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生男丁心切,就把希望寄托在女儿名字上,如莫言《丰乳肥臀》上官金童的七个姐姐名为“来弟、招弟、领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老舍《四世同堂》冠家二小姐名“招弟”。今广府地区仍保留这种习俗,如南海九江不少女孩就名为“来弟”、“招弟”。“弟”或换用为“娣”,如“带娣”、“转娣”等,读阳上调。《广韵》“娣”有去声上声两读,《广州话正音字典》“娣”收“tai5”和“dai6”,释“娣,娣姒,娣姒,古代称丈夫的弟妇,古代姐姐称妹妹为娣。”“娣”原义为弟妇,但此义与人名之义不合。笔者推测“带娣”、“转娣”实为“带弟”、“转弟”,因女儿之名故而以“娣”替换“弟”,“娣”应为“弟”上声读音的遗留形式。“弟”的上声读音虽在广州话中找不到确证,但在粤西阳江话、广西粤语和平话中,“弟”仍保留阳上调,粤语如阳江话tɐi4,玉林tai4,北流tɐi6/thɐi4,平话如石埠tɐi4、四塘tɐi4、那毕tɐi6/tɐi4。[13]粤西、广西粤语和平话保留了“弟”更早期的读音,因此陈澧所提及广州话“弟”的上声读音应不容置疑。
第三,“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九韵皆合唇音(上去入仿此)。他方多误读,与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十四韵无别。如侵读若亲,覃谈读若坛,盐读若延,添读若天,咸衔读若闲,严读若妍。广音则此诸韵皆合唇,与真谆诸韵不混,其善三也。”广州话“侵覃谈盐添咸衔”等韵部念为-m韵尾,如“侵tsam1”、“覃谈taam4”、“盐jim4”、“添tim1”、“咸衔haam4”、“严jim4”,与“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等韵的-n韵尾有别,如“亲tsan1”、“坛taan4”、“延jin4”、“天tin1”、“闲haan4”、“妍jin4”,故曰“广音则此诸韵皆合唇,与真谆诸韵不混。”普通话“侵覃谈盐添咸衔”等韵部念为-n韵尾,如“侵=亲qīn”、“覃谈=坛tán”、“盐=延yán”、“添=天tiān”、“咸衔=闲xián”、“严=妍yán”。《中原音韵》仍保留“侵寻”、“监咸”、“廉纤”等闭口韵,而到《等韵图经》时都合并到臻摄、山摄中。正因官话音两者混同,所以“御定《曲谱》于侵覃诸韵之字皆加圈于字旁以识之。”另陈澧提到“广音亦有数字误读者,如凡范梵乏等字亦不合唇,然但数字耳,不似他方字字皆误也。”“凡范梵乏”等字在《中原音韵》已归入“寒山”韵,变为不合唇。广州话也读为-n/-t韵尾,如“凡faan4”、“范faan6”、“法faat8”。《分韵撮要》将其列于二十五韵“翻反泛发”韵,与山摄合口字混同,可证广州话凡韵早在18世纪末期已为-n/-t韵尾。[5]这些字在部分广西粤语中保留了合唇读法,如玉林“犯fɒm”、“范fɒm”、“泛fɒm”,渠旧“犯fam”、“法fap”。平话也是如此,如石埠“犯fam”、“范fam”、“泛fam”、“法fap”。部分客家话也保留合唇-m/-p尾,如梅州“帆fam”、“犯fam”、“法fap”[14],廉江石角“凡fam”、“犯fam”、“法fap”[15]。
第四,“庚耕清青诸韵合口呼之字,他方多误读为东冬韵。如觥读若公,琼读若穷,荣萦荧并读若容,兄读若凶,轰读若烘。广音则皆庚青韵,其善四也。”陈澧所言“他方多误读为东冬韵”的依据应为官话音,普通话今音为:“觥=公gōng、琼=穷qióng、荣=容róng、兄=凶xiōng、轰=烘hōng”,但是“萦荧yíng”读音与“容róng”不同。普通话庚耕清青韵合口常用字读如东冬韵的还有“宏、永、泳、咏”等,此外还有陈澧未提到的登韵合口字“弘”,但仍有如“矿、横、倾、顷、营、颖”等字读音有别于东冬韵。《中原音韵》的登庚耕清青诸韵合口字兼收于东钟韵和庚青韵,表明元代官话这部分字已合并入东钟韵。广州话登庚耕清青韵合口字读音皆与东冬韵有别,如“觥轰gwang1、琼king4、荣wing4、兄hing1、弘宏wang4、永wing5”等字韵母为ing或ang,而东冬韵韵母为ung。
第五,“《广韵》每卷后有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如眉武悲切改为目悲切,绵武延切改为名延切,此因字母有明微二母之不同,而陆法言《切韵》孙愐《唐韵》则不分,故改之耳。……广音则明微二母不分,武悲正切眉字,武延正切绵字,此直超越乎唐季宋代之音,而上合乎《切韵》《唐韵》,其善五也。”广州话明母与微母均读为m声母,如“暮=雾mou6”、“美=尾mei5”、“慢=万man6”,故而陈澧说“广音则明微二母不分”。陈澧在《东塾初学编·音学》中已谈到“微母北人音与喻母合口无别,读微如围,南人音……或与明母无别,读微如眉”。普通话明母字读为m声母,微母字读为w声母,“微围”皆读为wéi,与“眉méi”相异,而广州话“微眉”皆读为“mei4”,读音无别。广州话“武mou5”、“眉mei4”、“绵min4”均为m声母,因此“武悲正切眉字,武延正切绵字”。关于明微二母的分立,陈澧在《切韵考·外篇》卷三说“广韵切语上字四十类,字母家分并为三十六,有得有失。明微二母当分者也,切语上字不分者乃古音之遗,今音则分别甚明,不必泥古也。”“三十六母者,唐末之音也。”《守温韵学残卷》所列三十字母唇音只有“不芳並明”,后人增益了“非敷奉微”。既然唐末三十六字母已有明微之别,那么《广韵》当然需要新添类隔更改切语。麦耘(2009)指出“在北宋施护(?-1017)的梵汉对音中,以微母字对梵文v,所译汉语音应已变为唇齿近音v[16]。”表明宋代明母为m声母,微母大致为v声母。由此可见,广州话明微不分的特点已超越《广韵》时的唐末宋代音,直可上溯至《切韵》《唐韵》时代的隋唐音。
《广州音说》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专门讨论广州话语音系统特点的论著,因为陈澧“考古韵书切语有年而知广州方音之善”,所以文中所列明微不分、咸深摄保留闭口韵、声调依清浊两分等几项音论可谓切中要害,深入揭示了广州话语音系统中声母、韵母和声调极具代表性的特点,至今在讨论广州话甚至粤语音系时这几项特点都不可或缺。
三、广州话浊上变去的趋势
通过对比考察,一百多年前《广州音说》所谈及“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的五项语音特征,至今大体没有发生变化。至于“上声之浊音”一项,《广州音说》所列举上声字多为全浊字,次浊字只有“敛”,加上第一项所列上声“勇”亦为次浊字。陈澧并未全面考察《广韵》上声常用字的读音,由此断言上声之浊音“惟广音不误”,“广音四声皆分清浊,截然不混”似乎过于草率。据十八、十九世纪的文献,《分韵撮要》不少常用浊上字归入去声,如“是、被、父、户、善、淡”等。《十级大成》把“部pò≥”、“在tsoi≥”、“近kɑn≥”等浊上字标为阳去调。从广州话今读分析,古浊上字存在分化,次浊字大多读阳上,而全浊字两分,部分读阳上,部分读阳去。考察全浊上声常用字,今读为阳上调的有“社、肚、绪、距、拒、柱、倍、被(棉被)、徛、似、柿、市、恃、抱、厚、妇、舅、旱、践、盾、愤、上(上山)、强(勉强)、棒、蚌、艇”等,今读为阳去调和阳上调的有“伴bun6/pun5”、“坐dzo6/tso5”、“淡daam6/taam5”、“近gan6/kan5”、“断dyn6/tyn5”、“重dzung6/tsung5”等。此外“肾”《广州话正音字典》只收san6去声,然口语“鸡肾”、“肾球”仍读阳上调san5,《广州方言词典》因此两读均收[17]。其余全浊上字皆读为阳去调。罗伟豪(1997)曾对《广韵》全浊上字进行统计,有约1/3全浊上字读阳上调,约2/3全浊上字读阳去调[18]。可见陈澧说“上声之浊音他方多误读为去声,惟广音不误”并不准确。值得注意的是,广州话两读并存的浊上字分层清晰,阳去调为文读层,阳上调为白读层。《广州音说》所举的常用字“弟”本有阳去调和阳上调文白二读,但今天阳上调白读音已经消失,这应是“浊上变去”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再如在19世纪前期、中期广州话文献中,处所动词常用“在”[19],如《十级大成》:“你在个处办乜野事呢”,“在”标为阳去调,应属文读音。《字典》只收dzoi6去声。如今广州话处所动词只用“喺”,读阴上调。广州地区的增城和从化方言处所动词仍用“在”,如“在屋”,增城念为ts‘oi5阳上调[20],从化念为ts‘oi5阳上调,均为白读音。通常乡下方言的演变较市区要慢些,由此推断广州话原处所动词“在”也曾经历阳去调和阳上调文白读二音共存的阶段。“弟”和“在”阳上调白读音被阳去调文读音取代反映出19世纪至今广州话浊上变去的趋势。变化过程应是原读阳上调的浊上字先出现文读音,形成阳去阳上文白两读共存的过渡阶段,然后阳上调白读音逐渐消失,只剩下阳去调文读音。今天仍可观察到这种变化,譬如“墅、殆、怠、骇”等字在《广州话正音字典》中注为阳上调,读作“墅soey5”、“殆toi5”、“怠toi5”、“骇hoi5”,但不少人以普通话的去声读音类推而将其念为阳去调,如“别墅soey6”、“殆尽doi6”、“懈怠doi6”、“惊骇hoi6”,由此这些字就产生了阳去调和阳上调两读。受普通话强势读音的影响,阳去调文读音逐渐覆盖阳上调白读音,如今大多数人已把“别墅”的“墅”念作阳去调,从而完成浊上变去的演变过程。正因如此,今天“弟”、“在”只剩下阳去调文读音,再也难觅阳上调白读音的痕迹。相较之下,一些并无普通话对应读音的口语字反而保存了阳上调读音,例如《广韵》:“盪,徒朗切,涤盪,摇动貌,说文曰:涤器也。”《广州方言词典》收“盪thɔŋ23”,念阳上调,意为“晃动”、“涮洗”。而同一音韵地位的“荡”则读为阳去调dong6,《广韵》同音的“盪”和“荡”在广州话中出现了分化。“浊上变去”是汉语常见的变化规律,林焘、耿振生(2004)指出,官话全浊上声变为去声在唐代已然发生,如白居易《自咏》之二上声“墅”与去声“树、处、去”押韵。又如敦煌出土文献《时要字样》“动”“洞”同音,“荡”“砀”同音,“舅”“旧”同音[21]。粤语自形成以来就一直受到中原汉语的影响,今广州话浊上字读去声应有中原汉语早期的覆盖层次,体现了与共同语一致的演变趋势。而粤语在南汉时期定型之后,北方官话及今天的普通话对广州话的“浊上变去”仍发生持续的辐射影响。
*本文曾在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2015年会(华南理工大学)上宣读,感谢黄高飞博士赐教并提供阳江话资料,谨此致谢!
[1]李绪柏.清代岭南大儒陈澧[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2]陈澧.东塾集·广州音说[M].广州:羊城西湖街刊印, 1892.
[3]陈澧,罗伟豪.切韵考[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4]罗伟豪.评陈澧《东塾初学编·音学》[J].中山大学学报, 2004(4):82-87.
[5]詹伯慧.广州话正音字典[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6]陈彭年.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7]佚名.新辑写信必读分韵撮要合璧[M].香港:陈湘记书局,1915.
[8]卫三畏(WELLS Williams).十级大成(EASY LESSONS INCHINESE)[M].澳门:香山书院,1842.
[9]张洪年.早期粤语口语文献资料库[EB/OL].[2016-02-20].http://pvs0001.ust.hk/Candbase/.
[10]DYER Ball.Cantonese Made Easy[M].3rd edition. Singapore,Hongkong,Shanghai:Kelly&Walsh Limited, 1907.
[11]黄锡凌.粤音韵汇[M].香港:中华书局,1941.
[12]罗伟豪.重读陈澧《广州音说》[C]//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99-205.
[13]陈海伦,林亦.粤语平话土话方音字汇[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14]李荣,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15]李如龙.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16]麦耘.从粤语的产生和发展看汉语方言形成的模式[J].方言,2009(3):219-232.
[17]李荣,白宛如.广州方言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18]罗伟豪.中古全浊上声与现今广州话声调[C]//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7:23-27.
[19]余霭芹.粤语方言的历史研究——读《麦仕治广州俗话书经解义》[J].中国语文,2000(6):497-507.
[20]何伟棠.广东增城方言同音字汇[J].方言,1990(4): 270-283.
[21]林焘,耿振生.音韵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Analysis on Phonetic Evolution Phenomena ofGuangzhou Yinshuo
CHENWei-qiang,JIANGZun-guo
(1.School ofUrban Culture,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 2.President’s Office,Foshan University,Foshan 528000,China)
Guangzhou Yinshuo is the paper devoted to discuss Cantonese pronunciation characteristics.From Chenli’s life experience we can concluded that the dialect at that time i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Cantonese. Its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roughly reflect the general Cantonese feature in the early to mid-19th century.The written time of Guangzhou Yinshuo should be after Qieyun Kao,probably at the same time of Dongshu Chuxue Bian Yinxue or later.Compared with the five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described in the book,it shows that the Cantonese pronunciation characteristics basically remained unchanged since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ago, but that Cantonese tone development trends of Zhuo Shang turning into Qu.
Yue dialect;Cantonese;Guangzhou Yinshuo;phonetic evolution
H178
A
1008-018X(2016)04-0073-06
2016-04-20
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两广粤客杂处地区方言接触层级特征研究”(15BYY040);2014年度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资助专项“18世纪以来广州方言历史演变研究”(2014GZY14)
陈卫强(1974-),男,广东广州人,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蒋尊国(1982-),男,湖南永州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