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珍珠不但发光,说的还是德语
2016-04-14卢盛舟
卢盛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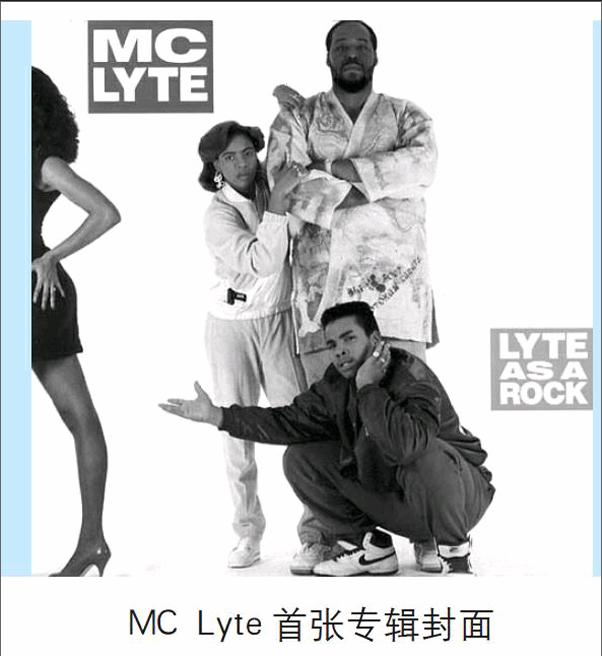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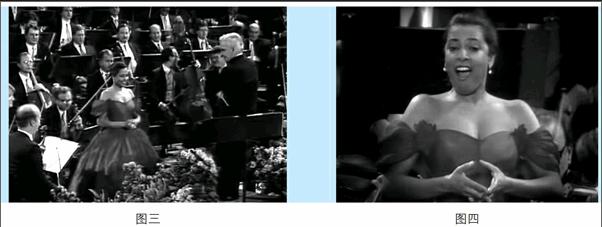
刚入职时,我的一个业余乐趣是每天寻找一个比喻,用来形容散发着职业生涯早期独有的谦逊和才华的年轻人。搜索范围限定在古典音乐界。比如:某某就像一九五五年的古尔德,就像千禧年前的郎朗……最近,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喻体—黑人花腔女高音凯瑟琳·芭特尔(Kathleen Battle),她在一九八七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完美演绎了小施特劳斯的名作《春之声》(Frühlingsstimmen, op. 410)。当时,她已经三十九岁了。但对我们人类来说,年轻可是个弹性概念!申请科研项目时,四十岁以下都算青年教师呢。而且,对于那一年的新年音乐会来说,她和卡拉扬都算是彻头彻尾的新人。一九八七年起,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不再设固定指挥,他们请来了卡拉扬。卡拉扬时值七十九岁,离去世时日无多。卡拉扬带来了凯瑟琳,使她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登上金色大厅舞台的歌唱家。两年后,小克莱伯在指挥新年音乐会时也选择了《春之声》,但他没有安排人声演绎。一种较为浪漫的说法是因为余音环绕。
芭特尔的声音甜美,如同迪士尼游乐园。我中意她对声音强弱的自如收放。她的自信不仅来源于声音,还来源于她的肢体语言和着装打扮,这些都是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感谢当时电视的普及,使我们得以欣赏到耳朵捕捉不到的东西;而如今网络的发达,让你可以坐在家里的沙发或高背转椅上,通过反复观看视频,发现一些秘密。把它想象成是教练观看下一个对手的录像,整件事将会充满快意。还因为有些东西,即便你在现场,即便你买了第一排的票,你也未必能看出。
我的观点是,欣赏这段表演的一个关键在于,解读当中的镜头语言和肢体语言,你会发现一场性别大战,一场人机大战。
首先是卡拉扬。他对自身形象和技术影像都很着迷。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他和法国电影导演克鲁佐(Henri-Georges Clouzot)合作过多次,其中最著名的影片当属卡拉扬执棒柏林爱乐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克鲁佐将总谱转译成剧本,把音乐家变成演员,再用剪辑的句法搭配音乐的节奏,但在合作中,卡拉扬没少跟克鲁佐发生争执,因为他很在意自己在镜头中的形象,最后两人不欢而散,分道扬镳。我们看到《春之声》引子加第一主题的演奏中,有二十四个小节,镜头悉数给了卡拉扬,当然是以仰拍的方式。同时,一把小提琴被带入到画面中,占据了摄像机前方这个重要位置,它构成了卡拉扬的权力和威望的投射平面(图一)。在所有中景镜头中,虽然芭特尔有时处于中央位置,但卡拉扬无一例外地比芭特尔高出一头,其中有一个镜头拍摄芭特尔和卡拉扬的侧面,芭特尔完全处于画面底部,肩膀仿佛被淹没一般,卡拉扬则高高在上。这个镜头长达半分钟之多,充分体现了指挥和歌唱家的从属关系(图二)。
再看芭特尔。她身着一袭红色高腰宽裙登台。这个选择很成功,因为红色使她在画面中成为了最明亮的人物。裙子是落肩领,让双肩完全露出。在这样的场合下,大面积的裸露是自信而非情色的暗示,它衬托的不是胸部,而是一颗大心脏。她的肤色并不太深,透着镍镀般的光泽。她向后梳着一头直发—那可是蓝调女皇贝西·史密斯(Bessie Smith)的标示性发型—从容地露出牙齿,微笑,先向正面的观众点头,欠身,然后转向右侧,再转向左侧示意,向左的转幅明显比向右的幅度大,因为卡拉扬站在她的左侧,她这么做是为了表示对恺撒的尊敬。卡拉扬的姿势也很值得玩味: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芭特尔,双臂收起,指挥棒就藏在腋下(图三)。此处,我们不宜走得太远,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把这指挥棒视为什么男权的隐喻,因为那东西,他还得挥动一整晚呢。
注意她的手势啊! 她一上来用左手托住右手,并握住,这种手势算不上强硬的手势,相反,它有时会被解读为矜持、柔弱的象征,但她右手无名指上佩戴的硕大钻戒冲淡了这种可能性,反射出自信的锋芒。我很欣赏的另一点是,她在乐团序奏的时候,一丝不动,目不转睛地望着远处,如同望着诗和远方,这个姿势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她对歌唱的渴望。开始唱第一主题后,她的身体和手依然保持原有姿势,这和她声音在音高上的跳动达成了迷人的张力。随着歌曲的进行,她多了些手势,但始终保持少量,身体摆动的幅度也不大,显得干净、沉稳。恕我冒犯,但如果你去看娜塔莉·德塞(Natalie Dessay)一九九三年在维也纳歌剧院首演时唱《春之声》的视频,你会觉得她抖得像个DJ。主题反复时,她得到了第一个特写镜头,我们看到她的面部表情自然比刚才要丰富、立体。进入第三主题后,在处理几个高音时,她露出了一种“蓝调表情”。在唱完高音后,她会以一种近似切分的节奏,做各不相同的表情,它们似对那些高音的回应,如同蓝调里的回应乐句。我在黑人蓝调歌手鲁斯·布朗(Ruth Brown)的表演里看到过这种老辣的表情切换。所谓“蓝调表情”,就是如此。之后,镜头捕捉到卡拉扬露出满意的微笑。在等待第一主题再现时,她嘴角上扬,露出俏皮而自信的微笑,左手食指同时指向她的钻戒。在唱歌曲最后一个高音颤音时,她第一次做出了尖塔手势—双手指尖交叉形成了一个尖塔,一直伴随最后一个音结束(图四)。塔尖手势是所谓的权力手势,用来在关键时刻表现自己的影响力。《黑道家族》里的黑帮头子训斥手下的时候,就使用这个手势。紧接着,她下巴扬起,画面淡出,切换到全景镜头,卡拉扬高她一等的权力关系被及时暗示。我们可以看见她并没有立刻转向卡拉扬,而是面向观众数秒,接受观众的掌声,然后才转向卡拉扬,让卡拉扬亲吻她的手背。注意,在这个环节中,手背没有必要主动抬高,大师为了显示绅士风度,自会屈尊俯就。我很欣赏她在此时此刻没有缄默,而是和大师沟通了几句。你不能表演一结束就像个不会说话的洋娃娃。等到她再次面向观众,接受雷鸣般的掌声时,她又将大拇指指向了钻戒。这个指向钻戒的动作有如整个表演的一个主题动机句。还有,在接过别人送上台的鲜花后,她始终温顺而感激地望着卡拉扬,尽职尽责地正对着他,而不是观众。这是“肚脐法则”的完美运用—肚脐的朝向角度能表现你对一个人的兴趣、忠诚和尊重程度。
芭特尔为她的才华和谦逊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这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别说这是过度解读。台上的许多东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凡是上过台的人都知道,即便最成功的演出,下了台后,你也时常会为刚才忘了在台下操练了无数遍的台词、动作和表情而懊恼。是这样吗?注意,芭特尔穿的裙子和鲁斯·布朗一九五五年在电视上唱《(妈妈)他对你女儿很差劲》(Mama He Treats Your Daughter Mean)穿的是同款。这件裙子应该是她自带的,因为后来我发现她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唱施特劳斯小夜曲的视频里穿的也是这条。还有,她唱过《夏日时光》(Summertime),和另外一个黑人女高音杰西·诺曼(Jessye Norman)录过一张灵歌专辑,由德意志留声机公司发行。是的,她跨界于古典乐和黑人音乐文化之间,在玩白人的东西时,她散发出一股摇摆韵味。
一九八七年的新年音乐会,芭特尔就像一个出现在父系社会中的女性访客。她后面坐的肯定是清一色的白人男性,因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直到一九九七年都没有招过任何一名女性演奏家,而我喜欢看她面对这种场面时所呈现的智慧和自信。同表演风格一样,从摇滚、蓝调,再到古典乐和说唱,黑人的自信也一脉相承。一九八七年,大放异彩的黑人女歌手还有MC Lyte,她录制了个人首张专辑,证明说唱并不是只有男人才能玩。非裔美国人的自信并非天生,它是美国百年来种族政策的产物。在《嘻哈美国》中,尼尔森·乔治不无挑衅地说:
在欧洲文学的尊贵传统里,不少死掉的白人作家(如但丁、弥尔顿)在作品里,都将骄傲列为七大罪之一。根据但丁《神曲》的炼狱篇,撒旦因骄傲被逐出天堂,这个堕落天使遂创造了地狱。或许对死去的白人来说,骄傲是件坏事。但是对仍活着、仍呼吸的黑人,骄傲自大至关重要。在一个人们长久以来厌恶鄙视黑人,将其妖魔化、堕落化的国度里,嚣张的傲慢往往是生存之道。
芭特尔为什么会受到卡拉扬邀请,成为第一位登上金色大厅舞台的歌唱家?这个问题似乎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在一九八五年,他俩曾合作过莫扎特的《安魂曲》。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古典音乐界几乎很少出现黑人钢琴家的身影呢?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按照回答另一个相似问题的思路来:为什么国际游泳赛场上很少出现黑人运动员?因为生理上,黑人骨质密度小,所以浮力小,速度就受到了影响;再者就是社会原因:贫穷,而游泳是一项投资成本不低的运动。
再说说芭特尔的德语发音吧。要唱德奥声乐歌曲,练习德语语音显然是必修功课。芭特尔的发音不错,能顺利发出小舌音—要模仿美国人说德语的刻板印象,一个诀窍就是把小舌音发成卷舌音。相比之下,卡拉扬说起德语来一点也不优雅,他说的德语不带奥地利德语的口音,或许因为很早就前往德国打拼的缘故。声带是人生的第一件乐器,但卡拉扬似乎无法胜任对它的指挥。他说德语时,一般风格急促,分句之间没有足够的呼吸,线条硬涩,还混着轻微的痰音,完全没有自己在音乐上追求的经过打磨、抛光的圆润音色,也远远没有他的对手伯恩斯坦说英语来得优雅。
德语和黑人女性很少也很难被联系在一起,这部分是因为德国很晚才加入西方国家掠夺非洲殖民地的罪恶行列中。我能想起来另一位和德语沾边的黑人女性,她出现在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被解放的姜戈》里,叫布鲁姆希尔达(Broomhilda)。昆汀在这部电影里设置了一个“会说德语能保命”的情节。本来被关进死屋的她因为会说德语,被安排和舒尔茨医生见面,去讨这个德国客人的欢心。她的德语说得不错,上来就用了一个礼貌的虚拟式:Es w?re ein Vergnügen, mit Dir auf Deutsch zu sprechen(很高兴能和你用德语交谈)。但按照德语的语用习惯,和陌生人第一次见面交谈,她更应该使用“您”,而不是“你”。我们看到,镜头转到两人私下交谈时,德语为母语的舒尔茨医生使用的便是尊称—“我能给您倒杯水吗?” 但他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不应该用小姐(Fr?ulein)这个称呼,因为(Fr?ulein)指的是未婚女子,而布鲁姆希尔达是有丈夫的,她的丈夫就是电影标题中的姜戈。
布鲁姆希尔达这个角色的前任奴隶主是德国人,所以被起了这么一个德国名字,它听上去像在影射瓦格纳歌剧里的女武神布伦希尔德(Brunhild)。但《被解放的姜戈》所设定的时代背景是一八五八年冬到一八五九年春,而瓦格纳的歌剧首演要到一八七六年,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名字听上去像在影射《尼伯龙根之歌》里的女王布伦希尔德。有意思的是,“Broom”在英语中指的是“扫帚”,毋庸置疑,它和一个奴隶的社会地位暗合。昆汀通过这个从u到o的元音变化,成功讽刺了那个时代—它过去了吗?—资产阶级白人男性的文化优越感,和由此产生的道德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