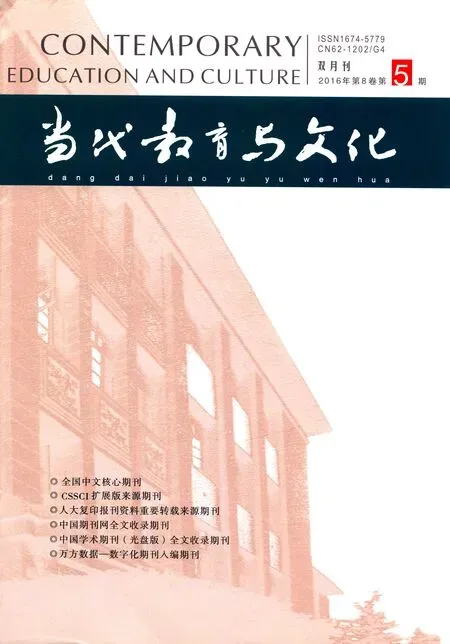论自我教育的文化历史意蕴
2016-04-14韩永红
韩永红
(广东肇庆学院教育学院,广东肇庆 526061)
论自我教育的文化历史意蕴
韩永红
(广东肇庆学院教育学院,广东肇庆526061)
人类文化的传承有两种方式: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从辩证法的角度,只有自我教育才是文化传承的内在根据和内在动力。所谓文化传承就是通过自我教育模式孵化出了一大批掌握了“文化力”的新的自我,正是他们使得一种文化事象、文化实体、文化氛围得以保存、延续、创造。纷繁复杂的中西方文化传承莫不如此,最终还是要通过一个个自我的适应、改变、改造环境中的自我塑造、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等一系列的自我教育活动表现出来。
自我教育;文化传承;历史沿革;文化意蕴
马克思认为,人类在其长期的历史进化中,一直在他们想方设法的智慧里,去逃出自然界,这种智慧就是文化。也因此,对文化的传承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部内涵。一般讲,人类对文化的传承有两种方式: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两者共同构成了人类教育的全部。从辩证法的角度,他人教育只是文化传承的外部条件和影响,只有自我教育才是文化传承的内在根据和内在动力。正基于此,笔者提纲挈领地爬梳了自我教育在人类文化传承中的历史流变和人文意蕴。
一、自我教育与文化传承
苏格拉底强调,引导着文化生成、发展、完善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人自己最本质的力量——自我。[1]因此文化不是抽象的,它就是通过人类社会中,无数个体身上迥异的“自我”特征诸如欲望、目的、思想、情感等反映出来的,再以群体方式凝集出的人类社会运行的政治、经济、伦理和宗教等,反过来,也正是人的欲望、目的、思想、情感的积累、提炼、升华创生着人类社会运行的政治、经济、伦理和宗教,从而体现和推动着文化的传承。那么个体把自我作为对象所进行的自我教育,从根本上就是,围绕着人的欲望、目的、思想、情感所展开的“自我”对“自我”最直接的塑造、建构和完善,在本质过程上,它和文化的传承是完全一致的,既所谓人的“自思”的存在就是他的文化本质,也是社会的文化本质。
这样,所谓的文化传承正如弗罗姆指出的,应该是“一批具有新的自我的新人的诞生,而不是一堆外在的文化事象的堆积和文化实体结构的堆积。”[2]这一过程是在一定生存意识的强力推动下,每个自我在自己当下独有的社会时空性存在中,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最直接的肉体接触开始的,汤因比把“最直接的肉体接触”看作是那些宏大的政治、经济、伦理和宗教等文化符号产生最肥沃的土壤。在其中每个自我初步起始了自己生命存在的某种价值感和意义感,具有了对改变自身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意识,之后在这个基础上,按照更适当、更确切的自我标准,对自己持续地进行自我教化,形成了某种人格规定和人格形象,及相应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接着逐步构筑出了新的自我的精神世界——符号意义系统、经验观念系统、情意价值系统、行动规则系统等,直至最后演化出了新的自我的人生愿景、世界图景和价值理想。每个人意识领域的这种变动,被称为“自我的嬗变”,其内含着一系列被弗罗姆称之为“社会孕化”的过程,包括“自我教化”、“ 自我默化”、“ 自我濡化”和“自我涵化”,这些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自我教育模式孵化出了一大批掌握了“文化力”的新的自我的新人,正是他们使得一种文化事象、文化实体、文化氛围得以保存、延续、创造,应该说这就是文化传承的一般过程,因此人类历史与其说是一部文化史,不如说更象是一部自我教育史,正如斯宾塞说的,人类所有文化都是“人类整体”自我教育的结果,在人类整体之外并没有第二者介入,也因此作为人类整体一部分的一个个个体要获得文化,也必定是自我教育的结果,中西方文化莫不如此。
二、自我教育在西方文化传承中的历史意蕴
(一)自我教育在西方古代文化中的传承
对所有存在中的存在者的主动追求和自我感知,这样一种自发的、最质朴的自我教育形态催生出了历史正溯的西方文化的起点-“爱智慧”和“哲学”,表现了古希腊罗马人对大自然内在客观规律的某种认识渴望,正是在这种主动探索中诞生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的核心——“理性文化”,而要找到大自然中蕴含的真正理性、正义和智慧,苏格拉底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自我发现,而西塞罗则认为,一切普遍性真知灼见都在你自己的观察中。之后随着柏拉图“绝对理性”的生成,古希腊罗马理性文化趋于成熟,围绕“绝对理性”的各种“柏拉图主义”的变式,控制着西方上千年的文化历程。
进入中世纪(公元5世纪—15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的世界。在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精心设计、变革和重构下,古希腊罗马理性文化与基督教发生了融合,出现了“神权文化”。前苏联学者科恩认为,正是这种文化第一次使个体清楚地有了“自我(self)-人格(personality)”这样的心理世界。[3]按照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一个人的“自我-人格”要想获得现世的安康和幸福,就必须通过“去欲、抑欲、移欲”的自我认识方法与“神”不断沟通,以达到对内在“自我-人格”的理性认知,这就是中世纪教会隐修制度。于是在教会人士的带动下,整个社会展开了自我观察、自我比较和自我评价等一系列的自我教育运动,它非常类似于现代心理学的自我分析。再之后就是将这种自我分析诉诸文字,产生了中世纪关于修士的大量自传、回忆录、书信集和其它个人文献集,从而人类第一次将围绕着自我的知、情、意的人格因素以宗教的面目进入到了西方文化的审美传统中,也因此中世纪传承“神权文化”的自我教育是属于“神”的,只有到了文艺复兴,自我教育才开始属于“人”。
中世纪人们问的是“我是谁”,文艺复兴(公元14-16世纪)问的是“我是什么”。 这种追问体现出人们“自我”心理世界私人化的快速增长,先是身体的私人化,之后是社会空间的私人化,最为重要的是时间的私人化,也即“个人时间”开始出现,个人存在的有限性开始为人们深刻意识到,并从而意识到个人应该在其有限的一生时间内,表现出“自我”的独有存在,这样凸显着“自我欲求”层次的文化境界——“个性文化”就产生在文艺复兴。人们在这种文化中初步获得了属于“自我”私人化的自主性,那么这个“自主”是用来干什么的?用涂尔干的话说,“自主”是用来“发展”的,“发展”这一概念就始创于文艺复兴。怎么发展呢?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拉伯雷指出,把“自我”中的需要、欲望、冲动都表现出来吧,用什么表现呢?用“知识”。[4]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号召人们遣用自己所有的身心功能去学习“自然的一切知识,一切的自然知识”,这是通往幸福的必经之途。那么这些知识从哪学呢?当时的学校(以“七艺”为主)绝不可能教,同时期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认定只有从自我教育中来。他认为,每个人只有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实实在在的自我教育,才能在百科全书式的人类知识中获得解放,获得尊严和价值,进而他第一次提出了自我教育的概念,即是指个人主动地去求知任何一个他尚未探究的领域,直到全面探究人类学说整个领域的活动。[4]
文艺复兴发现了真正的自我,同时也发现通过那个时代的“自我教育”要实现这个自我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只有到了近现代,随着科学的成型、成熟,真正自我的实现才越来越具有可能性。
(二) 自我教育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的传承
一般认为西方文化由三大因素构成:一是古希腊精神,二是基督教,三是科学。前两者是第三者成型成熟的催化剂。众所周知,近代科学(公元16世纪—18世纪)的成型、成熟是一批业余科学家诸如法国的笛卡儿、帕斯卡,英国的波义耳,荷兰的斯蒂文、列文虎克等自学的结果。洛克说,他们使用了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自我内省”法,即一种“安静地、不断地注视着自己心灵与自然碰撞的活动”,[5]在这种活动中,人的各种心理因素——知觉、表象、想象、记忆、思维等不断地融合交错、排列组合,其结果就是不断被提炼出假设、推论、演绎直到归纳等科学思维方式,整个这些过程被英国学者亚力山大·贝恩(Alisaunder·Bein)称为“人类的联想”,也因此,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传承就是由这种联想式自我教育完成的。可以认为,这种自我教育与科学规律之间存在着融通一体的本质关系。因为什么是科学规律?在物理学上,从牛顿力学到能量守恒与转换,无不渗透着“自维持、自平衡、自守恒”的法则;在化学上,从燃素说到元素周期律,无不渗透着“自排列、自构建、自转换”的法则;在生物学上,从血液循环到遗传理论,无不渗透着“自循环、自演化、自繁殖”的法则。因此所谓科学规律就是无不渗透着这样一些自我完善、自我塑造、自我建构法则的宇宙中的秩序。那么在人和科学规律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是一体的——人本身也是一个无不渗透着自我完善、自我塑造、自我建构的机体,那么掌握科学,就是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按照科学中蕴含的自我完善、自我塑造、自我建构的法则办事,也就是人的自我挖掘、自我提升和自我开发的过程,也就是自我教育的过程,正基于此,斯宾塞得出结论,“人类完全是从自我教育中取得进步的”。[6]
近代科学文化初步完成了科学知识之上的社会成型,而现代(公元19世纪—20世纪中叶)在此基础上完成着社会变革的无限发展,即制度乃至心智的社会成型,创建一种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现代人”是其最终目的,它折射出了文艺复兴的“自主性”,逐步地被锻造成了现代文化中人的“主体性”,因此现代文化也被称为“主体文化”。 杜威强调,现代社会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他必须对自身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环境进行主动地、独立地自我观察、自我设问、自我推理,以获得真理性的环境经验,去袪除不安和疑虑,杜威称之为主体性“反省思维”。它具有明显的扩张性、生长性与相关性,它会反过来推动个体产生更多、更高水准的反省思维,以更加主动地适应更高层次的生活环境,去袪除更多、更复杂的不安和疑虑,达到更多、更高水平的生活环境的稳定与和谐。就这样,从无数小的生活环境的反省思维达到稳定与和谐,到更多、更大的生活环境的反省思维达到稳定与和谐,直到国家、民族的反省思维达到稳定与和谐,这种主体式的自我教育就为“主体文化”所追求的那种“现代人”的塑造提供了最充实的原动力。
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主体文化”必然导致“异化”,现代心理学用三个分裂界定了“异化”, 个人的分裂、自我的分裂、人格的分裂,因此荣格说,现代人丢掉了灵魂,当代人在寻找灵魂。寻找的结果就是认为那种统一的、稳定的、客观的自我是个“科学的迷误”,是不正常的、不幸的,而多重的、多元的、善变的自我才是正常的、真实的、当代社会所追求的。这一转变逐步地抽去了,现代“主体文化”赖以立世的理性主义、基础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代之以非理性主义、反基础主义和多元主义,正是后者,生成了基于西方当代(20世纪中叶以后至今)知识经济之上的,对现代“主体文化”批判和反思的产物——后现代文化。
应该说,从尼采的角度,后现代文化是“上帝死了”的产物。之后深藏在人心理最底层的人性成分——想象力、潜能、冲动等等以“知识”的面貌被源源不断地挖掘出来,人类的类内实践不仅第一次超过了类外实践,而且引导、提携着类外实践的历史进程,标识着人类自我每开发一小步,就能拉动客观世界前进一大步的时代到来了。也因此我们不得不说,人类的自我挑战,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变为了改造客观世界的前提。然而尼采对此忧心忡忡,他说这必然导致人性到处游离、无所归宿,更糟糕的是人类文化必然会异常贫瘠,社会将变成让人们精神官能退化的禁闭室,那么如何克服这贫瘠呢?尼采的答案是:每个人都应该爆发出强烈的“想要的意欲力”,学会自我教育。[7]以使自己的想象力、潜能、冲动从流俗的道德和认识中跳出,去活出自己殊异的模态——个人化,并更进而获得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能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个人化自我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终身学习”的理念向全球进行了推广,接下来30年,各种自我教育模式如春笋般涌现,如自导学习、自主学习、自我教学、自律学习、自我管理学习等等,它们蔚然成风已经创筑出了学习型社会的现实体系,同时围绕自我教育形成了一系列学习型组织机构——学习型企业、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城市,更有甚者,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在酝酿《终身教育法》《终身学习法》和《自我教育法》,力图把个人的一种学习活动演变为一种组织化、制度化、目的化、有序化的自我教育事业。
然而福柯却认为,这只是权力变通下对人的又一种牧养,他提出的疑问是每个个体把自己的潜能挖掘出来后就能得到心灵的宁静和人生的归宿吗?[8]
福柯尖锐地指出,当代社会的迷惘昭示着马克思所呼吁的“改造世界”并没能实现,到头来还必须配合自我的深刻改变,但是那种规则取向的自我教育没有吸引力了,必须代之以个人生活化的自我教育,即像精致地雕刻艺术品一样来雕刻自我生活的活动,福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这种“自我技艺学”不仅包括传统的学习生活、学习阅读、还要学习死亡,甚至包括对人外貌的操纵,从各种装饰到美容整型等,都是这种自我教育的范围所指。福柯把他的自我技艺学称为“存在美学”,通过这些生活化自我审美价值的改变,现代人只是尝试着超越性地在后现代文化中找到一种心灵安逸的生存状态而已。
三、自我教育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历史意蕴
(一)自我教育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传承
“天道”文化是先秦文化(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的核心,诸子文化是先秦文化的中坚。在春秋动乱时代,先秦诸子始终在“谈论道”中探索着自我的全身远害之道,而“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今天所谓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之意,道之外别无他物,用老子的语言来说就是“自因”,就是“自身运行”,也就是自我教育。由此,围绕“自强不息、日新日进”的自我教育模式,成为了诸子的文化性格,孔孟老庄都是这种文化性格的典范,尤其是孟子系统地阐释了自我教育的要义、原则和途径。通过这些自强不息的自我教育,诸子的人生目标就是“涣其群”,彰显着个体思维向社会思维飞跃中“以我观物”的思维主体的执着性,使万物皆着我之色彩,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那种洋溢着主体乐感体验的,靠突然领悟和直观把握,凭感觉直接把握事物底奥的直觉智慧——直觉式自我教育。
应该认为,儒家文化从它诞生起,始终彰显以一种自我理念形态显世的,关涉人生发展的人文精神。然而从两汉到唐末宋初在直觉式自我教育推动下,其贯穿着一系列围绕“全面改造社会生活”的个体自我—群体自我—社会变革的宏大理想,这意味着一种法家化的政治儒学开始渗透进中国社会的骨髓,它极其淡化了由人伦纲常引发的“心”、“性”、“情”、“命”的自我陶冶和自我存养,更多地突出了自我人格中与国家兴盛相关的德性塑造,极其彰大了孔孟以来“自我修养”中社会功利性-“沛然德教溢于四海”。通俗讲,就是先自己不懈地、自觉地培养出仁、智、信、勇、刚这样的德性,成为“仁”德君子,才能使别人成为君子、以至国家、社会繁荣昌盛。因此,政治儒学中的君子不断地自进自取,以在实现自己社会理想和国家兴盛的过程中完善、完满本体自我和个体自我,并去推而广之地确立属于自己社会自我的儒家君子形象。然而,政治儒学在唐末五代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心性儒学在南宋朱陆两派对“理、性、命”的深刻阐述中,得到大规模的回归,形成了理学文化,这种文化在两宋的辗转流变中都在朱熹那里集大成。朱熹认为,内隐的至善的天地之性要变成外显的至善的气质之性,必须“学礼”,其进程是先学“事”之殊样,进至“礼”之形式,最后达到“理”之深得,其贯穿全过程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9]首先在大方向上,外显的至善的气质之性的获得是内隐的至善的天地之性的自我显露和自我复归;其次,这种显露是无法言说的,只有在一系列博学、审问、慎思中,通过身体力行的体验工夫,方能达至,所以教育者的教并不重要,而个体主动地自求、自得、自授才是自我发展的关键所在,这种自求、自得、自授的核心就是“不告以得之之妙,而告之以求之之方”。它贯穿在人们最日常生活对事物获得的知觉、思考、体悟中,进而也在存理去欲的层面上,使自身获得了道德选择的个性自由,最终成为了道德责任感和价值感的建设主体。
(二)自我教育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中的传承
中国近代(19世纪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承受着深重的灾难,面对这些灾难,从“洋务运动”到康梁维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强烈显现了自强不息的自我教育禀性。但是紧接着辛亥革命后的短短几年里,这种启蒙式的自我教育,已在中国能否在列强进逼下,继续存在的危机中越来越淡化,救亡图存已完全压倒了启蒙开化。这意味着中国人的注意力由启蒙开化转向了对社会的根本改造,由知转向行,由器具的盲从、制度的跟从跃迁到心智的彻底重塑,这就拉开了中国现代进程的帷幕——“新文化”运动。
中国现代文化(“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的帷幕拉开于“五四运动”,其时各种欧美文化思潮在中国流行,其共同特点是讲求“实效”, 都要求社会个体自觉地、自主地走出房屋投入到最实在的社会生活中,去研究人情、物理、民众心情,去随时随地进行精神陶冶以唤起对国家的自助、自救,对这种自我教育提倡最剧烈的是胡适,他认为“真正救国的预备在于每个人把自己造成有用的人才”,[10]这一观念在当时大多数知识人、学术人和文化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也因此,中国现代文化的传承是由这种“精英式”自我教育开始的。但是一个社会或民族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体现着她的“良知”,而其基本生产者的态度,则体现着她的“良心”。“良知”死了,这个社会或民族就会失去活力和方向感,“良心”死了,这个社会或民族就真的“死了”。于是,救亡图存中的中国现代社会,做为最基本生产者的无产阶级以新型“文明主体”的面貌,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号召中国人“起来斗争,自己解放自己”。就当时中国而言,这个“文明主体”就是农民,具体来说,就是农民的解放、获救和存亡就意味着中国的解放、获救和存亡。这一进程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认识和投入到农民中去。然而,中国自先秦以来,在书本上很难得到中国农民最真实的生存状况,不得不依靠自我教育,极其主动、自觉、自主地去最底层、最偏远地区,认识、辩析、提炼农民各种生活环境的种种生存境遇,以资为中国革命对象、任务、动力的基本依据,将这种“草根式”自我教育进行的最彻底、最广泛和最深刻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其中的杰出代表是毛泽东及其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实事求是”就是要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投入到中国革命最具体的问题中进行调查研究,去透析出中国国情的客观法则,然后依据这些法则制定出正确的政策、策略,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些政策的实践中,最广大地唤起农民,使他们也能够进行这种“草根式”自我教育,自己解放自己。因此可以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我教育的结果,更是共产党人唤起了中国最底层文明主体——农民自我教育的结果。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极端落后的生产力使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将摸索的重点,落实到了对生产关系的强调上,完全沿袭战争年代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想通过唤起全民的主观能动性自动、自觉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飞跃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彻底失败。
对这场失败反思的结果就是“改革开放”后,那种去政治化的“个人主义”自我教育被广泛唤起,人们不再从公共的道德范畴出发,而是从个人审美的视角来确证自我,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是自我不再是理性和道德的,而是肉体和感性的、更进而把这样一种美学性质的内在心理感受,作为了具有信仰意义的支撑融解到了生活态度中,从而为个人生活世界的自我发现奠定了真正的根基,并最终瓦解了人们对公共生活的热忱,致使那种能够监督、制衡社会的被称为“公德”的东西,正在日渐退出历史舞台。这种“个人主义”的自我教育最集中地体现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领域的各个层面上,其“丛林法则”式的生存机制,如利刃一样楔入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最深处,使得一个充满了欲望的“市民社会”阶层正在崛起。在这个阶层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主动、自主地追求着自己的私利。反过来这些最物质化的社会成果,又有力地推动了“个人主义”自我教育一次次地朝前跃进,直到新世纪来临,这种以挖掘主体“个性”能量为目的的“个人主义”自我教育,已开始成为生产力发展最主导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每个人自我教育的充分发展与国家、社会的繁荣昌盛,具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四、结语
人类与动物最大区别是因为有了自我,具体讲是在自我的内在生存方式——自我教育中产生的文化,使人与动物产生了质的区别。自我和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人类群体社会化的产物,尽管如此,围绕文化的一切运动形式,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的传承,最终还是要通过一个个个体的适应、改变、改造环境中的自我塑造、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等一系列的自我教育活动表现出来。因此,每个人在人类文化实践中的存在本质都是我在,但没有我,所以我生成着。人正是这样一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的存在物,所以自我教育几乎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生命的每时每刻。
[1]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5.
[2]张世英.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57-260.
[3]科恩.自我论[M].佟景韩,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96.
[4]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51,211.
[5]张瑞琨.自然科学史简编——科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历史对科学的影响[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55.
[6]胡毅,王承绪.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103.
[8]赵刚.知识之锚[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55.
[9]珍妮特·沃思,戈登·德莱顿.学习的革命——通向21世纪的个人护照[M].顾瑞荣,陈标,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5.
[10]孙培青.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50.
[11]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2.
(责任编辑陈育/校对云月)
O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mplication of Self Education
HAN Yong-hong
(School of Education,Guangdong 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526061,PRC)
Generally speaking,there are two ways of human cultural inheritance:education by othersand self education.Dialectically,only self education is the intrinsic basis and inner motive of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The so-called cultural inheritance is done througha cohort of new people with new selfand “cultural power” achieved through self education.It is these people that preserve,pass down,and create cultural phenomenon,cultural entity,cultural atmosphere.The complex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inheritance is no exception,which is ultimately realized through and reflected in a series of self education activities of individual selves such as self shaping,self-improvement and self transcendence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changing,and transforming the environment.
self education;cultural inheritance;historic evolution;cultural connotation
2016-08-20
韩永红(1970—),男,上海人,教育学博士,广东肇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教学心理研究
G 40
A
1674-5779(2016)05-007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