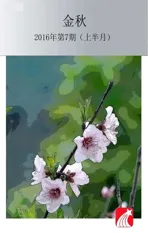那一场如诗如梦的忘年恋
2016-04-13胡平陈昕
◎文/胡平 陈昕
那一场如诗如梦的忘年恋
◎文/胡平 陈昕
板块邮箱:dasu666@163.com
2014年11月28日,全国大学生朗诵大会总决赛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方明深情朗诵了已故中国作协副主席张锲的长诗《生命进行曲》。听着听着,张锲的妻子、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院长鲁景超教授泪水滑落。
2014年1月13日下午,张锲因突发心源性心脏病猝死,倒在女儿怀里。文学界顿时一片哀痛。在张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鲁景超敬献上挽联:“老张,这辈子我没陪够你……”
张锲与鲁景超相差23岁,两人有着一段超越世俗的“忘年恋”,两人亦师亦友,张锲把一个戏校毕业的小演员一步步引领成为博导。而当张锲晚年患上帕金森症,鲁景超又像母亲照顾孩子般照顾他,两人用真挚的爱谱写了一段爱情童话……
最近,笔者专程采访了鲁景超。
“天意偏怜我,中年幸识君”
永远忘不了37年前的那个夏天,在北京锣鼓巷内的净土寺胡同1号,诗人、《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住的四合院里,我喜欢静静站在一棵大槐树下,听一个人谈话,他叫张锲,身材魁梧,个头一米八五,声音洪亮,谈起一篇篇作品构思,激情澎湃。
我15岁进人艺学员班,这时20岁不到。几年后,人艺排练话剧《祖国之恋》,作者正是张锲。排演本是由演员们分头刻印的。剧本印好当天,张锲找到我,翻开其中几页问:“这是你的字迹吗?”我赶紧邀功:“为了刻这本子,我熬了整整一夜。”他却把脸一沉:“鳖爬似的,太潦草。抄人家的现成东西,怎么还会有这么多错别字?”我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转身跑了。“文革”开始时,我才读小学二年级,接下来的学业,基本上都荒废了。
大约过了个把月,《祖国之恋》彩排获得好评,我的表演也得到了赞扬。这时,张锲老师又找到我,他开口就问:“还生气吗?其实,我也是一片好心。”说着,他把一本蝇头小楷递到我手上,密密麻麻,是他专门为我抄录的十几首唐诗和四五篇古文。“这些,你都要背下来。”“背?”我吓一跳。“学习古典文学,光读还不够,一定要扎扎实实地背。你很聪明,可聪明人到处都有,艺术家却凤毛麟角,关键在于自身修养。趁着年轻,多往肚子里装点东西,对你一生都有好处。”他让我抄录和背诵《古文观止》,一篇篇耐心地讲解,成了我的老师。我也知道了他曲折艰辛的经历。
张锲出生在安徽寿县瓦埠镇一个偏僻的村庄,父母都是乡村教师。他15岁入伍,解放后进华东大学皖北分校学习,创作和发表了很多诗歌,后调到《蚌埠报》任文艺副刊组长。1955年,他考取厦门大学中文系后,却莫名成为“胡风分子”,接着被打成“右派”,过了整整20年非人的生活。他拉过大粪,喂过猪,扛过大包,住过厕所……“文革”结束后,他的“右派”还没完全纠正,便来北京“北漂”寻梦。
我对张锲老师油然而生敬意。他穿的背心破得不成样,全身却燃烧着激情,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俩亦师亦友,从净土寺胡同那开着花的槐树下,走进一条条狭窄却温馨的胡同,也走进了那胡同般悠长而深邃的爱。他被我的聪慧和清纯所吸引,我被他的人品、才华和坚韧所感染,我们俩的“忘年恋”就这样开始了。
在张锲鼓励下,我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考试前,他一遍遍叮嘱我不要粗心,字要写工整,不要出错。考试那天,他把我一直送到公交站。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默默地给自己鼓劲:不要辜负他,一定要考上!结果,我真的考上了。
刚到学校,有很多人追求我,可我心里只有张锲。他来看我时,同学们起哄让他请客,他借钱请我、室友和一些男同学去新侨饭店吃西餐。后来,他笑着对好友刘震云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银子套不着姑娘。”刘震云笑道:“话糙理不糙。”张锲说:“其实我主要的用意,是想让景超身边的人多照顾她。”结果,那些追我的男同学都成了他的朋友和崇拜者。
我和张锲老师相差23岁,这在那个年代可谓惊世骇俗,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我跑到萧军叔叔家,委屈地大哭一场。萧军跟父亲是老乡,也是肝胆相照的好友。他说:“我只想问你一句,你喜欢张锲吗?”我点了点头。“既然你喜欢他,就尽管去爱他!人就得敢爱,敢恨,敢怒,敢骂。爱就要爱个痛快,不能窝囊,不能凑合!”大年初二,萧叔叔卷着一阵风雪推开我家的房门,冲着我父亲喊起来:“凡干涉儿女婚姻的,没一个有好下场。听着,如果你再给孩子捣乱,我可不客气!”他挥了挥手里的铁拐杖,还没等我父亲醒过神来,又卷着一阵风雪出去了。父亲愣了一会儿神,跟我大吼:“小倔头,还不给我追那老倔头去!”萧军叔叔的“干涉”,让我和张锲老师的关系终于柳暗花明。
不久,张锲受《当代》邀请,用两个月时间到河南实地调查采访,记录下1978年后中国大地跳动的改革脉搏。这年8月,他在《当代》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热流——河南漫行记》。经《光明日报》整版评论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后,《热流》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先后获得《当代》报告文学奖和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张锲出名了!他回到安徽,任蚌埠市文联主席,我和他只能鸿雁传书:“想是三生石上人,几番怨嗔几番情,从今浪迹天涯里,自有青丝系寸心。”“天意偏怜我,中年幸识君。历经沦落苦,更感缱绻情。小别兼方月,梦魂几度寻。良宵何所寄,耿耿一颗心。”他给我写了很多信,每封信都文思飘逸,字迹漂亮,我一封封编了号,至今还珍藏在几个大箱子里。
1984年12月,在中国作协召开的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张锲被推举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后留校当老师,我们终于在北京团聚了。
和你共担寒潮与风雷
1986年春节,我和张锲结婚,新房就在作协安排的一间旧宿舍里。房子虽小,但有爱就温馨。我们婚宴的桌子是用两张破办公桌、几个家电的盒子临时拼凑的,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唱歌,好不开心。
老张成了作协的“大管家”,分管作家福利、服务、后勤等工作,他不得不放下正鼎盛的创作。他走访时发现,很多老作家生活清苦。有的不但生前拮据,死后丧葬费和遗属的安置也成问题。而青年作家出书难。为了筹钱为作家办实事,他除了忙作协的行政事务外,开始四处奔走筹办中华文学基金会。
1989年1月,我们的女儿张钫(小名苗苗)出生。中年得女,老张喜不自禁。我本来天性懒散,觉得没必要再苦拼。老张却逼我学习,逼我写作。我写文章只是一时兴起,他却严厉地要我一遍遍改,我有时改得特别烦,竟把稿子撕了,坐在地上哭。他把我拉起来坐在椅子上,憨憨地笑着说:“哭吧!哭够了就明白了,什么事都在于一个坚持。”一次,我读到舒婷的《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我立有所悟,老张是希望我不断奋进,提升自己,和他举案齐眉。
我边读书边写作边读研,老张帮我认真修改每一篇作品,让我不断前进。我刊发在《知音》上的处女作《有女万事足》就是那时写的。当我的电影文学剧本《萧红》终于发表在《电影文学》上时,老张自豪地笑了:“孺子可教。现在我可有点崇拜你了。”
1994年,中华文学基金会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老张早出晚归,很少休息。1994年秋的一天,他突发心肌梗塞被送进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重症监护室,经过一夜的抢救才苏醒。一睁开眼,他就拉着我的手说:“有件事我怎么也放不下。不把路远这孩子安排好,路遥的在天之灵就不得安息……”著名作家路遥去世时年仅42岁,留下一个12岁的女儿。因她母亲刚在北京落脚,生活有诸多不便。我默默地点头,让他放心。后来,我们把路远接到家里照顾了一段时间。不久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出资,把她安排到北京市潞河中学寄读。老张此后一直关注着她,还抽时间去学校参加她的家长会。
经历了这场生死离别,老张更珍惜和我及孩子在一起的点滴时光,哪怕只有一点空,他也会为我和孩子去买衣物。他有很高的鉴赏力,以至于我后来的衣服、鞋帽、围巾,几乎都是他帮我买的,比我买的还要合身、得体。他是个有心人,把我所有发表的文章都收集起来,作为礼物送给我。在他的鼓励和督促下,我又读了博士,当上了教授,出版了散文集《爱没有终结》《有苗不愁长》。正当我们享受着琴瑟和鸣的幸福时,命运又开始了对我们的考验。
那几年,好几个中青年作家英年早逝,身后不是留下一堆债务,就是家属没工作。老张心痛之余,更全心帮他们解决现实困难,常忙得不着家。而且,他还要面对一些误解甚至流言的中伤。我努力为他分担压力和委屈,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身体不适也没放在心上。1998年9月,我被检查出患了子宫肌瘤,而且肿瘤已经相当大,我当即一阵眩晕。老张立刻赶回,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有我在,不会有事的。”手术那天,老张等在病房门外走来走去,直到护士手捧盘子出来,对他说:“你看瘤子长多大了。幸亏手术及时,不然谁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他深感后怕。
当我从麻醉中醒来,老张握着我的手,愧疚地说:“景超,对不起,我最近太忙,没有照顾好你。”看着他诚恳的目光,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他在,我什么都不怕。我们这段不被人看好的相差23岁的爱情,在岁月的洗礼中,历久弥新更加深沉……
你的离去也掩不住生命的高度
2006年,张锲从中国作协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闲暇时光,就开始出现严重的帕金森症状,走不稳路,记忆力也明显变差了。这一次,就让我变身“母亲”,照顾越来越像个孩子的他吧。
2007年,我已担任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院长,工作很忙,但就像从前他对待我一样,我宠着他,照顾他,并帮助他完成他最想做的事情——写作。老张凭借着顽强的毅力,用三年时间完成了《爱情奏鸣曲及其他》《晚成集》等数部作品。到2010年,他病情越发严重,行动和说话都不大利索了。为了尽心尽力照顾他,我尽量不出差,不在外面吃晚饭。我请了一个保姆在家照顾他,但生病后他非常依赖我,常使小孩子性子,非要我喂药,他才肯吃。
每天早上上班前,我都要帮他擦洗一遍身子。睡前我亲自给他喂药,帮他擦洗。他身躯高大,体重近100公斤,每次给他擦洗,都像是一场恶战。有一次,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学生雨霖来我家,我刚好给老张擦洗完。她见我高高挽着裤腿,满头大汗,全身湿透,还在打扮老张,并把药拿到他跟前哄着他吃。她当即红了双眼说:“老师,您真是太不容易了。”
老张本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对疾病带来的语言障碍,他内心十分痛苦,久而久之,他就不太愿意多说话,我就把他当个孩子哄。我不停和他聊天,时不时地逗逗他,他总是心领神会地望着我,那份眷恋和爱溢于言表。苗苗这时也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每次放假回来,我就让她多讲学校的事,跟爸爸撒娇逗乐。老张认真倾听着,脸上充满天真和快乐。
为了帮助老张恢复,我常邀请学生们来家里。我把他穿戴得整整齐齐,让他高大魁梧的身躯端坐在客厅沙发上。大家来了就一一跟他握手,他微笑着,显得很有尊严。学生们不是朗诵他的作品,就是弹琴唱歌,他大手在沙发扶手上拍着节奏,神采奕奕。看到我们永远手拉着手,学生们都羡慕得不得了,我笑着告诉他们,感情都是平衡的。那会儿我小,他大,他心疼我、督促我;现在他老了,病了,我就得照顾他、体贴他,我们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学生们都感动地说,再次“相信爱情”。
随着病情加重,老张越发贪恋我在他身边的每一刻。我无论回家多晚,我们家客厅那盏橘红色的灯永远亮着,我知道那是老张在等我。每当看到那灯光,我的心里就有暖暖的爱与责任在澎湃。2013年秋天,我给全国主持人大赛当评委,一天节目要通宵录播,我就告诉老张:“今天别等我了,我可能一晚上回不来,你身体不好,要乖,要早点休息。”他定定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那天节目一直录制到快凌晨3点,我一下节目,就急忙往家赶。我感觉,那盏橘红色的灯一定还亮着,那个执著的爱人一定还在等我。果然,一进小区,我就看到在寂静而黑暗的苍茫中,我们家依然亮着灯。钥匙刚旋进锁孔,我就听见了老张孩子般的笑声。他的眼神亮亮的,仿佛在说:“我还是等到你了。”我嗔怪地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心里却充满了暖意。
2014年1月12日,是苗苗25岁生日。晚上,老张突然微笑着对我和女儿说:“我很幸福。”女儿俏皮地问他:“爸爸,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人是谁?”他笑:“苗苗。”我说:“那我排第几呀?”他看着我,一脸深情:“你排老二吧。我太幸福了……”13日一早,我像往常一样帮他擦洗干净,临上班前对他说:“明天学校就放假了,我可以在家里好好陪你了。”可谁曾想到,这竟是我和老张最后的诀别!当天午饭后,司机梁师傅和苗苗搀扶他进卫生间洗脸,他忽然头一偏,就靠在苗苗身上瘫软下去。苗苗大惊失色,赶紧打120……当我从学校匆匆赶回时,老张还挺着一口气,当听到我叫“老张”时,他似乎终于了结心愿,心脏检测仪缓缓呈现出一条直线……
我不敢相信,那个和我相濡以沫的爱人就这样走了!我永远忘不了他和我告别时那眼神和微笑……
我开始整理老张的遗物,竟无意在书房里发现他写了一抽屉的“秀外慧中张锲致景超贤妻”这几个字。因为手颤抖,原本书法极好的他有的字写偏了,有的字写到了红纸外,即便写得最工整的几张,几个字的顺序也排列得不整齐,不知耗费他多少心血。听保姆说,前段时间,我一上班他就要求坐在书桌前,颤巍巍一遍遍地在红纸上写些什么,我快回来他就让保姆把这些纸藏起来。原来他竟是想为我留下最后的生命礼物。这也是他以自己一生的挚爱和眷念,送给我的最高评价。
我要配得上老张的赞赏,更要选择坚强。我挑选了他的部分优秀作品和照片,包括我一直珍藏的他以前写给我的一些书信、诗词,出版了一部精美的画册,还请苏民、方明、瞿弦和、张筠英、李立宏、康辉和欧阳夏丹录制了他的作品朗诵CD。2014年6月28日,“追梦者的歌吟——张锲文学创作65年”研讨会举行。王蒙、郑伯农、冯立三、何建民、刘震云等作家都对张锲的为人和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我静静地听着,心潮澎湃:“老张,你的离去也掩不住生命的高度。你带给我的回忆全是幸福,我们的爱没有遗憾。”
11月28日晚,在全国大学生朗诵大会总决赛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方明现场含泪激情朗诵了老张的长诗《生命进行曲》:“爱情的记忆永远新鲜,那如诗如梦如火如荼的青春……”听着听着,我仿佛又回到从前我们相爱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