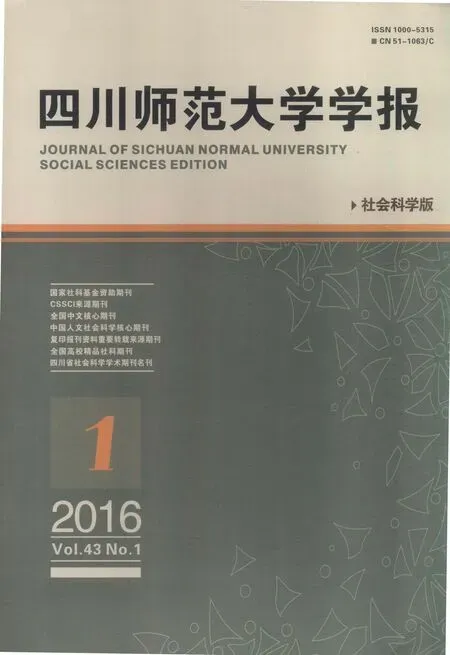转型期社会信任资源问题探析
2016-04-13程倩
程 倩
(南京理工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南京 210094)
转型期社会信任资源问题探析
程倩
(南京理工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南京 210094)
摘要: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变迁中,基本信任形成出现生发性困难的同时,信任的代际传导中上也出现了断裂,一定程度造成社会信任基本资源的缺失。这种状况与社会陌生化、信任的市场化是一个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演化过程。个体化、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转型中的风险性、不确定性,使传统性规则有效性开始丧失。城镇化、市场化融贯运转的整体性制度生成过程,也是个体意识在“陌生人社会”被改写和放大、社会生活模式被个体化的社会信任危机所影响的生发过程。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社会信任资源危机,反映了整个社会制度变迁及在个体和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的问题,需要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及结构化转变中得到解决。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信任;个体化;信任资源

当信任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讨论时,诸多疑问被带到讨论者面前:在中国经济大发展、思想大转变和社会大转型中,各种社会变迁如何引发不同领域信任资源变化及其存在些什么样的因素?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时,如何清楚准确地理解与判断信任的总体状况?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出现明显的个体化趋势或特征以及个体化的社会如何整合?这些问题一方面涉及通过中国社会转型的方方面面考察社会信任的斑斑点点,理解判断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具象关系,从社会运作内在机理和信任的本体性反思入手,从公共领域入手重新构建社会信任资源;另一方面也关乎充满利益摩擦和生存考验的社会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因为如何“转”、向何处“转”关系到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性目标的实现。
一社会转型中信任基本资源的变化
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以后,中国生活的转型引发了社会机构和中国社会形态的巨大变迁。它不仅仅表现为经济体制的转变带来的经济大发展,又表现于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引发的各种大变革,更表现在文化观念更新乃至心理世界的重构带来的社会思想大转变。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城乡之间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社会流动快速增长,人们在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和思想观念等不同层面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使得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在社会转型中因角色、精神等方面的不同而被碎片化,个人从传统社会结构中挣脱出来重新投入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密集变迁的时空当中,在迥然不同的历史与社会要素构造中共存,在高度复杂的动态社会系统中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越来越多的农村个体挣脱出小农经济生存模式,不再是靠天吃饭、安土重迁,不再过着代际复制的生活,而辗转于城乡之间,成为“农民工”。在劳动力、经济体制的大众成分中,在户籍制、单位制的瓦解或者松动中,个人在自觉与不自觉当中投入到陌生的环境——工作市场、城市管理或街道社区的控制与约束中。人们交往的范围不再限于熟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对象越来越广泛地投身于陌生人当中,原本的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和家庭家族等社会形式日益脆弱,传统义务处于游离的状态,个人“成为个体”(becoming-individual),在其无力控制的宏观结构状况中,人们既有的实践知识、规则体系和信仰乃至信任关系被打破。
(一)社会信任基础性资源空白的可能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发现,个体成年后的自我认同及信任机制与婴幼儿时期的“基本信任”与“基本怀疑”之间的张力关系密切。婴儿出生以后与养育者(母亲)的互动过程正是第一个社会危机——基本信任对怀疑的解决过程。婴儿脱离母体来到这个世界,有着先天的脆弱和焦虑,而内生出“依恋行为系统”,以调整与所依恋对象的亲密关系。如果养育者能以慈爱和习俗的方式满足其需要,婴儿能够把一大堆冲动汇集成时空在心理上的“束集”——“即使母亲不在场也不意味着遗弃,即相信母亲即使不在面前也会返回来的信念,而不至于产生过分的焦虑或狂躁,形成基本信任。因此,母亲在婴儿心目中同时具备了外在的可预见性和内在的确定性。通过母亲在场与不在场的反复交织,婴儿逐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的信任机制,借以克制由于母亲不在场而带来的基本怀疑,使自我认同持续得到维护。”[1]115可见,作为人格特质的基本信任是婴幼儿在早期的“婴—母”互动过程中习得的,并对其社会化过程产生持续的影响。这种信任一旦生成,就会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特质,是个体成长阶段决定社会信任能否顺利生成的一个基础性资源。
依恋对象是婴幼儿依恋行为探索的“安全基地”(security base),如果母亲作为依恋对象缺场或经常性被替换,“母婴依恋”(infant-mother attachment)无法正常建立,婴幼儿便可能产生分离性焦虑——本应在与母亲重复交往经历中内化生成的行为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无法完全建立,致使其行为、情感和认知等结构的正常发展受到影响,进而关联到儿童人格结构的生成,甚至影响到对他人的信任这一基本安全体系最深层的要素的发展,造成基本信任生成性困难,并引发后续社会化阶段信任资源基础性匮乏。审视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进程中,至少经历了两波婴幼儿从脱离母体起就被置身于社会的流动影响之中,产生了因儿童与父母分离而出现的其基本信任空白性危机。
建国以后,女性在家庭、教育、工作、公共关系等方面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一般女性的生活经历更为接近男性。一方面是国家建设需求与社会整合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如建国初期全民性质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得妇女的扫盲、教育和经济独立等如火如荼地进行,从身体和思想上解放了妇女。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传统的女主内育儿方式被打破,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大规模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鼓励与动员妇女工作顺理成章。在正常产假只有4个月不到的情况下①,伴随妇女大量就业所衍生的问题就是儿童养育问题,婴幼儿被普遍托付给祖辈或其他亲戚抚养。因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很多有隔代抚养甚至同辈之间带养的记忆。另一方面,在妇女解放与独立的大潮中,女性觉醒而产生的爆炸性社会政治动力,也使更多有所追求的女性越来越摆脱和家庭的直接联系,追寻“自己的生活”,从先赋性角色向获得性角色转变。教育使得她们越来越甩开特定的社会期待和经验局限,个人规划与她们的父母大不相同,不工作成为例外,即便在养育孩子阶段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后,妇女就业和流动性进一步加大,儿童养育问题在城乡二元的农村地区越加凸显。据全国妇联最新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多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其中父母双亲外出的占46.74%②。更多的调查显示,父母外出打工后,或者造成了“事实孤儿”的境况,或者选择迫不得已的“隔代”文盲式监护,这种状况易导致留守儿童“亲情饥渴”。同时,正处于成长发育期的留守儿童,由于与父母分开而缺少必要的教导与指点,更容易受到外界伤害。
现代女性就业和自然流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乡土社会日常的育儿观念和孩童的成长方式。无论从依恋理论还是人格发展理论看,母亲养育质量的下降对儿童信任生成有直接影响。如果婴幼儿在养育期和养育者(母亲)之间没有建立基本信任,婴幼儿在长成期就可能出现长期抑郁、暴力型焦虑等征兆;如果婴幼儿的养育缺乏母亲或固定监护人经常性、慈爱的照料,就会缺乏对他人或者他物的确定性意识,进而出现封闭性举止或者退缩性行为,体现为儿童应付不确定性和判定环境敌意的反应。就此,内在信任的缺场是对外部世界不可靠性的映射。一定程度上,婴幼儿基本信任萌生不顺利的过程内生着社会信任资源危机,或者说,个体的信任本能可以追溯到生命早期阶段。因为作为社会信任的普遍信任,来自于乐观主义的、开放性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是婴幼儿阶段从父母那里获得的,个体的生活史塑造其普遍信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任首先是习得的。
(二)代际传导断裂造成的信任资源匮乏
作为一种道德主义的信任,基础信任资源的本质建立于共享的价值观基础之上,“乐观主义、开放性和对外部的可控感构成这种共享的价值观,也构成了道德主义信任的基础,它比个人的经验更为重要,这种价值观更多是从父母那里习得”[2]21。由于基础信任来源于婴幼儿社会化早期,成年期后由于其普遍信任的特征,更容易相信他人,与他人形成合作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信任是共同生活的基础,信任可以决定公共生活,“充满信任的社会是公共社会(Civic Society),这个公共社会就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3]。
在中国社会市场化进程中,“陌生人社会”逐渐形成,在社会分层凸显的同时,阶层隔阂以及阶层的代际传递性也显著增强。人们包括信任在内的价值观越来越无法在早期家庭生活中获得,在父母自身已不再具备信任感、不再宽容并很少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的行为特征影响下,孩子也无法从中获得信任感的示范和引导,信任代际传递可能出现断裂。教育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表明,“不仅父母对外界环境和陌生人的信任很可能通过日常交流传递给孩子,影响孩子的信任水平,同伴以及包括学校在内的整个成人社会都影响着儿童、父母的信任水平”[4]。
现今社会意象中普遍存在的“防人之心不可无”、“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上当受骗的都是老实人”等话语,充斥于每个家庭的亲子对话之中。这些“谆谆教诲”究竟传递了什么呢?所有的这些告诫的话语背后,其实是父母对人性、他人可信赖程度的不信任或者弱信任。这些话语使孩子内生出“社会环境十分险恶,陌生人不可信赖”的社会认知。“陌生人是危险的、不可信任的”成为榜样人物心照不宣的缄默性知识,在其与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正常期待感的传递中,又成为普遍信任感缺乏被负面代际传递的典型③。
家庭对儿童价值观形塑有重要作用,而儿童价值观的形成对基本信任的样态具有持续而稳定性的影响。决定儿童是否信任他人的因素,并不取决于成长过程中外部经验的积累,而在于家庭内部和谐给予他的主观感受。如果家庭养育使得孩子具有安全感,能够与家庭成员形成良好的反馈和互动,孩子会逐渐地建立起基本信任和积极的正向情感。儿童成长中,伴随其社会化过程在横向范围及实践纵向中的延展,价值观逐渐形成并投射到他人身上,进而达致更多的亲社会关系。埃里克森的人格理论反映出家庭关系对于个体及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微观层面的家庭融洽会影响宏观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榜样人物的社会态度融入其家庭教育并传递给子女的影响时段可能有一二十年之久,其“当前的社会态度可能通过其对子女的影响而成为未来社会的主导价值观”[5]。也就是说,未来的社会主流文化、经济走势,包括社会普遍信任的状况等,在当下社会细胞的每个家庭中自发地、潜在地孕育和涵养着。
父母对于社会环境“非安全”评价来自于他们社会认知中的“风险”意识,而这恰恰是工业化发展的自反性结果,是转型期“风险社会”特征日益凸显的映射。从自觉市场化到自然的城市化,再到自为的城镇化进程中,流动性加强使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共同生活的熟人圈子,进入到陌生人社会,被结构化到既相互承认又相互竞争的关系模式中。高速扩张的市场化,更使竞争关系成为人际关系的主导方面。当谎言成为见怪不怪的现象被视而不见或保持沉默、被容忍,并成为每个人现实生活中深受其害的暗算;当某类行为或某个陌生人对人身安全的威胁或罪行被揭露,对家庭成员安全的担忧与日俱增;当知晓某种食品安全不受保障而做出饮食改变的反应;当某种亲密关系被背叛,而伤心欲绝,继而怒火难消……这些事件发生时,都让外部世界显得危机四伏、令人畏惧,促发更多防御性行为,并形成恶性循环——“无意识中关于人类整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似乎充满了作为基本信任的对立面的恐惧感,恐惧变得自我延续并自我强化,也获得了自身的动力”[6]75。就此,“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所有风险都是相对于人而言的风险,所有风险最终也都是由人的活动所造成的风险。这也就意味着,所有风险都具有人际关系上的根源”[7]。风险破坏了信任依赖的社会传统及惯例资源,也随之抽离了个体安身立命的社会信任价值根基。
二转型期社会信任资源危机症候
城镇化、市场化进程中,个体的利益追求在“陌生人社会”被改写和放大。人们从传统语境中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撤出,黑格尔所指称的“市民”及市民社会日益壮大,对自我利益的极致追寻和对“自由”的积极追求,一方面使传统社会交往网络分崩离析,另一方面使整个社会生活模式被个体化。当人们“为自己而活”又缺乏真正的个性时,其心理系统、价值系统的基础被打破。全面的市场化发展中,个体获得自由的同时,自利性的膨胀和社会的“失范”开始加剧。此时,各种关系越来越受制于市场的非人性化和商品化,社会信任资源遭到更大程度的破坏。
(一)社会的陌生化
工业化以来的社会陌生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尤其在全球化这个普遍的开放体系中,陌生人与熟人的区别并不取决于人们之间的交往频率,而由社会整体开放程度决定。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分散的、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这个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在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也较为简单,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8]10。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亲缘体系日益淡化,人们被抛入陌生人社会中。此时,人们之间基于亲情和熟悉的信任开始消失,对陌生人抱持普遍怀疑的态度。信任的传统资源要素,如熟悉的人际脉络、传统礼俗、同质性关系等,大多被驱逐于主流社会生活之外。陌生人之间的冷漠感及孤零无助,在车流不息、人潮汹涌、楼宇林立中加剧,不信任和风险以不同比例混融在一起,破坏了吉登斯所称的“本体性安全”。
市场化和城市化造就了中国社会地域性的陌生人社会,全球化、信息化则造就了一个全球性的陌生人社会。“社会成员开展活动时所处的环境,在活动模式尚不及巩固成为习惯和常规之前便已发生变化”[6]1。一方面,个体在非人情化的交换中不得不托付那些模糊浅显了解的人们,遭遇漫不经心、转瞬即逝的对待后,踯躅于就业和行业惯例的冷漠世界。另一方面,原本的乡土关系瓦解——不得不选择某种策略发生联系,却又带着疑虑和不信任。同时,人们因为各自的生存境遇和不得不面对的竞争聚集到一起,选择性地确定亲密关系,相互警惕乃至相互排斥,并把亲密关系之外的人视为毫不相干的人,保持足够的距离。当整个社会被“陌生化”时,传统礼俗社会的信任资源开始式微。
社会陌生化造成了对人际交往关系的冲击。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交往对象及交往方式等大体相对固定,群体性存在中的个人生活在家庭、同族乡党当中,社会关系网络较为固定且简单,社会生活相对静止,处于较为单一重复的连续状态。此时诚信恰是日常生活的“基因”,是信任关系产生的主要资源,使信任内生于个体情感自发而自然。但是,当一个人为了更直接、可见利益及资源的获取而不择手段,如坑蒙拐骗、“杀熟”或欠账赖账,只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且这种手段本身也被视为一种能力,社会信任资源便被极大地破坏了。
社会陌生化也使人们交往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受工具理性的利益目标驱使,再加上工业化和社会分工导致集体统一性的减弱及社会关系分化,人际交往短期效益越来越凸显,相互陌生的个体为了各自的利益既竞争又协作。而随着竞争的持续展开,引发各种消极行为——破坏公平竞争的垄断、霸权、欺诈、盛气凌人等行为屡屡发生。建立在血缘、地缘的熟悉关系基础上朴素的自然状态的人际交往不复存在——人们的生活环境变得复杂起来,人的流动、物的流动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资源、要素的流动,在制造复杂性的同时,也使得不确定性增强。由此,社会陌生化过程又是“风险社会”生成的过程。人们由于相互之间的信任缺失,转而依赖于对组织、权威、制度等的信赖。但是,当组织、专家乃至制度等方面的信任资源得不到保障,自身的权威无法及时有效地建立或者千疮百孔,甚至会引发更深层更广泛的信任危机。
“以1978年改革为原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自然历史和人为设计的两个路径中遭受冲击,特别在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目标逐步展开以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9]。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根基在于家庭生活,它限制了社会信任的范围,但经历了建国以后国家扩大化地混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政治“挂帅”式的统辖使得私人生活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后,又在改革开放阶段重新经历着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后,“建立在血缘、地缘、亲缘关系基础上的传统社会规范网络,将不可避免地被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建立在科层管理基础上的‘陌生人’社会网络所代替,从而形成新的社会结构,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10]。以市场为主体的私人领域突兀地崛起,日常生活领域碎片化回归,都使社会信任经历了结构化意义上的撕裂和破碎,转型期社会信任资源危机确实与中国社会的过渡性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信任的市场化
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后,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某种层面上甚至成为建构和统治社会的形式,因为制度、规范建设的滞后性,市场成为统摄社会、政治和文化不同领域的重要力量——相互联系的市场关系使整个社会像一张网,它用精细的、见不到的丝线把人和人编织到了一起,又排空了它们的主观社会关系内容,尤其是排除了特定的人格品性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明码标价,即使不标价也可以进行交易。社会生活越来越依靠利益驱动和价格杠杆,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组合,经济主体行为越来越具急迫的功利性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货币作为实现人类目的的纯粹中性的手段,最终变成了人类行动的绝对目的——在最彻底和毫无保留的意义上,变成了人们心理上的绝对价值,变为统驭人们的、无所不包的最终意图。“人们是那么浅薄,那么急功近利,那么容易满足于有限的成就,那么注重精心地营造世俗性的安乐窝。……把有限价值当作了人生的终极目标。这种终极关怀的失落,使个体伦理陷入道德的困境,伴之而来的就是道德选择迷惘和价值取向紊乱”[11]。
熟人社会中家族及人格化的依附为非人格化的依附所取代,如齐美尔所观察到的:“人类相互之间的依附尚未完全客观化,个人的因素还没有遭到彻底的排除。不过,一般的趋势无疑是朝下述的方向发展,即个体越来越依赖于人们的成就,而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它们背后的人格。两种现象有着同一根源,形成了同一过程中对立的两面:现代分工使得依赖增强,一如导致人格消失在它们的功能的背后,因为人格中只有一个方面发挥作用,所有其他方面都牺牲掉了”[12]80。如果“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13]192-193,传统“共同体”便开始解体,依附于共同体的个人获得了自主,个体以自身为目的,而把他人作为实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市场理念裹挟事物的能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没有什么能够抵御它的侵袭。“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甚至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这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14]79-80。社会信任也主要通过市场交易来产生和维持。当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近百年前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的描述今仍可见——“自私的计算被带进传统的兄弟关系之中”[15]302。
社会信任的市场化作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包含于上述变化之中,在行为的逻辑顺序上又是这些变化的结果。换言之,这种市场化的信任无论是作为关系呈现的样态,还是作为社会行动的机制,都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中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包含了社会系统生产和秩序的转换。此时,转型社会中的结构性特征,在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表现出相似性。例如,不同的逐利性经济行为背后,是利益熏心后的怀疑,及计算后借助于保证再决定付出信任的行动逻辑。社会信任的市场化成为主-客的双向构造。一方面,人们行为要接受市场外在的规约,非传统性因素通过实践意识内化到行动者主观结构中,形成诸如“逐利”与“守约”、“计算衡量”与“怀疑冷漠”等互有张力又相互依存的心理与观念结构。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是被动接受市场经济结构的制约,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意识展开实践,把主观结构外化到社会关系当中,进而改变着市场行为个体更大的行动场域,延展到日常生活的家庭范围,也扩展到个体以公民身份而存在的公共领域。在个体层面上,被市场化的信任是“理性”和“感性”的交织和混杂,表现为非线性的、不明晰的、却往往如此的行动层次当中。
在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却不甚规范的发展中,传统道德不再被广为接受和实践,更为严重的是,开放市场的国别跨越也使中国面临着全球风险社会的挑战。措手不及之中,社会原有的信任机制被迅速抽离,而更大风险在于,取而代之的“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自身也出了问题,专家不凭良心说话而是凭金钱说话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进而导致假冒伪劣充斥市场,直至出现了杀熟现象”[16]。这些都使社会信任陷入了资源匮乏的两难境地:产生信任的传统不再存续,新的社会交往机制除价格之外别无他物,信任无从谈起。这在根本上催生了中国信任危机的到来——社会转型期的不信任范围被扩大,由局部的、个别的不信任逐渐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加大了交易过程中的预付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公共领域中的政府管理绩效和法理性权威衰减;日常生活因缺失了社会关系润滑剂,群体关系及人际交往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加。
在文化层面,悄然出现的信任资源危机源还表现为转型期社会基本价值认同和伦理基础的崩裂及社会的高度碎片化。以劳动和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为基础的共同生活关系被摧毁或削弱,走出祖辈生活的熟悉乡土,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城镇、企业等抽象化的、非人格化的场域。此时,个体生活环境变化,传统和惯例乃至传统秩序消解,个人角色扮演随亲密群体的消失而难以确定,随之而来的是个体的茫然和无助,生活失去了确立性和方向感。此时,社会信任危机表现为“个体化孤独”——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行色匆匆,人际状况被霍夫曼形容为“世俗的不经意”——相互“朦胧”的短短一瞥,展示的人际特征不是冷漠,而是“礼貌性疏远”的刻意克制。此时,个体不经意远离了那些互动的、常规的信任建构活动。同时,网络社会的发展,尤其网络社交的匿名化特征,更压缩了社会关系运作的空间,传统的、以关系为核心的社会信任资源危机便不可避免。
“通常人们总是将不信任作为信任的对立面,……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信任的对立状态便是这样一种心态,它应被准确地概括为存在性焦虑或忧虑”[17]87。主体意识空前觉醒后,开始爆发性地争取自己的权益。然而,主体意识是自我与社会两极分离对立中的价值意识,与之相伴的往往是孤独与离散。个体间相互熟悉而产生信任的生活经验开始无用,既有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做出适应性调整。生活开始充斥复杂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并滋生出不安全感,随之而来的是个人生活信心的磨蚀。个体化孤独,是“生命的受挫折”——不能实现其感官、情感和心智的潜能。以发展生命为目的的精力开始分解,或转移为以破坏为目的的精力,而求生冲动受阻越大,想要破坏的欲望越强。因此,“破坏性是生命遭受挫折的产物”[18]]112。公交纵火、砍杀孩子等社会报复案件证实了这种转移的触目惊心。当这些破坏无一例外地来源于个体怀疑、孤独及报复心理时,印证了贝克的判断:“个体化进程导致了个体与社会之间新的直接性,社会问题直接体现为个体问题”[19]100。
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中国社会信任资源稀缺和诚信价值推广成为紧迫的社会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迅猛背景下,由于社会信任资源出现的诸多变化,社会信任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各政府机构,包括公共服务职业群体及各个部门,不得不面对个人诉求膨胀与政府应接不暇的瓶颈及张力,在一个讲究“民无信而不立”,有着“以吏为师”传统的国度,“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整个社会信任度下降、底线道德的缺失成为令国人困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政府自身在公平公正、诚实守信方面存在问题。因此,充分注意政府与民众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互信度衰减状况,在社会矛盾凸显中重视政务领域的诚信建设,才可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导(道)之以德”[20]。因此,以行动主义中的合作治理来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在公共生活的健全中提升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能力,在行动主义框架下建设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政务诚信体系以再生政府信任资源,成为改善转型期社会信任资源相对匮乏局面的基本路径。
注释:
①2012年4月28日修订签发的《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产假规定:女职工若顺产生育单胎,可享有98天产假(14周),难产者增加15天。多胞胎生育者,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15天。此前1988年的《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规定的正常产假是90天。
②参见2014年9月11日全国妇联新闻媒体通气会报告数据,转引自中国未成年人网http://news.kids21.cn/zx/sh/201409/t20140913_289895.htm.
③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指父母的能力、观念、行为、社会地位等传递给子女的现象。子女在各方面与父母越相似,代际传递效应越强。尼米—詹宁斯社会化研究 (the Niemi-Jennings socialization study) 分别在 1965 年、1973 年和 1982 年对青少年及其父母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进行了大规模追踪调查,并被认为是早期信任代际传递研究中最可靠的数据来源。该调查结果显示,父母的普遍信任水平与子女信任水平存在关联。国内信任代际传递的支撑性研究的学者较少,本文从中华女子学院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池丽萍副教授等学者关于信任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中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
[1]ERIKSON E H. Childhood and Society[M].New York: Norton,1963.
[2]USLANER E M.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3]USLANER E M.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Trust[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2000,115(4).
[4]池丽萍.“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信任的代际传递[J].青少年研究,2012,(4).
[5]池丽萍,辛自强.信任代际传递的中介机制:一个概念模型[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6]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M].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7]张康之,张乾友.在风险社会中重塑自我与他人的关系[J].东南学术,2011,(1).
[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程倩.论领域分离中的社会治理创新[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
[10]祝灵君,冉茜仪.个体化社会背景下的执政党认同[J].党政研究,2015,(4).
[11]罗建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原因的伦理解析[J].道德与文明,1998,(5).
[12]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1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5]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M].姚曾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6]翟学伟.信任与风险社会[J].社会科学研究,2008,(4).
[1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8]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19]BECK U.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20]程德慧.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公民诚信教育研究[J].党政研究,2014,(1).
[责任编辑:苏雪梅]
Trust Resources in Chinese Society’s Transformation Period
CHENG Qia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94, China)
Abstract:With the basic trust’s breeding difficulty amo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ust breaks down which to some extent caused the lack of basic resources of social trust. It is a complementary process with Chinese society’s de-familiar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of trust. The risk and indeterminacy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ividu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causes the decreasing of 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norm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otal system of urban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is also the process of adaptation and enlargement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in a stranger’s society, as well as the forming process of a social trust crisis with people’s social life pattern being individualized. The resource crisis of social trust happened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in soci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and thus needs to be settled in the moderniza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ing system.
Key words:soci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trust; individualization; trust resources
作者简介:程倩( 1969—),女,江西景德镇人,博士,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府改革与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 “中国特色政务诚信体系建设研究”(13BZZ0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政府信任资源再生研究”(12YJ81006)、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深化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研究”(13WTB030)、江苏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基地项目(14SSL43)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07-22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1-0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