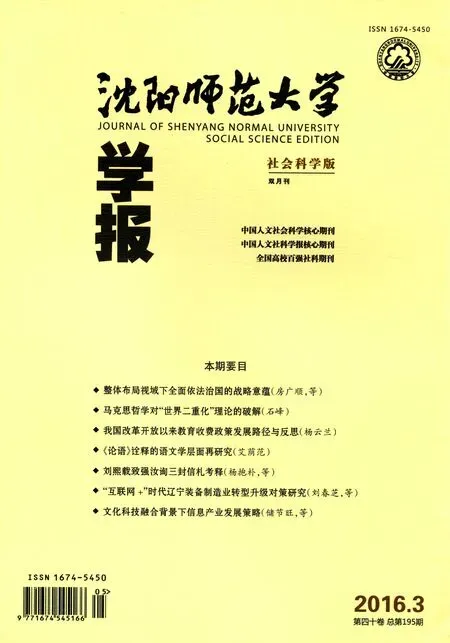《论语》诠释的语文学层面再研究——以《学而》篇“道千乘之国”章为例
2016-04-13艾荫范
艾荫范
(阜新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辽宁阜新123000)
语言学论坛
《论语》诠释的语文学层面再研究——以《学而》篇“道千乘之国”章为例
艾荫范
(阜新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辽宁阜新123000)
《论语》作为儒学首典,是迄今被解读得最为透彻的一部古文献。对儒学和孔子尽管有不一的评价,但人们觉得至少《论语》的语文学层次已经搞清,事实远非如此。《学而》第五章学界均认为是孔子的治国大纲,实乃误读。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孔子说,要引导据有千辆兵车大国的君主,要依礼的规定恭谨地祭祀,节省自身用度加以惠臣下,役使民众应当不违农时。
《论语》;语文学层面;阐释的循环
一
自总角之年初通《论语》,至今足足走过了七十又几个春秋。这中间,古今凡疏解它的权威性著作,从十三经注疏本何晏《集解》、朱熹的《集注》、刘宝楠父子的《正义》、现代程树德的《集释》、杨树达的《疏证》,直到当代杨伯峻的《译注》、钱穆的《新解》,以至李泽厚的《今读》,先后陆陆续续都研习或浏览过了。滋润之深,自非数语所可道尽。
《论语》作为儒学首典,自汉代形成齐、鲁、古三《论》各有经师传授以来,不论作为社会主流意识的反应堆,还是在科举时代的试题库,两千年中可谓阅人无数。特别是到了清代,朴学家们研习学术,几乎无人不从《论语》始,斐然成绩,多收进了《皇清经解》。民元以还,又有数位语文学大师疏理《论语》,如前举程、杨二氏,创成力作;再经当代名家的尽心锤炼,愈臻完善。因此,笔者可以有把握地说,《论语》在中国全部典籍中是被搞得最深最透最烂熟的一部。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里我的印象是,当代学者尽管在深层次,例如哲学、政治、伦理、宗教、历史等等领域,诸家各持立场,各秉一是,但在语文学层面,即从字面上解释《论语》,他们己经达到一致。例如前举当代杨、钱、李三大家,讲儒学各说各的道理,概念诠释也颇参差,但译文总体看却是一致的,由此我推想并且相信,时至今日,《论语》诠释的语文学层面己经解决。
但后来证明我这里只对了一半,即:诸家在语文义上达到了统一是真的;可是《论语》这个层面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它们有相当大的空间留给了我们,这是近数年,有几度把全部精力集中于《论语》原文,特别是在引进一些我觉得得力的新的阐释学理念的时候,让我渐生的一种新印象。如《宪问》第三十三章“骥不称其力而称其德”,对“德”的语文义解释,当代前举三家分别是——《译注》:品质;《新解》:德性;《今读》:品质,三家可以说完全一致。但当我引进这一章的互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曹操《短歌行》),复引上古多种旧籍佐证,再从甲金文字形义和上古音韵层面参互发明,淘洗出“德”之初义却应是意向、意志,而《论语》此章用的即此古义[1]。所以孔子这几句话应理解为:“人们所以用‘骥'来称呼千里马,不是因为它的气力,而是由于它的意志。”因为“骥”是“冀”的转注字,由字(词)根“冀”(希望)得义,所以“骥”字本身即具不断进取的涵义。《论语》中还有数处“德”当训为意志、意向[2]。如《颜渊》篇“君子之德”“小人之德”,意谓君子的意向,小人的意向;篇中两处“崇德”都是指尚志。《先进》篇“德行:颜渊、闵子骞……”,“德行”即志行。《述而》中孔子在生死关头坚信“天生德于予”,是说上天把它的意图(在《中庸》称“天命”,《墨子》称“天志”)降在孔子他的身上,让他担起“述”周文王体现之“文”的大任(《子罕》),所以仪封人才说老天要把孔子当成宣讲王道的“木铎”响亮地摇起来(《八佾》)。由此推开去,《诗》《书》中许多“德”都当如此训释。这就提示我们中国精神史、伦理史专家,应注意划分“德”这个原属于意志范畴的概念,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转化为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品行,而我们看到学界一直用后者替代着前者。
由此可见,一个词语文义的诖误如何影响到思想史的正确把握。因此《论语》的语文学层面释读还应当引起我们密切关注,值得我们继续深入下功夫探讨下去。
二
为了证实拙见,本文以下将试解被古今所有注疏家错会语意的《学而》第五章。
子曰:“道千乘之国,谨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上海古籍本《译注》称“此章是孔子论治国的大纲”。治《论语》的朋友清楚,“子曰”以下四句,古今注者除了对“千乘之国”规模大小有争论外,对属于“大纲”三句的解读,自东汉包咸注以后直至于今,诸家绝无分歧。包咸的注解是——
“为国者举事必敬慎,与民必诚信”,“节用不奢侈,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之”,“作使民必以其时,不妨夺农务。”
包氏把三句话划分成五个命题,故此朱熹《集注》明确地称“治国之要,在此五者”。
六十年前,杨树达先生作《疏证》更作了如下标点——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且于分出的每一句后征引多种文献证实,最多达十余条。
当代学者仅举李泽厚《今读》,其译文是——
孔子说:治理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慎重、敬畏地处理政事,恪守信任,节省开支,爱护人民,差使老百姓选择农闲的时候。
可见,李氏也持“五点论”,其他杨氏《译注》、钱氏《新解》全同。
荫范谨按:古今诸家对本章的理解可惜全都错了。可怪的是,《论语》这一章并没有古文奇字、失传的古义或后世少见的句法,那么两千年前,包咸领出的这条歧路何以让学界一直错到今天呢?孔子在《子罕》篇末那章,引四句逸诗后富有情趣地说了两句话:“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没有认真地思索罢,有什么遥远的啊!)笔者以为大家都不曾认真思考而轻信了包咸,包括我们当代可敬的语文学大师如杨氏籍咸。
但这里确实有一个学术方法论的误区,一个在今日从语文学层面疏理、解读古代典籍都容易陷入的误区。
钱钟书先生在辩析《左传·隐公元年》中“庄公寤生”之“寤”,“子姑待之”之“待”,“不义不”之为因果句而非两端句等等之后,联系中国学术史,把西方阐释学十分概要地展示给我们,说:“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旨。”又引戴震的文章彰显汉学的家法:“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躐等。”钱先生说,像这种由低走高、拾级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诠释,其实只完成了一半。还有另一半,那就是“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辞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如此“积小以明大,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释义之循环'者是矣。”[3]
我国自民元以来许多语文学者,大体是沿着乾嘉朴学道路走的。他们未尝不懂释义循环的道理;他们由字词到章句之后,肯定也会从章句回溯到字词,反复检验释义的稳妥贴切程度。但问题就在于,这个循环总体始终在语文学范围内:组句成章是否合乎条理,句法是否通顺,所释诸词的语义在句中各语位是否恰当——显然这是又沿着原来的路线缘阶而下,圆足只是这个小语境内的圆足。传统的《论语》语言学层面训解就是这么完成的。所以,即使杨树达先生援引那么多文献用为实证,因为一开始就从语文学出发界定了意义,证明只围绕五个命题证明,因此不可能增加任何新的东西,自然不容有任何突破。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笔者以为就出在阐释循环的后半段,即从整体返回局部的这一步。
首先在于我们如何看这个被局部合成的整体。假如我们像法国阐释学者保罗·利科那样,把《论语》的每一章都看成是一份完满的文本,就是说,它不是通常理解的那种随机记录的只言片语,而是一篇篇完整的文章,完整的“作品”,我们的理解立刻就会改观[4]。利科认为文本是阐释的本位,它建立在话语语言学而非语言语言学基础之上。话语(discourse)相当于汉语中的言谈或谈吐,它同索绪尔用以比照语言(Langue)的言语(parole)又不是一回事情,因为尽管言语己经被视为在人类社会交往中活化了的语言,但它既作为抽象规则和原理的语言对照范畴,那么它仍旧未离开作为共时语言学的界域,仍是一种抽象规定。而话语则不然,它的每一份即每一文本,都是在真实的语境中,是“活人”朝“活人”带有意向的言谈“事件”,因而对这种言谈的理解,只能在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围绕相关语境做动态的理解,而不是从词库(不论头脑记忆还是词典)中搜出意义,按句法组织起来达成那种静态关联。以人体为喻。文本式理解,要求从人的行走坐卧,整个机体运动中考核运动系统的器质和功能,而不是把人体放在手术台上“大拆八块”,解剖和观察骨骼、肌肉和神经的组织乃至细胞。
怎样从文本角度、立场去体会作品,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推演南宋张炎《词论》中对吴文英作品的批评,所谓“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那几句,有一段十分警策的言论。他说:“七宝之所以成楼台,可组织而不可拆碎”,就因为每个文本固然由词语构成,但它乃是由词人“熔铸以精心,运遣以遒笔,化零为整,以成片段,此藻采之所以组织,而七宝之所以楼台”。它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我们是在对整体的理解、欣赏中理解、欣赏这个整体,如果把它拆开,去掉按词人匠心安排的有机联系和在这种联系中发生的特有意蕴,变成一堆只拥有词典储备意义的词语,那它就完全改变了性质。所以先生又说,文本意蕴在“楼台弹指,而不在七宝拆碎。如云拆碎,岂唯七宝楼台,零碎珠玑,不成片段,即非七宝楼台,颓砖碎瓦,亦同零落。”[5]可惜这些精到的认识,在中国并未形成文本理论,今日需要,还须引进像利科这样“外援”!
这样,依据文本学的理念,我们下一步分析本章的结构。
首句“道(导)千乘之国”实际指的是公侯国主,即后面行为的发出者,它是本章的主词,后三句则是主词发出的行为。争论“千乘之国”之领地大小是无意义的,“千乘”是个模糊数字、象征符号,无非说它是周王朝分封的够规格的大国。那么以孔子名义宣示的这份“大纲”,从文本结构看究竟有几条呢?如果我们不盲从包咸,而是认真思索一下就会发现,以下三句本是三个并列的动宾分句,而且各被一个介宾结构修饰着,整理一下就是——
敬事以信,爱人以节用,使民以时。
或把介宾结构变为状语,成为——
信以敬事,节用以爱人,时以使民。
整齐后的表达式同原文的语意分毫不爽。由此我们看出,同“以时”作为“使民”的条件一样,“以信”是“敬事”的态度,“节用”是“爱人”的方式,两个介宾结构均为修饰语,不能同三个动宾结构等列而成为命题,古今的“五点说”实则是把当初的“三大政策”给碎片化了。还是前面那句话,如果我们动脑筋想一想,以标榜周礼的孔子名义宣示的领导公侯大国的规范,能够苛细到“讲信用,谨慎做事,节省支出,爱护民众”这等治百乘之家乃至十室之邑都用得上这种程度吗?包咸把秦汉以来地方官吏的开业术当成了西周大国的国策,显然既是社会历史的谬误,也是政治科层的谬误,用今日术语叫做模型讹谬。
那么,这三大政策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从三句的主干动宾词组可以觅得:一是“敬事”,“敬”这里是静词动用,“事”是什么容后专说。后两句“爱人”和“使民”,“人”和“民”是很有区别的概念,皇侃疏中已言:“人是有识之目,爱人则兼朝廷;民是暝之称,使之则唯指黔黎。”所以杨氏《译注》指明古代“人”有广狭两义,这里和“民”对言,用的是“指士大夫以上各阶层的人”的狭义,是精准的。这就清楚,后两句亦即“大纲”的第二、三项,分别是对国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二者应持的态度。由此不难推测,第一句即第一项的“敬事”,使用的动词“敬”比后面的“爱”更其庄重,其宾词“事”不只同“人”“民”一样属于有灵名词[6],而且地位应远在统治阶级之上。它是什么,我们迅速揭晓,因为它也是被古今诸家全部误解,又很可能是把包咸引上歧途的头一个伪标的,因之是破解的重点词语。
为了力求理解的客观可证性,我们在内在结构明朗化之后,下一步即寻找同型文本,在相互比照中也就是在文本互性中寻求理解。同型文本比照和近义词的比较一样,是切近语义的有效手段。
同型文本首先在《论语》的另一处。《宪问》第四十二章——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这里的“修己”就是“克己复礼”意义上的“克己”。本章“君子”是尧舜级的,面对的也是三类对象,二、三两类是“人”和“百姓”,当与“人”与“民”类同;一类已经出“敬”字,但对象未出。
以下再看《左传·庄公十年》连中学生都能记诵的“曹刿论战”。当齐国大军压境的时候,鲁庄公恃以为不败的国本是什么呢?
(1)“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2)“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3)“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其中之(1),无疑就是《论语》文本中的“节用以爱人”,而且让我们进一步明确,用来“爱人”的“节用”并不是一般地“节省开支”,而是专指国君本人节约用度,把自己的享用尽量简省下来加惠于臣下,以示君臣同体,且申亲亲之谊。第三句即第三项,《国语·鲁语(上)》的互文是:“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曹刿对曰:“是则可矣。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可证是对“民”的态度。在春秋传中是断狱中体察民情,在《论语》里是“以时使民”,事项不同,但同是如何在大事上体谅下层民众则是一致的。
后两项坐实了,我们这回把注意转到第一句即第一项。在《左传》(包括《国语》)中第二项是对天地祖宗的态度,能否同我们文本中的“敬事”、《子路》篇但存一“敬”字那句相互对应呢?对鬼神要持“敬”的态度,即一种诚惶诚恐既畏惧又崇拜的态度,这一点被李泽厚先生敏锐地觉察到了。他在关于本章的《记》中说:“‘敬'字多见于《论语》,乃一重要范畴,它既是一种外在态度,更是一种内在情感,源起于巫术礼仪中对上帝鬼神的尊敬畏惧,理性化后转为生活态度和情感要求,成为人性塑造的一个部分”。他认为这个“敬”字,经历了“由对鬼神的敬畏、敬重转化为对人事、伦常、政务的敬畏、敬重,再表现为对客观理则的敬重、敬畏”的发展历程,最后又提到巫术世界观之理性化乃中国古史及思想史一大关键等等重大问题。李先生不愧为一代学术领军人物,他把“敬”已经说透了,可是在这里却又说过了。他说“敬”的初义与宾语“事”之间其实只隔一层窗纸,居然没有被捅破,真是“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荫范谨按:事,祭也。《论语》中两次出现“子入太庙每事问”,还有“宗庙之事如(与)会同”,“事”全指祭祀。《诗·召南·采蘩》“公侯之事”,毛传:“之事,祭事也。”《周礼·宫正》“凡邦之事跸宫中庙中”,贾疏引郑玄:“事,祭祀也。”《礼记·礼器》“作大事必顺天时”,郑注:“大事,祭祀也。”《左传·昭公十六年》“有事于桑山”,杜注:“有事,祭也。”《公》《谷》二传中的“有事于太庙”“有事于武宫”等等,“事”也并指祭祀。
“事”之为义,同“敬”一样经历了由巫术到民事,由宗教到社会的过程。在甲、金文中,“事”与“史”“吏”同作,像以右手执贯穿一器之长竿,竿上飘出多条旗游一类带状物,它即后来的“中”字。此“中”当即《国语·楚语》史老教唆楚子“左执鬼中,右执殇宫”装神弄鬼的“中”,乃是大巫师召集、指挥鬼神的法器。所以“事”既指这种原始宗教活动,也指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史。史在上古与巫、祝同为宗教人士,他们分工有别,史多操觚摆弄文字与鬼神通往来,后来才成为帝王活动的记录员左、左史。“事”也一样,最初专指祭祀,后统指大事,直到泛指一切事务。综上言之,我们文本中的“敬事”,通过互文比照,再从文字形义上分析,完全可以证实它指的就是慎重而恭谨地祭祀上帝鬼神。前面我们说过,这第一项有灵对象必定高过国家统治阶级,它也只能是鬼神。
祭必言“信”,就如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中所说,指的是“祭神之物必依礼为之,不使超过规定”。鲁庄公说“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因为“加”不只是欺骗了神,盘剥了民,更主要是擅自改变祭者的身份,一种僭越不道,比如身为公侯而祭祀上帝,就证明有做周王的野心。因此祭祀必以信在《左传》中屡屡言之,如《桓六年传》:“祝史正辞,信也。”《襄公二十七年传》:“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昭公二十年传》:“祝史祭祀,陈信不愧。”等等都是。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中庸》),郊社之礼、尝之义是姬周王朝宗法制的精神和制度基础,是这个种性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以恢复西周礼乐制度为终身使命的孔子,必然把“敬事”上帝祖先置于执政之首。他对“事”是如此之“敬”:“子所慎者斋(祭祀前的净身净心)、战、疾”(《述而》),“入太庙每事问”(《八佾》《乡党》)又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俨然把自己看成了由里及表最合格的大主教。学界经常争论孔子的宗教信仰程度。问题的关键笔者以为,在孔子重要的不是上帝和祖先神灵之有无,而在于祭祀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模板,孔子所严加护持的是这个“礼”的观念和制度。
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也就是姬周种姓奴隶制的瓦解,从上层阶级对祭祀的态度鲜明地反映出来。鲁庄公已经把“敬事”置于“爱人”之后;《左传》围绕宗教和人事何者为先的重要言论,如随大夫季梁(桓六年传)、周内史过(庄二十三年传),都把民事置于宗教祭祀之前;到孔子时代,他的弟子子路就高调张扬:“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也把民事置首。所以到了战国儒学大师孟子那里,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道千乘之国这三大政策是古老的传统,是王朝为所封公侯大国制定的国策,因之也是周礼的一部分,在西周鼎盛期应是烂熟于政治家之口的公式和口头禅,所以在经典中可以发现很多互文,《左传》之外,如《墨子·尚同(中)》标榜古者圣王为政,事鬼神“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怠慢”,都是神、人、民三项;更早周武王在《牧誓》中指斥商王受:“昏弃厥祀弗答”(神),“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人),“暴虐于百姓,以奸究于商邑”(民),可见周王朝的三大纲领在那个时代已具规模。这些互文提示我们:《论语》编者把它书写在“子曰”之后,不过借孔子以重申和推重古礼,发明权并不属于孔子,这是我们治《论语》者应该明确的。像开始我们引述上海古籍版《译注》“段意”(荫范谨按:“段”字最无理,《论语》中各章多自成独立文本,并非一篇文章段落!)所总括“此章是孔子论治国的大纲”,“论”字远不如修正为“所坚守的”更为符合事实。
综上,笔者理解本章语意如下——
孔子说:“引导据有千辆兵车大国(的君主),要依礼的规定恭谨地祭祀,节省自身用度以加惠臣下,役使民众应当不违农时。”
三
现在我们从方法论角度,把对本章解读过程作一下梳理。
我们把前人、特别是当代几位名家的解说当作前理解,在此基础上把本章视为一完整、独立文本进行解读。这样首先理解孔子力推的“千乘大国”应是西周种姓宗法奴隶制分封的公侯之国;接着从直觉断出,治这样大国的要略一定是粗条条,不能是小块块,“五点论”肯定有问题。于是分析文本结构,果然现出整齐的各带介宾结构修饰语的三个动宾句;接着,由后两句“爱人”“使民”,反馈第一句的“敬事”,推出“事”是高于“人”的有灵名词,立刻就想到了《论语》“子路问君子”章和《左传》“曹刿论战”,再及季梁、内史过论祭祀与民事关系,由这些互文的平行比较,推断“敬事”一定指神;“事”的初义“祭祀”这时也涌现出来,再对它的形、义作一些分析,上述理解的理由更为充分。顺便地说,我们由互文关系推测,“子路问君子”章的“敬”后应脱了“事”字。这样我们就把空泛的“处理政事”改为“祭祀”,否定了古今的“五点论”而代之以三条纲领,使以孔子名义推出的这条西周盛世治国理政的理念、规范和金科玉律赫然展现人们面前。
显然,上述从整体理解局部这条路线,涉及到了两周历史,当时政治家治国的理念、经验,孔子的思想,宗教史、文字学等等,这也就是钱钟书先生提示我们“以大贯小”、“探本穷末”应涉猎的百科知识。如果我们的诠释最后仍要回到语文层面,那么上述涉猎的知识就都起到了扩大或改变语境的作用,包括整个文本的、句子的(或句群的)和词语的。从整体到局部,即把百科的把握斟酌转化为语文的理解,使二者高度相容,这应是“释义的循环”的最上乘境界。古人语略,不易把握,除了尽可能地廓清语境外,再一条就是了解古人的表达习惯,钱钟书先生所说“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辞异宜之著述体裁”所指即此;俞樾以下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诸贤更述《古书疑义举例》,发抉的尽是古人越出常规的表述习惯,理解古籍是绝不可忽视的。
[1]艾荫范.“德”在上古文献中的“志向”义[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8-52.
[2]艾荫范.《论语》语词新释举例[J].辽东学院学报,2013(4):66-70.
[3]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67-173.
[4]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5]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M].北京:中华书局,1993:725-726.
[6]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78.
On the Annotations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logy——A Case Study of“ Reining a Great State with One Thousand Chariots”in the Chapter of“ OnLearning”
Ai Yinfan
(Fux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ederation,Fuxin Liaoning12300)
As the initial code of Confucianism,Analects of Confucius hasthChapter“On Learning”as an example,the opinion generally accepted by academic circles regarded the chapter as Confucius'outline of governing a country,with which the author could not agree.The proper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Confucius said:As the king of a great state with one thousand chariots,one should offer sacrifice to gods and ancestors humbly according to the etiquettes,economize on personal expense to benefit his liegemen,and employ the masses at a proper time.”
the most thorough annotations among the ancient texts.It is commonly considered there left no confusion in the an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logy in spite of diversiform estimates of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us.Actually,that was not the case.Taking the 5
Analects of Confucius;the perspective of philology;cycle of annotations
I206.2
A
1674-5450(2016)03-0056-05
2016-02-25
艾荫范,男,吉林双辽人,阜新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责任编辑:杨抱朴责任校对:张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