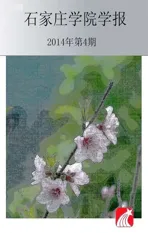中古史籍中的驼鸟“啖火食铁”考
2016-04-13张明
张明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中古史籍中的驼鸟“啖火食铁”考
张明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驼鸟作为古代中国的外来物种,在丝绸之路串联起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上扮演了积极角色。中国历代史籍对驼鸟形象都给予了关注,其中诸多史籍不约而同地记载了驼鸟啖火食铁的能力。这一现象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根据西域使臣或番客描述而记载,源于外邦使者或番客对驼鸟的夸张性描述。
驼鸟;啖火食铁;中西交流
历史上,驼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而进入古代中国。作为外来物种,驼鸟从汉唐以来就受到古人关注,古代典籍不同程度地记载了驼鸟的形象。从最初的简单叙述到后来外观特征、生活习性的描写,其中诸多史籍不约而同地记载了驼鸟具有啖火食铁的能力,本文即围绕驼鸟这一奇特能力展开探讨。
一、前人研究及问题的提出
驼鸟作为古代中国的外来物种,对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起到过重要作用。从历史学角度对驼鸟进行研究,当首推美国罗佛(Laufer,Berthold),罗氏对美索不达米亚鸵鸟蛋壳杯及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驼鸟作了详尽研究,[1]时至今日,对研究驼鸟仍具指导意义。日本田边胜美(Katsumi Tanabe)主要围绕人类不同器物上的驼鸟形象展开考察。[2]对于唐代史料记载的驼鸟,美国谢弗(Edward Schafer)[3]227-229及张星烺[4]198都进行了有益探讨,惜二者讨论简略。王建对张星烺一文作了深入的考释与补充。[5]68-71韩香撰文对驼鸟及驼鸟卵的传入时间及影响等有过详实考证[6],王颋对进入古中国的各种大型走禽尤其是驼鸟进行研究[7]39-56。另有学者对凤凰形象研究涉及到驼鸟,何新认为凤凰崇拜起源于上古石器时代的驼鸟,凤凰源于驼鸟①;刘金荣则认为驼鸟特征不符合上古文献中凤凰的区别性特征,孔雀才是凤凰形象的起源[8]。
笔者注意到,诸多史料记载驼鸟能啖火食铁,甚至粪便能入药,“人误吞铁、石入腹,食之立消”[9]1702,十分神奇。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驼鸟是杂食性动物,并不以火及铜铁为食,且笔者在现代中医药典也未见能使误食铁、石“立消”的“驼鸟粪”一类药,那古人记载驼鸟的这些神奇能力是一种凭空传说呢?还是同驼鸟一样,是一种“舶来品”?笔者通过梳理传统典籍对驼鸟形象的记载,结合现代研究,试对驼鸟“啖火”与“食铜铁”现象作一合理解释。
二、中国史籍中的驼鸟形象
驼鸟在中国历代典籍中有大鸟、大雀、大马爵、安息雀、驼鸡等称呼。中国典籍中最早记载驼鸟的是《史记·大宛列传》,其中记条支国“有大鸟,卵如甕”[10]3163,此大鸟即是驼鸟。张骞出使西域回中原后,安息曾“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10]3173。《汉书·西域传》亦载此事。驼鸟在汉武帝时已进入中原,《汉书·西域传》载:“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11]3928此大雀应即驼鸟,而外囿则指汉武帝的上林苑。外邦进贡驼鸟的明确记载是《后汉书》,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12]2198。可见,前三史关于驼鸟的记载并没有啖火食铁的奇异现象,也没有其体貌特征的描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驼鸟的记载逐渐详细,晋人郭恭义《广志》称驼鸟为“大爵”,特征是:“颈及(长),膺(鹰)身,蹄似橐驼,色苍,举头高八九尺,张翅丈余,食大麦。”[11]3890此处关于驼鸟的记载已经包含描述体貌特征。到了《魏书·波斯传》,我们开始看到了驼鸟“啖火”的记载:“波斯国……出白象、师子、大鸟卵。有鸟形如橐驼,有两翼,飞而不能高,食草与肉,亦能啖火。”[13]2271
收稿日期:2016-03-10
作者简介:张明(1987-),男,河北秦皇岛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研究。
①参见何新《“凤凰”补说》,载《河北学刊》1988年第3期,第92-94页;《谈龙说凤》,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页。
隋唐时期开始出现驼鸟“食铜铁”的记载,据《旧唐书》载:“吐火罗遣使献大鸟如驼,食铜铁,上遣献于昭陵。”[14]68《新唐书》亦载:“永徽元年,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铁,俗谓驼鸟。”[15]6252这里需要指出《旧唐书·波斯传》:“有鸟形如橐驼,飞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啖犬攫羊,土人极以为患。”[14]5312此处应是《旧唐书》将《魏书》与《梁书》的记载混在一起,前半部分取自《魏书·波斯传》,所不同者,“啖火”为“啖犬”,也许《旧唐书》作者并不相信这种大禽能“啖火”,并认为“火”乃“犬”字之讹,故加以篡改;后两句则取自《梁书》:波斯国“有鹫鸟啖羊,土人极以为患”[16]815,这显然是《旧唐书》误将驼鸟与鹫鸟混为一谈。另外,杜环《经行记》记载大食“有驼鸟,高四尺以上,脚似驼蹄,颈项胜得人骑,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17]5280。按天宝十年(751年),杜环在怛罗斯之战中被大食所俘,在西亚、北非等地游历10多年,这些地方正是驼鸟的栖息地,他有机会亲眼目睹驼鸟,故记载可信,但在杜环的记载里,并没有看到驼鸟能够啖火食铁。
这时期驼鸟虽仍稀有,但应为时人熟知,如唐代医学家陈藏器(约687-757年)曾记载:“驼鸟如驼,生西戎,高宗永徽中,吐火罗献之。高七尺,足如橐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食铜铁也。”并且认为驼鸟粪有“人误吞铁、石入腹,食之立消”[9]1702的功效。在唐以前,驼鸟的称呼多种多样,到了唐代,“驼鸟”这一称呼已经固定,说明时人对驼鸟形成了普遍认识。此时驼鸟一名,是唐人根据中古波斯语ushturmurgh(骆驼鸟)这种合成语写成的译名[2],这种称呼一直流传至今。
魏晋南北朝时期驼鸟能“啖火”,但未见有“食铜铁”的记载;而唐代驼鸟鲜见有“啖火”的能力,即是说,驼鸟饮食能力虽然奇特,但两个时期关注点并不相同。另外,唐人杜环并未记载驼鸟啖火食铁的现象,中原反而有此现象,不同区域的人对驼鸟的认识并不一致。
宋元之际,中西海陆交通发展迅速,交往密切,但并没有驼鸟进贡中国的记载,因此时人记载多是根据以往记载或番客之口,于是出现了将驼鸟“啖火”与“食铜铁”的神奇能力结合起来,即驼鸟能食“赤热铜铁”的记载。如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昆仑层期国又有骆驼鹤……食杂物炎火,或烧赤热铜铁与之食。”[18]113赵汝适《诸蕃志》记弼琶啰国(今非洲索马里沿海):“又产物名骆驼鹤,身项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甚高。”[19]102唐慎微《证类本草》:“驼鸟矢,无毒,主人中铁刀入肉,食之立销,鸟如驼,生西夷,好食铁。永徽中,吐火罗献鸟,高七尺,如驼,鼓翅行,能食铁也。”[20]828元人刘郁《西使记》:“海西富浪国,有大鸟,驼蹄苍色,鼓翅而行,高丈余,食火,其〔卵〕如升许。”[21]61周致中《异域志》:“大食弼琶罗国……地产骆驼鹤,长六七尺,有翼能飞,食杂物,或烧赤热铜铁与之食,生卵如椰子,破之如瓮瓮有声。国人好猎,日射兽而食。”[22]10
到了明代,驼鸟因郑和下西洋再一次进入中原,如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船队经过古里国,购得驼鸡以归。[23]8621《明史》中常见东南亚国家进贡驼鸡。[24]8448,8450,8453另外,史料中驼鸟啖火食铁的神奇能力并不多见。费信《星槎胜览》:“竹步国……驼蹄鸡,有六七尺高者,其足如驼蹄。”[24]19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下祖法儿国:“有禽焉,长身而鹤颈,足四尺而二爪,其状如骆驼,其名曰驼鸡,是食五谷。”[25]104金善《驼鸡赋》记载永乐年间“西南之国”进贡驼鸟,赋中称“永乐己亥秋八月吉旦,西南之国有以异禽来献者……皇帝御奉天门,特以颁示,群臣莫不引领快睹,顿足骇愕,以为希世之罕闻,中国所未见。其为状也,驼首凤喙,鹤颈凫臆,苍距矫攫,修尾崷崒,雄姿逸态,鸷武且力。衡不逾咫,高可八尺,名曰驼鸡。”[26]688马愈《马氏日抄·特迦香》也记载:“西域人进驼鸡在会同馆中……鸡高四五尺,毛紫赤色,长距大喙。”[27]35相比以前,明人的记载更加生动灵活。
需要一提的是,明初有一种大型走禽名为“火鸡”,如郑晓《吾学编》:“火鸡,大于鹤,颈足亦似鹤,软红冠,锐嘴,毛如青羊色,爪甚利,伤人腹致死,食炭。”[28]18陆容《菽园杂记》卷五:“尝闻火鸡食火,犀食棘刺,野羊刳腹取脂,脂复生……皆未之信。近日满剌加国贡火鸡,躯大于鹤,毛羽杂生,好食燃炭。驾部员外郎张汝弼亲见之。”[29]57-58这种火鸡即是今日的鸟纲鹤鸵目鹤鸵科的鹤鸵,即“食火鸡”,主要栖息于东南亚和澳洲北部,体型较驼鸟稍小,脚爪强壮锐利,因喜啄火炭,被称之为“食火鸡”。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驼鸟与食火鸡是同一种动物,这是错误的。[9]1702
有清一代未见有贡入驼鸟的记载,记载驼鸟的史料也不多见。南怀仁《坤舆图说》:“南亚墨利加州骆驼鸟,禽中最大者,形如鵞,其首高如乗马之人,走时张翼状,如棚行,疾如马,或谓其腹甚热能化生铁。”[30]786这里驼鸟“腹甚热能化生铁”是南怀仁听他人说的,本人应该并未见过。清代记录下了所见与“火鸡”形状相似的“大鸡”“驼鸡”。如陈王猷《观贡鸡歌并序》:“雍正己酉秋,暹罗国所贡也。鸡高可三尺许,大可八十斤。”[31]171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广南异物进驼鸡……鸡高三尺花冠翠,羽背有双峰,似驼之肉鞍也。”[32]19-4据上述史料来看,清代所贡“驼鸡”并非驼鸟,而是鹤驼,即“食火鸡”。因此,明清两代记载驼鸟出现“啖火”的现象,大多由于将驼鸟与食火鸡混淆在了一起。
三、对驼鸟“啖火食铁”现象的认识
中国古籍记载了许多可以吞火食铁的奇禽异兽,但多是神话传说,并无依据。然而古人笔下的驼鸟异食能力却非神话传说,而是确有其缘由。
首先古人笔下的驼鸟异食当非自己观察而来,而是源于番客之口。唐人得知驼鸟“食铜铁”最初源于吐火罗国使者的描述,以往西域使者进献驼鸟,唐人多以“大鸟”“巨鸟”呼之,如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西突厥使臣进献的驼鸟即被称为“条支巨鸟”[15]10,而到永徽元年(650年),吐火罗国进献驼鸟,唐人才第一次称之为“驼鸟”①《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认为“驼鸟”一词成为中世纪远东地区对驼鸟的俗称,而驼鸟古名在唐代并没有完全绝迹,如武德三年贡入的“条支巨鸟”。实际上唐以前的史料并不见有“驼鸟”的称呼,直到吐火罗使者的进贡,“驼鸟”这一名称才正式出现于中国典籍。参见谢弗、吴玉贵《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此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铁,俗谓驼鸟”[15]6252,因驼鸟在中原并不常见,“俗谓”当非唐人对这种鸟的称谓,而是吐火罗国等地区对驼鸟的俗称。当时波斯语称为ushturmurgh,即“骆驼鸟”,吐火罗使臣告诉唐人,而唐人据此简译为“驼鸟”。吐火罗国使者必定也会对驼鸟生活习性作一番介绍,因此,史料中一方面是唐人自己的观察,如“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翅而行”,另一方面“日三百里,能啖铁”应该是吐火罗国使者告知后得知的。对于贡入中原的这种珍稀动物,唐人极为珍重,唐高宗即将驼鸟献于太宗陵前,如果不知道驼鸟的生活习性,不可能饲铁,更不可能让它日行三百里。古代外邦使者或番客常常对进贡中原的物品进行夸张性描述,如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记载西胡撒马儿罕进二狮子并叮嘱:“每一狮日食活羊一羫,醋密酪各一瓶。”陆容对此不以为然:“狮子在山薮时何人调蜜醋酪以饲之,盖胡人故为此以愚弄中国耳。”[29]70再如,亲历驼鸟栖息地的唐人杜环记载驼鸟“颈项胜得人骑,行五六里”[17]5280,而吐火罗使者进献的驼鸟居然能“日行三百里”,其中明显有夸张成分。由于外国使者贡入的驼鸟珍贵稀见,中原人自然对胡人描述的驼鸟奇特习性深信不疑,后人以讹传讹,以致出现驼鸟能食“赤热铜铁”。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驼鸟不分年龄均有啄食行为,啄食砂粒等硬物有助于胃肌磨碎食物。驼鸟每天的啄食行为可多达3 000-4 000次,由于频繁的啄食行为,时常会吃入一些石子、铁片、钢丝、树枝等杂物,但会导致胃肠道阻塞等疾病。[33]为了满足驼鸟吞食硬物的需求,上世纪初的南非驼鸟养殖场还专门提供一定数量的石块和沙砾供驼鸟啄食。[1]因此,驼鸟“食铜铁”应该是古人对驼鸟生物行为夸张性的描述。另外,驼鸟的好奇行为也值得注意,驼鸟对任何事物都非常好奇,它们对发亮或浅色(尤其是黄、绿和白色)的物体最为敏感和好奇,开始接触时它们会用喙不停地啄,一直持续1-2天才会停止。[34]因此,驼鸟“啖火”应该与此有关。
明人笔下的驼鸟没有任何异食能力,相反,其食物只是简单的“五谷”。其主要原因如前文所述,明代驼鸟是随郑和下西洋进入中原的,没有经过番客的肆意吹捧,而明人似乎对驼鸟的记载也模糊不清②如金幼孜《驼鸡赋》记载驼鸡:“稽往牒而莫征,考载籍而难辨。”参见金幼孜《金文靖集》,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 24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另一方面,明代驼鸟产自阿拉伯地区,历史上的驼鸟在犹太人世界并不受欢迎,其肉也是不洁净食物,罗马帝国时期,驼鸟会在狩猎竞技中被猎杀,或作为食物,一些人还认为驼鸟吃进肚中的石头能治病,而直到穆斯林兴起后,驼鸟成为财富与高贵的象征。在穆斯林世界没有人会喂这种高贵的动物火或者铜铁,因此其独特的生活习性在阿拉伯地区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
至于驼鸟粪能使误食的铁石、入肉的铁刀“立消”,这是古代中医对驼鸟啖火食铁的附会——驼鸟连铜铁都能消化,说明驼鸟粪具有化铁石的功效,这显然毫无根据。正如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指出的,驼鸟几乎能吃所有的东西,但并不见得能消化所有的东西,驼鸟吞食硬物是为了更好地消化食物,但过量吞食则容易致病。现代驼鸟养殖业屡见有驼鸟因过量吞食异物而致病的例子③参见吕渭纶《原因不明的驼鸟食沙病》,载《北京农业》,1996年第7期第30页;何光明、孟国校《驼鸟误食异物手术一例》,载《浙江畜牧兽医》,1998年第4期第36页。,说明驼鸟并不能消化沙石等硬物。更有甚者,有人认为驼鸟粪能铸刀,如明人方以智在《通雅》中记载:“《唐书》吐火罗献大兽,食铜铁,日行三百里,其矢可铸刀,其言西域苍鹅饲铁取粪作刀,即驼鸟之类也。”[35]900这些现象当是与驼鸟能“食铜铁”联系在一起。这种附会在古代医籍中常见,如《饮膳正要》记载:“妊娠所忌:食兔肉,令子无声、缺唇。”怀孕妇女忌食兔肉,不然孩子将会是兔唇;又如鸳鸯“若夫妇不和者作羹,私与食之即相爱”的功效,这显然附会鸳鸯相守不渝的习性,实际上,我国古代文人有将兄弟比作鸳鸯的,而以鸳鸯比作夫妻,出现于唐代,[36]78因此鸳鸯肉的神奇功效是子虚乌有的。诸如此类将药效与动物习性附会在一起的例子十分常见,毫无科学依据,不足为信。
综上,通过梳理中国典籍中的驼鸟形象,尤其是驼鸟的“啖火食铁”,我们可以看到中原记载下的驼鸟不断丰富多元,作为一种动物,驼鸟形象更加立体鲜活,体现了古人对驼鸟的认识更加深入明晰。中国典籍中驼鸟的异食能力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根据西域使臣或番客描述而记载。驼鸟由于自身生物特性而出现的这种异食能力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经过西域使者或番客的夸张性描述,加之传统中医的附会传说,使得驼鸟身上笼罩了一层神秘面纱。驼鸟“啖火”“食铜铁”的习性同它的名字——“骆驼鸟”一起传入中国,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人的视野,更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繁荣发展的一个例证。
[1]Laufer Berthold.Ostrich Egg-shell Cups ofMesopotamia and theOstrich in Ancientand Modern Times[J].Field Museum of NaturalHistory inChicago,1926,(23):1-50.
[2][日]田边胜美.所謂大鳥、大鳥卵にする西アジア美術史的考察[J].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82,(89):18-27.
[3][美]谢弗,吴玉贵.唐代的外来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张星烺,朱杰勤.唐人所记中亚之动植物[M]//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
[5]王建.张政烺编注《唐代所记之动植物》摭证[M]//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
[6]韩香.鸵鸟及鸵鸟卵传入中国考证[J].西域研究,2009,(3):60-72.
[7]王颋.条支大雀——中国中近古记载中的大型走禽[M]//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刘金荣.凤凰驼鸟说质疑[J].浙江社会科学,2008,(7):81-85.
[9]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3]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刘喣.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7]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8]周去非,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9]赵汝适,杨博文.诸蕃志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0]唐慎微.证类本草[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21]刘郁.西使记[M]//王恽.玉堂嘉话.北京:中华书局,2006.
[22]周致中,陆峻岭.异域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3]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4]费信,冯承钧.星槎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1954.
[25]黄省曾,谢方.西洋朝贡典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6]金幼孜.金文靖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27]马愈.马氏日抄[M]//丛书集成初编:第289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8]郑晓.吾学编[M]//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9]陆容,佚之.菽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0]南怀仁.坤舆图说[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31]陈王猷.观贡鸡歌并序[M]//澳门纪略.中国方志丛书:第10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32]吴伟业.梅村家藏稿[O].宣统三年董氏诵芬室刊本.
[33]李华周,韩永利,阎立新,等.鸵鸟行为及其利用与防患[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1,(3):294-298.
[34]杜安娜,彭克美,宋卉.人工育雏期非洲鸵鸟的行为[J].养殖与饲料,2006,(5):39-42.
[35]方以智.通雅[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36]忽思慧,尚衍斌.《饮膳正要》注释[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程铁标)
Toward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Ostrich's"Eating Fire and Iron"
ZHANG Ming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The ostrich,as an alien species of ancient China,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 through the Silk Road.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image of the ostrich in Chinese historical books,in which the saying that an ostrich had the ability to eat fire and iron is recorded.This phenomenon is not fabricated but recorded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s from Western envoys,who exaggeratedly depicted ostriches'habits.
ostrich;"eating fire and iron";China-West communication
1673-1972(2016)04-0045-04
K20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