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的理念与现实——以古典共和治国纲领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分析
2016-04-13张凤阳
张凤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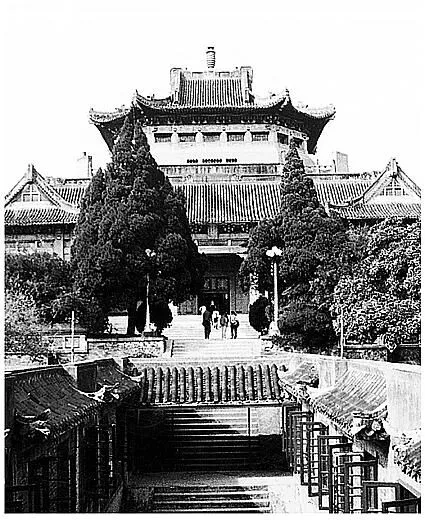
公共性的理念与现实
——以古典共和治国纲领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分析
张凤阳
摘要:“公共性”是共和传统所确立并一贯秉持的治国宗旨。在古典共和时期,基于这一宗旨的国家治理有两条主要进路。一条进路是:为确保“天下为公”,怎样通过教化和培养,引领公民对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做出优先选择?可称为“德治”。另一条进路是:为免于“天下为私”,如何借助混合与均衡,防范公权蜕变成操控在个别人或个别集团手中的私器?可称为“法治”。考虑到当今条件下的良好国家治理依然要环绕“公共性”的价值中轴,设法达成“德治”与“法治”的动态平衡,因此,对古典共和治国纲领做类型学分析,就不是单纯的知识考古,而应被视为一项有现代启示意义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公共性; 古典共和传统; 公民美德; 混合政制
在今日政治话语中,“公共性”的价值正当是不言而喻的。说“公共”权力应该且必须在“公共”的轨道上运作,以增进“公共”的利益,时下已不限于知识界的学理论述,而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广泛意义的公众信念。这种信念源自哪里?其本然意涵究竟是什么?如何在公共性理念的导引下进行制度规划?怎样才能准确理解实施良好国家治理所应遵循的行动方针?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深入挖掘古典共和传统的政治文化遗产。
追溯共和传统的源头,人们会把欣赏的目光投向古希腊和古罗马。但是,雅典、斯巴达和罗马的治国模式,事实上有着不小的分别;及至当代,在共和主义阵营内部,也仍能听到“新雅典派”和“新罗马派”两种不同的声音*大致说来,阿伦特(Hannah Arendt)、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等人属于“新雅典派”;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佩迪特(Philip Pettit)等人属于“新罗马派”。。按照“新罗马派”的看法,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共和国,对外不受他人的统治与胁迫,对内免于暴君的专制和奴役,所以,其根本特征可界定为无支配的“自由”(佩迪特,2006:40)。 “新雅典派”则强调,公民在私人-社会领域享有不受无理干涉的“豁免权”,远不意味着在公共-政治领域享有商议国家事务的“参与权”。考虑到普通个人的自由身份或能为一个绝对君主掌管的法律所保护,因而,只有透过公民积极参政的“民主”,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共和传统的精髓(波考克,2012:60)。在学理意义上,共和主义家族的内部之争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能否以及如何逻辑地提炼古典共和传统的“理想类型”,进而对“新罗马派”与“新雅典派”的观念分歧提供一种互补性解释呢?
众所周知,“共和”是英文“republic”的汉译,而“republic”一词来自拉丁文“res publica”,意指“公共财产”或“公共事业”。如果以此为着眼点,把“共和”的核心价值诉求理解为“公共性”,那么,“公民美德教育”与“混合均衡政制”这两个深受古典共和思想家推崇的基本治国方案,在理路上便显得十分通畅。前一个方案是“积极”的:为确保“天下为公”,应该教化和培养公民,引领他们对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做出优先选择。后一个方案是“消极”的:为免于“天下为私”,理当设置一种限权架构,防范公共权力蜕变成操控在个别人或个别集团手中的私器。这样,古典共和传统的“理想类型”就可以逻辑地概括为“公共性”导引的“德治”和“法治”。若谓“德治”方案旨在塑造品格高拔的积极公民,“法治”方案旨在防控任性妄为的专制力量,则“新雅典派”推崇的“民主”和“新罗马派”偏爱的“自由”,便不过是一套完整的共和治国纲领的局部性论点而已。本文将尝试解释这套治国纲领的内在理路,并就其当代启示意义作扼要说明。
一、 “天下为公”的治国理念
按照当今的流行表达,“共和”通常被说成是一种对应于“王政”的政体类型,而且,走向“共和”的历史进步意义,往往在“反暴君专制”的极化形式上予以确认。这种表达原则上没错,但它多少忽视了,关于“共和”的价值证成,恰恰需要对“王政”做某种理想化的勾勒。唯有这样,才能更充分地显示两者在治国理念上的实质差异,进而说明,“共和”如何以扬弃的形式将“王政”的合理因素包含于自身之中,并通过对“王政”局限的克服而实现了政治文明史上的划时代变革。这样的证明方式尤其适用于古典情境。
在城邦时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王政”曾一度流行,然而,像古代东方社会那种王位世袭和大权独揽的绝对君主,却是少见的。早期雅典、斯巴达、罗马列王的即位,一般要经过某种形式的推举,而且,元老院、人民大会一类的议事机构,事实上也都是“王政”时代的创制。因此,从“王政”到“共和”,并不意味着决然的历史断裂。但问题是,即便那些对贤明君王怀有乐观期待的古典思想家,也喜欢把“王权”类比为“父权”。柏拉图曾勾画过一个命令发布的纲目,大略是:父亲命令子女;门第高的命令门第低的;年老的命令年轻的;主人命令奴隶;有力量的命令没力量的;有智慧的命令没智慧的;祭司命令俗众(布舒,2006:47)。透过这个纲目,自不难揣摩,慈爱、仁厚、智慧以及神明所托的至尊和威严等等,差不多就是关于君王之“好”的可能想象了。
需要指出,一些被奉为共和思想奠基者的古代哲人,例如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也不是在抽象意义上无条件地否决“王政”。按照他们的看法,如果君王主持公道,关爱国民,遵循礼法,倾心维护共同体的公共福祉,那就理当称之为仁政并予以首肯(亚里士多德,1995:132-133)。但亚里士多德提示说,“家政”与“国政”之间的类比不好引申得太远。因为,家长管束的是子女及家奴,而政治家统领的却是“平等的自由人”(亚里士多德,1995:19)。前者属血缘-宗法关系,重在“情”;后者属政治-法律关系,偏于“理”。职是之故,期待君王对国民就像家长对亲属那样从心底生发出一种深深的爱怜和体恤,实乃奢求,何况还有数不胜数的昏君和暴君。历史教训告诉世人,先王也许圣明,可庸才子嗣继位或无道僭主上台,却往往撕破仁爱面纱,不仅在统治中一味诉诸强力,还会益发残暴,最终变成吃羊的牧羊狗。退一步,就算是那些罕见的有道君王,骨子里也把百姓视为子民。不论他怎样行仁政,都改变不了其政治统治的奴役本质。因为,奴役的本质在于“支配”,而不是“实际的干涉”,正如当代共和主义学者佩迪特所强调的那样:“即使奴隶的主人被证明完全是仁慈宽厚的,他或她也仍然在支配奴隶。”(佩迪特,2006:41)在这个意义上,“共和”与“王政”秉持完全不同的价值信条。对“王政”来说,最好的国家治理不过是“大私”即“大公”;但就“共和”论,视“公天下”为“私天下”,乃根本性的腐败,断不可取。所以,西塞罗强调,唯其在“公法”和“公益”的基础上聚合人民,将国家当作一项“公共事业”来治理,才可以谈论货真价实的共和国:
国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西塞罗,1997:39)。
如果联系罗马共和国的良好政治实践来解读这段文字,至少可以作出如下推论:(1)国家是属于全体公民的“公有物”,而不是属于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私有物”。所以,(2)公共权力体系应向各代表性社会力量敞开,而不能为一家一派排他性地把持。这意味着,(3)公共事务的议决,要经广泛审议,而不可单方独断。进而,(4)遇有矛盾分歧,宜按合法程序并用和平方式来化解,而不能动辄武力相向。这又要求,(5)参与国家治理的公民个人或团体,应将维护和促进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摆在优先地位,而不能假借公权来满足私欲。概言之,“公共性”乃“共和”的价值中轴,举凡权力的配置、政府的组织、法律政策的制定、群体诉求的协调、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国民福祉的增进等等,都必须环绕这个价值中轴来进行。
通常认为,按地域组织国民构成了国家的一般形式特征。库朗热以其精到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原始信仰依然保持强大影响的古代条件下,要将若干血缘-宗法族群结成既定空间版图内的政治共同体,一种有效凝聚邦民的“新型宗教”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古代立法家设立城邦祭坛并推行公餐制度的缘由(库朗热,2006:147-148)。现今的史学研究和政治学分析均表明,掌控城邦的“祭祀权”乃君主统治的首要关切,因此,面对城邦保护神所行的宗教仪式,不但要把各原生族群的众多成员聚合成休戚与共的“我们”,还得把“家—国”共同体置于君王的最高统领之下。“王权把所有事务环绕在一个至高的中心四周,并将它们组织起来。它的合法性源于神授。”(安德森,2005:18)这就是“王政”的价值根基。
古典共和思想家并不否认,血缘亲情具有天然的聚合力,但问题是,对一个按地域组织公共生活的政治共同体来说,将城邦的稳健寄托于“前政治”的血缘—宗法关系终归是不可取的。亚里士多德强调,人们之所以进行政治联合,根本目的是要追求一种“最高的善业”,因此,城邦在发生顺序上看似后于个人和家庭,但就本性而言,却先于个人和家庭,其道理就好比“全体”先于或高于“部分”一样(亚里士多德,1995:8-9)。古典共和所面对的问题情境是,如果原始的宗教资源不能径直征引,那么,何以把一个个分立的“部分”聚合起来并将“全体”的诉求置于优先地位?根据库朗热的考察,在城邦发展史上,随着被保护人的解放,平民力量的崛起,以及城邦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个问题愈显突出。如是,怎样确立一个能够凝聚民心的新的政治正当性理据,就成了实施良好国家治理的关键所在。库朗热认为,古代共和国的创制之所以是一场“革命”,与其说是在明面上打到了某位“暴君”,不如说是通过诉诸“公共利益”而从政治文化的深层解构了“王政”的价值基础:
现在进入了新时代,旧的传统和宗教已无能为力。从今而后,唯有公众利益才是一切制度的力量所在,它超越个人意志而令人们服从。这就是罗马人所谓的res publica(公众事务),希腊人所谓的τó χοινσν(公共利益),它是古老宗教的替代者。从此制度及法律都因它而兴废,城邦中一切重要的事物都视它而决定。从此以后,人们在元老院或民众大会上讨论法令或政体,个人权利或政治制度时,不再请教于宗教,而问公共利益如何(库朗热,2006:298)。
用现代性的政治话语来说,共和国既是一项“公共事业”,则为全体公民谋幸福,便构成其最基本的治国宗旨。这是天然正当的绝对命令。佩迪特将这项命令表述为“完全且只能服务于人们共同的和公认的利益”,并特别强调了三个否定性的约束条件:“禁止国家考虑那些被认为是不关乎公民之‘利益’的善;禁止国家考虑那些被认为是不关乎‘公认’之利益的善;禁止国家考虑那些被认为是不关乎‘共同’之利益的善。”(佩迪特,2006:378)据此,它宣布那些夸夸其谈的“无为”国家是非法的;它宣布那些强奸民意、独断专行的“家长制”国家是非法的;尤为重要的是,它宣布那些只考虑个人、家族或集团私利的“派系”国家是非法的。假使打一个比方,也许可以说,“公共利益”俨如共和国祭坛上的一位新“神主”,它作为制度安排和施政方略的终极正当性理据,在功能意义上,不啻是一种世俗版本的“政治神学”或文明政治生活的“公共宗教”。
与古老的宗教相似,经过长期规训,这种“公共宗教”已融入公民的精神血脉,成了他们坚定不移的政治—道德信仰。在公共生活中,捍卫“公共利益”乃一神圣律令,不仅向既定的政府组织永远发出“应当如何”的价值诉求,而且提醒人们对以公权谋私利的“政治腐败”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与古老的宗教有别,“公共利益”之于共和国的公民,不独需要情感的虔敬,更意味着理性的论辩。库朗热指出,从前在“王政”时代,城邦利益在特定情景下的确认,或听凭君王独裁,或信从教士占卜,或两者兼而有之,于是,国家治理便实质性地呈现为某种“政治巫术”。而“共和”时代的到来,则开启了国家治理的“脱魅”过程。它向世人宣告,在价值信仰层面,捍卫“公共利益”是无条件的;但在政策规划层面,何为“公共利益”却是可讨论的。“要知道公共利益是什么,最简单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召集民众,咨询他们的意见。”(库朗热,2006:298)这样,“共和”便昭示了一个理性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政治发展路向。
当代共和主义思想家阿伦特强调,在实现机制或呈现方式上,“公共性”意味着“公开性”和“公众性”(阿伦特,1999:38)。因此,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不是王宫密室,而是向全体公民敞开的透明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民为商讨公共事务而集会,或慷慨陈词或悉心倾听或相互激辩。同时,公正的法律和规范的程序,又为化解分歧提供了游戏规则,遂使集体共识得以达成。因为亲自出场,直接参与公职人员的选举及公共事务的议决,公民便在心底滋生一种担当国家主人的强烈感受;反过来,这种感受则进一步激发其政治热情,从而鞭策他们以更加自觉和积极的姿态履行公民义务。这样,在共和国与公民之间就确立起一种牢固的共生关系。阿伦特将这种关系模式描绘为一个“共有的世界”,说公民进入这个世界,就像一群老友围绕一张桌子落座,既彼此区分也紧密相联(阿伦特,1999:40-43)。谓之“命运共同体”。
从根本上讲,这种“命运共同体”的属性不是“血缘—宗法”的,而是“公共—政治”的。西塞罗有言:“任何社会关系都没有国家把我们联结得这样紧密。父母是亲爱的,儿女、亲戚、朋友是亲爱的,但祖国则包容了我们所有的爱。”(Cicero,1991:23)因此,属于同一个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信奉同一个神祇,尽管易于形成认同,却不是爱国的充足理由。共和国之所以成为公民的忠诚和热爱对象,归根到底是因为它的优良政制和公正法律承载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公共善。在这样的关系模式中,公民为祖国的伟业而自豪,并愿意担当责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同时也为祖国的危难而忧心,所以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勇敢地奔赴战场,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古典共和传统所极力高扬的公共精神和公共情怀。
二、 培育优秀公民的“德治”
在古典时期,培育优秀公民的“德治”通常被视为一项基本国策。一种代表性说法是,城邦的治理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性格的高下”,因此,必先提升人民的素养,然后才好谈论“较高的政治制度”(Cicero,1991:23)。详细评述古代立法家和思想家出具的各类“德治”方案,超乎一篇短文的可能驾驭水平。为便于理解古典共和的治国理路,不妨通过几个简单的设问,看一看“公共性”的价值诉求如何在教育实践中得到了贯彻。
——共和国为什么要兴办育人工程?
在古典语境中,“德性”(Arete/Virtue)一词的原意是“优秀”和“卓越”(麦金太尔,1995:154)。要活得出众、高贵而不能平凡、庸俗,这是古典伦理反复叮咛的人生意义之所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德性就是一种使人成为善良,并出色地运用其功能的品质。”(亚里士多德,1992:32)一般而言,特定“功能”的出色发挥要依托某种不凡的“天赋”和“技艺”,譬如擅跑之于运动员、口才之于演说家等等,但是,仅当服从和服务于正确的目的,超凡的“天赋”和“技艺”方能在根本上成就人格的“卓然”与“高拔”。因此,从“目的—手段”的辩证关联来看,广义的“德治”差不多就是“公民教育”的同义语,其实质是“以德驭才”,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古典时期的主流政治思想家,通常都强调国家的某种伦理目的。在“王政”体制下,这种伦理目的的达成,主要仰仗“明君”,间或也诉诸“贤贵”,至于“良民”,除对统治者的忠诚和恭顺外,并不需要什么参与政事的公共美德。但是,“共和”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一方面,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共和国的政权由全体公民来“共享”,共和国的事务由全体公民来“共治”,所以,公民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以及积极影响公共决策的强烈的主体效能感,便成为共和国政治过程的一个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出于“公共性”的要求,公共权力又不可被假公济私地使用,公共论坛亦不能沦落为集团私利的博弈场所,公共秩序更不能被偏执情绪和过激行为所滋扰破坏。这样,对共和国的良好治理来说,公民教育就显得格外重要,堪为一项基础性的政治文化建设工程。
——公民美德教育有何原则要求?
大略而论,公共精神不外“奉公”和“守法”两端。因此,共和国的良好治理首先要求,进入政治过程的每一位公民都应将“公共利益”摆在优先地位。他们可以陈述个人见解,也可以相互质询和论争,但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商国是,根本是为了寻求促进公共利益的最佳方案。这同时又要求,参与公共决策的每一位公民都必须遵守法律及有关程序,并本着“公共理性”的原则,对自己的意见或建议提供可以合理辩护的正当理由,而不可一味突出个人偏好,甚至进行不法威胁。“一个共和主义的公民不是一个任意妄为地、冲动地或鲁莽行事的人,而是一个按照他或她也参与制定的法律行事的人。”(达格,2007:200)
西塞罗强调,相对于普通公民,政府官员应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道理很简单:公共职位实质性地联系着有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因此,一当政府官员丧失道德约束,共和国就会被拖进政治腐败的漩涡。在西塞罗看来,“任公职”意味着“做公仆”,所以,为官之德的精髓在于全心全意为共和国服务。这尤其要把握两点:一是关切“民众的福祉”,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不计较个人得失;二是着眼“国家的整体利益”,顾全大局,不可偏袒一部分人而辜负其余的人(Cicero,1991:33)。若普通公民克己奉公,政府官员一心为公,共和国的良好治理岂不就水到渠成吗?这是理想的期待。
——哪个领域才能展现公民的优秀和卓越?
客观地说,古代共和国公民的私人生活绚丽多彩,这已为史学研究所证实*可以参见利奇德:《古希腊风化史》,杜之、常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基弗:《古罗马风化史》,姜瑞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但是,“实然”与“应然”之间往往存在紧张。在古典共和语境中,经营私人事务及获取私有财产的合理性之被肯认,仅限于为参与公共生活提供必要保障,而其本身并无什么“目的论”意义的自足价值。阿伦特指出,“阻止城邦侵犯其公民的私人生活并使每份财产的界限保持其神圣性的,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对私有财产的尊重,而是这一事实: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房子,那他就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因为他没有适合自己的立足之地。”(阿伦特,1999:23)比较起来,在古典公民美德教育方案中,反对将私人事务凌驾于公共事务之上,还只是一种“弱”表达,其“强”表达见于伯里克利的那个著名演说:“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修昔底德,1997:132)在私人领域,一个人可以做营生聚财富,可以居家安乐,也可以交友联谊,所以会自然而然地勾起人们的欲望和兴趣。但是,按照古典共和的价值观,沉溺于私人生活而不能自拔,是一种堕落,只有投身公共领域,一个公民才能超越狭隘的私密体验而打开一道公共性视界,进而以其睿智的见解和果敢的行动,在开放透明的政治舞台上展示作为大写的人的德性辉光。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动物”优于和高于“社会动物”*在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来,古典共和对私人生活的贬抑,很有些道德专制意味,不足为今人效法。关于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之争,需要做专题讨论,这里暂且搁置。。这也就是为什么阿伦特着意强调“卓越”一词仅仅与“公共领域”相关联。“公共领域是为个性而保留的,它是人们能够显示真我风采以及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唯一一块地方。”(阿伦特,1999:32)如果对这块地方再行区分,便有两个典型场域,即保家卫国的“战场”和公共论辩的“广场”。
——“勇敢”的武德如何在爱国主义框架中恰当表述?
一般认为,“爱国主义”典型体现了共和国公民的公共情怀。正因如此,“勇敢”便在“共和”的美德谱系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面对死亡而不畏惧,就是“勇敢”(亚里士多德,1992:53)。但严格说来,“勇敢”既非“胆怯”亦非“斗狠”。英雄在征战搏杀中展示的豪迈气概固然令人敬仰,但是,将“勇敢”尊为崇高德性,并不因为它是单纯的个人品质,而在于它是一种捍卫共同体所必须的公共品质。为了超个人的价值而勇敢地冒险和献身,乃是休戚与共原则的杰出体现,所以应该得到崇高的荣誉。反过来看,“某个把荣誉当作如此伟大的善的人,必将志愿冒生命之险并准备勇敢地去死。”(麦金太尔,1996:58)这是一种高贵气节。它不仅因为勇武和刚强,更因为源于公共责任感的克己和忠诚,而显得庄严伟大。在古典时期,尚武之风盛行者,先有斯巴达后是古罗马,其典型的公民形象,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农夫—战士。自古至今,军人的诸多品质,如勇武、坚毅、果敢、吃苦、奉献、团结、守纪律等等,都受到不少思想家的推崇。不过必须指出,仅仅用“武德”来附会“爱国”,却是片面而有害的。亚里士多德在很多方面修正了柏拉图的论点,可他十分认同老师倡导的这一原则:立法的根本宗旨应落脚在操持“和平”而不是“战争”(亚里士多德,1995:389-394)。西塞罗说公民对祖国的忠贞和奉献是一种比亲情友情更具包容性的大爱,但他关于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审慎区分却提醒人们,切不可把“爱国”等同于“黩武”(西塞罗,1997:112-113,120-121)。辩证地看,在共和国面临生死存亡的非常时刻,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听从祖国召唤,奔赴前线,奋勇杀敌,这是他的义务;而在和平时期的常态国家治理中,每一个公民又应该与其他伙伴成员一道,围绕公共事务展开讨论,就公共政策的制定进行对话和协商,这也是他的责任。唯其透过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发明,才能对“公民爱国主义”给出完整而准确的理解(Maurizio Viroli,2002:69-70)。由此推衍,“勇敢”之为美德,也就不独表现在激烈厮杀的“战场”,还表现在自由论辩的“广场”。以身殉国的赤诚无畏令人感动,主持公道、捍卫公益的大智大勇不是同样令人敬佩吗?
——“雄辩”的文才何以成为积极公民的必备修养?
阿伦特尝言,纯粹的暴力是“无声的”,不过是动物性的“前政治手法”。相形之下,国家的良政善治,“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言辞和劝说而不是强制和暴力来决定。”(阿伦特,1999:21)因此,在共和国的公共空间里,到处都充满了“声音”:法庭辩论天天举行,公民大会常有演讲和议决,就是在散步途中偶遇,也会为共同关心的公共事务争得面红耳赤。按照议事规程,政治论辩当然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无理取闹;但是,确认并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发言权,却是共和国的首要政治法则。如果用暴力强迫人们就范,仅是权贵出声,而整个社会陷入沉寂,那怎么可以妄称“公”、“共”、“和”呢?
在古典时期,雅典民主将论辩之风推到了极致。后来的罗马共和国不能完全与之媲美,却也是积极推行。关键在于,共和国既是“公天下”,则公共审议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其国家治理的常态。当代共和主义思想家斯金纳指出,投身公共生活的公民需要具备两项基本的参政议政能力:“发现真理的理性和使他的听众接受真理的口才”(斯金纳,2005:87)。因此,“修辞术”和“雄辩术”就成了共和国公民教育的重要项目。西塞罗认为,生动感人地表达公共利益,能产生凝聚民心、催人奋发的效果。所以,共和国的善治,首先要求政治领导人出色掌握并灵活运用雄辩术,以说服民众接受合乎公共利益的法律及政策。普通公民或许不具备演说家的天赋和技能,但他们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以便对公共舞台上的各种主张做出独立判断,并择善而从之(西塞罗,2007:320)。按照古典共和的美德伦理,不管是健硕的体魄与高强的武功,抑或是精妙的修辞与激扬的雄辩,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工具性的“技艺”。某些人对这类“技艺”的掌握和运用可能达到了“卓越”的地步,所以显得出类拔萃。但不能据此断言,他们就是共和国的栋梁之材。西塞罗强调,目的论意义的公民之“好”,在于对共和国满怀忠诚,自觉自愿地服从和服务于公共事业,“恪守信仰、遵循公正”,不仅“为共同的利益工作”,必要时还“为共同的利益献身”(西塞罗,2007:141-142)。概言之,只有以德为先,德才兼备,才能充分展示共和国优秀公民的整体形象;而培育这样的优秀公民,则是一项关系到共和国能否永葆“公共性”的长远大计。
三、 防范公权私有化的“法治”
从逻辑上说,公民美德乃良政善治的可靠保障,因为,当家作主者品格高拔,断不会以权谋私和假公济私。但现实地看,人不是天使,也成不了天使。所以,“德治”方案究竟能取得怎样的极限成效,是不好盲目乐观的。事实上,古典共和思想家之所以突出“公共事务”的价值优先地位,正由于他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私人事务”几乎会天然地成为人们的首要关切。大量政治腐败案例提示人们,公共权力不受限制地操控于一人之手会被滥用;不受限制地操控于少数人之手也会被滥用;若掌握在多数民众手里而缺乏有效制约,其滥用同样会达到惊人的地步。如是,一种旨在防范“公权私有化”的混合均衡政制,便顺理成章地进入古典共和思想家的视域,并受到了高度评价。
在古典时期,混合均衡政制的萌芽形式见于诸多城邦,而其充分展现,则无疑在罗马共和国。有史学家解释说,对罗马共和国的观察,若只注意执政官的权力,便好像是君主政体;倘只注意元老院的权力,又似乎是贵族政体;如只注意人民大会的权力,则仿佛是民主政体。而罗马人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使这三种权力既彼此掣肘又相互配合,从而达成了某种良好的动态平衡。按照西塞罗的概括,混合均衡政制取三种良好政制之精华,它包含了“卓越的王政因素,同时把一些事情托付给显贵们的权威,把另一些事情留给民众们决定”(西塞罗,1997:60)。考虑到这一论点已为人熟知,因此,有必要附加探讨的是,兼具“混合”与“均衡”双重特征的古典共和政制及其运作,对思考现代性的国家治理有什么启发?
历史经验表明,大国治理需要一个慎思明辨的立法机构,也离不开一个执行有力的行政系统。曼斯菲尔德认为,罗马执政官就是一个“在共和主义背景下可以称为强大执行官的人”(曼斯菲尔德,2005:84)。依据罗马共和国的典章制度,执政官握有最高行政和军事权力。召集元老院和人民大会,提出议案,负责执行通过的决议,固属其职权范围;而维护国内治安,代表国家与外邦交涉,特别是作为军队最高统帅在军事行动中行使临机处置大权,更凸显了其强力威势。执政官的名字还用作共和国的纪年,加上其在主持国家的宗教仪式、庆典活动等方面所扮演的醒目角色,一些历史观察家透过执政官的作为而看出某种君王气象,想来是很自然的。
谁都清楚,拿执政官类比君王只是一种隐喻,不好较真。在历史上,无道君王的暴虐统治曾给罗马人留下痛苦的记忆,所以,自打废“王政”的那一天起,防范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专权,就成了共和国的一项头等任务。罗马人采用的办法是执政官的选举制、限任制,还有同僚协议制。时至今日,除采用委员制的国家外,已很难在政府系统的金字塔顶找到彼此可以依法行使否决权的“双头”或“多头”。当代政治学者从罗马行政长官的称谓引出一个“普力夺”(Praetorian)概念,用来描述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衰朽乱象,似乎是在暗示,同僚协议制无力缔造一个强大政府(亨廷顿,1988:175-181)。但罗马人也有弥补“双头”执政官缺陷的举措,那便是“独裁官”(Dictator)的设置。西塞罗辩称,在共和国遭遇外患或内乱的非常状态下,按法定程序给一人授予临机决断的全权,对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西塞罗,1997:55)。问题在于,一当这个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的非常举措被抛开短任期限制而变成政治生活的常态,“独裁官”就异化为我们所熟知的那种“独裁者”了。因此,罗马共和国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是,良好的国家治理需要一个强大的执行官,但这个执行官必须接受民主与法治的严格约束。
自古至今,基于元老院的权威影响而断言罗马共和国的贵族属性,俨如定论。这个定论当然有根据。在名义上,虽说元老院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但由于每届执政官任期很短,开疆拓土又使人民大会显得笨重,因此,以稳定、连续及灵活见长的元老院,便在事实上成了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在共和时期的罗马,执政官采取的每一项重大行动,事先都要向元老院垂询;人民大会通过的法案,一度也要经元老院核准才能生效;元老院不但对行政官员进行指导和监督,还管理财政,掌控国家的公共收支;此外,在军事、外交和宗教事务等广泛领域,随处可见元老院的权威身影;而且,元老院的决议,习惯上也都是被人们当作法律来遵守的。透过罗马国家的正式名称——“罗马元老院及人民”,自不难体会,元老院的位阶是多么显赫了。
在“民主”成为强势话语的今天,“贵族共和”常常遭人诟病。歧视平民的门阀做派和富人政策,大概是民主人士指控元老院当家理政弊端的主要论据。从“实然”的历史状况来看,这样的论据确凿无疑。但古典共和思想家对“贵族”与“寡头”的严格区分,暗含了一个“应然”的价值取向,亦当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在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表述中,“贵族政体”的纲目是“才德”,“寡头政体”的纲目是“财富”,前者为“正宗”,后者属“变态”,彼此间存在实质性差别(亚里士多德,1995:199;西塞罗,1997:47-49)。毫无疑问,要达成良好的国家治理,必须对垄断资源分配、谋取集团私利的“寡头”加以驯服。然而,将罗马共和国的“贵族”径直等同于豪强劣绅而一棍子打死,在思想方法上却并不怎么可取。按照古典共和的美德伦理,作为理想类型的“贵族”,逻辑地联系着“优秀”和“卓越”,也就是说,在元老院出任公职,并不仅仅取决于门第血统,更重要的还得看有没有克己奉公的道德节操,是否具备掌理国事所必需的智慧、慎思、明辨,或许还有宏大的气场和优雅的风度。现如今,“贵族”的名号已是明日黄花,但亚里士多德的那句话依然值得我们三思:“议事有赖于成熟的智慧”(亚里士多德,1995:367)。这是深谙治国之道的醒世恒言。
在古罗马,“人民大会”原是“王政”时期的创制。“共和”将这一制度继承下来,并发展出了一些新形式。从广泛意义上说,先后出现于罗马共和国政治舞台的各类人民大会均有“民主”性质,尽管其程度有所不同*一说罗马共和国先后有四种人民大会,即,库利亚大会、森都利亚大会、特里布大会和平民大会。。最高行政长官必须通过人民大会选举授权,元老院或高级行政官员提出的议案要经人民大会表决才能成为法律,有关剥夺被告全部公民权的刑事案件也得由人民大会终审,凡此种种,都显示了人民大会在政治过程中的民主化功能。但细加考究,人民大会制度还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平衡性张力结构。在罗马共和国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人民大会——森都利亚大会和特里布大会,多少有点像立法机构中的上院和下院,前者的贵族色彩浓一些,后者的平民味道重一些。现代民主理论巨擘卢梭对特里布大会甚是偏爱,认为其排除了元老的立法审议及“保民官”的专项选举,在制度设计上充分体现了“人民性”,并评论说,当傲岸自负的贵族不得不向一个平凡的“人民官吏”低头的时候,就真切领教“民主”的威力有多大了(卢梭,1982:156-157,160-161)。
按照某种流行的历史叙事,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变迁往往被表述为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但是,这样的定性即便不说是歪解,至多也仅仅讲对了一半。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当然是史实,而且,在经久的较量中,双方都耍过手腕,间或也使一些上不得台面的阴招。可我们不能忘了,在共和国良好治理的时期,无论平民还是贵族,总体上都能保持克制,他们一并审慎地守护着那道最后的合作底线。不妨说,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勋业之一,便是确立了一套合作型的利益博弈机制。若没有这样的机制,“共和”岂不成了“共斗”?辩证地看,当“贵族”的气焰过度嚣张时,理应借“民主”的力量进行反向牵制,但话又说回来,假使“民主”的力量扩张到难以约束的地步,政治平衡也会被打破。罗马共和晚期,代表平民利益的“保民官”蜕变成派系斗争的工具,其飞扬跋扈,令正义人士深恶痛绝。西塞罗斥责他们使“崇高”沦为“卑鄙”,俨然是“没有理智、失去任何美好希望的可恶的野兽”(西塞罗,1997:264-265)。这样的教训告诉今人,良好的国家治理不仅要驯服“寡头”,而且要疏导“民粹”。
像“德治”方案一样,在古典共和治国纲领中,以混合均衡政制为载体的“法治”方案,根本说来也源于“公共性”的价值规设,只不过,前者侧重“积极作为”,后者突出“消极防御”罢了。按照混合均衡的制度设计理路,盖因共和国是“公天下”,所以就必须对假公济私和以权谋私的政治腐败保持高度警觉。公共权力落到一人手里,不受限制,叫做“僭主化”,必须防范;公共权力落到少数人手里,不受限制,称为“寡头化”,也必须防范;公共权力落到多数人手里,不受限制,乃是“民粹化”,同样必须防范。反过来说,一当独霸性的政治力量得到有效控制,便会生成一种正能量,从而推动国家治理实现多元并包、互惠共荣的良好和谐。西塞罗这样表达了共和国的善治之道:
如同演奏弦乐、管乐和声乐时需要保持各种不同的乐音之间的某种和谐,精微的听觉会对它们的任何变音和不协调感到难以容忍,这种和谐靠对各种声音进行调整而协和一致;由上、中、下各种阶层协调意见组成的国家也像声乐一样,靠各种不同因素的协和一致而发出协调的奏鸣。歌唱时音乐家们称之为和谐的东西,在国家中称之为和睦,这是每个国家的最紧密、最牢固的安全纽带(西塞罗,1997:98)。
四、 结语
如果取一种俗白的说法,也许可以把整套古典共和治国纲领简约地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公共性”,两个基本点即培育优秀公民的“德治”和防范公权私有化的“法治”。统合起来,可作如下推论:(1)对古典共和传统来说,“公共性”乃本源性的一阶价值,就像入世而又超验的信仰,构成了评判所有制度安排和政治行为的终极合法性理据。因此,(2)就价值诉求而言,共和国的政权必须运行于“公共”的轨道,追求“公共”的幸福,达成“公共”的善业。这俨如来自神圣之域的绝对律令,天然正当且永远有效。但是,(3)在形而下的操作层面,若监察既定的政府组织或政策实践,看其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公共性”要求,则只能投以挑剔和苛刻的目光,并始终保持怀疑。这等于说,现实的国家治理模式不可能完美,总有这样那样的瑕疵或弊端。所以,(4)要不断趋近“公共性”,必须积极开展公民教育,围绕公共精神和参政素质两大方面努力培养公民之“好”。但要清楚,公民素养应该且能够逐步提升,却永远达不到尽头。这意味着,(5)并非“天使”的世俗公民,一旦大权在握,不受约束,便存在误用或滥用公权的可能。因此,为不致背离“公共性”,必须架构一种权力制衡的混合政制,为护卫良好的公共秩序树立一道坚实的法律屏障。根本说来,(6)无论培养优秀公民的“德治”还是防范公权私有化的“法治”,都派生于“公共性”的价值本源,并服务于“公共性”的价值目标。假使国家治理偏离了“公共性”宗旨,公民德行发生异化,权力架构失去平衡,共和国的江山也就合乎必然地改变颜色了。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如何解释罗马共和国的覆亡是一个经典议题。但是,基于一种更显宏大的历史视野,这个议题的要归,与其说是一个罗马事件毋宁说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对古典共和传统而言,现代民族国家成长和工商社会崛起所提出的挑战,才真正具有总体性质。就此而论,大国何以“共和”及工商社会何以“共和”,乃是现代国家治理的要点和难点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阿伦特(1999).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波考克(2012).德行、商业和历史.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
[4]布舒(2006).《法义》导读.谭立铸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5]达格(2007).共和主义公民权.伊辛主编.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6]亨廷顿(1998).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沈崇美、王冠华译.北京:三联书店.
[7]基弗(2000).古罗马风化史.姜瑞璋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8]库朗热(2006).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利奇德(2000).古希腊风化史.杜之、常鸣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0] 卢梭(1982).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1] 麦金太尔(1995).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 麦金太尔(1996).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3] 曼斯菲尔德(2005).驯化君主.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4] 佩迪特(2006).共和主义.刘训练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5] 斯金纳(2005).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王加丰、郑崧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6] 西塞罗(1997).论共和国论法律.杨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7] 西塞罗(2007).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8] 修昔底德(1997).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 亚里士多德(1995).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 亚里士多德(1992).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 Cicero(1991).OnDuti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 Maurizio Viroli(2002).Republicanism.New York:Hill and Wang.
Ideal and Reality of Publicness:
■作者地址: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Email:zfy@nju.edu.cn。
■责任编辑:叶娟丽
◆
A Political Cultural Analysis on the Principle of Classical Republican Governance
ZhangFengyang(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Publicness is the principle established and held on to by the republican tradition.In the ancient republican era,there existing two major approaches deriving from this principle.One is the so-called Virtuous Governance,which aims to ensure “the republic is for all” by educating and cultivating the citizen to ascertain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will guard and promote the common interest.The other lies in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about how to prevent public power degenerates into the private tool at service of certain individuals or limited groups for their own agenda recurring to “Mix and Balance”,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rule of law.Given the fact that it is still necessary at present to carry out the principle of publicness and manage to achieve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virtuous governa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f good governance is to maintain,the typ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principle of classical republican governance is in consequence not only a pur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but more importantly,a research which bears revealing meanings to the modern time.
Key words:publicness; classical republican tradition; civil virtue; mixed regime
DOI:10.14086/j.cnki.wujss.2016.0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