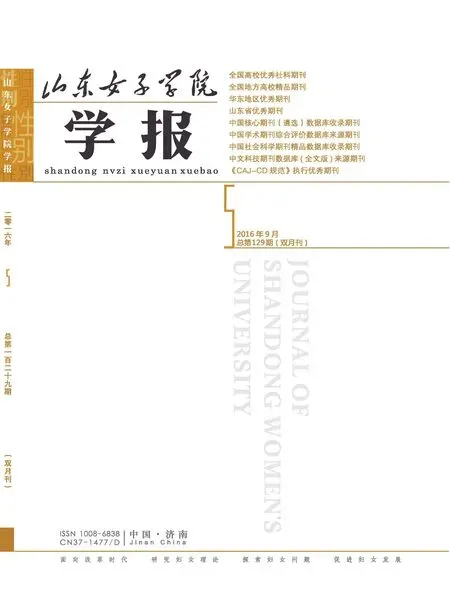《唐律疏议》中性别法规范表述技术评析
2016-04-12关丹丹
关丹丹
(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经济特区法治战略研究基地,海南海口 571158)
《唐律疏议》中性别法规范表述技术评析
关丹丹
(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经济特区法治战略研究基地,海南海口571158)
摘要:以《唐律疏议》为传统中国调整两性法律关系的代表进行分析发现,其大量运用性别相关的法律术语、构词形式等技术来对律文进行表述,标志着性别法规范立法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完善。分析《唐律疏议》中性别法规范的表述技术,可明显看到体现礼教内涵和性别偏向的趋势,这主要是受了中国传统的性别差等立法观念的影响。
关键词:《唐律疏议》;性别法规范;表述技术;性别差等观念
当中国传统礼教思想形成“三纲”的立法原则后,中国历代法典的制定即以此为指导,而此时期法典中调整两性关系法规范所应用的立法技术也主要是服务于维护三纲中“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立法思想。“通过家庭和谐实现社会整体和谐,是传统中国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1](P11)这种依托于家庭的管理模式适应中国古代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使国家的管理成本减少,管理水平提高,社会的生活更加安定。所以,纲常礼教思想下应用性别技术设置的罪名注重对家庭伦理纲常的维护。可以说,纲常礼教思想为《唐律疏议》中的性别规范奠定了两性宗法差等的内在理论基础。对《唐律疏议》进行分析发现,其所应用的性别表述技术是对中国传统礼教思想的反映。
一、体现礼教内涵的性别表述技术
要达到调整社会、家庭两性关系的目的,性别相关法律用语的应用是两性关系法规范的表述基础。《唐律疏议》中性别相关的法律用语在传统中国两性关系表述技术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其在前代性别相关法律用语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制度化规范,并赋予这些性别相关法律用语以宗法纲常礼教的内涵,这些较为完善的性别相关法律用语也为后世所继承或发展。
(一)表述礼教内涵的性别称谓
“男”“女”“夫”“妻”“父”“母”等表达社会及家庭中两性关系的基本词汇,由于其具有较强的稳固性而得以传承。但是,对比秦汉时期表述家庭中亲属性别的词汇,《唐律疏议》通过立法技术对相关词汇的内涵进行了细致划分。
第一,《唐律疏议》立法者继承了秦汉时期在法律词汇之前增加设定条件的词,以构成新词的技术方式,但是又在此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其一,表示条件的词汇概念性、逻辑性增强;其二,运用带有儒家礼制文化的词汇,以便于对宗法礼教制度下大家庭的组成成员身份进行区分。
以汉《二年律令》与《唐律疏议》中关于“母”这一基本词汇用于母辈亲属称谓之时的表述技术为例进行对比。汉《二年律令》中分为“母” “大(泰)母”“叚(假)大母”“主母”“后母”几种类型①,其中“母”和“大(泰)母”是指与犯罪的子孙辈有直系血缘关系的祖母辈、母亲辈,而“叚(假)大母、主母、后母等亲属称谓都是与犯罪的子孙辈无血缘关系的拟制祖母辈、母亲辈(类似于继母)的称谓”[2]。而《唐律疏议》中母辈称谓的词汇则更加多样,祖母辈的可根据姻亲关系分为“祖父母”“外祖父母”,根据辈分来分由高至低为“高祖母”“曾祖母”“祖母”;母亲辈的“母”之类型可从生殖、遗传、养育、婚姻、谱系角度分为“亲母”“嫡母”“继母”“养母”“慈母”“出母”几类称谓②。同时,用“嫡”“慈”“出”这类礼教含义下的词汇对“母”之类型进行区分,也意味着在法定亲属称谓中加入了宗法身份的内涵。由此可见,《唐律疏议》立法技术方面对性别称谓的内涵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有助于律文从多角度应用不同概念范畴的同一组性别称谓,加入礼教词汇作为区分条件也便于宗法差等思想在制定律文时得到体现。
第二,对平辈血缘关系家庭成员的称谓进行性别区分。秦《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与汉《二年律令》中,同血缘且平辈的两性称谓可不进行性别区分,用一个词来指代,如“子”“孙”“同产”等,如果要单独指代其中的某一性别的话,则用“子男”“女”“男同产”“女同产”等词来表示。虽然《唐律疏议》中“子”“孙”两词依然同时代表男女两性,但是在某些条文及语境中仅指代男子,且不需在词前增加表示性别的条件。如“妇人因夫、子得邑号,犯除名者,年满之后,夫、子见在有官爵者,听依式叙。”[3](P26)条文中所指的“子”,首先在律文的表述上与“夫”相对,其次在历史语境之中,唐代有官爵者一般是男性,所以此条中的“子”是仅限儿子,而不是同时代表儿子和女儿两性。又如《唐律疏议》规定:“其妇人犯流者,亦留住,……若夫、子犯流配者,听随之至配所,免居作。”[3](P32)其中,由于唐律有女性犯流者不会流配的规定,所以律文中“子犯流配者”的“子”是仅指儿子。同时,《唐律疏议》律文中也常把“父子”合称、“母女”合称,又有“嫡子”“庶子”“嫡孙”“庶孙”之称,这里的“子”“孙”均只表示男性。
另外,亲属称谓中变化最大的是秦汉律文所用的“同产”一词。《唐律疏议》时无“同产”,而是分别用“兄弟”“姐妹”两词来指代之前“同产”的概念。这种表述技术的变化,说明有唐一代的同辈称谓用语倾向于将两性进行区分,亲属称谓的性别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也说明同血缘平辈男女之间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也需要进行细致区分。历史现实表明,传统中国宗法制度下具有对家庭性别进行区分的需要,如在家庭责任或义务以及家庭资源的分配上同血缘平辈的两性具有较大的差别,所以,这种表述技术才有其存在的价值意义。
第三,表述两性关系性别称谓的技术,一般是对等出现的,如秦汉时期就存在的“夫妻”“父母”等称谓用语,这些称谓一开始就仅是表述家庭中两性的对等身份,但《唐律疏议》通过用训释语句的表述技术赋予称谓以礼教内涵。以“妻”这个最常用的称呼为例,其《唐律疏议》中充当犯罪主体或客体时,被赋予了很多礼教意义。“夫者,妻之天也”的训释表达了夫具有比妻高的地位,而“妻者,齐也”,则从语源上表达了妻与夫地位的最大接近性,拉开了与妾、媵、婢的距离。由礼教训释语句表述性别称谓的技术,充分说明了男女之间纲常礼法下地位等级的不同,也与《唐律疏议》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立法原则密不可分。
(二)表述礼教内涵的核心词语
“十恶”和“五服”作为《名例律》中总则性质的规范,其突出表现了维护纲常礼教和宗法等级的内涵。“十恶”和“五服”并不单指一种罪状,它是采用“数字”结合具有概括性意义的“核心词”的构词方式,对某一类法律术语进行总括。
以“十恶”和“五服”词为例,其分别由数字“十”和“五”结合概括礼教制度下最需要惩处的“恶”行及判断宗法血缘关系下亲疏远近的“服”制制度构成的。“十恶”包括十种恶行,“五服”代表五种服制,这种构词技术说明《唐律疏议》中的法律术语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类似由“数字+核心词”的概括性法律固定语还有“三不去”“七出”“五刑”“八议”等,而这类法律固定语基本是对礼教规范的概括继承,其中一部分词汇是由礼教内容调整家庭中两性关系的法律用语,如“七出”“三不去”是对家庭婚姻关系解除条件的规范,“十恶”中的部分规范是对违反家族伦理纲常设置的罪名,“五服”之中男女两性服制要求不尽相同。
(三)表述礼教内涵的其他词语
以“詈骂”犯罪为例,在《唐律疏议》中“詈骂”行为的对象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与犯罪人身份有特殊关系的人。如果在家庭中卑幼对尊长“詈骂”的,则分为不同的身份进行处罚,子孙詈祖父母、父母者绞,而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只徒三年。也就是说,在家庭中有血缘关系的子孙,无论男女,对祖父母、父母实行詈骂行为的,都处以严重的绞刑,而无血缘关系的女性,即通过婚姻行为结合的女性卑幼对祖父母、父母有詈骂行为的则处以较轻的刑罚。也就是说,如果夫妻二人均对祖父母、父母有詈骂行为的,则两者男性为绞刑,女性为徒三年。从结果来看,其处罚体现出对女性宽恤的内容,但实际上詈骂行为入律本身就是对礼教的维护,而对男性詈骂行为处罚的出发点是血缘关系和宗法身份,对女性詈骂行为处罚的出发点则是生活关系和因夫取得的家庭宗法身份。所以,在对詈骂行为处罚时专门设立对妻妾较轻的刑罚是具有技术合理性的。
另外具有礼教内涵的用于调整两性关系的法律固定语还有:同居相为隐、违律为婚、嫁娶违律、有妻更娶、以妻为妾、以妾为妻、居父母及夫丧嫁娶、父母被囚禁而嫁娶、义绝等。
二、体现性别偏向的立法表述技术
传统中国法典主要是以刑法规范来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要对性别法规范进行表述就需要涉及两性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罪名和行为规范的法律用语,出于宗法制度和礼教原则的影响,这些法律用语通过一定的构词或者表述技术而在《唐律疏议》中具有一定的性别偏向性。
(一)法律用语设置本身有性别偏向
首先,《唐律疏议》中设置具有上下语义定位的性犯罪罪名,特别是“强奸”罪名的设定体现了性别偏向。与秦汉时期只通过描述犯奸之行为来制定规范的技术方式不同,《唐律疏议》有专门表述奸罪的罪名,并设定不同的专用词汇来对不同形态的奸罪进行表述。如“奸”罪分为“强奸”“和奸”“媒合奸通”三种③,“奸”是上义词,可统称犯奸行为的罪名,“强奸”“和奸”“媒合奸通”是下义词,其对犯奸之行为进行具体区分。其中,“和奸”和“媒合奸通”具有通奸的表征,犯罪主体为男女两性,而“强奸”由于暴力伤害的表征,其概念范畴是男性实施的性犯罪行为。由于在唐代对于男女生理差别的认知,所以对于“强奸”的实施主体认定为男性,其司法实践也未见有女子强奸男子、男子强奸男子的案件。虽然这种性别偏向在现代看来可能不够全面,但是根据唐代现实社会情况,通过性别偏向界定法律词义,对于提高司法实践的操作性有很大帮助。
其次,《唐律疏议》在调整两性关系的律文中普遍应用专门表述两性行为的法律用语。例如关于离婚行为,《唐律疏议》用“离异”一词作为总称,并从不同的侧重点及不同的行为情节应用,“和离”“离异”“两离”“各离”“并离”几种法律用语对离异行为进行表述,从“和”“异”“两”“各”“并”几个词的运用来看,离婚是两性之间的行为,不具有偏向性。
《唐律疏议》律文表述中还应用具有性别偏向性的法律行为词语,专门用于指称女性行为或男性行为。如“改嫁”“再醮”“改适”都表示妇女在“擅去”“夫亡”情况下同别人结婚的行为,“后行” “转嫁”等也是对妇女再婚行为的法律用语,而男性基本只用“再娶”一词来表述再婚行为。“怀孕”“乳育”“怀胎”“妊娠”等则是对女性特有的生子这种生理行为进行表述的法律用语。另外,同是用“娶”字,其前面加不同的词语就表示不同性别的婚姻行为,如“婚娶”是指男性娶妻,而“嫁娶”则表示女性嫁人。“别籍异财”则是指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令户籍或分家析产的行为,这里的子孙只是指代男性,因为女性没有另立户籍及分家析产的权利。
从性别偏向词语的数量来看,表述女性行为的专门用语较多,又以再婚的行为为例,《唐律疏议》对女性再婚行为用了多种不同的表述词汇,而对男性再婚行为的表述则简练得多,说明《唐律疏议》律文对女性行为进行限制和规范的方位更多。
(二)用律文具体语境表述性别偏向
《唐律疏议》中的部分词汇在一定律文中具有性别偏向性。如“尊长”一词包括男性尊长和女性尊长,而在共犯条款的规定中,“尊长”④则特指男性,即使是女性尊长参与共犯的造意,也“仍以男夫独坐”。又如“兼丁”一词,由于“丁”一般指一户之中承担刑罚、赋税的男性丁口,“兼丁”即指一户之中的多个男性丁口。而在《唐律疏议》律文⑤中,女性也可能在一定情况下等同兼丁,即“犯徒应役而家无兼丁者”,如果妻子二十一岁以上可等同兼丁,或者“妇女家无男夫”的情况下,妇女也可兼丁。
“尊长”与“兼丁”两词在上述两条律文之中具有不同的性别偏向意义。首先,从两词本身的性别表征来看,“尊长”一词本身可指代男女两性,代表着家庭中位于崇高地位成员的尊称,其对家庭成员和家庭事务享有较高的管理权利,而“兼丁”一词本身只指代有劳动能力和赋税能力的男性丁口。其次,从具体条文中两性权利义务角度来看,“尊长”在共犯条款中要为家庭成员的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免除了家庭成员的法律责任;“兼丁”在“诸犯徒应役”条款中则需要承担刑罚、役使等社会责任。再次,从法条的具体性别内涵来看,共犯条款中的“尊长”一词偏向男性,犯徒应役条款中“兼丁”一词偏向女性。由上述三点结合具体两性社会实际情况分析,女性在“尊长”一词的普通含义下,享有较高的家庭权利,而在共犯条款中“尊长”一词偏向男性的设计使女性尊长摆脱了承担刑事法律责任的义务,体现了对女性的体恤;而女性本不能成为丁口,说明女性在社会劳动中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创造能力在农业社会并不被认可,但是在“诸犯徒应役”条款中只要符合条件即可被看作“兼丁”,则是为了避免百姓以丁口少为由逃避赋税、役使责任⑥,及犯罪人以家无兼丁为理由逃避刑事处罚。
由上述分析可知,《唐律疏议》中一般法律词汇的设置技术是按照两性宗法礼教关系原则来制定(如包含两性在内体现家族成员身份的“尊长”一词),或者按照两性生理差别原则来制定(如男性称“丁”),而特殊情况下要对上述词汇进行具有性别偏向的设置。这种特殊情况包括保护女性及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
(三)用年龄界限表述性别偏向
在《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与《二年律令》的秦汉时期,主要应用设置不同法定词汇来表述同一刑名下两性不同的处罚方式,而《唐律疏议》中主要用年龄来设定行为或责任界限来表述两性在生理和宗法上的差别原则。
如对“缘坐”⑦的规定,男性八十以上、女性六十以上可免缘坐之罪;对于对犯罪人不举劾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如果“妇女及男年十五以下”[3](P167)则勿论。又如流刑,女性即使犯流也不会被流配,对于家人谋反,母女、妻妾并流的,如果“女及妻妾年十五以下、六十以上”[3](P33)也是免于流配的。上述规范基本都是通过用年龄界限来对女性进行保护,其主要体现了传统中国一直以来对男女生理及行为能力、责任能力差别对待的思想,也就是两性生理差别观念和两性宗法差等观念的体现。
三、性别差等观念对表述技术的影响
立法者在确定了两性关系的立法原则、价值取向及法律手段之后,就面临把观念中的性别立法观念转化为文字符号的需要,即通过表述技术将性别规范用法律语言表述成文。否则,无论是多么精细、实用、完善的立法设想,至多也只能存在于立法者个人脑海之中而已。在传统中国两性关系法规范的制定发展过程中,各朝代根据当时国情下两性的社会关系及思想文化等国情的变化,以性别法律语言符号为工具,表述当时立法者的性别政策及意志,基本以“既要准确无误地表述立法者的意志,又要易于人们所理解和遵循”[4](P314)的技术原则为遵循目标,从而有效地向百姓传播国家肯定的性别观念的技术和方法。性别法规范的语言构成与一般法律文本的构成相同,都是由词语、语法、修辞适当结合而组成。而考察《唐律疏议》中两性关系表述技术应用的独特术语,能够展现立法者是如何通过立法技术对不同时期传统中国两性关系进行协调的。
从《唐律疏议》中性别法规范的表述技术来看,其所应用的表达方法和法律用词技巧均受到传统中国性别差等立法观念的影响,表现出对纲常礼教的强力维护。如“十恶”中部分规范、“五服”制度及“亲属相容隐”原则,因其对两性宗法身份差等的有效维护,而一直作为法律固定用语在历代法典中得以传承,并在《名例律》中发挥总则性指导作用。另外具有礼教内涵的用于调整两性关系的法律固定语还有:违律为婚、嫁娶违律、有妻更娶、以妻为妾、以妾为妻、居父母及夫丧嫁娶、父母被囚禁而嫁娶、义绝等,均在历代传统法典中得以传承沿用。
伴随专制统治程度的加深,为了确保对两性关系的调控效果,两性宗法差等原则地位也不断提升,传承性性别法律用语的内涵向性别身份差等的方向发展更新。以“母”之称谓的发展过程为例:如前所述,《二年律令》中用于母辈亲属称谓主要根据直系或拟制血缘关系分为“母”“大(泰)母”“叚(假)大母”“主母”“后母”几种类型;而《唐律疏议》中则从生殖、遗传、养育、婚姻、谱系角度分为“亲母”“嫡母”“继母”“养母”“慈母”“出母”6种称呼,并用“嫡”“慈”“出”等具有礼教含义的词汇对“母”之类型进行区分,既体现了表述技术的发展,又加入了宗法身份内涵;《大明律》中概括为三父八母,对“母”之内涵进行更细致的概念划分;《大清律例》通过置《服制图》与《名例律》之前的技术手段,提升了宗法内涵下性别称谓在律文中的地位。
如果性别法规范适用的法律术语与性别立法观念的发展不符,则其必然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如秦汉的“同产”一词即能指代同父同母或同父异母所生之兄弟姐妹,用一词表述兄弟姐妹体现了秦汉时期对家庭中平辈两性的平等地位。而《唐律疏议》时已无“同产”之概念,分别用“兄弟”“姐妹”两词来对律文进行表述,这种表述技术的变化,说明有唐一代及之后的同辈称谓用语倾向于将两性进行区分,宗法身份特征更加明显,应用于性别规范之中也体现了平辈两性不平等的法律地位。
纲常礼教立法文化是中国传统刑律发展到完备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确定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指导原则,礼的精神由性别立法技术的运用反映到调整两性关系的法规范之中,其“集中表现为差等性和家族制”[5](P186)。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即是由注重身份等差和宗法血缘关系的纲常名教所赋予的。从《唐律疏议》的表述技术来看,伴随着宗法礼教思想入律及家国一体体制的构建,性别差等在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中,更趋向于指代因姻亲、血缘或拟制而形成的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家庭性别身份之下的性别差等。传统中国宗法家庭身份之下的性别差等主要是以通过服制亲疏来判定,这可以说是传统中国立法文化的一大民族特色。
注释:
①“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叚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参见《二年律令·贼律》。
②“亲母”称呼,参见萧榕主编的《世界著名法典选编·中国古代法卷·唐律疏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第6条。“嫡母”“继母”“慈母”的称呼,参见萧榕主编的《世界著名法典选编·中国古代法卷·唐律疏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第52条。“养母”“出母”称呼参见萧榕主编的《世界著名法典选编·中国古代法卷·唐律疏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第345条。
③“诸和奸,本条无妇女罪名者,与男子同。强者,妇女不坐。其媒合奸通,减奸者罪一等。”参见萧榕主编的《世界著名法典选编·中国古代法卷·唐律疏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第415条。
④“尊长谓男夫者,假有妇人尊长,共男夫卑幼同犯,虽妇人造意,仍以男夫独坐。”参见萧榕主编的《世界著名法典选编·中国古代法卷·唐律疏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第42条。
⑤《唐律疏议》第27条律文的规定:“诸犯徒应役而家无兼丁者,妻年二十一以上,同兼丁之限。妇女家无男夫兼丁者,亦同。”问答:“答曰:家无兼丁,免徒加杖者,矜其粮晌乏绝,又恐家内困穷。一家二丁,俱在徒役,理同无丁之法,便须决放一人。”参见萧榕主编的《世界著名法典选编·中国古代法卷·唐律疏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⑥《唐律疏议》第245条的疏议:“差遣之法,谓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凡丁分番上役者,家有兼丁,要月;家贫单身,闲月之类。”参见萧榕主编的《世界著名法典选编·中国古代法卷·唐律疏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
⑦“谓缘坐之中,有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虽免缘坐之罪,身有官品者,亦各除名。”参见萧榕主编的《世界著名法典选编·中国古代法卷·唐律疏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第18条。
参考文献:
[1]朱勇.权利换和谐:中国传统法律的秩序路径[J].中国法学,2008,(1):3-11.
[2]王辉.汉代家族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52.
[3]萧榕.世界著名法典选编·中国古代法卷 [Z].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
[4]曹海晶.中外立法制度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黄源盛.汉唐法制与儒家传统[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
(责任编辑赵莉萍)
收稿日期:2016-06-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秦汉法律术语与立法技术”(项目编号:14YJC820084);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海南省高等学校法律人才培养‘双向交流机制’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Hnjg2015-26)
作者简介:关丹丹(1983—),女,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海南经济特区法治战略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法律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6)05-0076-06
On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of Gender Legislation inTheSimpleLawofTangDynasty
GUAN Dan-dan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Base of Legal Strategy in Hainan Special Economic Zone, Haikou 571158, China)
Abstract:The Simple Law of Tang Dynasty is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aw in administering gender relations. Its extensive use of gender-related legal terminology and word-building marked a great advance in gender legislation and technology. Analysis of narrative techniques of gender legislation in this book shows the obvious propriety in Li and gender bias, which bears indispensable relation with Chinese gender prejudiced legislation.
Key words:The Simple Law of Tang Dynasty; gender legislation; narrative techniques; gender prejudiced notion
·女性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