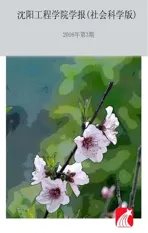诗画一律及其图文张力解读
2016-04-12杨向荣叶荷健
杨向荣,叶荷健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诗画一律及其图文张力解读
杨向荣,叶荷健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苏轼提出“诗画一律”,强调诗与画在表情达意上有着可以融合交汇的共通性。就“诗画一律”命题所体现的图文张力而言,其中关键点在于如何处理诗与画的关系。诗与画,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学与图像,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各自的矛盾冲突,它们的相互言说建构了二者的内在张力。
诗画一律;图文关系;图文张力
在中国古代,诗与画自古就被视为姐妹艺术,因此,考察中国古代诗学中的图文关系、诗画关系特别是中国古代的“诗画一律”命题无疑是我们不能绕过的话题。然而,诗歌与绘画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随着艺术自身的发展,诗画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诗与画,或者说文与图,抑或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学与图像,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各自的矛盾冲突,它们的相互言说建构了二者互文表达的内在张力。
一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就谈到了诗画的差异性。“绘事图色,文辞尽情”[1]136。刘勰认为,绘画长于描述事物的外在形貌,而诗歌则长于表达作者的内在情感。随后陆机也区分了“丹青”(画)和“雅颂”(诗),他在《文赋》中认为“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1]158。刘勰和陆机强调了绘画与诗歌的差异性,但中国古人更多是强调诗画的同一性,如孔武仲云认为诗与画“二者异迹而同趣”(《东坡居士画怪石赋》);张舜民认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跋百之诗话》);叶燮认为“画者,天地无声之诗;诗者,天地无色之画”(《赤露楼诗集序》),等等。
苏轼是“诗画一律”命题的直接提出者,他所提出的“诗画一律”命题表明了诗画的相通性:画中有如诗般的令人回味不尽的感觉,而诗中则有如画般的优美形象,读诗可以让人们的脑海中浮现画意,而观画可以让人们脑海中涌现诗情。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1]143此论也成为中国“诗画一律”观的主要理论依据。在另一首诗《韩干马》中,苏轼在《苏轼文集》又写道:“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此画此诗真已矣,人间驽骥漫争驰。”[1]2630诗中提到的“无形画”与“不语诗”可谓是对他“诗画一律”命题的极佳阐释。此外,苏轼在《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还特别指出,画家有着与诗人同样的特点:“古来画师非俗士,模写物象略与诗人同”[1]11。在《次韵吴传正枯木歌》中又写道:“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4]135。在苏轼看来,画家对外在世界的模仿和创造性加工,与诗人的形象性思维有着共通之处,这也正如清代沈宗骞在《山水·避俗》中所言:“画与诗,皆士人陶写性情之事;故凡可以入诗者,均可以入画。”[1]516
对于苏轼的“诗画一律”命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具体说明。
首先,“诗画一律”强调自然清新的审美风格。在苏轼的表述中,“天工与清新”是对“诗画一律”内涵的解释。天工是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风格,清新是与天工相对应的清丽风格。在苏轼看来,好的诗画均要有天工与清新的审美风格。从“诗画一律”的理论建构来说,天工与清新强调了诗与画在描摹物象、创造意境、寄托神思方面的同一性。苏轼强调形象创造的生动传神性,认为不论是诗歌还是绘画,都应当强调以传神为主。他认为诗与画只有以传神为目标,才能实现天工与清新的审美效果,传达出自然而然和浑然天成的清新美感。为了具体说明这种审美风格,苏轼在评点他人诗画时均以此为审美评价标准,如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中写道:“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其身与竹画,无穷出清新。”[4]117在《跋蒲传正燕公山水》中写道:“画以人物为神,花、竹、禽、鱼为妙,宫室、器用为巧,山水为胜,而山水以清雄奇富变态无穷为难。燕公之笔,浑然天成,粲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3]2212在《又跋汉杰画山》中写道:“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卷。汉杰真士人画也。”[3]2216在《书柳子厚南涧诗》中评柳宗元的诗为“清劲”,在《跋黔南居士渔父词》评黄庭坚词为“清新婉丽”,等等。
其次,“诗画一律”强调诗画的言外之意和象外之旨,追求一种意境美。金代王若虚在其《滹南诗话》曾评述过苏轼的“诗画一律”命题。“‘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夫所贵于画者,为其似耳;画而不似,则如勿画。命题而赋诗,不必此诗,果为何语?然则坡之论非欤?曰:论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不窘于题,而要不失其题,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实,无得于心,而借此论以为高。画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托云烟暮霭,谓之气象。赋诗者茫昧僻远,按题而索之,不知所谓,乃曰格律贵尔。一有不然,则必相嗤点,以为浅易而寻常。不求是而求奇。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矣,岂坡公之本意也哉”[6]294!王若虚的评点相当精辟地道出了苏轼命题的内在精髓:“妙在形似之外。”“形似之外”即苏轼所强调的言外之意,苏轼认为诗歌应当营造言外之境,给人们无尽的遐想,如他在《题渊明饮酒诗后》评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索然矣。”(《题渊明饮酒诗后》)
对于绘画,苏轼也同样强调象外之旨,他在《王维吴道子画》中比较王维与吴道子的绘画,认为王维的画更有象外之趣,因而技高一筹。“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2]153。苏轼在《题王维画》中认为,吴道子画得再好也只能称为“画工”,而“摩诘本词客,亦自名画师”[7]828。苏轼以“画工”来论吴道子,而称赞王维的画“得之于象外”,是因为他认为象外之景和无画之画才是绘画的最高境界。在他看来,绘画是为了表现画家的心胸情感,即“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史鉴类编》曾评王维的诗“如上林春晓,芳树微烘。百啭流莺,宫商迭奏。黄山紫塞,汉馆秦宫。芊绵伟丽于氤氲杳渺之间,真所谓有声画也。非妙于丹青者,其孰能之”[8]378。此论断可谓与苏轼对王维的评价如出一辙。对此,后人也有不少附论,如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东坡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最妙,然须知作此诗而竟不是此诗,则尤非诗人矣。其妙处总在旁见侧出,吸取题神,不是此诗,恰是此诗。”[8]68清代赵翼则在《论诗》指出:“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出东坡,意取象外神。羚羊眠挂角,天马奔绝尘。其实论过高,后学未易遵。……吾试为转语,案翻老斫轮。作诗必此诗,乃是真诗人。”[10]1545
再次,“诗画一律”强调诗与画的融合与渗透。苏轼从中国古典诗画艺术的特点出发,在提出“诗画一律”的命题后,又对诗与画的相通性展开了论述。如前文所述,苏轼十分推崇王维,他在评价王维的诗画时还提出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命题,认为诗与画二者可以相互渗透,从而进一步对“诗画一律”命题进行了补充阐释。在《蓝关烟雨图》中苏轼写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曰:‘蓝溪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补摩诘之遗。’”[5]541王维的诗受禅学影响很深,充满了禅意,内容上多描绘自然山水之美,风格上淡泊含蓄而韵味深长,读之如画;王维的画则为南宗文人画之始祖,以萧条淡泊的意境与简约清新的画风为风格特色,又渗透了文人的意气和逸品。其水墨山水画法将虚无、空灵、飘逸之味表达得恰到好处,观之如诗。王维不仅是南宗画的创始人,也是神韵诗派的大家,他将诗画艺术熔于一炉,又糅合以禅意,而苏轼所言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指的也是王维这种诗画相互渗透、以诗情入画景、以画景入诗情的审美风格。这也正如金代李俊民在《锦堂赋诗序》中所言:“士大夫咏性情,写物状,不托之诗,则托之画,故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得之心,应之口,可以夺造化,寓高兴也。”[11]605需要指出的,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命题所强调的诗画交融,主要指的是诗和画在意象上的相通,使无形的诗在意象上具有了画的形象,无声的画也具有诗的意味,而不是指具体的写诗作画的技巧上的等同。如苏轼《韩干马》中的“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即是认为杜诗咏马富有生气,如同“无形画”,而韩干画马蕴含诗意,如同“不语诗”。
二
在苏轼提出“诗画一律”命题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宋代文人和画家中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态度。士大夫文人纷纷以此法作诗绘画,以意趣为宗旨,强调诗画的渗透交融。此时兴起的文人画就是以此为奉行的准则,并将王维的诗画视为标准。宋代开始出现诗歌与绘画内容上搭配出现的现象,到了明清时期则逐渐演变成了题画诗的出现,即画家要会作诗,并且绘画一定要题诗的情形。题画诗的画意主要是指绘画所体现出来的神韵以及诗意,如张彦远提出的“意存笔先,画尽意在” 的观点。张彦远所言的“画尽意”中的意,也就是指画要体现神韵和诗情。而刘长卿在《观李凑所画美人障子》中曰:“爱尔含天资,丹青有殊智。无间已得象,象外更生意。”[12]740刘长卿认为诗要有象(画意),才在象外生意(诗情),可谓从意境的角度完美地阐释了诗画的结合。
题画诗主要是强调诗情与画意的相互交融和汇合,即在用诗阐释画意的同时,用画意来渲染诗情,也就是说,题画诗要传达出诗情画意。可以说,诗情与画意是构建题画诗艺术形象的特殊手法,同样也是诗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并逐渐在明清时期成为评判题画诗的一条重要的审美标准。不过,从题画诗的发展来看,明清时期绘画的意境已不再靠形象表达,而让位给了诗。明清题画诗中画的意义要靠所题诗句的内容来表达和完善,同一幅画,如果题不同的诗,则可能使画的意境完全不一样。因此,“诗画一律”命题在明清时期逐渐演变成“题诗入画”,这种机械的融合就如同唐代张彦远提出的“书画同体”命题在明清时期演变成“以书入画”一样,其实已偏离了“诗画一律”命题的理论初衷。虽然如此,但笔者以为,题画诗是以诗意来补画,即在绘画的基础上以古典诗词的意境来补充阐释画意。以此观之,题画诗体现了诗画的图文互生关系,诗与画作为不同的艺术类型,但却在同一个空间呈现,并达到内在艺术精神和审美旨趣上的同构共通。诗与画在题画诗中可谓互为图文,二者构成互读或互义的张力关系。
对苏轼的“诗画一律”命题,不少诗论家与画论家们纷纷附论,赞同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后人纷纷针对苏轼的命题给予了评述,并针对其中的诗画张力关系展开了激烈探讨。在后人对苏轼“诗画一律”命题的阐释与解读中,大体上可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诗画一律”强调了诗画的想通性和一致性,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一也”。张舜民在《跋百之诗话》中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5]512孔武仲在《东坡居士画怪石赋》中云:“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趣。”[5]511黄庭坚在《次韵子瞻子由题〈憩寂图〉》中云:“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作无声诗。”[5]511等等。苏轼的同时代诗论家晁补之在《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二首之一中曾写道:“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12]434“物外形”就是画外之意和画外之旨,也就是画中的诗情和诗意;“画外意”是指诗歌要传达出画态和画意,即虽然诗歌长于抒情和言志,但也要“贵有画中态”。晁补之所说的诗要有“画外意”和“画中态”,其实也就是苏轼“诗画一律”命题的另一种表达。另一宋代画论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也写道:“‘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哲人多谈此言,吾之所师。余因暇日,阅晋唐古今诗什,其中佳句有道尽人腹中之事,有状出人目前之景;然不因静居燕坐,明净几,一炷炉香,万虑消沉,则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即画中生意,亦岂易及乎?”[13]612此外,如明代李贽在《诗画》中说:“卓吾子谓改形不成画,得意非画外,因复和之日: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14]365清代叶燮在《原诗》中也认为诗与画能“尽天地万物之情状”,“故画者,天地无声之诗;诗者,天地无色之画。……画者形也,形依情则深;诗者情也,情附形则显。”[14]324以上诸论,可谓都是对苏轼诗画观的认同和再阐释。
另一派认为,诗与画是不同的艺术形态,不可能真正实现“诗画一律”。如明代杨慎在《论诗画》中认为,苏轼的“诗画一律”命题强调“言画贵神,诗贵韵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论也。晁以道和公诗云:‘画写物外形……贵有画中态。’其论始佳。盖欲以补坡公之未备也”[16]367。在杨慎看来,苏轼的观点有失偏颇,而晁补之的观点则是对苏轼观点的进一步完善与补充。明代张岱在《与包严介》中也明确指出诗与画是两门不同的艺术,各有其擅长的活动范围。“弟独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摩诘一身兼此二妙,故连合言之。若以有诗句之画作画,画不能佳,以有画意之诗为诗,诗必不妙。如李青莲《静夜思》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有何可画?”[17]135陶元藻和陆滢也表达了与张岱相似的观点。陶元藻在《轩孙村居小照题词》中说“凡林峦蒲溆篱落诸风景之寓于目而可画者甚多,惜诗之不可画者十居八九”[18]152。陆滢在《问花楼词话》中说“昔人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然亦有画手所不能道者”[18]94。明代李东阳在《麓堂诗话》认为,不能将诗与画笼统地看待,诗之“不能穷”在于世间万物之“理无穷”也,如勉强以画来与诗并论,只能是“小道”罢了。“自有诗以来,经几千白人,出几千万语,而不能穷,是物之理无穷,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今令画工画十人,则必有相似而不能必出者,盖其道小而无穷。而世之言诗者每与画并论,则自小其道也”[18]1373。清代学者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诗题中不关主意者,一二字点过。画图中具名者,必逐物措置。惟诗有不能状之类,则画能见之。”[18]112方薰道出了出了画与诗的不同之处,并且指出,诗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画却能够再现出来。而沈德潜则强调在表情达意上,诗比画更有其独特的优势,“能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在沈德潜看来,诗与画相比,在表情达意上更成熟,也更精炼,而且,诗中能表达的东西也远比画要多,故“画家未到者,诗能神会之”(沈德潜《书高宝意太史画声集后》)。以上诸论,可谓都是对苏轼诗画观的质疑或反对。
三
就苏轼提出“诗画一律”这个命题的本意来说,是想强调诗画有着共同的“言外之意”和“象在之旨”,即在表情达意上有着可以融合交汇的共通性。而诗与画是否可能真正做到融合与汇通,这是后人在解读苏轼的命题时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在杨慎对苏轼的质疑中,杨慎无非想表明,诗与画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因为在表情达意上不可能完全趋同。因此,就“诗画一律”命题所体现的图文张力而言,其中关键点在于如何处理诗与画的关系。
德国人莱辛在《拉奥孔》中曾详尽强调了两者的界限和区别,认为诗是语言的艺术,长于表现时间中发生的动作状态,画是造型艺术,长于表现空间中的位置。而现代学者钱钟书在其《中国诗与中国画》中也批判过这一命题,指出“诗画一律”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命题只能用在神韵诗和南宗文人画上(王维是神韵诗派的宗师和南宗画的鼻祖)。中国传统诗歌一般以杜甫为正宗,绘画则以南宗画为正宗,以王维坐第一把交椅。“画品居次的吴道子的画风相当于最高的诗风,而诗品居首的杜甫的诗风相当于次高的画风”[22]27。钱钟书在分析莱辛的《拉奥孔》时,将诗画的区分归结为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差异。钱钟书以此为出发点,结合中国的诗画艺术实践,对“诗画一律”命题中的图文张力进行了具体分析。在《读〈拉奥孔〉》一文中,钱钟书写道: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七批驳了这个无稽之谈:“此好奇者为之。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从那简单一句话里,我们看出他已悟到时间艺术只限于一刹那内的景象了。‘止能画一声’五个字也帮助我们了解一首唐诗。徐凝《观钓台画图》:‘一水寂寥青霭合,两崖崔奉白云残;画人心到啼猿破,欲作三声出树难。’……诗意是:画家挖空心思,终画不出‘三声’连续的猿啼,因为他‘止能画一声’。” 徐凝很可以写“欲作悲声出树难”或“欲作鸣声出树难”,那不过说图画只能绘形而不能“绘声”。他写“三声”,寓意精微,“三”和“一”“两”呼应,就是莱辛所谓绘画只表达空间里的平列(nebeneinander),不表达时间上的后继(nacheinander)。所以,“画人”画“一水”加“两崖”的排列易,他画“一”而“两”、“两”而三的“三声”继续“难”[23]64。
中国古人画故事,也知道不挑选顶点或最后景象。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七《题摹〈燕郭尚父图〉》:“往时李伯时为余作李广夺胡儿马,挟儿南驰,取胡儿弓引满以拟追骑。观箭锋所值,发之,人马皆应弦也。伯时笑曰:‘使俗子为之,作箭中追骑矣。’余因此深悟画格。”看来唐人早“悟”这种“画格”。楼钥《攻愧集》卷七四《跋〈秦王独猎图〉》:“此《唐文皇读猎图》,唐李小将军(李昭道)之笔。……三马一豕,皆极奔骤;弓既引满而箭锋正与豕相值。岂山谷、龙眠俱未见此画耶?”李公麟深能体会富有包孕的片刻,只要看宋人关于他另一幅画《贤己图》的描写。岳珂《程史》卷二:“博者五六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卢,而一犹旋转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观者皆变色起立”;“投”即“骰”,“贤己”出《论语·阳货》:“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避免“顶点”,让观者揣摩结局,全由那颗旋转未定的骰子和那个俯盆狂喊的赌客体现出来。《独猎图》景象的结果可以断定,《贤己图》景象的结果不能断定;但两者都面临决定性的片刻,划然而止,却悠然而长,留有“生发”余地[23]76-77。
钱钟书对诗与画的区分无疑有其合理性,诗与画是艺术的不同门类,诗歌作为语言艺术,存在于时间形式中,绘画作为图像艺术,存在于空间艺术中,诗是听觉艺术,画则是视觉艺术。其实,不仅仅是诗与画,我们在前文所分析的书与画,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也可以将之归结为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关系。在钱钟书看来,在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中,论画尚虚,而论诗尚实,这说明了古典艺术批评传统对诗和画的评价标准并非完全一致,这在客观上也道出了中国古代诗画关系张力的复杂性。
与钱钟书的观点不同,朱光潜则道出了诗与画的共通性。在《诗论》中,朱光潜写道:
苏东坡称赞王摩诘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一句名言,但稍加推敲,似有语病。谁的诗,如果真是诗,里面没有画?谁的画?如果真的是画,里面没有诗?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说过:“诗为有声之画,画为无声之诗。”宋朝画论家赵孟溁也说过这样的话,几乎一字不差。这种不谋而合可证诗画同质是古今中外一个普遍的信条。罗马诗论家贺拉斯(Horace)所说的“画如此,诗亦然”。尤其是谈诗画者所津津乐道的。道理本来很简单。诗与画同是艺术,而艺术都是情趣的意象化或意象的情趣化。徒有情趣不能成诗,徒有意象也不能成画。情趣与意象相契合融化,诗从此出,画也从此出。[1]137
在朱光潜看来,诗画有其共通性,只是各自的表现形式不同,诗倾向于无形,画偏向于有形,诗是一种有声语言,而画表现为一种无声的语言。在诗歌中可以找到画意,在绘画中可以体会到诗情,两者存在于彼此的相互言说与模仿中,体现出文与图的内在张力。就我们所分析的 “诗画一律”命题而言,“诗画一律”是指诗画这两种艺术的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关系。如苏轼认为诗要有画境,画要有诗意,前者要求诗的情志要通过生动具体的形色物象来显现;后者要求画不仅要表现形色,更要从中传达出情志意蕴。笔者以为,诗与画在表现形式上有着共通之处,虽然二者各自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但两者仍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诗画的这种关系体现诗画在相互模仿和相互言说中的互仿张力,而郭熙所说的“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也可以说是这种互仿张力的极佳注脚。诗与画互为补充,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它的意境通过语言叙述得以实现。我们对诗歌中意境的理解,往往是根据诗的描述并通过联想、想象,最终在脑中形成一幅画面。诗与画的相融点在于共同的意境,所谓诗画相生,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也都是建立在共同的意境之上。此外,在反映生活和表现技巧方面,诗歌与绘画也是相通的,二者可互通有无。作诗写文可以汲取绘画的表现手法,可以增强形象的可视性,使作品形象更生动、更具体,而绘画可以汲取作诗写文的一些创作技巧,可以使画面更集中,表情达意也更鲜明,更富有诗的韵味。
明代夏履先曾说:“图像似作儿态。然史中炎凉好丑,辞绘之,辞所不到,图绘之。昔人云:诗中有画。余亦云:画中有诗。俾观者展卷,而人情物理,城市山林,胜败穷通,皇畿野店,无不一览而尽。其间防景必真,传神必肖,可称写照妙手,奚徒铅堑为工。”[1]280夏履先的话表明,图能传达辞(文)所不能传达的东西,通过图画的形式,可以弥补“词所不到”的缺陷。图像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视觉和感官的刺激,图像更需要用眼睛和心灵去读。图像所蕴含的意义内蕴,需要运用理性的方式才能理解。语言的逻辑可以将图像无法言传的美表达出来,可以将心灵看到的一切内化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只有依靠语言的抽象能力和深化能力,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图像的美。
[1]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苏轼.苏轼诗集合注[M].冯应榴.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4]苏轼.苏轼选集[M].张志烈,等.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
[6]李福顺.苏轼论书画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7]苏东坡.苏东坡全集:第14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8]北京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袁枚.续诗品注评[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10]赵翼.赵翼诗编年全集:第4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11]张金吾.金文最[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陈邦彦.康熙御定历代题画诗:下[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
[13]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14]殷晓蕾.古代山水画论备要[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15]京大学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杨文生.杨慎诗话校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17]谭邦和.历代小品尺牍[M].北京:崇文书局,2004.
[18]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9]乔亿.大历诗略笺释辑评[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20]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1]方薰.山静居画论[M].台北:台北艺文印书馆,1947.
[22]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2.
[23]钱钟书.钱钟书论学文选:第6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
[24]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25]黄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伯灵校对伊人凤)
Analysis on the Uniform of Poems and Paintings and Its Graphic Tension
YANG Xiang-rong,YE He-ji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News,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Sushi proposed the idea of the uniform of poems and paintings,which emphasized that communicating views of poems and pictures can be merged togethe.In terms of the graphic tension,the key point is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ems and pictures.Poems and pictures,in broad meaning,the literature and image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contradictory with each other,and form the tension of them.
the uniform of poems and painting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ems and pictures;graphic tension
2016-01-08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R02)
杨向荣(1978-),男,长沙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美学与艺术哲学研究。
10.13888/j.cnki.jsie(ss).2016.03.003
B83-0
A
1672-9617(2016)03-03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