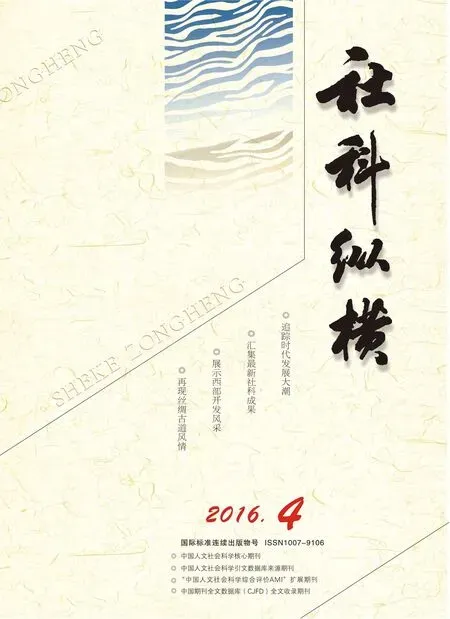情感增强技术引发的人类尊严丧失的伦理问题探析
2016-04-12康小梅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030006
康小梅(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山西 太原 030006)
情感增强技术引发的人类尊严丧失的伦理问题探析
康小梅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030006)
神经科学和神经技术近年来的迅猛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人们开始探索神经技术在治疗疾病之外的使用,情感增强技术就是其中的一种。本文主要考察情感增强技术引发的对人类尊严的侵犯的伦理问题。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1.情感增强技术对人的自主性的侵犯;2.情感增强技术的使用导致人类的主体地位的丧失。情感增强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需要我们仔细考察,同时也警告我们要慎重地使用这一技术。
情感增强自主性主体地位伦理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增强一直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目标,而且人类也从未停下提高自己的脚步。人类在不断努力的同时,增强也一步步成为现实。情感是我们对外部环境的一种内在的反应,情感的反应是我们对外部世界评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价值判断。人们总是倾向于建立起正面的价值判断,收获积极的情感,变得更加快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情感增强。20世纪以来,随着神经科学和神经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兴的情感增强技术有能力通过药物、技术设备甚至是基因来增强人的情感,但是这种神奇的可以操控人的情感的技术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劳永逸的安全感,而是引起了一系列负面的效应,也引发了哲学和伦理学的各种争议。
一、情感增强技术
与传统情感增强技术不同,新兴的情感增强技术是健康个体利用药物、技术设备或基因的手段来改变健康个体的情感反应。SSRIs是一种血清素再吸取抑制剂,服用这些药物后增加的血清素会让人感觉不到痛苦而且会增强人的自我价值的感觉。如心得安,在“创伤性事件发生后的六小时内服用它可以减弱这些事件造成的情感伤痛”[1]。除了药物方式,还有医疗器械、手术以及基因植入的方式来达到情感增强。DBS(深部脑刺激)随着其技术的深入发展现在人类已经能够将其用于改变人的情感功能。而通过基因手段的介入,人们能够使得后代拥有他们所期望的情感特征。我们将这些技术称之为情感增强技术,并不意味着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增强人类的情感为目的。事实上任何生物医疗技术最初都是为了治疗某种特殊的疾病而产生,只是这些技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开始用于非治疗的目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增强的目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情感增强技术其实是治疗某些精神心理疾病的技术用于健康个体提高其情感功能。
二、情感增强技术导致的人类尊严丧失
情感增强技术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的确给我带来了益处,它能帮助陷入抑郁和焦虑的人们变得快乐起来,也能够使陷入悲伤和痛苦的人们摆脱心理阴影,重新开始积极乐观的生活。但是这些快乐却不是该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结果,情感增强技术的使用由于将人的情感状态作为技术作用的对象,对人的自主性造成了侵略,而更进一步说,人也变成了技术的客体,人的主体地位已经沦陷。
1.对人的自主性的侵略
第一,根据康德主义,自主性是自由意志的一个方面,它是引发一个人行为的原因。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理性之人的尊严来自于它的自主性,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决定。一个人拥有自主性就表示他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选择,或是对特定的情境做出评价。在情感增强技术的作用下,人的情感反应受到技术的干扰甚至是控制,使得人类不再有能力按照自己真实的意愿做出对外部世界的情感的反应。有一种药物心得安,可以让我们在痛苦的事情发生后不再感觉到那么难过,减弱创伤性事件对我们造成的痛苦回忆。那么这种减弱了的痛苦的情感回应就不是主体在自主状态(至少不是思想的自主状态)下所作出的,而是受到了药物作用的影响作出的。
第二,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快乐的、幸福的、积极的情感体验,通过情感增强技术来达到这些目标同样会造成对我们的自主性的威胁。因为快乐的体验并不是通过自我的努力得到的,例如帮助别人、听一场音乐会或与朋友聊天,而是技术造就,是人工添加的。Maartje Schemer认为情感增强的药物威胁到了人类快乐的本质。他说,“人工的情感完全把感觉与生活,内在的感觉与外在的联系完全割裂开来。人类所追求的快乐是与真实发生的事情或与我们做过的事情相关,而药物给予的快乐是机械的,药物为我们创造出的是一种没有来源的虚无感,因此是没有意义的”[2]。当我们用情感增强技术的方式来获取我们希望得到的情感反应时,我们就已经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失去了自己通过努力来达到这些目标的机会,也失去了在我们努力的过程中所收获的乐趣和成就感。那么即使我们是快乐的,也是在牺牲了我们的自主性的情况下获得的。
第三,在很多情况下,增强不是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而是被迫进行的。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获得对自己的情感的认识,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周围的人都在通过情感增强技术获得了比我们更多的快乐时,我们就会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处于劣势,会不满足于过于平淡的生活,认为自己的生活还缺少足够的幸福感,会希望追求更多的快乐。周围的环境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一种潜在的强制的力量,让个体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选择情感增强,即使需要花费相当多的资金。这种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侵犯了人的自主性,因为个体做出情感增强选择的行为可能并不是出于内心真正的意愿。
2.人类主体地位的沦陷
“大自然中的无理性者,它们不依靠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所以他们至多具有作为工具或手段的价值,因此我们称之为‘物’。反之有理性者,被称为‘人’,这是因为人在本性上就是目的自身的存在,不能把他只当做‘物’看待。人是一个可尊敬的对象,这就表明我们不能随便对待他”[3]。情感增强技术的实施会冒着我们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风险。我们说自我是或有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是回应原因的能力。当我们把自己当成机器,用直接操纵的方式修改大脑、情感和认知程序的时候,我们将冒着任何东西都能让我们变成机器的风险。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说的“异化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在对大脑进行直接操纵来达到情感增强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把自己当成是理性的存在,而是当成技术的客体,我们经历了自我的异化。
情感增强技术的问题在于(“百忧解”指代是任何治疗精神问题的化学方式)是它以一种适合于机器的方式来对待人。并不把一些人的问题当做是他们对情景评估的回应,而是把他们当做表现了一种故障。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是认知。情感不仅仅是对情境的内心深处的回应,它们反映了我们对情境的评估,而且在原则上,是有理由的。Freedman认为“如果我们用仅仅是机械的程序例如精神药物学的方式来对待情感回应或信仰时,就会导致出现一种威胁。情感增强技术的使用导致我们用“机械论”的术语来对待自己,这些术语与我们作为自由和有责任的主体的存在是格格不入的”[4]。我们在把自己机械化的过程中威胁着我们自己作为一种特别的存在的自由、有责任的、理性的主体。当我们在对人的精神状态进行操纵的过程中,我们技术手段的介入都必然将人视为客体。在这一过程当中,技术成为了主体,而人则沦为客体。
总之,当我们通过神经生物技术的手段得到增强的情感的时候,我们获得的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肤浅的替代品而不是我们通过真正的自我的努力实现的真实的情感。我们用技术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精神状态的同时,贬低了人类自身的价值,丧失了我们作为人类独特的尊严,沦为了技术的附属物。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不论这些被动增强的动机是为了自己、国家、雇主的利益,还是为了孩子、自己的前途,它们都忽视了被增强者的自主权、影响了他们的自我判断能力,从而使其丧失了自主、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尊严。
三、结语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关于情感增强技术所导致的伦理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在增强中才会出现这些伦理问题,而是与增强相比,对精神疾病的治疗会较少地面对这些争议。因为我们在面对治疗的效果和产生的伦理问题时往往会考虑一个利害的比率。当一种治疗方式可以治愈病人的疾病时同时产生较少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既包括身体的副作用也包括社会的副作用)时我们就不会选择放弃它。当然,治疗疾病也会有不同的方式,我们需要在不同的方式中选择相对利益最大而争议最小的一种方式。这种选择就需要我们结合多方面的因素来进行衡量并作出科学的评估。而在涉及到增强的使用中,我们就应该更加注意,必须在使用时将其引起的伦理问题纳入考虑,考察情感增强技术使用的利弊,做出科学理性的选择。
[1]Adam J.Kolber.Ethical Implications of Memory Dampening [A].edited by Martha J.Farah Neuroethics:An Introduction with Readings[C].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2010:97.
[2]Maartjie Schemmer.Ethics of Pharmacological Mood Enhancement[A].Jens Clausen,Neil Levy edit,Handbook of Neuroethics,[C].Springer Press,2014:11,1177~1190.
[3]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71
[4]Freedman,C Aspirin for the Mind?Some Ethical Worries about Psychopharmacology.In E.Parens,ed.Enhancing Human Traits:Eth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M].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35.
[5]Neil Levy.Neuroethics: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M].London,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120.
[6]GingerA.Hoffman.TreatingYourselfasanObject:Self-Objection and Ethical Dimensions of Antidepressant Use [J].Neuroethics,2013,6:170.
R-052
A
1007-9106(2016)04-0147-03
康小梅(1991—),女,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方向为神经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