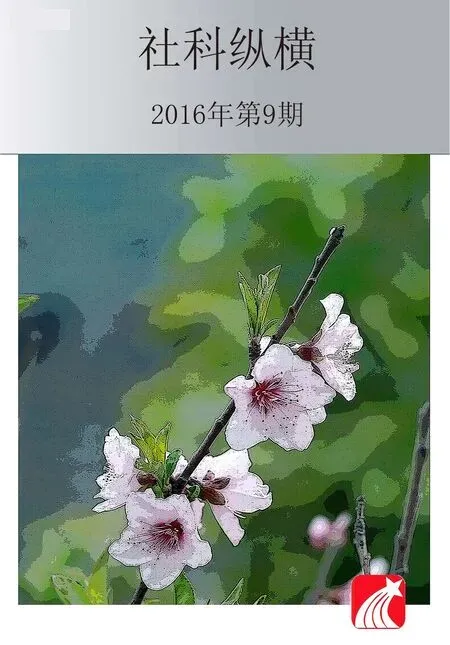浅析重庆谈判前后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舆情互动与民主协商
2016-04-12陈开江杜俊华
陈开江 杜俊华
(1.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重庆401320;2.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重庆400044)
浅析重庆谈判前后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舆情互动与民主协商
陈开江1杜俊华2
(1.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重庆401320;2.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重庆400044)
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舆情互动是实现民主协商的前提,而民主协商则是中共同民主党派进行舆情互动的初衷和直接目标。在重庆谈判前后,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建言献策,对谈判施加影响,中共则与民主党派深入地展开了舆情互动与民主协商。这是重庆谈判能够顺利达成《双十协定》的重要原因。中共由此而与民主党派人士打成一片,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民政府的统治。这有助于为当前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深入开展民主协商提供一些启示。
中共民主党派重庆谈判舆情互动民主协商
中共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在抗战时期,中共和民主党派为了共同抗日,限制国民政府的独裁,已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合作。由于民主党派力量在抗战期间的深入发展,加之他们较为注重反映和传递国统区民众的呼声,到抗战结束时,民主党派所反映的社会舆情已上升为国统区民众舆论的重要表现形式。在重庆谈判前后,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建言献策,对谈判施加影响,中共则与之深入地展开了舆情互动与民主协商。中共与民主党派由此而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为建国后双方的深入合作夯实了基础。本文通过梳理重庆谈判前后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舆情互动与民主协商,探讨舆情互动与民主协商的相互关系,以期对当今中共同民主党派深入进行民主协商提供一些启示。
在重庆谈判期间,我国的民主党派主要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其时的民主同盟主要由三党和三派组成,即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第三党(重庆谈判时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均是在重庆谈判结束后的解放战争期间组建的。中国致公党虽然早在1925年就已成立,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海外总部就基本上中止了活动。因此,文中所述的民主党派主要是中国民主同盟。
一、谈判前夕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舆情互动
八年抗战,中华民族以伤亡3500多万军民、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累计超过6000多亿美元的沉重代价,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连年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均强烈反对再生战事,普遍希望战后国内和平,重建家园,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早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5年7月28日,中国民主同盟就通过时局宣言向国共两党“痛切呼吁”:全国人民“所蕲求者,惟在中国之民主与团结”,“倘使团结无望,民主不行,则抗战之成果不保;或更于胜利在望之时,我竟演成内战。过去牺牲,尽付东流,国家前途,宁堪想象?如必执小群而遗大众;重私斗而忘公仇,则所谓领导抗战,解救人民,于义安在?是不仅自毁其光荣之历史;抑何词以对我数万万支撑抗战多灾多难之同胞。此则国共两党,共有责任,而执政之党,尤无可诿责者也”[1](P49)。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1945年8月15日),民盟中央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公开喊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并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普选”产生“全国人民所一致需要的国民大会”,“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以“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等十条主张,要求国共两党对其主张“给以充分的考虑”[2](P135-137)。
但民众的和平梦在抗战胜利后却面临破灭的危险,这从蒋介石于1945年8月11日发布的受降命令便可看出几丝端倪:各部队“对敌放弃要点,应即派部队进驻”,“距敌较远之部队,应察状况可能向前推进”,而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命令第十八集团军所辖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3](P48)。
在剥夺浴血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之受降权的同时,蒋介石就已经埋下了内战“地雷”。蒋自己也深信“驻防待命”根本束缚不了中共军队,故而在同日他发出了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电报。此后他又于8月20日和23日发出了两封电报,催促毛赴渝谈判。在电文里,他大打民众舆论牌,“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磋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4]蒋介石三次电邀毛赴渝谈判,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广大民众渴求和平的心理,民众舆论为之兴奋不已,均期盼毛泽东能应邀赴渝参加和谈。各持中间立场的报刊纷纷转载蒋之电文,不少民主党派人士也发声附和。
中共对蒋介石的谈判诚意持怀疑态度,早在蒋发来第一封电报时,就明确指出:“请毛往渝全系欺骗。”[5](P223)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判围绕赴渝谈判而浮现出来的民众舆情,认为应向广大民众尤其是向民主党派人士指出事实真相。为了揭穿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回应民主党派的呼声,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布《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要求国民党“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中共“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解决,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6](P4-5)。中共的时局宣言采纳了民主党派人士的不少建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维护了民主党派的利益。
民主党派的和谈呼声也使中共领导人认识到,如若毛不赴渝,共产党势必在舆论上陷入蒋介石布下的不义圈套,被国民党指斥为内战的发动者、破坏国家的统一和民众的公敌。到时候蒋就会以民众舆论为借口,通过战争来对付共产党;民主党派可能因此而疏远共产党,甚至被蒋介石利用。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权衡,最终议决让毛赴渝和谈。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所言:“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7](P1052)
二、谈判期间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舆情互动与民主协商
1945年8月28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和谈代表团乘坐美军飞机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张澜、沈钧儒等民主党派人士纷纷赶至机场迎接,中外记者也蜂拥至现场采访。毛向在场的民主党派人士和记者发放书面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建立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8]。通过书面谈话,毛泽东广泛宣传了中共的谈判主张,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民主党派人士对中共谈判态度的疑虑,还推动了民主党派向中共靠拢。
在国共谈判期间,为了对谈判施加影响,民主党派人士纷纷阐发其谈判主张,希望能引起国共谈判双方的关注和高度重视。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张申府于9月10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谈判之际与问题的解决》一文。他通过该文希望“在谈判之际”,“双方停止任何或有的军事摩擦”,“双方保障尽量让人说话,尽量让人贡献意见,而且尽量征求人的意见”;呼吁尽快解决国共争端,“在今日这个紧急迫切的时候,问题要解决,就要快,不要拖。拖只有把问题拖大,最后没有一点好处”[9]。
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在9月14日发表了《对目前时局谈话》,重申“胜利到来,举国人民都一致希望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凡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不仅遭到国人之坚决反对,且友邦不许”,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并提出了解决国共争端的建议:“目前解放区之军队及政权问题之解决,须着眼于实际的情况,觅取妥当而切实的过渡办法,因此等军队与政权,系由当地人民取自敌人,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至于行政系统之统一,军队还于国家,本属一个民主统一国家之绝对的原则,但其实现之先决条件在以全国政治能真正民主化,无任何党派的军队,无任何党派特殊利益的保留”[10]。
民盟领导人张澜于9月18日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上发表了《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提出了以下建言:“目前为国家团结统一之绝好时机,国家一切问题应乘此时机求彻底之解决,更应求全盘之解决。惟其如此,则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目前商谈之中心问题,不外政治与军事。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目前军事问题,积极须着眼于国防,确保国家之自由、独立;消极须着眼于化除畛域,保障国家之和平建设……如能操用全盘统筹之编遣计划,以目前养三百个师之物力,移用于极少数量之常备军,而此种常备军,绝对超越党派关系,绝对遵守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之原则”[11](P20-21)。
1945年9月26日,闻一多、李公朴、罗隆基等民盟代表组织昆明各界628名爱国人士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通电全国,告诫国人“有些专制主义者,还在想打内战”,呼吁“国共两党应该竭诚相见,以人民利益为重,采用公开方式,邀请民主党派及进步人士参与协商”,并提出了“彻底实施民主改革,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立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并召开政治会议,成立全国一致的民主政府”等六大政治主张[12]。
中共则一方面积极通过公共平台尤其是新闻媒体平台了解其时民主党派人士的情况和想法,体察其所传递的民众舆情,另一方面中共同民主党派人士展开了广泛的的会谈接触。在会谈接触过程中,中共和民主党派相互坦诚相待,交流各自的政治观点。民主党派向共产党详尽阐述了他们的意见和呼声,中共则向民主党派宣示了共产党的主张和面临的实际情况,由此双方实现了充分的舆情互动。在舆情互动所铸成的良好氛围中,中共与民主党派就重大问题和相互分歧进行民主协商。在意见协调一致后中共积极吸取民主党派人士建议中的有益养分,民主党派也进一步向中共靠拢,积极配合和支持中共的政治主张。
为了与民主党派人士更深入地进行舆情互动和民主协商,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谈判间隙,多次探望、会见民盟领导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在抵达重庆后的第三天(8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就专程到“特园”拜访张澜。当晚,中共代表在“桂园”举行晚宴招待民主党派人士,借宴会平台中共与民主党派人士对谈判内容进行了初步磋商。9月2日,民盟中央在“特园”设午宴回请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席间中共与民盟双方深入研讨了国内局势,中共进一步宣传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并通报了国共两党的谈判情况。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又于9月10日晚在“桂园”设宴招待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张申府等民主党派人士,对近日来国共谈判的最新进展情况再次进行了通报。次日,毛泽东在“桂园”会晤黄炎培、沈钧儒等民主党派人士,再度就团结协商问题与之交换意见。毛泽东还特地于9月15日赶至特园与张澜长谈,毛向张澜透露了谈判的初期成果和面临的分歧,二人就如何维护谈判成果进行了深入协商。
中共代表还注重通过公共演讲平台与民主党派人士进行舆情互动。在9月18日下午由国民参政会举行的在渝参政员茶会上,毛泽东在致词中乐观地认为“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呼吁“各党各派应在上述方针之下”,“团结一致,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13]。
由于民主党派人士的政治主张所凝集的民众舆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统区广大民众的呼声,在重庆谈判时中共在作出决策前尽可能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采纳了他们的不少建议。中共于9月3日正式提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其以下内容上充分吸取了民主党派人士建议:“承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之方针”;“结束党治”,“迅速采取必要办法,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的地步”;“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协商国是,讨论团结建国大计、民主的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及抗战后复员善后等项问题”;并提出了“释放政治犯”、“保证各项自由”、“取消特务”等实现“党派平等合法的必须办法”[14](P20)。其谈判意见不仅让民主党派人士对中共持赞许态度,还使中共代表团在谈判中经常处于主动地位。
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对谈判内容的误会和分歧主要通过舆情互动和民主协商来予以化解。民主党派人士希望借中共的谈判谋取更多的权益,他们担心共产党在谈判中被国民党诱骗,作出妥协性让步损害民主党派的利益。而中共为了满足广大民众的和平愿望,实现缔结和平协议,在谈判方案中作出了重大让步,甚至放弃了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共放弃民主联合政府的谈判主张引起了民盟领导人张澜等人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及时与之沟通,消除双方的误会。在国共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国民党散布谣言,其媒体放出口风,把谈判停滞不前的主要责任推卸给共产党。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及时与民主党派人士频频沟通,向他们揭露重庆谈判陷入僵局的真相,宣示中共的民主主张,抨击国民党的专横和对民主条款的打压。经过中共代表与民主党派人士之间的深入沟通,使之充分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他们对国民党刻意阻扰和谈的行径进行了批评,在舆论上有效地配合中共谈判,使国民党在谈判中陷入被动。
重庆《新华日报》在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舆情互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他们相互间进行沟通和化解分歧的重要平台。中共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全面报道民主党派的和谈主张和建议,从而更全面地倾听民主党派人士对谈判的呼声;另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的相关报道向民主党派人士披露谈判双方存在的分歧,中共主动做出的重大让步,国民党的暗中作梗。中共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分歧在于民盟的“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和“军队属于国家”等政治主张[15](P20-21)。对此,《新华日报》特地于10月2日刊发社论《民主的政治和民主的军事不可分割》,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的军事实际上是民主的政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两者是不能互相分割的。鱼不能离开水,人民的军队离开了人民的政权,其唯一的结果便是消灭。”“消灭了”人民的军队,“让全国人民都处在旧式的军队的控制之下,让全国的军队的革新失掉一个基础与模范,对国家有什么好?消灭了人民的军队,其下文当然就是消灭人民的政权”[16]。
中共通过诚恳的舆情互动和民主协商,博得了民主党派人士的认可和支持。为了响应和落实重庆谈判内容,在重庆谈判即将结束之际(1945年10月1日至12日),民盟在渝“特园”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议决了《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等文件,其《政治报告》主张:政治会议“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对当前国家的一切问题逐步地积渐地求得全盘彻底解决”;联合政府是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的途径,”是“实现军队国家化,彻底消弥内战,平息党争的唯一枢轴”;国民大会“必须是代表真正民意的机关,而不是任何党派包办操纵的机关”[17](P79-81)。这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中共的谈判主张。
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最终于1945年10月10日签定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民主党派人士与中共代表之间广泛的舆情互动和民主协商,是重庆谈判最终得以达成《双十协定》的重要原因。《双十协定》议决“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国民政府还在《双十协定》中明确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18](P250)。这表明国民政府也被迫认可了各民主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因此,《双十协定》也是民主党派的胜利。其时正在召开的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对此发表宣言称:“这次国共谈判决定由政府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与同盟一贯的主张正相符合”,决定“采取积极的态度以为应付”,并希望通过党派间的政治协商,使“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能够早日成为现实”[19](P89-90)。
中共和谈代表在渝谈判期间同民主党派人士展开了广泛的舆情互动和民主协商。通过与民主党派人士之间的舆情互动和民主协商,中共使民主党派充分了解和深刻领会了中共的主张和方针政策,纠正了对中共的一些误解和偏见,在政治立场上向中共靠拢。中共领导人则通过民主党派充分了解了国统区民众的相关情况和意愿,洞悉了民主党派人士的思想状况。这为共产党正确分析和认识形势,完善其方针政策,更广泛地团结和争取国统区民众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谈判结束后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舆情互动与民主协商的深化
但《双十协定》的墨迹还未干,蒋介石就下发“剿匪”密令,调集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民主党派人士对此愤怒不已,他们强烈谴责国民党的内战行径,“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20](P102)他们身先士卒,积极组织和参加反内战活动。黄炎培致信在渝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建议组织”包括各方代表的调查团,“前往冲突发生地点,商谈解决”[21];张澜、沈钧儒等倡导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开展反内战集会,呼吁国统区民众行动起来制止内战;民盟昆明支部还积极参与和推动了当地高校学生掀起的以反内战为目标的“一二·一”运动。
在此期间,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舆情互动与民主协商呈现深化发展态势。中共代表和重庆《新华日报》不时向民主党派人士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内战和独裁行为。在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停战谈判之际,周恩来同志还专程拜访张澜,就停战谈判问题交换意见。1945年12月底张澜致函国共双方政协代表,要求国共两党的军队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元旦”“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22]。由于民众舆论的压力和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的胜利,国民政府不得不接受中共和民主党派人士的要求,于1946年1月10日与中共达成了“停战协定”。在随后召开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民盟代表与中共代表密切配合,相互沟通,共同协商,为国家的和平与民主建言献策;在议决重大事项时,民盟与中共事先会下交换意见,会中采取联合行动,同国民党作斗争,使之最终通过了有利于人民冲破国民党独裁的五项决议。
但国民党继续坚持维护和扩大其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试图强化其独裁统治。他们无视重庆谈判成果,竭力破坏政协会议召开,阻扰政协决议的落实,甚至不惜对留在重庆的中共谈判人员下毒手,制造了黑茶山空难。其后竟于1946年6月底悍然策动全面内战,置民众和平意愿于不顾。这引发民主党派人士对国民政府的强烈反感,他们一方面通过公开声明和宣言,抗议内战;另一方面他们加紧与中共合作,积极声援和支持国统区爱国群众掀起的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而国民政府也加强了对民主党派人士的残害。他们对那些反内战独裁的民主党派人士,在屡屡施以威胁和殴打都难以使之屈从的情况下,竟无耻地采用暗杀手段来遏制民间的异己声音,李公朴和闻一多等民主党派人士惨遭杀害。
血腥的暗杀非但没有达到国民政府的预期效果,反而促使更多民主党派人士认清了国民政府的真面目,他们对它彻底寒心,开始拒绝与国民党合作。在由国民党独揽、为其独裁披上合法外衣的伪国民大会召开之际,绝大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响应中共号召,联合抵制和抨击违背政协决议的伪国大,拒绝参加国民党在伪国大后改组的政府。这使国民党试图利用伪国大孤立共产党和实现内战独裁政策合法化的图谋破产,国民政府统治的权威光环因此而急剧消退,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境地。恼羞成怒的国民党试图强行管控和打压民主党派,乃至强令解散了民盟等民主党派。但这反而推动了不少民主党派人士与中共携手合作,并肩作战,共同投入到反对罔顾民意的国民政府的斗争中来。这些民主党派人士从此走上了反蒋道路,他们成为中共领导的反对国民政府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重要力量。
结语
重庆谈判表明,民主党派所承载和传递的社会舆情已成为国统区民众舆论的一大表现形式,研判民主党派人士的政治呼声,积极与民主党派展开舆情互动与民主协商已成为当时中共的一大统战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其阶级本质决定了它能倾听民主党派呼声,与之能有效地进行舆情互动。中共通过民主党派来了解和体察国统区的民众舆情,进而以其诚意反映和代表民意,赢得民心。而国民党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虽然它也曾一度关注来自民主党派的民众舆情,但其拒绝包容和广泛分享政治权益的一党专政立场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认可并接纳民主党派,同民主党派切实展开舆情互动和民主协商。这也使国民党的权威光环逐渐消退,民主党派人士开始疏远、敌视乃至反对国民党。
经过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舆情互动,民主党派人士真正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在重庆谈判结束后他们与中共之间的政治合作日益深入,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共在民主党派中的威望和影响与日俱增,这有效壮大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声势和力量。到后来,大部分民主党派与中共形成了事实上的统一战线关系,共同反对国民政府的内战和独裁。
由此可见,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舆情互动是实现民主协商的前提,只有通过舆情互动,对双方的意愿和要求进行深入沟通,才能有效化解双方的误解和分歧,真正实现民主协商。民主协商是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进行舆情互动的初衷和直接目标,双方只有通过民主协商取得系列成果,才能深入推动下一波舆情互动,为舆情互动和民主协商的良性循环打下坚实基础。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舆情互动和民主协商也是共产党群众路线工作方式在统战工作中的具体应用,为其统战工作注入了活力。
[1]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A].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2]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A].载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重庆谈判纪实[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3]日本投降后中共动态资料汇编[G].无编者及出版地,1945.
[4]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定大计[N].中央日报,1945-08-21(2).
[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A].载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重庆谈判纪实[C].
[7]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A].载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8]毛泽东同志谈话[N].重庆新华日报,1945-08-29(2).
[9]谈判之际与问题的解决[N].重庆新华日报,1945-09-10(2).
[10]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对目前时局发表谈话[N].重庆新华日报,1945-09-14(2).
[11]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A].载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第十卷中[C].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
[12]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通电[N].重庆新华日报,1945-09-26(2).
[13]在渝参政会昨日举行茶会,毛泽东同志出席致词[N].重庆新华日报,1949-09-19(2).
[14]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A].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5]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A].载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第十卷中[C].
[16]民主的政治和民主的军事不可分割[N].重庆新华日报,1945-10-02(2).
[17]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A].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C].
[18]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A].载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重庆谈判纪实[C].
[19]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A].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C].
[20]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为制止内战发表谈话[A].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C].
[21]黄炎培先生呼吁立即停止冲突[N].重庆新华日报,1945-11-02(2).
[22]民主同盟致函国共双方,请迅即停止内战[N].重庆新华日报,1945-12-31(2).
D231
A
1007-9106(2016)09-0129-06
*本文为2015年第三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际环境嬗变视阈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历程研究”(15FDJ002);2015年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党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两党对民众舆情的研判应对及其经验得失研究”(2015SKG227)。
陈开江(1977—),男,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思政部讲师,硕士;杜俊华(1971—),男,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心负责人,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