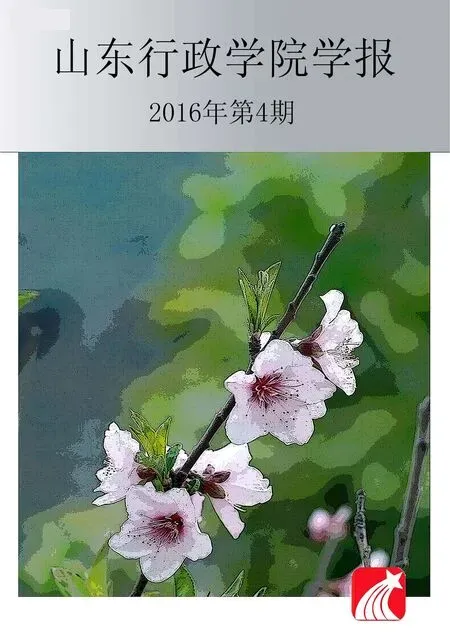陕西作家贾平凹的本土书写
2016-04-11谢悦
谢悦
(西北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000)
陕西作家贾平凹的本土书写
谢悦
(西北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000)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读者可以嗅到浓郁的陕西乡土气息,正是因为他谙熟民俗风情,他的作品才能极为和谐地融化在那些风土人情之中;因为贾平凹对自己所生长的土地有着极其深沉的情感,才使得他的作品更具悲天悯人的批判性。他一面为乡村文明和传统文化逐渐被侵吞浸染而唱出凄凉的挽歌,一面又为传统文化中那些顽固残留的劣根性而悲叹。在贾平凹的作品中,读者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秦魂,那就是关中传统文化重礼贵教的精神内核和经世致用的原则。无论时代和文学的潮流如何翻腾变化,贾平凹总能扎根陕西这片土地,用生命写出最璀璨的文学篇章。
贾平凹;乡土情结;本土书写
一、关于贾平凹小说的研究归类综述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中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他的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均有着很高的成就。对于贾平凹的研究也一直是文学学术界的热点,从中国知网上搜索到的情况来看,2000年之后关于研究贾平凹的学术论文已有数百篇之多,研究的方向也十分全面,将其梳理总结后发现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大类:
1.关于贾平凹小说《废都》的研究。这一类研究文章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其内容主要针对《废都》人物塑造和叙事展开讨论,其中既有对《废都》的批判,认为《废都》是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也有对《废都》饱加赞誉的文章,认为《废都》的小说特性预示着宏大叙述已经被解构,真实述说了中年人的经验和心境,其中更不乏一些理性探索、冷静辨析的文章,如雷达的《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等,对《废都》的写作结构、小说意象、人物塑造等进行了全面具体的客观评析。可以说,对于小说《废都》的研究是开启贾平凹作品研究的第一道门。
2.关于贾平凹小说的叙事范式进行的研究分析。这其中包含了关于贾平凹小说的语言特色的研究、人物形象塑造创新的研究、漫流式的情节结构处理的研究、神秘化叙事的研究等诸多细分。关于贾平凹的叙事范式,大部分学者还是较为推崇的,著名学者韩鲁华曾说“中国叙事即强调了叙事的整体性、流动性、模糊性和散点透视性”,[1]他认为贾平凹传承了真正的中国式的文学叙事,并给予这种叙事方式以高度的赞扬;而关于贾平凹的语言特色方面在学术界也有着较高的评价,如黄世权在 《日常说话与民间狂欢——论贾平凹作品的叙述语调》一文中说,“这种叙述语调是向民间自由立场的回归,是日常生活无羁自由的弱化狂欢”,是文学上零距离的表达方式;在人物塑造的创新方面,贾平凹素有“鬼才”之称,他塑造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大部分学者将其和“魔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从神秘化的角度去分析他的创作思路,并挖掘出其笔下人物背后所隐含的意象解说和宗教思想,透过庞杂神秘的人物体系进而归纳出贾平凹的文学态度和写作思路。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中,他大胆尝试了许多处理手法上的变化和别具一格的创新,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尝试,所以对于贾平凹叙事范式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3.地域文化对贾平凹创作的影响。这一类的文章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最多的一类。大量学者关于这方面的探索都是从“商州系列”来展开,随之从《废都》以进入到贾平凹笔下独特的城市文化之中,再从《高老庄》等系列作品来揭示社会生活中的传统的颓败。李自国总结道,“商州:皈依灵魂的误读;西京:失却家园的废都;高老庄:超越激愤的还乡”,[2]很好地总结了贾平凹创作中的本土文化探索路径。贾平凹作品的内在文化体系和他所受到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在贾平凹地域创作的研究方面,就显得更为复杂和交融,其中主要有对乡村文化的追忆,也有对城市文化的反思,同时还有对传统文化的追寻、现代文化与传统的碰撞与冲突等若干方面的探索。肖云儒在《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中总结了贾平凹在小说创作中的内在文化体系,即“文化和谐、文化错位、文化崩溃和文化建构”,这是目前针对贾平凹文化体系研究中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理论研究。
在三秦山地和传统文化的包裹之下,贾平凹成为追求本土味道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童年、少年经历及其该地区的巫鬼文化现象都对贾平凹的创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浸润和影响,这也成就了他的写作风格和作品风貌,所以对于地域文化方面的研究在关于贾平凹的研究中具有极为深刻的价值和意义。但在这一类的研究中,针对贾平凹作品中本土书写的研究都较为零散,对这一视角的丰富和完善还需要我们加以更多的投入和关注。
二、作家贾平凹的本土书写
说到作家的本土性,贾平凹无疑是这方面的佼佼者,贾平凹的本土书写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所蕴含的内容也包含了多个层次,如其作品中浓郁的乡土风格、民风民俗下的各色人物、面对乡村文明和传统文化逐渐被侵吞浸染的批判语境、扎根本土的价值观、陕西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等诸多方面。我们在梳理了关于作家贾平凹的第三类研究后,有意对贾平凹作品中的乡土文化及贾平凹本土书写的几个方面进行系统有机地融合,对其进行多方面地讨论和分析。
(一)贾平凹作品中的乡土气息
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嗅到浓郁的陕西乡土气息,正是因为他谙熟民俗风情,作品也仿佛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极为和谐地融化在那些风土人情之中。这种本土性在文学作品中往往起到天然的积极效用,我们可以将这种本土性的影响来源理解为家乡的水土和家乡的人两个方面。
1.家乡的水土。贾平凹的家乡,正是他文学创作的宝地——商州,因此说到贾平凹作品的乡土气息,就必须从商州说起。商州是贾平凹的文学之根,从《怀念狼》,到《废都》,到《浮躁》,再到《秦腔》,我们可以看到贾平凹文学创作的陕西地图,这是一张从商州到西安,再回到商州的地图。对于他的家乡商州,他曾有过这样一段表白:“商州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是一块相当偏僻、贫瘠的土地,但异常美丽,其山川走势,流水脉象,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乃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构成了极其丰富的、独特的神秘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仰观可以无奇不大,俯察可以无奇不胜。”故乡的土地深深地滋养着贾平凹的创作灵魂和生命,以至于他的作品中所创造出来的角色和场景是那么的亲切熟悉,就像我们自己的家乡和我们身边的父兄邻里。
在小说集《山地笔记》[3]中,可以看到作者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这里偏远贫瘠却山清水秀,这里古老落后却神奇灵秀,这里的风俗包罗万象,这里的人物形形色色,大量的民俗细节都在贾平凹的书中有着生动而详细的描画记录,正是这些海量而生动的细节才搭建起了贾平凹小说如此多元的文学殿堂。
2.家乡的人。相比于80年代的寻根派,贾平凹对民族文化的运用也要更高明些,他不是为了本土性而本土性,也没有把文化当作文学作品的全部,文化的元素只是他作品中的一些原料和调味品,他的小说则是完全挣脱了民族文化的格局和框框,一路“性情”到底。
在他的笔下,人物的性情中流露出本土性的民风民俗,而民风民俗中又进一步地展现出人性。例如《马玉林和他的儿子》[4]中的马老汉,他用耗尽自己的生命来坚守着以德报怨,宽容隐忍的做人准则,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令人心灵震撼的道德光芒;《天狗》[5]中的天狗,面对师娘时,他本可以在“招夫养夫”的情况下行使丈夫的权利,但他却“发乎情止乎礼”,淳朴真挚,坚韧而有原则;《古堡》[6]中的张老大,他勤劳智慧一心为公,全心全意地想帮助乡亲致富,最终却落得一个被逼而死的结果,令人无奈心酸,同时也写出了村人的自私和仇富的愚昧心态。在这些栩栩如生却形色各异的人物形象中,读者既能看到高尚、质朴的农民本性,也能看到愚昧、丑陋的农民劣根性;既描摹出了人性的美好,也揭露出了人性的凶残、贪婪。贾平凹对人物塑造的成功正是来自于他所生活的村庄,他从真实的邻里乡亲的身上汲取养分以激活自己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物的身上捕捉到浓浓的乡土地气,这也是他的作品得以生动鲜活的原因。
(二)贾平凹作品中的乡土情怀
一个作家的乡土情怀主要来源于作家对苦难社会的忧患意识,来源于作家内心深处对童年生活的记忆与体验。乡村与都市的对立碰撞,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冲突隔阂,历史沉思与未来展望,这些都显示了作家对社会深层问题的由衷的关怀与思考,而贾平凹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他对长安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身份归属感,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乡村和中国城市已成为他创作的重要内涵,他的文学精神集成了长安乡土文化中的悲悯情怀和底层文化,在他的作品中时时刻刻地强调着这种情感的表达。
1.乡土情怀中的悲情表达。与《废都》同时出名的有个乐器叫“埙”。不少人看了《废都》[7]知道了“埙”。小说里的落魄文人周敏没事儿就在老城墙上吹埙。埙,这种低调的乐器演奏出来的醇厚悠长的声音可以穿过远古的蛮荒,可以击穿秦时明月汉时关,可以轻飘飘托起唐朝的霓裳羽衣,可以承载宋朝的花间词章、元朝的如梦小令,听到埙的声音,我们可以沿着飞沙弥漫的栈道,从千年之前一路流传到今。埙是中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吹奏乐器。贾平凹曾在散文 《埙和鬼都是可爱的》中说:“我喜欢埙,它是泥捏的东西,发的是土声,是地气。现代文明产生下的种种新式乐器,可以演奏华丽的东西,但绝没有埙那样蕴含着的一种魔怪。上帝用泥捏人的时候,也捏了这埙。人凿七孔有了灵魂,埙凿七孔有了神韵。”[8]正如贾平凹喜欢的乐器一样,他的许多作品和文字中也透出一股“埙”的意味,可以说埙也是贾平凹作品中的陕西调子,一曲曲呜呜咽咽的埙声是贾平凹笔下的最好乐器,这种晦涩沉郁、深沉凝重的格调正是他创作的特别之处,往往给人一种悲戚、哀婉的感受,意蕴颇深。例如在小说《废都》中就充斥着这样的笔调,主人公庄之蝶迷恋于肉体情欲与精神废墟,受困于知识分子意识深处的自恋和道德的沦丧,最终陷入到更深层的痛苦和彷徨中,使得全书都被蒙上了悲性的色彩。评论家雷达曾说:书中写到庄之蝶时常用一个词,叫“泼烦”,作者正是通过主人的“泼烦”来表达自己的忧虑。描写现代都市的《白夜》[9]也是如此,夜郎、宽哥等小人物通过各式的挣扎于沉浮乱世,却不能避免悲剧命运的结局,这也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彷徨与深沉的忧世情怀。
2.乡土情怀中的批判性。我们说,作家生活的语境是其语言创作风格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空气。正是因为贾平凹对自己所生长的土地有着极其深沉的情感,才使得他的作品更具悲天悯人的批判性。在他的作品中有着对现代城市文明和传统农耕文明的双重批判,既批判了农民的落后与愚昧,也批判了城市文明中的冷漠和矛盾,以及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互相冲突的今天,人们对生活和生命的困惑。在他的作品《高老庄》[10]中,原始的乡村土地被现代商业文明所污染破坏,同时暴露了传统文化中丑陋的一面和传统文化分崩退化的问题。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担子和文化担子,充满了对民族文化前途的忧思。
他一面为乡村文明和传统文化逐渐被侵吞浸染而唱出凄凉的挽歌,一面又为传统文化中那些顽固残留的劣根性而悲叹,他用一种置身事外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生长并热爱着的这片土地,企图通过文字振臂高呼,引起注意和共鸣,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作家强烈的文化批判情感。契科夫说:“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着责任的人,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贾平凹正是这样的作家,他的身上就带有这种充满责任感的批判情怀,而这种书写悲情和感伤的情怀往往都表现出苦涩沉郁的创作文风,正如同低沉的埙所发出的时代颤音。
乡土情怀是一个作家摆脱不开的精神纠缠,也是一个作家永远的文化情结,它对于作者文学思路的形成、创作手法的追求、艺术境界的升华都起着决定性作用。贾平凹生于三秦土地,对于家乡的认知和情感正是经历了从欢乐到忧郁、从困惑到悲伤、从绝望到超越的过程,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作家从单纯走向成熟的不断发展的乡土情怀。
(三)贾平凹作品中的乡土灵魂
“从以地方为写作对象的写作者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其写作方式可分为两种,即他者的书写与自者的书写,而自者的书写又可分为‘离乡’式写作、‘返乡’式写作与‘在乡’式写作。”[11]贾平凹正是典型的“在乡”式写作。作为一个强调本土书写的作家,只有真正地扎根于秦地才能写出秦魂,写出本土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1.扎根本土的价值观。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秦声弥散、秦韵流淌,以及浓浓的秦味和无处不在的秦魂。贾平凹就像一颗大树,深深地扎根在陕西文学的这片土地上,他所处的文学视角也散发出这种扎根本土的调性。
贾平凹曾在《山地笔记》的序中写到:“我是山里人,山养活了我,我也懂得了山。后来,我进了城,在山里爱山,离开山,更想山了。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活了,文笔也活了,我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我们可以从贾平凹笔下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身上管中窥豹,看出贾平凹对故土深沉广博的热爱和他的陕西视角。成名后的贾平凹也未曾离开陕西土地,身居都市的他始终把笔触对准最富有地气和生气的本土秦人,比如小说《高兴》[12]中的一系列角色,有乞丐、拾荒者、民工、妓女,他们游荡在西安城里的边边角角,如同陌上浮尘,漂泊无依,他们的命运和情感都和这个社会的发展紧紧相扣,一个极为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命运在作者的笔下浮现出来,这也是作者野心的表达,如果没有扎根于人民、扎根于土地,就无法创作出如此生动的角色群体;再比如《土门》[13]中的成义对城市中最后村庄的守护失败,他们和城市进化这台巨大机器的抗争博弈却被击得片甲不留,最终沦为城市化的牺牲品,这样的表达让读者为之痛心。贾平凹在本土题材的创作上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进击超越,这全都源于他对这片土地和土地上人民的深厚的感情。
2.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贾平凹身上的这种秦魂,还包含着陕西人“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乡约文化。比如《秦腔》[14]中的康田生觉得儿子替人打土坯却打下一堆烂货,即便已经交工,却过意不去,执意亲自登门为人家重新打好;四妹子则是对乡邻做出承诺,凡是购买她的种鸡,出了任何问题她都会上门服务,从不失信于人。这样的例子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比比皆是,而这些自然而然的本土书写正是因为他身上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烙印。贾平凹从小受到的就是非常传统的家庭教育,在他的家中对长幼尊卑、仁义孝道等方面的要求极为严苛,家中有家训、族内有族规、一个大的村落则有自己的乡约,这些陕西关中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都秉承着重礼贵教、经世致用的原则,并充分地渗透到作者的文学创作中去。
贾平凹以自己生长的土地为依托,给大家勾画出了一副陕西土地的“清明上河图”。他怀着对故土、对亲人的赤子之心,以谦卑富有同情的写作伦理和细致绵渺的叙事艺术,记述下了乡村和社会发生的那些或大或小的变化;他以一个作家的广博和深沉,用纸笔完成了对作家自我和现实世界的双重塑造。
三、对贾平凹本土书写的研究意义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最为典型的乡土叙事作家,以农耕文化和乡村文化为依托的长安传统文化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正因如此,他的创作才有着多层次的思想内涵和文学深蕴。我们现在探究贾平凹的本土书写,正是为了深入了解贾平凹的文化心理和创作风格,挖掘他创作中所呈现的“乡土情结”在长安文化本土书写中的意义。
(一)对贾平凹本土书写研究的理论意义
贾平凹的本土书写是根植于三秦土地的。最早对三秦文化、对陕西作家作品影响的研究,是1997年陕西师范大学李维凯教授所著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他首次从秦文化的角度切入,全面系统地阐释了贾平凹等陕西作家作品与乡土文化的关系,开启了这方面研究的先河,1998年,他又在兰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了《20世纪秦地小说的文化轨迹》,其中详细地阐述了秦地文化对陕西作家作品及创作心态的深层影响。但就从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一方向的研究和著作来说,探究作家的乡土情结与本土书写的关系的大都是泛谈类的,即便有较为深刻的研究和挖掘,但对某一具体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还是较少的,尤其是受限于地域文化观念的影响,其中许多研究往往把重点放在“长安文化”上,而忽视了“长安文化”往往是辐射于整个关中地区乃至整个秦地、西北的,也有一些研究偏执于贾平凹笔下的“乡村文化”,缺少对贾平凹城市作品的梳理。
对作家本土书写的研究,即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文学所构成影响的研究,应该是细化并具体的,我们对贾平凹本土书写的探究正是基于此而进行的。贾平凹的本土书写是一个全面而庞大的课题,其中所蕴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因此从作家贾平凹本身出发去深入了解他的乡土文化创作背景和创作思路,能帮助我们了解到他的作品的内部书写动因。了解了他的本土书写,即是把握了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解构他的作品层次,从题材的选择到叙事的方法,从话语的主题风格到作品的审美高度,从艺术构思到美学趣味,都可以反映出他本土书写的思想路径与创作纹理,体现了贾平凹独特的创作风格,因此对贾平凹本土书写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对贾平凹本土书写研究的现实意义
面对贾平凹这样的乡土作家,我们可以看到他始终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徘徊,这种矛盾和焦虑的心态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创作,并清晰地呈现在作品之中。对于他作品中的这种背景和心态进行具体的剖析和深入的解读,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贾平凹这样的乡土作家内心彷徨的根源,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精神危机和现实矛盾,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挖掘和弘扬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常说了解文学就能了解世界,因为文学本身就富有现实关照的意义。贾平凹早期商州系列作品中对商州乡土风情的讴歌,中期《废都》等作品中面对城市文化冲击的绝望和困境,后期《秦腔》等作品中对精神世界的重构,都是贾平凹的现代性焦虑产生的复杂因素,即对中国飞速发展的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质疑、对古老乡村文化的希望和失望、对回归传统精神文明的渴望,等等,这种种的复杂情绪,也是现代中国人乃至全人类普遍面临的社会课题。我们探究贾平凹的本土写作,是以探寻贾平凹的创作伦理为切入点,进而对社会问题进行文学表达和动态的展现,这也是我们对贾平凹本土书写研究的现实意义。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地域性的现代文学创作必须具有发展务实的眼光和态度,这就要求作家和学者在进行本土书写的同时也要把握住文化发展的精神实质,强化作家的社会意识和人类意识,找寻文学与地域、时代的联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展现出秦地文学本土书写特有的文化优势。
贾平凹从“废都”来,他吼着“秦腔”,憨厚、朴实的外表透着浓郁呛人的“黄土味”,他的作品中浓厚的商周地方风貌、风土人情和他对中国农村、农民的独特视角的理解,是他作品中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乱吼秦腔,来一碗长面喜气洋洋,没调辣子嘟嘟囔囔!”一曲陕西歌谣唱出了秦人的特点,也唱出了这方土地所孕育出的精气神儿,而这土地上不仅能生出这样豪放的歌谣,还能长出一颗质朴又璀璨的丑石——文学奇才贾平凹。一个“凹”字,正是他人生路径的写真。生活,文学,虽然曲里拐弯,却曲径通幽;虽然总有起伏,却总是向上。弯弯曲曲、晦涩难懂、土得掉渣的调子,正是贾平凹的陕西调子。作家贾平凹不在乎身后有多少读者,他在乎的是在写作中精神领域的自我释放,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文人式潇洒,他才能真正地创作出吸引读者的优秀文学作品。无论时代和文学的潮流如何翻腾变化,他总能勇立涛头,扎根陕西这片土地,用生命写出最璀璨的文学篇章。
[1]韩鲁华.论带灯及贾平凹中国式文学叙事[J].小说评论,2013(04):43-56.
[2]李自国.论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家园意识[J].当代文坛,2000(06):24-28.
[3]贾平凹.山地笔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4]贾平凹.鸡窝洼人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5]贾平凹.贾平凹作品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6]贾平凹.古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贾平凹.废都[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8]贾平凹.说舍得: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9]贾平凹.白夜[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10]贾平凹.高老庄[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11]汪政.地方作家反哺本土的杰作 [N].光明日报,2016-04-03.
[12]贾平凹.高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13]贾平凹.土门[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
[14]贾平凹.秦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编辑:鹿风芍
I206.7
A
2095-7238(2016)04-0113-06
10.3969/J.ISSN.2095-7238.2016.04.018
2016-05-20
谢悦(1986-),女,西安广播电视台文学编辑,西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