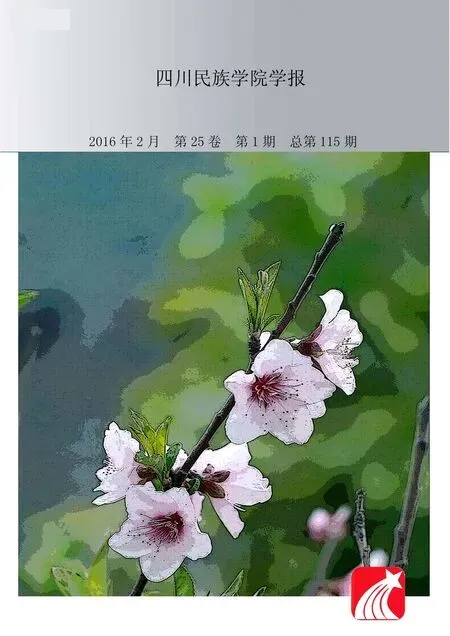东汉汉羌关系述论
2016-04-11王东岳
王东岳
★历史·文化★
东汉汉羌关系述论
王东岳
【摘要】东汉时,羌族取代匈奴成为其最具威胁的边患,连续不断的羌汉战争不但给给东汉王朝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亦动摇着东汉的统治基础,最终东汉王朝在羌汉人民联合攻击之下走向灭亡。东汉汉羌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激烈的民族对抗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因此,后世学者有必要对东汉汉羌关系进行深入的总结、分析,以为后世借鉴。
【关键词 】东汉;汉羌和战;治羌政策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Qiang and Ha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ang Dongyue
【Abstract】Qiang had ever become the most serious border threat for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because of its national power. On the one hand, the frequent wars between Qiang and Han were the serious economical burdens for the governme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wars had shaken the regime base. And finally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perished due to the wars. But it's necessary for the later scholars to think over the wars between Qiang and Han, an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Qiang and Han in that period.
【Key words】Eastern Han Dynas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Qiang and Han; governing policies in Qiang
相比于西汉,东汉时期的汉羌关系基本可以用“战争连年”一词进行概括,东汉与羌人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多达百起,遍布整个东汉王朝。这些战争历时长久,耗资巨大,虽然在灵帝时彻底解决了羌人的反叛,但汉祚也因此而衰,无奈史家感慨:“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1](《后汉书﹒西羌传》)。由于东汉时期羌汉战争频繁,为数众多,不能一一而详,因此只以较重大者进行论述,以掌其概要。
一、东汉中前期与烧当羌的和战
烧当是秦厉公是时无弋爰剑的十三世孙,由于烧当在汉元帝时“复豪健,其子孙更依烧当为种号”[1](《后汉书﹒西羌传》)。但至其玄孙滇良时,“世居河北大允谷,种小人贫”[1](《后汉书﹒西羌传》),常常受到强大的先零、卑湳等部落的侵犯。滇良父子忍辱负重,待实力增长之后就集合部众及其他诸种起来反抗并且夺取了先零等居住的自然条件优越的榆中地区,烧当羌“由是始强”。强大起来的烧当羌“常雄诸羌”,并与东汉政府冲突不断。
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滇良二子滇吾及滇岸寇陇西塞,陇西太守刘盱、谒者张鸿先后与其战,但均以失败告终,直到明帝永平元年(58年),东汉遣中郎将窦固及捕虏将军马武将“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郡羌胡兵及驰刑”[1](《后汉书﹒马武传》)合兵四万进击滇良,才“大破之”,滇岸、滇吾遂先后皆降。
汉章帝时,烧当羌复反叛出塞,此次反叛历时长久,给东汉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建初二年(77年),滇吾子迷吾“与诸众聚兵,欲叛出塞”[1](《后汉书﹒西羌传》),金城太守郝崇与滇吾战,崇兵大败。汉朝镇压的失败导致羌胡勾结寇边,护羌校尉吴棠对此无能为力,朝廷遂以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傅育虽在军事上先后击败了迷吾、号吾兄弟,但在处理二人归附问题上方法不当,遂导致两人又先后复反叛。对于反叛无常的迷吾兄弟,东汉于章和元年(87),派傅育及陇西、张掖、酒泉诸太守共领兵二万合击迷吾。傅育在追击迷吾途中,遭到伏兵,“夜突育营,营中惊坏散走,育下马手战,杀十馀人而死”[1](《后汉书﹒西羌传》);傅育战死之后,张纡代为护羌校尉并派兵大败迷吾,受到重创的迷吾兵败请降。为报傅育被杀之仇,张纡在受降时,“设兵大会,施毒酒中”,遂诛杀酋豪八百馀人,“斩迷吾等五人头,以祭育家”[1](《后汉书﹒西羌传》)。
张纡在个人仇恨的驱使下,设计杀死迷吾的做法,激起了迷吾种人的怨怒。迷吾子迷唐遂“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女及金银聘纳诸种,解仇交质,将五千人寇陇西塞”[1](《后汉书﹒西羌传》),张纡面对“种众炽盛”的迷唐“不能讨”,朝廷遂以张掖太守邓训为校尉。邓训改变单纯以军事镇压的方法而以金钱财物离间诸种,“由是诸种少解”。但直到和帝永元四年(92年)邓训病卒,聂尚、贯友、史充、吴祉相继为校尉,他们或以财货离间或以军事进行打击,但迷唐时叛时降,终未彻底解决。永元十二年(100年)时,迷唐因不满与其结盟的累姐种附汉,击杀其酋豪,这种暴虐行为最终导致迷唐“党援益疎”。此时的护羌校尉周鲔趁机将兵三万出塞击之,此战颇有成效,迷唐“种人瓦解,降者六千馀寇,分徙汉阳、安定、陇西”[1](《后汉书﹒西羌传》)。迷唐本人则率其残部不满千人,远遁赐支河首,从此其势力不再对东汉构成威胁。至此,由迷吾、迷唐父子引起的历章、和二帝,前后绵延二十余年,东汉政府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动乱至此结束,长期的战乱也给羌、汉百姓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与苦难。
二、东汉中后期与先零、锺羌等的和战
先零羌是东汉另一支强大的羌族支系,其种人居住于大、小榆谷之间,势力强盛,往往与其他诸羌结盟协同寇边,在东汉安帝时终成大祸。
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东汉政府遣骑都尉王宏率金城、陇西、汉阳等郡的降羌数千骑出征西域,由于王宏粗暴行事,且羌人又担心久征不还,因此部队行到酒泉时,众羌大多叛逃。先零羌的滇零借此机会“与锺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1](《后汉书﹒西羌传》),虽然此时的羌人归附日久,已长期不习兵事,他们“或持竹竿木枝以伐戈矛,或负板案以为盾,或执铜镜以象兵”[1](《后汉书﹒西羌传》),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力日衰的东汉政府也无法进行有效的镇压,而是“郡县畏懦不能制”[1](《后汉书﹒西羌传》)。其后,锺羌与先零先后两次次击败前来镇压的邓骘军队,于是滇零更加狂妄,“自称‘天子’于北地”[1](《后汉书﹒西羌传》),封官授印,建都丁奚城(今宁县灵武东南)。然后招集诸羌,“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三辅,断陇道”[1](《后汉书﹒西羌传》)。至此,羌人的反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侵袭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河西、陇右等边郡,而是深入到三辅重镇以及赵魏内郡,大大加深了东汉政府的统治危机;对于羌族自身而言,他们也从混乱无组织的零星反抗朝着有组织有目的的起义发展。
面对羌族强盛的进攻势头,东汉在镇压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防卫。首先,为防止羌民南下威胁京都洛阳,东汉政府将京城的五营精兵集中屯于孟津;其次,又在魏郡到中山之间修筑了六百一十六所营坞,以防羌民东进。又因为边郡太守长官多是内郡人,并不专心守战,而是纷纷上言请将边郡百姓内徙以避寇难。朝廷被迫实行部分放弃的收缩战略,“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1](《后汉书﹒西羌传》)但举家迁徙对这些百姓来说不仅意味着生活上的不便,而且也会损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正如王符在潜夫论中所说:“民之于徙,甚于伏法。”[2](《潜夫论·实边篇》)因此他们不乐去旧。州郡长官就以暴力相对待,毁坏庄稼、村落以及防御设施,强制百姓内徙。边吏的暴政加上连年的饥荒蝗灾,致使百姓 “丧其太半”[1](《后汉书﹒西羌传》)。因此,东汉强制徙民的措施反而将部分百姓推到了其对立面,遂出现了“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1](《后汉书﹒西羌传》)。永初六年(112年),滇零死,其子零昌立,杜季贡及零昌同种狼莫继续合谋攻汉。此后数年,汉与零昌、狼莫、杜季贡数战,各有胜负。直到元初四年(117年)校尉任尚派人先后刺死杜季贡及零昌,次年刺杀狼莫为止,为时十余载的以先零羌为首的叛乱才暂时告一段落。但东汉政府为此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馀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1](《后汉书﹒西羌传》)。
顺帝时期的羌叛情况极为复杂,虽然每次反叛的时间较短,但是由于参加反叛的羌种复杂,涉及塞外羌以及内郡羌胡,甚至亦有东汉官员受羌人引诱而叛逃塞外,因此对江河日下的东汉王朝来说,其打击是重大的。
锺羌是东汉中后期时期另一支强大的羌人支系,时常联合别种羌袭击东汉边地,且时叛时降,难以解决。顺帝永建元年(126年)时,陇西郡的锺羌反叛,校尉马贤将兵七千人在临洮击败锺羌,锺羌大豪遂率领种人降汉,至此凉州部稍安。但边郡的安宁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顺帝阳嘉三年(134年),锺羌良封等复寇陇西、汉阳,朝廷遂拜击羌数有功的马贤为谒者镇抚诸羌。马贤于次年先后领兵进击良封、且昌等锺羌酋豪,良封、且昌先后皆降。顺帝时期锺羌的两次叛乱至此告一段落。
但其后东汉分别以天性刻虐的来饥、刘炳为并、凉刺史,他们“到州之日,多所扰发”[1](《后汉书﹒西羌传》),遂导致且冻、傅难等羌于永和五年(140年)攻金城,并联合西塞及湟中诸羌胡联合“大寇三辅,杀害长吏”[1](《后汉书﹒西羌传》)。羌胡诸兵再次兵临三辅,朝廷震恐,来饥、刘炳被免,复派马贤为征西将军,发兵十万屯汉阳;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三郡修筑坞壁三百所以备羌胡。但马贤在次年射姑山一战中兵败战死,马贤曾数次成功平定羌人叛乱,熟习羌务,是抗击羌胡的一大强将,如今马贤的战死遂使诸羌更加肆意,“东西羌遂大合”[1](《后汉书﹒西羌传》)。之后,巩唐种、罕种羌趁机相继为乱,“烧园陵、掠关中,杀伤长吏”[1](《后汉书﹒西羌传》),凉州诸郡再次陷入战乱的漩涡,朝廷又一次被迫徙凉州百姓于三辅内地,派兵屯三辅。马贤战死后,东汉政府于汉安元年(142年)启用赵沖为护羌校尉,赵沖改用怀柔之策以招降叛羌,罕种羌遂“率邑落五千馀户诣沖降”[1](《后汉书﹒西羌传》),至此,羌乱的威胁稍稍缓解,“唯烧何种三千馀落据参?(属安定郡)北界”[1](《后汉书﹒西羌传》),东汉政府遂在汉安三年(143年)集中进攻烧何部,烧何种战败“诸种前后三万馀户诣凉州刺史降”[1](《后汉书﹒西羌传》)。
羌人的叛乱少解,护羌从事马玄于建康元年(144年)“将众羌亡出塞”。护羌校尉赵沖在此次追击马玄的战役中,由于所将降胡于中途叛逃,赵沖在追击所逃降胡时遭遇伏兵而战死,但其“前后多所斩获,羌由是衰耗”。此次叛乱虽然很快平定,但是也反映出东汉王朝在对待羌人政策上的无能为力以及漏洞百出。
桓灵之世,已是东汉季世,诸羌相结,“自春至秋,无日不战”[3](《通鉴记事本末·诸羌叛服》)并且羌胡数次兵至三辅,“覆没营坞”、“烧民庐舍”;东汉王朝终在羌人及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走向末日。
三、东汉治羌政策评议
在对待羌人的政治制度上,东汉政府并没有很大的创新,其做法基本因袭西汉。但从治羌效果来看,两汉可谓大不相同。西汉时,羌人叛乱次数少,时间短,对社会的破坏性小;而东汉时羌人叛乱连绵不断,形势复杂,社会破坏性极大。故有学者提出,东汉的治羌政策是错误的。问题是相似的政策制度,如何会有不同的效果,这是值得后世学者深思和解决的问题。形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是及其复杂的,现作以简要分析:
首先,东汉时羌人的大规模内徙为羌汉矛盾的激化提供了温床。吕思勉先生曾说:“羌兵不若匈奴之强,众不逮鲜卑之盛,而患转甚于匈奴、鲜卑者,以其居塞内故也”[4],这种观点固然有合理之处,但并不是根本原因。因为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的羌人内迁以接受先进的中原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民族融合的表现,若东汉政府以及地方官吏管理方法得当,就能避免不必要的民族矛盾。但是由于这些内迁的羌人得不到应有的待遇,“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1](《后汉书﹒西羌传》,甚至出现安夷县吏强娶卑湳羌妇的事情。而且东汉政府在“以夷伐夷”思想的指导下,经常离间诸羌之间的关系,征发羌民出征,这就引起了众羌的不满,安帝时的滇零叛乱正是东汉强制征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民出征西域而引起的。由此观之,内徙的羌人不但处于社会的下层,而且还要频繁为东汉政府出战卖命,这也就无怪乎羌人对东汉王朝带有敌对态度,双方矛盾便一触即发。
其次,两汉政治中心的变化,对两汉的边防部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影响到羌汉关系。西汉时由于帝都长安近胡,为了保卫帝都的安全,极为重视长安附近边郡武装力量建设。以郡太守为统领的边郡兵是边郡的常备军,由于边郡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战争又比较频繁,因而边郡除太守设置幕府,以长史佐辅领兵外,在各要塞还往往置若干部都尉,具体负责各屯区的军事安全,“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5](《汉书·地理志》)。据统计,西汉北边24郡共设有55个部都尉,因此,西汉边郡兵拥有相当实力抵御寇掠,一旦有变,能够迅速有效的予以解决,因此羌人不敢肆意妄为。
而东汉定都洛阳,政治中心向东南移动,长安、三辅、凉州等地的政治地位自然有所下降。东汉政府又实行以防守为主的边防收缩战略,光武帝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官”[1](《后汉书﹒光武帝纪》),以后尽管在陇西、金城等地偶有都尉的复置,但只是“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6](《盐铁论》)已非西汉之通行之制;又于建武二十三年(47年)“诏罢边郡亭侯吏卒”[1](《后汉书﹒光武帝纪》),即罢省了西汉以来的边郡侯望系统。两相比较东汉的边防部署远不及西汉严密,这就使羌人有了可乘之机。
东汉政治中心的变化还影响到东汉政府对待凉州、陇右等地的态度上。安帝时,先零羌的滇零侵汉、寇三辅,历时数年耗费巨大而不见功效,致使朝廷出现了弃守凉州的做法,其原因就在于边郡的“两千石、令、长多内郡人”,“痛不著神,祸不及我家,故争郡县以内徙”[2](《潜夫论·实边》)。这样的事情在西汉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首都长安靠近西陲,凉州、陇西之地的安危与长安的存亡息息相关,唇亡则齿寒,西汉政府不会弃凉州而不顾。
最后,羌人“不立君长,无想长一”的社会组织形式,也给东汉平定羌乱带来了一定的不便。羌人的这种相对无组织形式,致使部族众多、各自为战,西汉对匈奴实行的和亲政策首先是行不通的;又因为羌人支系众多,他们时而单独寇边时而联合侵汉,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领导核心,以致东汉政府就算想主动出击,也因为羌种众多且没有一个有效的攻击目标而作罢,东汉政府只能被动的一次又一次地镇压此起彼伏的羌人起义。
参考文献
[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东汉]王符.潜夫论[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3][宋]袁枢.通鉴记事本末[M]. 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4]吕思勉.秦汉史[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p238
[5][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6][西汉]桓宽.盐铁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责任编辑:林俊华]
作者简介:王东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邮编:710000)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824(2016)01-004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