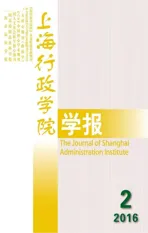参与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兼论社会主体视域下社会管理体制的构建
2016-04-09高建华陆昌兴
高建华 陆昌兴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桂林541004)
参与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兼论社会主体视域下社会管理体制的构建
高建华陆昌兴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桂林541004)
摘要:从社会主体的研究视角出发,参与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是社会主体社会管理的两种主要形式。参与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需要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探索和借鉴多样化的社会参与和自治方式、培育和发展自治性社会组织、锻造公民和社会参与和自治能力、发挥社会自组织规范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以及加强社会主体社会管理体制构建等方面有所作为。
关键词:参与式社会管理;社会自我管理;社会管理体制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社会管理视域下政府与社会双重管理体制建构研究”(批准号:11YJA630018)、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和谐治理视域下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决策优化研究”(编号:11FZZ005)和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项目“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2015JGA220)的阶段性成果。
陆昌兴男(1988-)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从社会主体的研究视角出发,参与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是社会主体视域下社会管理的两种基本治理形式。如何构建参与式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体制机制,是社会主体视域下社会管理研究绕不开的话题。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社会主体视域下参与式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的理论逻辑、实践框架和体制建构等进行分析和论述。
一、参与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社会主体视域下社会管理的两种治理方式
在社会管理的研究上,存在着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政府的社会管理取向,即研究政府如何对社会进行管理,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另一种管理取向是社会的社会管理取向,即在“社会管理”概念中,“社会”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一般含义的‘社会管理’是相对于国家管理(或曰政治管理)的一个概念。相比之下,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对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的自我管理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管理。”[1]
对应着这两种管理取向,人类社会经历了三种形式的社会管理:政府社会管理、参与式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的历史进程。在原始社会里,“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2](p172)这时的社会管理由于没有国家和政府存在,实行的只能是社会自我管理。到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政府社会管理、参与式社会管理的历史过程。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管理是极端的政府社会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政府社会统治。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有时会“以超然于社会之上的面貌出现,制定和实施某些社会发展和运行需要的所谓‘公共政策’,甚至‘顾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要求的政策”[3](p70),甚至会允许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管理中来,如1998年英国《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关系协定》(COMPACT)就规定:“一个健康的志愿与社区组织是民主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与志愿和社区组织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将有利于制定更好的政策,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取得更好的社区治理效果”[4],等等,但国家职能的主体还是资本主义统治,这时的社会管理仍然是政府社会管理,不过允许一定程度的参与式社会管理存在。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政府社会管理也将继续存在,但由于国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民参与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成为社会管理的主流。此时的社会管理大多是参与式社会管理,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政府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将走向完全的社会自治即社会自我管理阶段。人类社会历史类型与社会管理对应的类型如下表所示:

表1 社会历史类型与社会管理类型对应表
政府社会管理、社会参与管理、社会自我管理是从社会管理主体角度对社会管理模式所做的类型划分。理论认为,以政府为管理主体的社会管理被称为“政府社会管理”。如陈振明等认为,“政府社会管理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系统的、规范的社会政策和法规,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建设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5];以社会作为管理主体的社会管理被称为“社会自我管理”,或“社会自治”,即“社会管理社会”。如周红云认为,“社会管理首先应该强调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因为从根本上说,最广泛起作用的、维持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自动调节机制必然是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6]
而对于什么是参与式社会管理,有人从“协同治理”的角度定义参与式社会管理。如张有亮、赵龙认为,“参与式治理是指基于共同的目的和利益,不同的组织和个人走到一起凝结成一个团体共同民主协商,投票决策,管理社会各项事业的过程。”[7]有人从社会参与的角度定义参与式社会管理。如陈剩勇、徐珣认为,“参与式治理强调以公众的社会参与行动为媒介,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格局中推进社会行动结构的变迁。”[8]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参与式社会管理应该是指社会参与社会管理,也即社会参与政府社会管理的过程,就好像“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有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9](p231)一样,“参与式社会管理”应该是指“在政府治理能力较高而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的现实情形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但出于有效治理需要,政府同时保护并尊重社会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并通过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推动落实各项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直至将其纳入到已有法律体系,从而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10]的过程。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政府社会管理概念中,政府历来被当做政府社会管理的当然主体,而且是最重要的主体,而其他的管理主体都是政府赋权于它们去解决政府“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情,抑或是民主运动的开展迫使政府放权于社会的结果。此外,“参与式社会管理”除了具有通常所说的“社会参与政府社会管理”的传统意蕴外,笔者认为,参与式社会管理还应包括政府参与社会的自我管理过程等。这是因为,在现实的社会管理实践中,政府不仅是社会管理的主导者,也可以成为社会管理的参与者,通过政府参与社会自我管理实践,可以解决社会自我管理过程中的权威性不足、管理能力欠缺等问题。至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管理,尽管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管理与“参与式社会管理”在概念上有些许的差别,如“合作管理”强调政府与社会在社会管理地位上的平等,在管理方式上的民主协商等;“参与式社会管理”主要强调政府与社会关系上的主从关系,参与效果能否达成取决于管理主体的态度以及管理主体与参与者的博弈程度等[11],但是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在此不作细微的区别,我们把“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也纳入到“参与式社会管理”的范畴。毕竟,不管是“合作治理”式社会管理还是“参与式社会管理”,其管理主体都参与了社会管理的相关管理活动。
政府社会管理、参与式社会管理、社会自我管理是社会管理在社会管理主体方面划分的三大常态。作为政府社会管理,本人在相关论文中已做了论述[12],在此不再赘述。而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管理,参与式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是社会主体社会管理的两种主要形式。
(1)社会作为社会管理主体的必要性。关于社会自我管理的问题,大多是从公民社会理论谈起的。如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独立于政治国家,“主要由‘需要的体系’构成的经济交往领域,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所构成的,不能与政治国家相混淆,不能为政治国家所淹没的非政治的社会自主领域”。[13](p168)现代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更是认为,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管理事务,属于政治领域的事务由国家或政府来承担,属于经济领域的事务由市场来承担,而介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事务则由社会来承担,这就是“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法理论。
(2)社会管理与社会参与。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单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认可,就可以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中心。[14]善治理论认为,“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14]而“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理论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而是合作互补关系。“国家和社会都不是固定的实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它们的结构、目标、支持者、规则和社会控制都会发生变化,它们在不断地适应当中互相转化和互相构造。”[15](p57)
(3)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社会自治,意即社会自我管理。张康之教授从行政哲学的角度对它的理解是:“社会自治是这样一种治理:它以服务为内容,在社会自治体系中,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之间会经常性的易位。治理者同时也是被治理者,被治理者同时又是治理活动的参与者。”[16]燕继荣教授的定义为,“社会自治是指社会生活中各类组织(自发组织)、团体(党派和利益团体)、机构(非政府机构如学校、社区管理机构)企业和个人对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17]笔者认为,所谓社会自治,也即社会自我管理,是相对于政府治理而言的,以政府的存在和治理为前提的,又与政府的社会治理相区别的社会自我管理过程,包括公民的自我管理和社会的自我管理。它表明,社会自治的主体是社会,而非政府,是社会自己对自己的管理,政府社会管理和社会参与管理不属于社会自治的范围。
社会自我管理抑或社会自治,是社会管理发展的最高层次,是人类社会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笔者在另一篇论文认为,“社会管理不仅是指政府社会管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社会自我管理。即使是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其终极目标是促使社会实现社会自治,使社会成为无政治的自治社会。”[18]不过,社会自我管理或社会自治相对于遥远的未来社会的难以企望的关照,社会自我管理也有现实的理论关怀和现实必要性:①公民社会理论的现实关照。理论认为,对于自治的社会来说,尽管国家有存在的必要,但国家本身是一种可能的“恶”,若无外力约束,国家权力将会危及社会自治权利的实现。②民主的吁求。俞可平教授指出,“社会自治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之一,是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实现自我解放的基本形式,是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基本政治形式”。[19]③社会现实的需要。一方面,“政府失灵论”认为,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存在“失灵”的一面,即政府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存在“管不了”、“管不好”的方面,需要社会组织等加以弥补;另一方面,社会参与社会管理或社会自我管理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补充,是承担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等等。
二、参与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2个案例
1.参与式社会管理:北京“朝阳群众”模式
北京“朝阳群众”社会管理模式是这样一种管理模式:北京朝阳区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一方面实行驻区民警制,通过民警加强对各个社区的社会管理;另一方面,在社区社会管理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各个社区的社会管理,朝阳区政府采取了发挥所在小区群众积极性的办法,使小区群众参与到配合驻区民警小区治理中去,最终形成小区治理的“天罗地网”。其治理模式结构图和作用机理如下图1所示:

图1 北京“朝阳群众”治理模式结构图
第一,上图中,A代表朝阳区公安派出所,B代表驻区民警,C代表“朝阳群众”。A对B用实线“→”,代表A对B实施派出和管理,即驻社区民警B接受A的指派和命令;C对B用“虚箭头”,代表C 对B传送社区信息,即“朝阳群众”C通过各种形式对社区的“巡查”,把发现社区的“问题”线索向驻社区民警B及时汇报,驻社区民警B根据具体情况要么自己处理,要么把所搜集的信息向派出所A汇报,并由派出所A派出民警与驻社区民警B一同解决,从而构成了“派出所A”通过派出“驻社会民警B",然后“驻社区民警B”通过“群众C”的参与,实现了派出所对所辖社区的有效治理。
第二,上图“驻区民警B”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居于圆圈的“中心”,圆圈的“边缘”是“朝阳群众”,从而构成了“中心-边缘”,也即“指挥-参与”结构。当然,“朝阳群众”尽管处于结构图的“边缘”,但其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是“核心”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通过“朝阳群众”的特殊方式和机制来实现:(1)“朝阳群众”的“整体性”。作为一个“群体”,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而可以发挥“群体”的“整体协同”效应;(2)“朝阳群众”监控方式的“非公开性”和“秘密性”。一方面,可以使违法犯罪分子因不知道谁是监控者而无法躲过群众的监控,同时,“朝阳群众”的非公开性也有利于保护“朝阳群众”不被打击报复;(3)“朝阳群众”成员构成的“群众性”和监控方式的灵活性。“朝阳群众”之所以被称为“群众”就在于它在人员构成上的“群众性”,“他们或许只是在树下乘凉的老人,也有可能是商场超市里身穿制服的保安,还有可能是晨练遛弯买菜时所见的平凡毫无特色的芸芸路人”,这些“群众”的“群众性”和“普遍性”让不法分子防不胜防。(4)一定的沟通举报渠道和处理机制。“首先,巡逻员们要是在社区里发现小的可疑情况,或者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便可向所在的巡逻组长反映,组长在接到线索汇报后,也会和责任区的负责人继续沟通,最后,社区责任区的负责人会把搜集到的线索及时反馈给社区民警”。[20](5)一定的群众关怀和举报激励机制。“朝阳群众”之所以具有“举报”积极性,除了“朝阳群众”“嫉恶如仇”的自觉性和“群防群治”、“邻里相望”的“自身责任担当”以外,必要的激励机制也是必要的。如北京市公安局制定了《关于实施群众举报涉恐涉暴线索奖励办法的通知》,对举报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朝阳群众”社会管理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群防群治”公众参与式社会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是主导者,公众作为社会管理的参与者,共同实现对社区社会管理的合作管理或共同管理。这种参与式社会管理一方面可以发挥各自的管理优势,另一方面可以克服政府或社会任何单方面“不可治理性”缺陷,通过政府与社会合作,从而达致“共同治理”的目的。
2.社会自我管理:杭州“和事佬协会”模式
社会主体的社会管理,不仅包括社会参与管理,而且还包括在特定情况下的社会自我管理,即社会自治。清华大学学者贾西津提出,“社会没有自治能力会非常危险”。她指出,“国家直接面对单个民众是一种非常不稳定、会产生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模式,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模式。”“民主的运作要依赖于基于民情的自由结社,依赖于一个公民社会。当中间阶层被打断的时候,恰恰是革命最容易发生的时候。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间结构起到了社会自治、缓冲社会危机、防止极端和暴力革命的作用”。[21]
浙江杭州“和事佬协会”就是一个化解社会矛盾、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该社会组织以“和为贵”为理念主要从事化解社区矛盾和纠纷工作,其组织成员由社区成员自愿组成或由居民推荐产生,一般由社区内的离退休党员、干部、教师、医生、政法工作人员和社区楼宇居民自治会长、单元居民自治组长担当。其模式结构与作用机理如下图2所示:

图2 杭州“和事佬”协会模式结构与作用机理图
在这个结构模式中,一方面,基层社会组织“和事佬”协会在化解社会矛盾和进行社会管理中发挥着主要的自治作用,如上图中,“和事佬”协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位于圆圈的中心位置,表明群众的公共事务管理由处于中心位置的自治性群众组织“和事佬”协会自行解决,“和事佬”协会成为了群众解决内部公共事务的一个平台和舞台。“群众”与“和事佬”协会之间用“实线”箭头,表示“群众”在解决内部公共事务时对“和事佬”协会的依赖。另一方面,“和事佬”协会也发挥着“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参与作用。如上图中尽管政府与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在解决内部矛盾和纠纷中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政府”与“和事佬”协会之间用“虚线”箭头,是表示:“和事佬”协会组成人员部分是离退休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这种密切关系构成了“和事佬”协会在调解社会矛盾时的“政府”信用资源和资本,是“和事佬”协会顺利开展工作的“信誉”保障和“信任”基础。“和事佬”协会之所以能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源于“和事佬”协会具有以下特点和优势:
第一,“和事佬”协会的基层自治性。作为群众性基层自治组织,“和事佬”协会以“身边人掺和身边事”、“民间智慧化解矛盾纠纷”的“和事佬”做法,“相比于与其无较大瓜葛的政府机关,居民更愿意相信这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调解员,觉得他们就像自己的家人,更为自己考虑”。[22]另一方面,社区里发生的事情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小事也无需拿到政府层面去解决,即使需要拿到政府层面去解决,最初的社会调解也是必要的,可以起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效果或者以“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再找政府”的先行“自治”理念,努力做到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达到“小事尽量不出楼道,大事尽量不出社区”的效果。
第二,成员组成的公认性和“权威性”。“和事佬”一般由社区内德高望重的的成员自荐或居民推荐产生,提高了“和事佬”的公认度、权威性和办事积极性。
第三,专业人员背景性和离退休政府官员参与性。“和事佬”协会成员与以前的邻里纠纷“协调员”“老大妈”不同,除了要有“协调”的热心和积极性以外,还需要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和事佬”协会成员不仅有热心公益的离退休党员、干部,还有熟悉法律知识、持有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法律工作者,甚至还有离退休政法工作人员,他们的“调解”为化解社区矛盾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专业基础、威望基础和信任基础。
第四,行为的劝导性和思想政治工作到位性。作为民间调解组织,“和事佬”协会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和“调解”,主要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和事佬”在实际工作中总结了“和事佬”“三字经”调解工作法,即“缓”、“暖”、“理”。所谓“缓”,是指“对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纠纷要循循善诱,耐心疏导”;所谓“暖”,是指“对当事人情绪激动、欲‘争一口气’的纠纷要笑脸相迎,缓和情绪”;所谓“理”,是指“对当事人强词夺理、无理取闹的纠纷要批评教育,以理服人”。[23]
第五,处理问题的弹性和不拘形式性。“和事佬”协会作为一种颇具弹性的调解力量,在调处纠纷时不需要当事人提出申请,也不拘泥于形式、地点、程序,一经发现,主动介入,当场解决,也不需要专门的文书或书面记录,尽管“和事佬”作出的调解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居民具有很好的约束作用,对于化解具体的矛盾纠纷十分便捷有效。[23]此外,“和事佬”协会离得近、叫得应,也是“草根”力量更容易化解民间矛盾的重要因素。
三.参与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方式创新、实践路径与体制构建
北京“朝阳群众”模式和杭州“和事佬”协会模式为我们如何开展参与式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提供了经验借鉴,但是参与式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如何做好,还需要以下努力:
1.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合理确定政府与社会职能,逐步实现政府还权于社会。无论是参与式社会管理还是社会自我管理,都涉及国家权力放权于民、放权于社会的问题。为此,必须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1)参与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视域下的政府与社会关系不同于统治行政时期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统治与服从关系,而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或此消彼长关系。总的来说,参与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涉及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就是政府要赋权于社会,要么让社会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参与者,要么让社会与政府平起平坐通过平等协商对社会实施“共同管理”,要么让政府参与社会主体社会管理过程,要么政府退出社会管理,由社会自己实施自我管理或社会自治。(2)参与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视域下政府与社会职能要进行相应调整。在参与式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视域下,政府不再是“总体性社会”时期政府职能“包罗万象”,而是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该政府管的政府要管好,不该政府管的政府要有意识地让权给社会或市场。当然,如果政府和社会、市场都不能管好的事情,那么就由政府与社会、市场合作管理。(3)参与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视域下社会主体社会管理是对政府社会管理的必要补充。无论是参与式社会管理还是社会自我管理,政府与社会管理原则上不再是对抗关系,而是一种伙伴关系,或相互依赖关系。一方面,政府不是万能的,在社会管理某些方面会存在“失灵”,需要发挥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社会失灵”或“志愿失灵”,必须在某些方面加强政府的存在和协调。
2.探索和借鉴多种形式的参与式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方式。长期以来,我国不同地方通过不断探索,已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诸如北京“朝阳群众”参与管理模式、杭州“和事佬”协会自我管理模式以及上海静安区“社区矫正”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等等,但是我们在参与式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还需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深化:(1)关于参与式社会管理的主从关系方面,可以有公民参与政府社会管理,也可以有政府参与社会的管理,形成黄宗智所说的“集权的简约治理”[24]模式。当然,也有社会自我管理过程中政府参与社会自治过程。(2)关于参与式社会管理中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问题,理论上认为有三种模式:主导者/职能单位模式、谈判协商模式、系统的协作(协同)模式,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3)关于社会自治的方式创新。社会自治不仅是公民实现自我管理的重要民主权利,是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促进力,因此必须加强以“社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等为内容的社会自治进程。社会自治有赖于公民和社会组织共同功能的发挥。如相对于公民参与社会自治而言,北京“朝阳群众”就发挥了“群防群治”的社会管理作用,除此之外,部分城市开展的交通“志愿者”服务和部分城市开展的“交通协管员”执勤服务,就是公民参与社会自我管理的有效形式。此外,社区自治、行业自治、志愿性社会组织自治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自组织自治等等,都在社会自我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培育和发展自治性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社会参与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的组织载体。作为社会管理的组织载体,无论是参与性社会组织还是自治性社会组织,体现参与性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的最根本特性就是其组织自治性。如果社会组织缺乏自治性,那么社会参与管理或社会自我管理就缺乏意义。为此,首先,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国家应该充分发挥自身阶段拥有的主导功能,创设有利于各种制度逻辑间相互促进、融合而非强化相互抵触的基本制度框架;还应逐步转变现阶段过于细碎、分割与落后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防止不利于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制度逻辑成为主导逻辑”[25];其次,社会组织自身要主动寻求发展空间。只要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应尽可能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特别要重视底层“草根”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第三,要放松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的环境,特别是在社会组织的“进入”方面应该更进一步放开,以促进真正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形成。
4.锻造公民和社会参与与自治能力。在“强政府”、“弱社会”的背景下,一方面,理论上认为公民和社会参与与自治是民主行政的本质要求,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公民、社会参与建设;另一方面,公民和社会对政府长期形成的对社会控制性管理已形成了“路径依赖”和麻木,从而产生“社会管理参与”的“冷漠”。因此,在公民和社会参与与自治问题上,一要政府加强引导,二要政府放权。无论如何,政府对社会的过度干预,不仅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而且对公民和社会参与和自治能力的提升也有负面影响。当然,政府向社会放权,除了政府要摈弃“管制”思维以外,还要进行“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的思维转变。三是公民和社会组织要有参与和自治实践。一方面,政府要有意识地组织公民和社会参与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决策过程;另一方面,要发挥公民和公民组织自组织管理和服务功能,多由群众开展群众性自治活动,以此提高公民和社会组织自治习惯和自治能力。
5.发挥“村规民约”式的社会自组织规范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社会自组织规范是实施社会自我管理的重要“法律”遵循,对社会自我管理起着指导、规范和制约的作用。“村规民约”式的社会自组织规范包括:(1)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契约,村规民约的控制力是全体村民对自身部分权利的自由的让渡而形成的公共权力。”“村规民约获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同,是村民切身利益的集中体现”[26],对农村社会管理具有规约作用。(2)社会组织规约。在自治性社会组织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组织(包括行业组织、行业协会等)的组织自律或行业自律非常重要。这种“自生自发秩序的力量”,不同于国家法律制度所建立的带有强制性的法律秩序,是“国家法律秩序的重要基础和有力补充”。[27](3)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款”。如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地区的侗族“款约”(侗族地区“习惯法”)就对三江侗族地区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进行了“款约法”规定,这些款约无疑对民族地区社会自我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
6、加强社会主体社会管理体制的多层次构建。(1)建立政府为主导,社会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主导的作用,发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权力资源和组织资源作用,有利于社会管理的秩序化运行和权力节制关系。(2)建立社会为主体,政府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主体的社会管理,不仅要发挥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作用,在某种情况下还需要“借用”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权威”作用和“信用”资源作用。(3)建立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社会管理体制,也即政府和社会在社会管理体制建构过程中是一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和社会在社会管理过程中通过平等的民主协商共同解决社会管理中的社会管理难题。(4)建立政府宏观调控的社会自我管理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体制。即政府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放权于社会由社会实施自我管理;当社会自我管理出现问题时,政府才出面干预。(5)建立完全自主的社会自我管理体制。一要培养公民的自我管理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二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组织权力运行机制建设。三要建立正常的成员进入和退出机制以及正常的议事规程和违规行为处理规则;四要加强“权力”资源和“权威”资源建设。社会自我管理中“权威”资源比起“权力”资源来说更具效力。但是,在“权威”资源缺乏或不足的情况下,必要的社会制约“权力”也是必要的,不过,这种社会权力是社会成员公认的组织权力和公民通过民主协商或参与而形成的社会自治制度性权力。
参考文献:
[1]施雪华.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成就、问题与改革[J].学习与探索,2013,(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李劲夫,朱平.国外非政府组织主要功能剖析及其对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启示[J].长沙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
[5]陈振明,李德国,蔡晶晶.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概念辨析[J].东南学术,2005,(4).
[6]周红云.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与政府改革[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5).
[7]张有亮,赵龙.创新社会管理:参与式社会管理新论[J].长白学刊,2011,(4).
[8]陈剩勇,徐珣.参与式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杭州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J].浙江社会科学,2013,(2).
[9]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0]严国萍,任泽涛.论社会管理体制中的社会协同[J].中国行政管理,2013,(4).
[11]张康之.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J].行政论坛,2008,(6).
[12]高建华.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定位与体制建构[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2).
[1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
[15]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6]张康之.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社会自治[J].南京社会科学,2003,(9).
[17]燕继荣.协同治理:社会管理创新之道——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13,(2).
[18]高建华.社会管理:政府社会管理抑或社会自我管理[J].行政论坛,2014,(4).
[19]俞可平.更加重视社会自治[J].人民论坛,2011,(6).
[20]池海波,王慧.揭秘北京朝阳群众:由五股力量构成[EB/OL].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601/c1002-27084283.html.
[21]贾西津:社会没有自治能力会非常危险[EB/OL].http://www.ngocn.net/news/361163.html.
[22]高聪,陈建.我国民间调解组织发展之初探-—基于杭州社区“和事佬”协会实践与发展的思考[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1).
[23]何玲玲,孙金霞.杭州下城区:“和事佬”调解机制化解民间矛盾[EB/OL].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 20090319/15382002.html.
[24]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开放时代,2008,(2).
[25]王诗宗,宋程成.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13,(5).
[26]高鑫.论村规民约的社会控制力[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3).
[27]吴碧林,眭鸿明.行业协会的社会功能及其法治价值[J].江海学刊,2007,(6).
(责任编辑方卿)
Participatory Social Management and Social Self-managemnet: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e Orientation——Also on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 Subject
Gao Jianhua / Lu Changxing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 subject,social management includes participatory social management and society selfmanagemnet. Participatory social management and social self-management need to rebuild government-society relations,explore various management ways,foster and develop autonomous social organizations,and exert the rol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regulations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management systems,etc.
Keywords:Participatory Social Management;Social Self-management;Social Management Systems
作者简介:高建华男(1971-)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5-9-29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6)0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