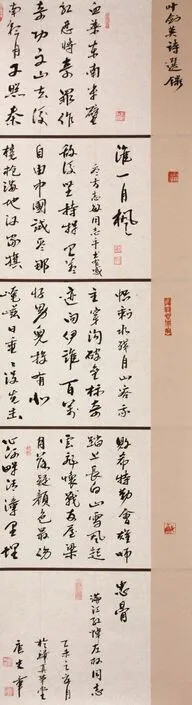唐史章沉默的守望者(节选)
2016-04-08赵立春
文/赵立春
唐史章沉默的守望者(节选)
文/赵立春

安得艺指挽天河,秉御秋毫写春秋。他出生于上世纪青灰色的水墨村落,执油灯照亮前路;五十年后的今天,他脚踩别样的人生路,却以笔勾勒着大同世界。他是艺术家,其造诣与他的名字一样稳重:进则名垂青史,退可断字成章。
为生命注入阳光
正值辰时,八月的峰峰此时正经历着一场罕见的太阳雨,雨声时续时断,空气中膨胀着一丝迷蒙的雾霭,也为今天的出行增添了别样的情趣。黑龙洞畔下车,见一缕阳光投向前方的建筑层,那里是今天的目的地——唐史章书画艺术工作室。
“六十年代,对于我们上一代的人而言可能是家灾国难,对于我们下一代的人可能是天方夜谭,对于我们,可能只是似真似幻的童年。每个人各自的童年或幸福或苦难,我们记住了很多,也忘记了很多。”就在我全心戒备地准备迎接一个书画世界时,唐史章开篇这段意味深长的概述将我从中抽离出来,隐隐感觉到,这次峰峰之旅所得到的,可能不只是文墨精神这么简单。
随着唐史章言辞愈加详细,笔者跟他一起进入了那段满目苍痍的过往,一个对于任何人而言都不愿再去回忆的时代。
1962年,全国粮荒刚过不久,大跃进的残影还停留在当代人的脑海里,除了满腹的热情,人们的生命框架几乎无所支撑。唐史章在这年的冬季出生在磁县白土镇一个平凡的农民家庭,与其他小伙伴不同的是,唐史章在白天玩闹之余,还可以捧着父亲平日里的作画的手稿细细品味,那些亮丽的色彩、细腻的笔触,都令他向往不已。
“在那个时代,顿顿能填饱肚子的人几乎没有,很多人一生都在种地,像我父亲这种兼顾绘画艺术的人很少,当然那个时候不能称为艺术,就是自己写写画画,村子里 谁家需要了就帮忙给人描个玻璃画。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玩的时候也能用小棍在地上画出个花鸟之类的轮廓,小伙伴们也时常来我们家看我父亲的一些练习手稿。”谈话之余,唐史章不时望向窗外,又抬头看看墙上画框中的花鸟,眼眶含着泪花,嘴角极力抿着。我不忍开口,痛断肝肠的回忆里,必定有些不想被人触碰的悲凉。
那是他父亲的作品,父亲前几年去世后,只有这些水墨还能隐约透出老人的影子,他每天都对着这些字画发呆,似乎在回忆过往与父亲学画时的点点滴滴,又似乎在愤恨那个年代,父亲几乎所有的练习手稿都毁于一旦。
诚然,那是一场毁灭文明的大革命。那个时候,唐史章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学生时代除了参加劳动和平时的学习,唐史章为学校设计的板报经常在全校各次评比中遥遥领先,这更坚定他学画的信心,可是水彩并非像现在一样攒点压岁钱随处都能买到的平价货,当年的水彩在农村属于稀有货物,即便是父亲需要的时候,也要骑车几十里去县城或市区才能买到。
唐史章指指窗外,“我们那个年代的太阳比现在要亮很多,但童年色彩是比较灰暗的,大家清一色的黑灰衣服,房子是青砖青瓦,即便有彩色电视,播出来也是色盲一样的视觉效果。唯一出彩的,就是墙上各种各样的红色标语,就像深夜里汽车的远光灯,醒目却也刺眼。”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这种概念我不是很清楚,也许这段话所表述的意义远不像我表面理解的那么简单。有历史的人,气场都比较厚重,他们会把流于岁月的荒芜重拾编制,为记忆重新染色,无需改写历史,只是在过去的世界为现在的自己搭建一个可以缅怀的空间,为父亲,也为自己。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热朝冲淡了陈旧的经济体制,商业的全面崛起带动了经济的整体复苏。高中毕业后殿唐史章顺利地进入峰峰矿务局通二矿,从农民转变成为一名工人,身份的转变带来的是思想觉悟的提高,清闲之余唐史章常提笔写一些通讯报道,将自己的所见所得融入字里行间,这些报道经当地矿区传到了邯郸市的报社,得到了上级领导们的重视,唐史章被调到了新闻宣传报道部门,这给了他更大的艺术发展空间,他将从小跟父亲学到的书画技巧用在了采区办的黑板报上,新颖的样式、专业与趣味性融合得到了矿领导的高度评价。接着,唐史章一路平步青云,十年后,诸如“优秀团干部、优秀共产党员。峰峰矿务局十大青年标兵”这些数不清的头衔并未使唐史章感到麻木,就在周边人都能看到他前程似锦的时候,唐史章做出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下海经商。
“正所谓万事开头难,没有经济基础,没有从商经验,一个文弱书生做出这样的决定在那个年代需要很大的勇气,二十多岁的年纪,长年累月呆在矿区,对青春是极大的浪费,不如趁着年轻拼一下。现在想想,如果当时不狠下心来走出这一步,我肯定要后悔一辈子,苦也罢,累也罢,创业之路本就没有捷径,懒散娇气的人注定一无所有。”说着他站起身,从藏盒里把外出旅行的照片一张张拿出来,“经商的这些年我去了很多地方,看到学到了很多东西,知道了什么是生意,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