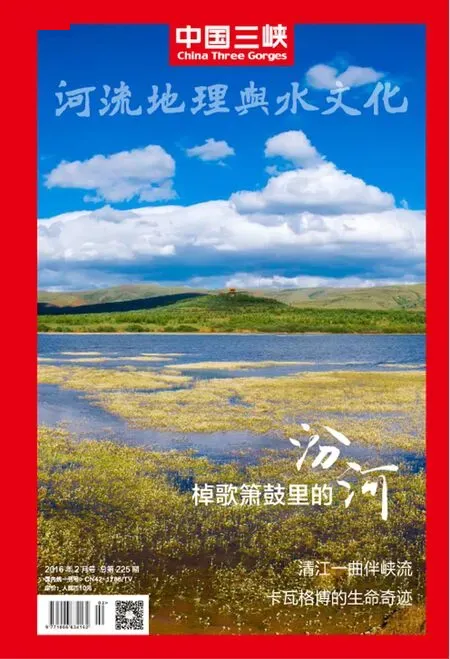管涔之山,汾水出焉
2016-04-06丹菲
管涔之山,汾水出焉
文/丹菲编辑/吴冠宇

发源于山区的汾河,经过太原城时,一改最初的野性,变得宽广、宁静,一派文艺小资。驻足在此,视野开阔,心胸不由得也能豁达起来。汾河,沿着古老的河道从北向南穿越太原城,它所携带的时间印迹,深深镌刻于人们心底,成为精神的底片。上善若水。对于水的特殊感情,让太原人或者任何一个山西人,对母亲河汾河怀有无限的敬意。
汾河源头之水经过巨大的龙嘴喷洒出来。摄影/王牧
人说山西好风光
地肥水美五谷香
左手一指太行山
右手一指是吕梁
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
你看那汾河的水呀
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
……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京上学,新年联欢会上,同学们相互点名表演节目,点到我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让我唱《人说山西好风光》,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来自山西。这首歌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插曲,创作于1959年,由张棣昌谱曲、乔羽作词、郭兰英演唱,上世纪60年代开始响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之作。如今再次聆听,扑面而来的仍然是那个年代清新健康、积极向上的气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歌中将山西的山河大地和百百生活做了精要的概括,仿佛看到豪气满怀的歌唱家郭兰英正站在黄土塬上,背北向南,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吕梁山,再由远及近,望着一条大河欢快地流过脚下的小村庄,耳畔依稀能听到哗啦啦啦的流水声。不知是人伴河唱,还是河伴人唱。
汾河,与山西的煤和醋一样,是山西的响亮标签。
《宁武府志》载:“楼子山,管涔诸峰之一也,其西山间有神祠,祠下汾水源所出,有古碑刻云‘汾源灵沼’,岁月不可考。”人们将汾源之神想象为水母娘娘,长久以来,她在此驻守,被人们祭祀崇拜。
傍水而居,是人类的本能。一条奔腾绵延的河流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史上,重量级的河流如黄河、长江,常常被中国人津津乐道。像一棵树一样,河流枝繁叶茂,根干与枝叶共同弹奏着宇宙生命的旋律,随意拿出其中的一部分,都可以窥视到文明的全息风貌。汾河,黄河的第二大支流,也是山西省最大的河流,流经6市29县(区),全长716公里。
汾者,大也,汾河因此而得名。从古至今,汾河在山西省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围绕它,千万年的人文延展,情感沛然。
汾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东寨镇管涔山脉楼山下的水母洞及周围的龙眼泉、支锅奇石支流,流经东寨、三马营、宫家庄、二马营、头马营、化北屯、山寨、北屯、蒯通关、宁化、坝门口、南屯、子房庙、川湖屯等村庄后出宁武,全程流经忻州、太原、晋中、吕梁、临汾、运城6个地市,29个县市区,在河津市汇入黄河,干流全长716公里。《山海经》载:“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西流注入河。”《水经注》也载:“汾水出太原汾阳之北管涔山。”可以看出,汾河的发源地自古就很明确。
管涔山林海茫茫,溪流淙淙,风光旖旎;因藏有汾河源头,灵气充盈,是人们远行踏青的好去处。源头之水母洞,弥漫着神秘的宗教氛围,折射出当地人对大自然淳朴的敬畏和感恩之情。河流就像一条流动的脐带,人们怀着朝圣之情溯流而上,来看望伟大的母亲。千万年行走,偶尔回归,再来汲取脐带原初的养分,补充拼搏世间的能量。
《宁武府志》载:“楼子山,管涔诸峰之一也,其西山间有神祠,祠下汾水源所出,有古碑刻云‘汾源灵沼’,岁月不可考。”汾源灵沼是宁武古八景之一,如今此处依然是一幅优美的山水画。人们将汾源之神想象为水母娘娘,长久以来,她在此驻守,被人们祭祀崇拜。1995年,当地人在此新修了汾源阁。
水母娘娘是位美丽的女子,身材娇小,鹅蛋脸,斜挽着高高的发髻,披着红斗蓬,笑眯眯地端坐于莲花座上。座前有一口井,便是神秘的汾河之源。走到井前,对水母娘娘和母亲河汾水之源的敬畏让原本还在嘻嘻哈哈的我们,突然安静了下来。每个人轮流用辘轳将水打上来,装满预先备好的空瓶子。轮到我时,略有些胆怯地接过了辘轳,松开绳索,缓缓放入井里。没想到木桶很快就触到了水面,稍稍倾斜,水便装满了。站在源头,曾经令我朝思暮想的汾源圣水就这样触手可及,轻而易举便获得了。万分欣喜地提上来,情不自禁就举到嘴边,细细品尝它的甘洌。形容汾源水,唯独“甘洌”这个词最准确,此时此刻可真正体会到了汉语的美妙。如此被呵护起来的源头水,根本无需做任何人工过滤与消毒,是真正的放心水、保健水。我虔诚地用水抹额头、眼睛、脸颊,希望水母娘娘赐我心明眼亮。灌满的瓶装水我带回家送给了女儿和爱人,希望他们也能得到汾源之神的护佑。

汾河源的水母娘娘。 摄影/王牧
智勇双全的台骀心容天地阴阳,找到了水与人和谐共处的大道。后有金代诗人贾益谦在《台骀庙》诗中歌颂台骀曰:“分野扪参次,山川奠禹先,乱水汾洮别,诸姬沈姒联。”
源头的水母娘娘更多地带有民间宗教信仰的色彩,而汾水之神是一位被载入史籍的大英雄。中国人都知道大禹治水,禹是历史上最牛的治水英雄。但许多人并不知道,比禹早数百年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位了不起的治水大师,他叫台骀。台骀,为上古帝喾时代的人,担任治水官吏,是金天氏少昊的后代,所属部族是最早的一批晋人,其故事散见于《左传》《山海经》《史记》《水经注》等典籍。
远在荒蛮上古时期,洪水滔天,泛滥成灾,被授为玄冥师(负责治水的官吏)的台骀为平复水患,辗转忙碌于如今的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广大地区,降伏水魔,造福人民。台骀的父亲本就是玄冥师,可谓是出生于治水世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宣汾洮、障大泽……帝用嘉之”(《左传·昭公元年》),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终成正果。从此水归河道,远走大海,人水合欢,百百过上安生日子,国家也太平了。因为治水有功,台骀受到帝颛顼的嘉奖,被封为掌管汾州一带的地方官员,受到当地沈、黄、蓐、姒等国家的祭祀和爱戴。

宁武台邰庙。民间传说每年农历五月十八是台邰的生日,当地要举办庙会以示庆祝汾水之神的生诞。 摄影/刘朝晖
台骀一生的大部分时候就活动在汾河流域,那时的汾河充满最初的野性,水流湍急,气盛势高。智勇双全的台骀心容天地阴阳,找到了水与人和谐共处的大道。台骀死后,被人们尊为汾水之神,又称台神。数百年之后,大禹父子治水的故事简直与台骀父子治水的故事如出一辙,这是历史巧合,还是大道奥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台骀先于共工孔壬、鲧禹父子之前治水,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称为“华夏治水第一人”,实在当之无愧。后有金代诗人贾益谦在《台骀庙》诗中歌颂台骀曰:“分野扪参次,山川奠禹先,乱水汾洮别,诸姬沈姒联。”
汾河心平气和地流淌着,极大地滋养和惠顾了两岸的人民。之后,华夏文明在富庶的晋南地区迅速成长,尧、舜、禹相继在晋南建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有确凿的考古遗迹和出土文物佐证。追根溯源,不能否定台骀在改良汾河流域地理环境的功劳。地理之上,再产生人文、经济、政治,人类历史首先是从大自然走出来的。
如今,在汾河岸边的宁武、太原、侯马等地区,依然保留有不同规模的台骀庙,以祭祀汾水之神台骀。其中侯马台骀庙是汾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祭祀汾水之神台骀的古代庙宇。《左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平公生病了,很想搞清楚自己为什么生病,便找人询问,其人说:因为国家很久没有祭祀台骀了,是台骀在作祟。晋平公虔诚地又问大学问家子产:台骀是何方神仙?子产回答:黄帝之子金天氏少昊后代叫昧,昧生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台骀,因治理汾、洮二河有功劳,而被封于汾河流域,由此看来,他就是汾水之神。于是,晋平公下令在汾河边修建台骀庙以祭祀。这个故事叙述完整,非常清楚地交代了至少在距今2500多年前的晋平公时期,晋都新田(今侯马)就已修建起台骀庙。而考古界也给了不容置疑的实证,在汾河边的侯马东台神村发现 的大型夯土台基,据专家考证,即为晋平公时期的台骀庙遗址。现存的台骀庙,则位于西台神村汾河滩南侧的古翠岭上,坐北向南,造型独特,呈船形的城堡,为元、明、清时期重建。站在城堡高高的城墙上,视野开阔,千亩莲花正在怒放,汾河遵照2500多年前治水大师台骀的心思,温驯地向西流进黄河。

洪洞接姑姑送娘娘民俗活动中,迎亲队伍正在过汾河。 摄影/ 王牧
太原晋祠建筑群里,也有台骀庙。台骀成功治理了当时的汾河、洮河(即今位于晋南闻喜县境内的涑水河)和大泽后,人们方在太原安处生息,故又称台骀泽,也就是晋祠之东盛产晋祠大米的大片稻区。
晋祠的台骀庙,并不是一处很显眼的建筑,一般的游人都不太关注这位上古治水人物;来
此祭拜的,多半是张百人,他们对自家的族谱或许比对一条河流的前世今生更为熟悉。但人们唱起“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地流过小村旁”时,仍然充满无限深情。河流之水,即便在大地上有萎缩之时,可在人们心中,一直长流不断。汾水之神台骀,人们仍然可以在古籍中读到他的丰功伟绩,也可以在庙宇里找到他的不老容颜。他的真实存在,使一条河流安澜,无论多么艰难,仍然固守数千年前的一场人水盟誓。

跨越汾河上的祥云桥。 摄影/ 贺子毅
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多风干燥、雾霾严重的钢筋混凝土构筑的现代都市里,水的在场仿佛就是魂灵的最后坚守,使一座经历自然环境变迁和历史风暴吹拂的古老城市依然具备活力和朝气。
汾河孕育了太原城几千年的发展,在经济开发建设的大潮下,也曾一度遭遇危机。
20世纪70年代后期,汾河中下游逐渐断流,太原城区段的水流瘦弱不堪,并成为了工业和生活废水的排污渠,环境恶劣。“引黄入晋工程”给干渴的城市注入新的精气神,山西母亲河汾河接纳了中华母亲河黄河的乳汁,延续哺育一方人民之责。有一半的太原人,用的喝的是引黄入晋工程之水。细究引黄入晋工程之水,已分不清哪些是黄河水分子,哪些是汾河水分子。从黄河分流而来的水通过人工输水管道,最后汇入汾河,再流向包括太原城在内的缺水之地。
干渴涸竭的山西近些年在生态建设上下了狠功夫,龙城太原的都市改造及绿化工程也初见成效。作为太原人,在有时的沙尘雾霾之外,也欣喜地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蓝天白云。城市高架桥的修建使交通拥堵现象明显改善。我家住在学府街,原来去太原火车站怕堵车,常常有意绕滨河路再走迎泽大街,不堵车的情况下也需要40多分钟,如果堵车就一个小时之外了。而如今重修了并州高架路,去太原火车站只需15分钟,大大改善了交通拥堵的状况。

汾河源头河道景观。 摄影/樊丽勇
汾河从北到南贯穿太原城。以汾河为界,太原城大体上分河东和河西。主要城区和山西省、太原市政府职能部门大都在河东,河西主要是工业区和城乡结合部。依汾河而建的滨河公园是太原人的骄傲所在,紧紧围绕“人、城市、生态和文化”的主题,属于公共景点,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是太原人休闲、娱乐、健身、养生的好去处。
1998年,太原市委、市政府对太原城区段胜利桥至南内环桥6公里范围内的河道进行了治理美化,蓄水,种植花草树木。2000年,工程刚刚竣工,瘦弱的汾河滩里重新注满大水,太原人争先恐后,如过节般涌向汾河岸边,享受一条河流被重新整治后所带来的丰盈和美景。人们不约而同将这新生的河流,称作汾河公园或滨河公园。
之后的几年里,太原人加大了对汾河的治理美化,继续向北、向南延伸,实施了二期工程建设,并在胜利桥以北2.4公里范围内,建设成“自然、生态、野趣”的湿地公园,书写了城市绿色生态的一篇大文章,对城市小气候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滨河公园的建设融入了大量的人文历史、园林景观和绿色生态等元素,将这段流经太原市的汾河当作宠儿一样,呵护、培养和装扮。沿河设有步道、绿化带、广场及公路。绿化带和广场分设不同的主题,种植形式内容各异的植物,建构个性语境的亭台廊榭、雕塑、草地、沙滩等。而东西岸并行的两条单向公路,即滨河东路和滨河西路,便是太原城最早的高速路,许多司机宁愿绕行,也要在滨河路上跑上一段,亲近她。宽阔的汾河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架优美壮观的现代桥梁横跨两岸,这些桥梁造型不同,各有喻意,不仅是为交通之便,也充分点缀了河流,还表达了一座城市对一条河流的热爱赞赏之情。每当夜晚华灯开放,桥与河霓虹闪烁,流光溢彩。在这些桥中,有一座是不走车,是专用于游人观景的几何流线型桥梁,十分现代时尚,暖心贴意。
对河流的深情和对水的稀罕,这一点可能许多南方人不懂北方人,更不懂干旱的黄土高原人。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到了太原,我从火车站接上他,专门通过东西向的迎泽大街,上了汾河东岸的滨河路,再向南、向东才拐进内城区,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只是为了让他对我们太原城有个美丽的印象。因为从北到南的那段滨河路,可以看到汾河和汾河上的几座大桥。但我的小心思,朋友根本没看出来,他以为路就是这样走的,城市则大同小异,一条河几座桥算什么。他来自江南,湖泊和河流见得太多了。而我作为太原人,对水的宝贝情怀,对城市唯一河流的珍爱之心,又不能为他这个江南人所懂呢。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多风干燥、雾霾严重的钢筋混凝土构筑的现代都市里,水的在场仿佛就是魂灵的最后坚守,使一座经历自然环境变迁和历史风暴吹拂的古老城市依然具备活力和朝气。

太原汾河北端湿地。 摄影/樊丽勇
我的工作单位就在迎泽大街汾河桥东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午餐后,我都要下到桥底下,沿着汾河散步。一天向北,大约走1.5公里到达漪汾桥,再返回迎泽桥;一天向南,大约走1.2公里到达双塔西桥,再返回。在这来来回回的走动中,春夏秋冬,四季轮转。沿岸的风景绿了又黄,黄了再白,然后再发新芽,重绽鲜花。河中小岛、河边沼泽地,常常有候鸟驻足,河中的野鸭则是一副主人的样子,悠闲自在。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两岸突然间就又冒出了新派的高楼大厦。

蓝天碧水绕龙城。 摄影/樊丽勇
汾河公园独有的风光,给太原增添了别样的关于水的内蕴。除了一排排滨河新型住宅小区、现代商务区,这些年,沿岸新建的文化公益设施让人无限欣慰,如山西省博物院、山西省图书馆、太原市博物馆、太原市图书馆、山西省体育中心、山西煤炭交易中心、碑林园、山西大剧院等等,改善沿岸环境的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沿着微波荡漾的河流,漫游行走,观赏日新月异的两岸风光,太原这个城市不仅能以她2500多年的古老历史骄傲,同时她也是具有现代都市范的。许久或窝在室内,或远走他省,偶尔再来汾河岸边,无论是体验车流的速度、林立的高楼,还是窥视洋溢着自信、从容微笑的人群,都鲜明地感受到太原城的变化,小康生活似乎在这个城市,首先以精神面貌的形式展现着。
太原人在全国的口碑不赖。以一个土生土长的太原人的客观角度来讲,太原人的综合素质真的还不错:内心淳朴实在,勤劳刻苦,低调内敛,但喝酒和做人都豪爽守信,真诚热情。虽然放在全国看,太原的经济发展偏下,但民间却深藏着各色能人、文化人、艺术家,像历史上的王之涣、王昌龄、罗贯中,到现在频频在境外获奖的新锐电影人贾樟柯、科幻小说《三体》的作者刘慈欣,都是山西人的骄傲,也是太原人的骄傲。
无论晨昏,还是白日,汾河两岸都能看到许多太原人,老人带着小孩,男女青年相伴,一家三口说说笑笑;散步的、慢跑的、跳跃的……就连大桥下面,人们也利用来做了天然的歌唱舞台,总有那些精力充沛的人,十分愿意将时光嫁接于河流,以期滋润平实的生活。随着年龄增长,我不再仅仅对远方充满向往,也终于试着阅读自己的城市,并学着爱她,包容她。
汾河水清澈沉静,两岸造型各异的建筑倒映在水中,野鸭漂浮,水鸟翻飞,一时竟让人忘了是在干旱缺水的北方黄土高原。发源于山区的汾河,经过太原城时,一改最初的野性,变得宽广、宁静,一派文艺小资。驻足在此,视野开阔,心胸不由得也能豁达起来。汾河,沿着古老的河道从北向南穿越太原城,它所携带的时间印迹,深深镌刻于人们心底,成为精神的底片。上善若水。对于水的特殊感情,让太原人或者任何一个山西人,对母亲河汾河怀有无限的敬意。
人的意志和现代工程,让一条河流再次繁盛。人水盟誓固守在汾河边,不断上演,当汾河重新注满宽阔的河床,一条河不仅是一条河,它成为一个现代化都市不可或缺的灵量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