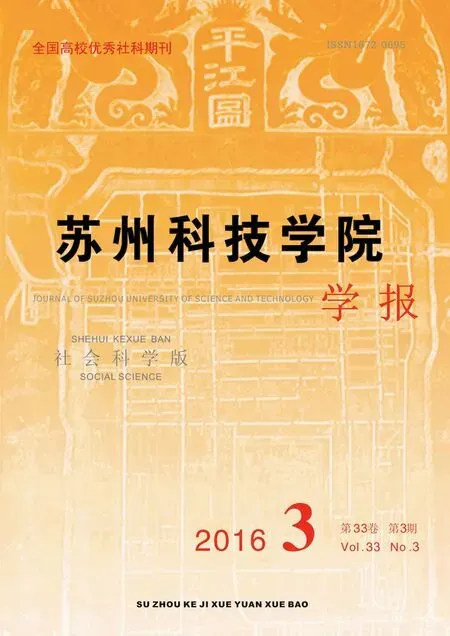诗社幸见收,名场应见斥*
——査慎行结社活动探论
2016-04-05祁高飞
祁高飞,孙 玲
(合肥工业大学 基础部,安徽 宣城 242000 )
诗社幸见收,名场应见斥*
——査慎行结社活动探论
祁高飞,孙玲
(合肥工业大学 基础部,安徽 宣城 242000 )
摘要:雅集结社在清代江南有了充分的发展,江南文化家族大多把它作为本家族惯常采用的诗性存在方式,江南海宁査氏家族也不例外。查慎行晚年与许汝霖等结“四老会”、与同宗五兄弟举“五老会”等会社,并且创作了一系列的娱老诗作。其诗歌的内容主要在于抒发闲适之乐,但始终难以放怀。其艺术特征在于以“浑浩流转”助增诗歌的清韵风调、用典巧妙、对仗工整。查慎行结娱老会而刻意避开“社”字,可见其对文人结社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是从开始的极力排斥、拒绝到晚年的主动结娱老之会,由此可揭示那一时代文士的文化生存状态。
关键词:查慎行;四老会;同宗五老会;雅集结社
清代江南基于地缘与家族的雅集结社是士人不定期的文学节日,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此类文会活动以最生动直观的样本,为那一时代文士的诗性生存状态留下永恒的记忆。虽然清初朝廷为维护政权而实行了政治与文化的高压政策,屡申严禁立盟、讲学、结社之令,但事实上清初“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1]。查慎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雅集结社活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社会学、地域文化学现象。对查慎行结社活动形式、表现特征、诗歌价值等问题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笔者从查慎行交游及结社的相关文献出发,试图通过一定的考释补益清初江南文人结社的基本镜像。
一、许汝霖、査慎行等结“四老会”
查慎行(1650—1727),初名嗣琏,字夏重,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又号初白,海宁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内廷。曾随康熙出游,有“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 (《连日恩赐鲜鱼恭纪》)*见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三十,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下文所引查慎行诗句均出自该书,皆不再出注。之句,时人称其为“烟波钓徒查翰林”[2]780。所作古诗及律绝,局度精整,格调老成。康熙五十二年(1713),乞休归里,家居十余年。雍正四年(1726),因弟查嗣庭讪谤案,以家长失教获罪,被逮入京,次年放归,不久去世。
康熙五十三年(1714),辞官归里的查慎行参与了浙江海宁许汝霖倡导的“四老会”。“四老会”中另外两人分别是杨晚研、陈訏。许汝霖在《致晚研他山两馆丈倡举三老会》中言:
特钟吾晚研先生及查他山馆丈……其会曰三老。每一年祁寒酷暑之外,约于九月、三月一会,会必三日,一日登眺,一日清谈,一日游艺。先期半月单刺走订,三日前再一邀,临期不更,速隔夕登舟黎明赴会……如此计之,一年不过三会,一会不过三日,一人一年所费不过三金,而收四时之嘉景,作九日之快谈,啸傲酣歌,真足千古。[3]
由此可知,此会始由许汝霖倡导发起,最初邀请杨中讷、查慎行二人,待到真正雅集赋诗的时候陈訏也闻讯加入,故曰“四老会”。查慎行《齿会集(尽甲午一年)》序中亦云:“甲午(1714)春杪座主大宗伯许公邀杨晚研宫赞、陈梅溪侍御为娱老会,仆以门下士忝充四人之数,周而复始,迭为主宾。”[4]卷四十三
“四老会”第一次雅集时,査慎行作诗《三月晦日偕杨晚研、陈梅溪赴座主大宗伯许公之招流连三日敬赋五言古体诗一章用志盛事兼订后期》云:
世会赖人持,进难退仍易。公归天下仰,乡曲风先被。逖矣黄发期,旷哉赤松志。远收伊吕迹,近托张邴契。洛社与睢阳,高情千载嗣。九人不迨半,猥许门生厕。良辰春夏交,胜践东西寺。年尊耄将及,兴逸衰犹未。篮舆出匪遥,杖藤行可置。堂无丝竹闹,庭有烟霞腻。外静绝市欢,中虚得池位。虽然营圃墅,亭榭随布置。不穷土木妖,所以矫豪侈。何尝废宴衎,刍豢薄滋味。不列水陆珍,所以警贪鄙。初焉立家法,久乃变风气。道大等行藏,心空冥同异。乘流坎斯止,众取我则弃。欲知鹏鷃游,岂外逍遥义。欲知名教乐,即此真率意。一会日经三,一年会须四。非疏亦非数,天赐皆君赐。幸生山水乡,各有登临地。创举良独难,后期当以次。
根据以上记载,再结合许汝霖诗“一望两山来四叟,高吟描尽画图中”(《次悔余韵》其一)、“五十年来重此会,好同诸老一追论”(《又次悔余韵》)[5],可以得到如下信息:“四老会”在是年3月15日首创,与会者4人;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主持诗会,抒发志向,承传风雅,上追洛社。同时,诗中又言拒兴土木以矫豪奢之风,废宴衎薄滋味以戒贪鄙之习,故此会亦有导引社会风俗的美好愿望,至于愿望达成的手段和方式则为以身立范、循序渐进,“初焉立家法,久乃变风气” ;约定活动时间为除却“祁寒酷暑”的三月和九月,每年四会,会必三日;预计活动内容为一日登眺,一日清谈,一日游艺,饮酒赋诗作啸歌林泉之乐。此四老会在硖川一地影响深远。距离许汝霖、査慎行等人结“四老会”约三个甲子后的光绪癸巳年(1893),蒋学坚在《论硖川人诗三十二绝句仿元遗山论诗体》中仍提及此次结社活动:“久住京华宦兴阑,归偕四老结骚坛。徜徉山水吟怀健,谁识当时一品官。”小注中云,“许时庵宗伯曰:予告归里,与陈梅溪、查初白、杨晚研诸先生结‘四老会’”[6],可见后世文人对此结社活动的仰慕与追思。
“四老会”雅集成员为许汝霖、杨中讷、陈訏、査慎行四人,除陈訏外都有仕宦经历,现就成员做简单介绍。
许汝霖(1640—1720),字时庵,浙江海宁人。由庶吉士授编修,历赞善,督江南学政,时称得士,仕至礼部尚书,致仕归。著有《德星堂诗集》五卷、《德星堂文集》八卷。据高廷珍《许时庵先生传》载:“先生自为诸生,即以文章学问推其乡祭酒。年四十余登第入词馆。”[7]又《清诗纪事》“许汝霖”条载其为“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进士”[8]742。许汝霖入“四老会”时年最长,为75岁。
杨中讷(1649—1719),字端木,号晚研,海盐籍海宁人,雍建子。康熙辛未(1691)二甲第一授编修,典试河南,升中允,出视江南学政,著《丛桂集》。俞宝华曰:“杨中讷视学江南既罢官,筑园于武原曰拙宜,与尚书许汝霖编修、查慎行御史、陈勋修香山洛社故事,赋诗饮酒于其间。”[2]822杨中讷结“四老会”时为66岁。
陈訏(1650—1722),字言扬,号宋斋,海宁人,贡生。官淳安教谕,有《时用集》《勾股引蒙》。陈訏结“四老会”时65岁,与查慎行同岁。
虽曰“四老会”,然雅集时并不以上述四人为限。次年再次雅集时,是远上人以及杨中讷之子、陈訏之子亦与会。査慎行作诗《座主宗伯许公再邀杨晚研、陈宋斋梅溪及余为五老之会席上分赋二章时立冬后四日》云:
又作名园三日留,欵门人各有扁舟。宵能纵酒晨还醉,晴便登山雨即休。且喜大家添一岁,未应高兴减前游。黄花已老丹枫嫩,斟酌初冬胜晚秋。勿论雪北与香南,谷水东西亦有庵。行处人言星聚五,序来吾忝齿居三。缁黄世外关存没是远上人仍入坐,南山张道士已下世,风月尊前助笑谈。错料诗成如噉蔗,后来居上得无惭晩研、梅溪两家令子俱从游,诗又先成故戏云。
由此诗可见,“四老会”最初的约定与之后的雅集活动并不能一一对应。从时间上来看此诗作于“立冬后四日”,与约定的三月或九月雅集并不吻合。而希图通过“何尝废宴衎,刍豢薄滋味”来纠奢靡之风的愿景在这次雅集中变成了“宵能纵酒晨还醉”的豪爽与欢乐,他们顺其自然“晴便登山雨即休”的生活态度,甚至恣意助兴以抒泉林之乐的娱老理想在此次雅集中得到释放。值得注意的是,雅集中有“是远上人”与“两家令子”的参与,可以想见儒释两家推杯换盏、笑谈风月、切劘文艺、交流人生的现场情景以及活动中父慈子孝、其乐融融、诸老享天伦之乐的现场氛围,而强调“后来居上得无惭”,又透露着对子辈文学修养提升的欣慰与鼓励。
二、査慎行举同宗“五老会”
査慎行并非“四老会”的发起者,然“四老会”娱情养性的活动氛围却非常契合他晚年的心态。他将聚会赋诗视为归田乐事,并于是年秋(1714)效仿“四老会”,联同宗兄弟复举“五老会”。査慎行外曾孙陈敬璋云:“秋,族兄季方(瑊)招为五老会于西林庵,同会者:族兄观延(嗣鉴),曾三(人斌)、芝田(璹)两弟与先生,凡五人。”[9]31査慎行在其《齿会集》序中亦云:“其秋同宗兄弟年六十以上者凡五人,复有合醵之饮,大抵季必有会,会必有诗,一年中唱酬者十居二三,因以‘齿会’名吾集,亦归田一乐事也。”[4]卷四十三可知此次同宗“五老会”举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秋,与会者为査瑊、査嗣鉴、査慎行、査人斌、査璹五人。
就同宗“五老会”的活动情况,査慎行亦作五言古诗一首《季方兄招同声延兄、曾三、芝田两弟于西林庵为同宗五老会席间喜赋时甲午中秋前三日》中云:
古人重睦族,笾豆礼无废。奈何世教衰,此义久云晦。家宗远有绪,望实乡国最。伐木歌卒章,吾犹及前辈。宦游卤莽出,晚景侵寻逮。归到忽一年余去秋八月十三日抵家,今恰一年矣,病多逃酒债。喜闻折柬召,唤起初心在。八月撰良辰,五人合嘉会。两兄吾所敬,两弟亦吾爱。居近三里中,年皆六旬外。茅庵傍先垄,径转苍山背。风日假清光,松篁发幽籁。僧来具茶荈,童去携鲑菜。飞动惬平生,老狂余故态。流光弦释箭,盛壮已难再。但愿五白头,偷闲辄相对。
同宗兄弟举“五老会”折射出海宁査氏一门文风鼎盛的创作实际。“年皆六旬外”的五位白发老人,聚首一处慨叹光阴似箭、良会难得,继而抒发兄弟情深的真挚情感,体现出人生最大的关怀,诚可谓“莫道夕阳晚”“人生重晚晴”。值得注意的是,“兄弟情深”这一主题在査慎行娱老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弟劝兄酬又一堂,依然同产似君良”(《仲冬二日招诸兄弟续举真率会,明日芝田弟诗来,次答一首》)*此处用典出自《新唐书·孝友传》:“(刘君良)四世同居,虽族兄弟犹同产也。”详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290页。、“家有弟兄如老友,身除疾病即顽仙”(《寒露后六日偕东亭、德尹、曾三、芝田诸弟集季方兄晓天书屋,芝田以诗索和次原韵》)、“同游特许缁随素,一醉频烦弟劝兄”(《后六日德尹治具邀诸兄弟登龙山,小憩西林庵,再过妙果山房看菊二首》其一)。其《四杖图歌》序言中亦云:
雍正甲辰(1724)秋,润木以省墓乞假,信庵南宫下第。仲冬望后,相继到家,时余年七十有五,德尹七十有三,润木已开第七秩,信庵最少,亦平头六十矣。白首兄弟,重聚一堂,此生此乐,何可多得。沈子松年为绘《四杖图》,图成,余首唱一篇,嘱诸弟共和。”[4]卷首
兄弟情深的内容何以在査慎行诗歌中多次复现且读来感人至深呢?其一,这与査慎行重睦族的思想有关。清代海宁查氏诗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浓郁的文化传统和良好的交游环境,查慎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学文黄宗羲。受诗法于钱秉镫。与朱彝尊为中表兄弟,得其奖挹,声名渐起”[8]。适时的奖掖与提携对诗人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如爱婿心切的陆嘉淑拿着查慎行的词稿求见老友王士禛时说:“此子名誉未成,冀先生少假借之,弁以数语。”[10]辞官后的查慎行深知相互奖引与鼓励的重要性,故其归里是年的八月十九日,即到父母墓前祭奠,作《长假后告墓文》云:“誓以未尽余年,依栖丙舍,和协兄弟,教训子孙,仰答亲恩,下绵世泽。”[11]157“和协兄弟”是他在父母墓前发的誓言,而联同宗举“五老会”,就是具体实行的途径。此会不仅叙兄弟情义,而且也担当起课教子弟的责任,《査慎行年谱》载:“冬,续举真率会。先生与同宗兄弟劝酬齿序,杖履肩随,较农桑,量晴雨,间与田父野老咏歌盛世。且举家课集子弟之能文者,试之,有志者,期以上进;自弃者,勉其改行。”[9]31家族内部的文学活动、庭训教导为文学技艺的精进提供了和睦融洽的沟通氛围,“夏重七十外刻诗,查浦继之,兄弟互相为序,天伦唱和之乐,坡谷不如”[12]。其二,在文网森严的时代背景下,海宁查氏曾遭受两次大的打击,均与文字狱有关。一是康熙二年(1663)的庄氏明史案;二是雍正四年(1726)的査嗣庭试题案。査慎行能在为官多年之后全身而退,庆幸之余更有“福兮祸所伏”的隐忧。为此他举同宗“五老会”就多了一层以身垂范、保全家族的含义,“长夏家居与德尹约为书课,弟方纂辑《北史》,余点勘《毛诗注疏》,中有疑义,互相剖析。此情不异曩时,所增者白发耳”[4]卷四十六。而后来查慎行兄弟査嗣庭因文字狱获罪而牵连査氏一族,也从侧面印证了他的隐忧。将同宗“五老会”放到特定时代背景中去考察会更显人情脉脉,甚至有同宗友人相互慰藉、抱团取暖的意味。
三、査慎行怡老会诗写作特点
查慎行所主持或参与的“四老会”、同宗“五老会”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学现象。这些怡老会与具有强烈功利指向的八股文社不同,与其他具有较为鲜明文学诉求的诗社也不同。其诗会的形式远远大于内容,文学活动在这里表现出鲜明的工具性。也就是说,在查慎行结社过程中,诗歌创作主要是创造一种社会性活动的现场气氛的工具和方法,诗歌多抒发老至之情、林泉之乐、雅集之欢,正如以下失题诗所言:“青箱已付儿孙业,白发还寻山水缘。霭霭烟云扶短策,春郊群讶地行仙。”[13]与会的是一批同乡或同宗的耆儒,历经风波的生命终于在家乡的林亭盘栖,长期的政治生存焦虑业已在日常性和审美化的田园生活中淡化,他们需要一次次朋旧知心的耆年雅集。“万事付弹指,一门多拂衣。侵晨移尔艇。触热扣吾扉。相对成三老,人间此会稀。”(《喜东亭弟滇归见过时德尹亦归故居》)在名园翠峦中,在对香山之风的追攀和回忆中,使最后的时光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实现自我的终极关怀。如查慎行诗《座主许公别后寄示七律二章叙连日山游之乐再次来韵》云:
茫茫宦海阔无边,几见虚舟济巨川白香山诗,巨川济了作虚舟。退步始知原有地,掉头谁信不关天。高人入社同招隐,大老还乡例好禅。得御篮舆吾窃幸,乞身多及太平年。
就查慎行在雅集中的诗作而言,其艺术上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以“浑浩流转”助增诗歌的情韵风调。査慎行试图利用同字、词或音调重复的语言特点创造出诗句的流利畅达、宛转舞动、澹宕摇曳之姿,助增诗歌的情韵风调,以此突破怡老会诗歌创作陈陈相因、平铺直叙、缺乏新意的通病。在其为数不多的雅集诗赋中,此类诗例俯拾皆是。如“招提游更招提宿,四五人添八九人。自有此山无此会,勿论谁主复谁宾”(《立冬后二日座主宗伯公偕晚研、梅溪枉过村居,次日移榻妙果山房,再游菩提寺得诗四首》其三)、“不负年年为此会,乡山恰恰占佳名”(《后六日德尹治具邀诸兄弟登龙山,小憩西林庵,再过妙果山房看菊二首》其一)、“笑将闲事成忙事,已补登高又补诗”(《后六日德尹治具邀诸兄弟登龙山,小憩西林庵,再过妙果山房看菊二首》其二)、“已是田居又索居,得君诗胜得君书”、“草木年随草木俦,师门昨梦感同游”(《陈宋斋有新年试笔见寄诗即次去年中秋齿会二章韵再叠奉酬》)。就诗句内容而言,多是一些老套词汇的复现,“读来让人产生审美疲劳”,甚至“诗情与诗兴已然僵化”[14]。然就诗歌形式和音节而言,上举诸例却别有一番情韵风调,读来让人眼前一亮,其奥妙就在于诗作的疏宕舞动、浑浩流转。
其次,巧妙用典,对仗工整。査慎行娱老诗作虽是在轻松欢快的氛围里写成,然却十分讲究,这与他慎言慎行的个性似乎相关。其用典一是表达对朝廷的忠心,如“远收伊吕迹,近托张邴契”;二则抒写结“四老会”赋诗不过是主持诗会,延续风流,如“洛社与睢阳,高情千载嗣”。而其讲究对仗则更为多见,如“踏屐堪寻菊,登高例有诗”(《重阳后十日曾三弟招集西林庵,是日微雨,杲山法师不期而至》)、“乾鹊声中客欵门,画船衔尾泊篱根”(《立冬后二日座主宗伯公偕晚研、梅溪枉过村居,次日移榻妙果山房,再游菩提寺得诗四首》其二)、“齿虽似马徒加长,学不如农岂有秋”(《陈宋斋有新年试笔见寄诗即次去年中秋齿会二章韵再叠奉酬》)、“能文客到先投句,好事僧来尽乞书”(《立冬后二日座主宗伯公偕晚研、梅溪枉过村居,次日移榻妙果山房,再游菩提寺得诗四首其二》)、“兴到尽拚双屐往,力稀全靠一笻支”(《后六日德尹治具邀诸兄弟登龙山,小憩西林庵,再过妙果山房看菊二首》其二)。另一种独特的现象是査慎行娱老诗中流水对比较常见,即出句和对句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意思贯通下来的,如“再举重阳会,何妨十日迟”(《重阳后十日曾三弟招集西林庵,是日微雨,杲山法师不期而至》)、“知是它生缘境在,每逢佳处辄逡巡”(《立冬后二日座主宗伯公偕晚研、梅溪枉过村居,次日移榻妙果山房,再游菩提寺得诗四首》其三)、“五日为期六日迟,流光如驶讵堪追”(《后六日德尹治具邀诸兄弟登龙山,小憩西林庵,再过妙果山房看菊二首》其二)、“明朝梦觉三竿日,始信齐州接醉乡”(《仲冬二日招诸兄弟续举真率会,明日芝田弟诗来次答一首》)等等。巧妙的用典、工稳的对仗几乎遍布査慎行的每一首娱老诗作,如此作诗的方式在轻松愉悦的创作环境下似乎略显呆滞,然而却可以更大限度地将所见所感用较强的语气说出,同时也可以避免因文字而惹祸事。
第三,就査慎行娱老诗内容而言,在其优游林泉、抒发闲适之乐的同时,似乎始终难以放怀,不时地想到报效朝廷,如“报答朝恩还有处,白头相见祝年丰”(《立冬后二日座主宗伯公偕晚研、梅溪枉过村居,次日移榻妙果山房,再游菩提寺得诗四首》其四)、“远收伊吕迹,近托张邴契”。正如雍正帝在査氏一族因査嗣庭案牵连入狱后所言:“查某忠爱拳拳,固一饭不忘君也。”[15]由此,査慎行及其幼子克念俱蒙恩放归田里。査慎行亦因此感激涕零,语家人云:“圣恩高厚,涓埃难报。幸不亏体辱亲,全而归之,死无憾矣。”[8]202査慎行不管是在朝为官还是隐逸为民,其诗作始终不忘报答圣恩,这也使得他及家人在突遭文字狱牵连时得以从轻发落,其中缘由不言而喻。
四、査慎行对文人结社态度的转变
査慎行结“四老会”、同宗“五老会”时刻意避用“社”字,是因为在査慎行看来,它们与传统的怡老社是有区别的。区别并不在结社形式、活动内容或者章程上,而是深植于査慎行谨小慎微的内心深处。爬梳査慎行关于结社的诗作可以发现,他对文人结社的态度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从开始的极力排斥、拒绝,直到晚年才主动结娱老之会。
康熙丙寅年(1686)査慎行有诗《次冯文子南归》云:“筑台逃文债,支户辞吟社。静观得妙理,扰扰何为者。因君又多言,余习吾未舍。”这首诗作于査慎行37岁时,“逃文债”“辞吟社”之语说明此时他对文人结社这一现象没有热衷的表现,甚至有拒绝和极力排斥的姿态。这一态度无疑深受杨雍建的影响。
杨雍建,字自西,号以斋,海宁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由高要知县行取给事中累官至兵部左侍郞。杨雍建在顺治十七年(1660)时为礼科右给事中,曾上书朝廷严禁社盟陋习,作《严禁社盟疏》。奏疏中他将社盟之害归结为两点:一是分立门户,植党营私。“盖其念始于好名,而其实因之植党,于是家称社长,人号盟翁。质鬼神以定交,假诗文而要誉,刻姓氏则盈千累百,订宴会则浃日连旬。大抵涉笔成文,便争夸乎坛坫,其或片言未合,思构衅于戈矛,彼此之见既分,朋比之念愈切,相习成风,渐不可长。”[15]二是结交有司,把持衙门。“又有不肖之徒,饰其虚声,结交有司,把持衙门,关说公事,此士风所以日坏,而人心所以不正也。”[16]对此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士子文人不得立社,投刺往来不得使用“社”“盟”字样。“请敕该部再为申严行该学道实心奉行,约束士子,不得妄立社名,其投刺往来亦不许仍用社盟字样,违者治罪。倘学臣奉行不力,听科道纠参,一并处治,则陋习除而朋党之根立破,朝廷大公至正之意于此见矣。”(《黄门奏疏》卷上《严禁社盟疏》)[17]杨雍建的上书很快得到了朝廷的许可,是年,清廷即颁布了严禁士子结社立盟的敕令。
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年)夏,30岁的査慎行离乡赴荆州入杨雍建幕,开始长达三年的幕僚生涯。据杨雍建《敬业堂诗集序》载:“己未春,余奉命抚黔阳,而同邑查子夏重,短衣挟策,自吴涉楚,追及之于荆江梦渚之间。其时疆场未启,豺虎塞途,余提戈策马,自铜仁间道崎岖,溪谷崖篝,孤军转战,一旅深入,帐下健儿能从者不过数十人。夏重独忼慨与俱,经年而后抵贵治,相与仰视飞鸢,俛蹈荆棘,烽火昼红,箫笳夜咽,未尝一日不同之也。”[18]查慎行《慎旃集》小序也记载其己未年入杨雍建幕一事:“己未夏,同邑杨以斋先生,以副宪出抚黔阳,招余入幕。”[4]卷一由此可知,査慎行与杨雍建关系较为亲密,故他很可能受《严禁社盟疏》的影响较深。
试看査慎行康熙三十九年(1700,庚辰年)从杨雍建幕府中客座三年后返回故里时所作的一首诗:
诗社幸见收,名场应见斥。鱼熊古难兼,较若辨黑白。细思百年内,倏忽驹过隙。蚁封看扰扰,虫语听啧啧。不如两相忘,举琖酹花魄。退之言可废,此日胡足惜。(《荆州兄过一茎庵饮香林亭下次韵四首》其四)
在査慎行看来,值得庆幸的是诗社“见收”,而由此引起的名利之争应该受到斥责。对结社一途他自言“不如两相忘”,纵观历史百年都不过是“倏忽驹过隙”,那又何必执着呢?杨雍建的奏疏以及朝廷的禁社敕令无疑在社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一年査慎行作《送德尹典试广东二首》诗云:“七千里外动征轮,寒薄重裘雪洗尘。疏柳爱飘江上笛,早梅催发驿前春。名场后进虽多士,诗社前游顿少人。”诗中言“名场后进虽多士”,然而却没有几个热衷于结社一途,对此现象他并不惊奇,亦未作评价,只是借此表达对友人远行的不舍。
虽然査慎行在结束幕僚生涯之后远离文人结社,然清初激烈的朋党之争仍将他卷入其中。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月,洪昇于宅第中招伶人演出他所作传奇《长生殿》,时读书太学的査慎行随在京名士醵分往观。给事中黄六鸿以孝懿皇后佟氏病逝尚未除服、国丧期间张乐为大不敬劾之,与会名士皆牵连获罪,査慎行亦在其中,这就是所谓“《长生殿》事件”。此事之后査慎行即更名为“慎行”,字“悔余”,同时告诫友人“摇手休呼旧姓名”(《送赵秋谷宫坊罢官归益都四首》其一),这不仅是出于应科举考试的需要,也见其心理被影响之甚。这一事件究其根源乃是“出于南、北两党之交攻,殆无疑义”[11]149,査慎行可谓“躺着中枪”,由文人雅聚而惹祸上身的现实版在他身上真的就发生了。从査慎行选择更名换字这一举动,可以看出此事对他触动很大,忘掉故我、谨言慎行的想法也在此时根植于他的内心深处。康熙四十九年(1710),“《长生殿》事件”发生21年后,61岁的査慎行仍然对文人雅集持排斥甚至否定的态度。郭于宫、范密居等人结社京都,在正月十九日邀友朋聚会观剧《长生殿》时邀请査慎行参加,而他却借故推脱了。査慎行因此作诗《燕九日郭于宫、范密居招诸子社集,演洪稗畦〈长生殿〉传奇,余不及赴,口占二绝句答之》,可见之前的“《长生殿》事件”在其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以致多年之后仍不能释怀,“诸子社集”宁肯缺席,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排斥文人结社,似乎成了査慎行后期为官的一条戒律,他将自己封闭起来,从不主动参与任何文人社集活动。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准备乞休归里的他才有两首与结社有关的诗作。而通过这些诗歌,我们似乎能一窥其隐藏内心多年的秘密。《次日社集张匠门斋同人皆和余种花诗再叠前韵四首》其一云:
平生数交游,湖海浪驰骋。迩来嗜好别,取友亦取静。与君邻巷居,跬步烦引领。阔疏辄累月,会合或食顷。一笑两心同,无波如古井。
这首诗歌将平生交游视作“浪驰骋”,否定自己交游的意义,这在文人士子以交游广泛为傲的明清两代实为罕见。说到自己的兴趣,査慎行直言“取友”之余更喜静心养性,应友人之约赴会,虽邻巷而竟不知路,“跬步烦引领”。再看其赴会的活动,“阔疏辄累月,会合或食顷”,累月不见的友人,赴会时却要匆匆离去,究其根由则是内心“无波如古井”。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赴会呢?稍晚的另一次赴社集之作道出了其中的缘由,试看《留别诗社诸同人次张匠门见送原韵》:
去住何关此一官,衰年只别友朋难。烟霄过眼看如雾,草木论心臭比兰。身在梦中谁独觉,事当局外每长叹。是间着我初无谓,狮子林中一野干禅宗语录有“野干随逐狮子终不成狮之语”。
离别京城,辞官归里,査慎行心中惦念的不是仕途得失,而是难别友朋,这也就解释了内心如此抗拒结社行为的查慎行何以要在此关节去赴友人社集。令人费解的是,既然如此珍重友朋之谊,何以友人近在咫尺的时候却“阔疏辄累月”呢?査慎行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始终难以释怀,正与他的名字“慎行”“悔余”一样,其患得患失矛盾复杂的心理特征,以及努力自保追求独处的行为方式,对一个处于文网高张时代的封建士大夫而言,应是无可厚非,但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却也阻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
余论
査慎行的结社活动是时代背景下文人群体的一个缩影。清廷立国未稳,连颁禁社令,高张文网,大兴文字狱,尤其是对江浙一带重点“照顾”,种种打压扼杀了士子文人的心灵,“士”的生气与活力被深深地戗伤,明末清初趋于极盛的文学社群也一度萎缩、潜埋,査慎行因此有“诗社幸见收,名场应见斥”之叹。明末由具有高昂士气的文人所组成的复社、几社等大型文学社群慢慢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惊忌、失落与幻灭的文人在远离朝廷视野的范围里所组成的极富家族性、地域性的核心文人会社。他们依然在宴饮赋诗,承续传统,然而却多了一层保存自我与家族的忧虑,幸运的不是诗社“见收”,而是谨言慎行带来的“福利”。作为群体心灵波段的文化载体,社群诗歌也与个体心灵呼应同步。
参考文献:
[1] 杨凤苞.书南山草堂遗集后[M]∥《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47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
[2] 阮元,杨秉初.两浙輶轩录:卷十[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3] 许汝霖.德星堂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5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71-72.
[4] 查慎行.敬业堂诗集[M].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5] 许汝霖.德星堂诗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5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308.
[6] 蒋学坚.怀亭诗续录:卷一[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55.
[7] 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十二[M].清雍正刻本.
[8] 钱仲联.清诗纪事:六[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3259.
[9] 陈敬璋.査继佐年谱査慎行年谱[Z].汪茂和,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10]王士禛.带经堂诗:卷六[M].刻本.1762(清乾隆二十七年).
[11] 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12]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M].清光绪刻本.
[13] 钱仲联.清诗纪事:五[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2961.
[14] 王文荣.明清江南文人结社研究[D/OL].苏州:苏州大学,2009:131-132[2015-10-11].http:∥epub.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
[15] 沈廷芳.翰林院编修查先生慎行行状[M]∥钱仪吉.碑传集:卷四十七.清道光刻本.
[16] 平汉英.国朝名世宏文:卷七[M].清康熙刻本.
[17]谢国桢.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172.
[18]黄万机.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22.
(责任编辑:袁茹)
* 收稿日期:2015-11-02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博士专项科研资助基金“明清皖南文人结社研究”(J2014HGBZ0120);2016年度合肥工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培育计划项目“清代安徽文学社群研究”(JS2016HGXJ0020)
作者简介:祁高飞,男,合肥工业大学基础部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和明清诗文研究;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695(2016)03-0063-07
孙玲,女,合肥工业大学基础部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典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