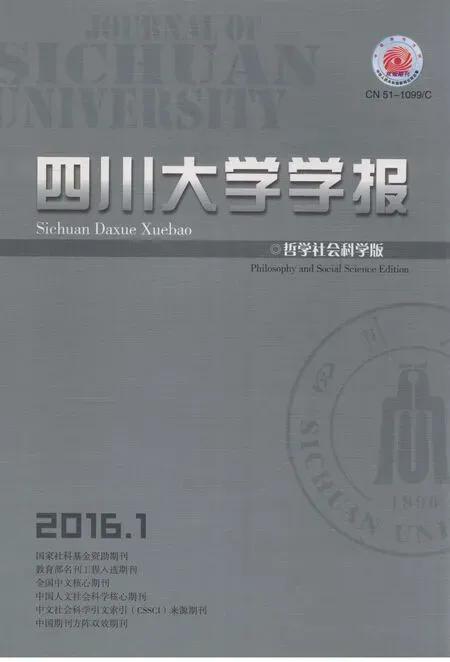中国处理印度驻西藏商务代理处的政策措施及其影响(1961—1963)
2016-04-05戴超武
戴超武
中国处理印度驻西藏商务代理处的政策措施及其影响(1961—1963)
戴超武
摘要:中国和印度在1954年4月签订的《1954年协定》中规定,两国在对方国家设立三个商务代理处,该协定1962年6月期满。从1961年开始,中印两国围绕着如何处理即将期满的《1954年协定》,特别是印度驻亚东、江孜和噶大克的商代处,展开了激烈的交涉和斗争。由于西藏平叛后中印关系的根本变化以及印度对西藏地区的全面禁运,中国判定印度这些商代处的作用不仅在于控制西藏地区的经济和边贸,而且还是印度的情报据点。西藏工委在中央的指示下,采取措施迫使印度完全撤销其驻藏商代处。印度商代处的撤销,标志着中印关系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通过迫使印度撤销其商代处,达到了清除印度在西藏地区的政治及经济影响的目的。与此同时,中国中央政府加快推进西藏地区的经济转型,以改变其依赖进口和边境贸易的模式,从而使西藏逐步走上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进程中,西藏工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1954年协定》;印度驻藏商代处;西藏工委;中印关系;藏印贸易

1954年4月4日,中国和印度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区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下简称《1954年协定》),其中规定两国在对方国家设立商务代理处(以下简称商代处);中国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和噶伦堡设立,印度在西藏的亚东、江孜和噶大克设立。这些商代处的设立对当时中印贸易和藏印贸易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由于《1954年协定》为期8年,1962年6月3日期满;因此,从1961年开始,中印之间围绕着《1954年协定》的存废,特别是如何处理印度驻藏商代处,展开了激烈的交涉。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撤销商代处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①《关于1954年中印协定期满后如何处理问题的请示》,外交部报陈毅和周恩来审批的报告,1961年11月28日,档案号105-01803-0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下文所引档案未作说明者均藏于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不再一一注明。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印政治关系在1959年西藏叛乱后的变化,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对尼赫鲁内政外交的认识、对印度民族主义性质的判断,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学界以往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协定存废本身,而未深入探讨撤销商代处的交涉过程及其对中印关系的重大意义。②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阅朱广亮:《中印两国关于1954年“中印协定”期满失效问题的外交交涉》,《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1期。该文在论及中国处理印度驻西藏商代处的相关政策措施时,或论述不足,或忽略重要问题。本文在系统利用中国外交部新近解密的档案以及印度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可资利用的其他重要资料,探讨中印两国围绕着《1954年协定》期满后的存废问题,特别是在撤销商代处问题上所进行的交涉和斗争,以期揭示这一时期中印关系变化的若干重要特点及其对中印关系的深远影响。
一、《1954年协定》期满前中印在藏印贸易上的斗争与中国对待印度商代处的基本态度
1947年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在西藏地区的一系列特权,其中包括英国通过侵略所获得的在亚东、江孜和噶大克等地设立商代处的权利。亚东是西藏南部通往印度的最重要的门户,亚东开关设市,是1888年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的重要收获。根据1893年清廷同英国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条款九款续款三款》,亚东在1894年正式开关设市;英国在此设立商代处,任命商务代表,处理与贸易相关的事宜。英国在第二次侵藏战争后,于1904年同西藏地方签订《拉萨条约》,确定亚东、江孜和噶大克为商埠。江孜是英属印度与拉萨、日喀则商路的交汇点,噶大克地处后藏要道,是阿里地区的中心。1904年和1906年,英国先后在江孜和噶大克设立商代处。*有关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以及相关条约的谈判,参见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五章;有关亚东开关,见该书第94页;有关《拉萨条约》的谈判及主要内容,见该书第127-131页。有关1893年《藏印条款》的全文,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566-568页。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还可参见胡岩:《雪域高原不会忘记: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噶大克商代处由于气候和住宿条件的限制,由英印政府在西姆拉的机构进行管理,所有人员在冬季时撤回西姆拉。上述三个商代处均由英印政府驻锡金政治专员公署行使管辖权。*有关英国和英印政府驻藏机构以及商代处的沿革,参见房建昌:《也谈英国在藏机构沿革及其活动概述》,《西藏研究》1995年第2期;刘武坤:《西藏亚东关史》,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房建昌:《近代外国驻藏机构及其官员的活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3期;喜饶尼玛:《英国驻藏机构沿革及其侵略活动概述》,载《近代藏事研究》,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房建昌:《英、印驻噶大克商务代办及国外探险西部西藏小史》,《西藏研究》2001年第3期;张永攀:《英属印度驻藏机构及其官员论述(1904—1947)》,《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2期;徐百永:《民国时期英国驻拉萨代表团的设置及其活动》,《中国藏学》2006年第4期。有关印度方面商代处的相关论著,可参见 Bhawan Singh Rawat, Travails of Border Trade, Munsayri, Pithoragarh: Malla Johr Vikas Samiti, 2009.《1954年协定》规定,中国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和噶伦堡设立商代处,印度在亚东、江孜和噶大克设立。
1959年3月的西藏叛乱及解放军平叛不仅是中印关系的转折点,也是中印经贸关系和藏印贸易的转折点。作为对中国平叛的反应,印度政府再次对西藏实施贸易封锁和禁运。更为重要的是,1959年8月和10月,两国在边境争议地区的朗久和空喀山口发生武装冲突后,印度扩大贸易封锁的范围,开始实施全面禁运政策。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是印度决定对西藏实施全面禁运的关键因素,*有关印度在1959年西藏叛乱后所实施的禁运政策,参见戴超武:《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贸易管制和禁运与中国的反应和政策(1950—1962)》,《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而中共中央有关《1954年协定》存废的决策考虑以及对印度驻藏商代处的处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随着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的展开,印度“在经济上与我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是对西藏实施禁运。“平叛以后由于印度的禁运,已换不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此次印度禁运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我机关部队的;至60年61年对西藏农牧民也封锁禁运,如大米、白面,甚至有些地方连青稞也在禁运之列”。*阿里外事分处:《阿里地区市场与商人的情况》,1961年10月,档案号105-01122-05;《对印方7月15日来照的意见》,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并江孜、亚东、阿里外事分处的电报,1961年9月9日,档案号118-01047-08。在亚东口岸,仅有少量的一般生活用品可以进口,印方严格控制生产资料、仪器、西药等出口,禁止工交建筑器材等出口。“这一时期,国营公司基本上未作进出口生意,亚东贸办仅购进2.5万元的货物”。在阿里地区,印度关卡扣押大米,“对我去印度经商的群众和边境居民百般刁难,如阻挡、拘押、殴打、勒索、没收我发的证明书等等”。*《对印方7月15日来照的意见》;阿里外事分处:《中印边境贸易情况》,1961年10月,档案号105-01122-02。西藏与不丹之间历来有盐粮交换的边境贸易,西藏平叛后,不丹禁止边民背粮食到西藏进行交换,边贸陷于停顿。印方关卡还加大对中国过境人员的检查,过境贸易所填表格从过去两份增加到三份,手印从22个增加到33个。同时印方检查站人员还详细询问西藏改革、区乡干部姓名、交通运输、设防以及其他军政、经济等情况。*阿里外事分处:《中印边境贸易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禁运的实施是不平衡的,“总的情况是东紧西松,如北方省较紧,喜马楷尔和旁遮普省较宽,拉达克更宽”。在禁运过程中,印度商代处配合印度政府,“纵容印商走私漏税,扰乱市场”;一些印商未获中方批准入境,非法从事营业活动。“我所需要的物资印方不许出口,但我不需要的高级消费品则大量涌入”;如进口手表4000多块,经过检查站登记的不超过1000块。*《复藏印贸易情况》,西藏外贸局致外贸部、外交部并请转驻印度大使馆的电报,1961年6月8日,档案号118-00959-02;《报目前亚东市场及外商情况》,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工委的电报,1961年8月26日,档案号118-00959-02;《印度在亚东市场活动情况及其企图》,西藏外事处致电西藏工委、外交部、及各外事分处,1961年6月5日,档案号118-00959-12。
其次,印度利用禁运破坏人民币的信用。印商一度拒绝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与藏商做生意要使用卢比或麝香、金银以及羊毛等土特产。亚东商代处在1961年4月召集印度商人和尼泊尔商人开会,以申请不到外汇为由,指使印商拒绝使用人民币。5月以后印商虽一般不再拒用,但普遍贬低人民币的价值。在1961年3月份以前,人民币与卢比的比价是7~8角人民币兑换一盾卢比;3月中旬以后,亚东黑市一盾卢比换1到1.5元人民币,最高时甚至2元才能换一盾卢比。然后印商“要求按我牌价(5.66角换1卢比)要求外汇,这样转手之间即可获得数倍利润”。1961年第一季度亚东外商申请外汇达60万元,而银行当时只有外汇30万元,满足不了外商的要求;在亚东,印商手中掌握约70多万人民币,个别印商一家就有9万多。另外,在西藏实施币制改革收兑藏钞时,当地银行因人民币不够,曾给印商打过欠条。印方在亚东和帕里直接操纵印商,对中方收兑藏钞时打给印商的人民币欠条,不准印商前去兑换,“其用意无非是企图逼我改变收兑时比价,提高藏币比值”,“这也是印方叫嚣外汇问题的原因”。*《对印方10月26日照会所提三个照会的意见》,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电,1959年11月27日,档案号118-00821-01;《印度在亚东市场活动情况及其企图》;《复藏印贸易情况》;《报目前亚东市场及外商情况》;《对印方7月15日来照的意见》。
第三,印度商代处对违反禁运条例的印商进行清理。在亚东,到1961年10月,商代处仅允许5家印商继续经营,其余的因为违反禁运政策,均被作为“挤走对象”做了处理。*《报亚东印商代处活动情况》,西藏外事处致电外交部,1961年12月11日,档案号118-00950-11。5家印度商号分别为阿罕达斯、西米拉木、锡金贸易公司、库西拉木和阿米纳尔。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原件中并未标明这些商号的外文名称。与此同时,印方尽力拉拢尼泊尔商人,商代处召开的外商会议及其他活动,均请尼商参加,“布置对我的统一行动”。商代处发放货物出口许可证时,对尼商很宽。1960年12月至1961年3月,亚东三家尼商进口的货物数量占亚东外商进口货物的38%,被列入黑名单的印商甚至领不到许可证。*《复藏印贸易情况》。
此外,印度政府在西藏平叛后还公开限制中国驻印商代处的活动。印度外交部1961年递交中国驻印使馆一份备忘录,内称“为了安全的理由”,从8月16日开始,中国驻噶伦堡商代处人员不得走出噶伦堡市区以外,如要出限定范围之外,需事先提出书面申请,并获得噶伦堡区长的书面许可。对印方的这一举措,中国驻印使馆在8月15日给外交部和外贸部的电报中建议:“原则上对其所列限区我今后不再去,避免向印提出申请”,同时“考虑到我在藏对印方机构采取类似限制,但由于五四年协定即将期满也可暂不报复,以便谈判时更加有利和主动。”外交部于8月19日复电指示:以备忘录的形式向印度外交部提出交涉,“对于印方所列限区,同意原则上今后不再去,避免向印申请”;同时电报也指出:印方此举“看来是对我蓄意报复,在交涉中对方如提出我对其在藏机构的限制问题,可按我1960年4月6日复照有关部分驳回”。*《印又将限制我噶商代处人员行动》,驻印使馆致外交部的电报,1961年8月11日,《印进一步限制我驻噶商代处行动范围》,驻印使馆致外交部并外贸部的电报,1961年8月15日,《复我驻噶商代处人员行动受限制事》,外交部致驻印度大使馆的电报,1961年8月19日,档案号105-01061-01;中国驻印使馆给印度外交部的照会,1960年4月6日,参见《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一册,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印,1960年,第461-462页。
实际上,印度决策者内部对如何处理这一时期的印藏贸易是存有分歧的。印度外交秘书杜德(Subimal Dutt)反对中止一切贸易,他在1961年4月曾向尼赫鲁建议:即便是政府决定不再续签1962年3月到期的中印贸易协定,但贸易还是应继续下去,因为这符合边民的利益,而他们的忠诚则是印度所需要的。*Note from Dutt to Nehru, 4 February 1961, Subimal Dutt Files (SF), 46, 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 New Delhi.对于印度在西藏叛乱后所采取的举措,中方认为,“边界问题和对西藏的破坏活动是其反华政策的两个内容”,而对西藏的破坏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的破坏。这种经济上的破坏体现在“对我封锁禁运,凡我需要物资和边民习惯交换的生活必需品等均禁运出口,但倾销高级消费品(据估计去年走私进口手表达15000只),捣乱市场,压价套汇,打击我人民币信用”。*西藏外事处:《关于印度目前对西藏做法的看法及对策的意见》,1961年3月29日,档案号118-00955-05。因此,藏印贸易“不仅是一场尖锐的经济斗争,而更重要的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编:《我国对印度贸易(包括藏印贸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1960年4月,档案号105-00997-02(1);《复藏印贸易情况》。对印度禁运,“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印度封锁禁运的各种矛盾,打破印度的封锁禁运,争取进口一部分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在平叛期间虽加强边境地区警戒,但同时规定“在非军事行动时,仍可适当地维持边境上的小额贸易往来”。*阿里外事分处:《阿里地区市场与商人的情况》;西藏外事处:《平叛期间外侨出入境居留、旅行暂行办法(内部掌握)》,1959年12月,档案号118-00775-01。
然而,禁运仍对西藏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造成的某些经济困难甚至超出了西藏工委的估计,特别是物价上涨和藏民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到1961年年中,“亚东市场生活用品上涨40%~100%。外商在拉萨黑市收购黄金和麝香每两价格均达250元,外商利润竟高达百分之百甚至两倍以上”。禁运造成的影响在阿里地区较为突出。由于阿里地区长期与内地隔绝,交通运输不便,所缺乏的粮食,“一直都仰给于比邻的尼泊尔和印度;人民生活所需之日用百货,则主要仰给于印度。另一方面,印度纺织工业所需之羊毛、印度边民所需食盐和民用羊毛,绝大部分须由阿里进口”。因此“长期以来,我阿里群众与印度边民之间的以毛粮和盐粮互换为大宗的边境贸易,一直是很发达的”,“国货还不能全部满足需要”。1959年以前,阿里地区每年同印度的进出口总值,各约250万元。1959年西藏平叛后,由于印度的禁运,藏印过境贸易的商人和进口货物都有所减少。据普兰海关的不完全统计,1960年7-11月,该县同印度的进出口总值,各约17万元。*《复藏印贸易情况》;阿里外事分处:《中印边境贸易情况》。根据这一报告,1959年以前,阿里每年向印度出口食盐约200万斤(普兰40万斤,日土50万斤,扎达10万斤,噶尔10万斤,改吉、改则、仲巴三县90万斤),出口羊毛110万斤,羊绒20万斤,占总产量的70%左右。每年从印度进口粮食约200万斤,茶叶约10万斤,棉布约20万码,红白糖约10万斤。
印度禁运的另一个明显影响是导致西藏地区出现了“供应紧张、货币贬值的严重现象”;在西藏工委看来,必须“迅速加强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因为“敌对阶级和反革命分子利用我们在经济上的某些困难和经济工作中的缺点”,“乘机进行破坏和散布不满情绪,在粮食、商品供应和金融三个问题上向我们进攻”。*《西藏工委通知迅速加强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1960年4月7日,《西藏工委就财经工作中出现的被动情况和拟采取的若干紧急措施向中央请示报告》,1960年4月8日,参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68-169页。为此,工委在中央的指导下,采取措施,一方面力争解决当前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也反击印度的禁运。除采取币制改革、加强对外商的税收管理、设置海关以及加强外汇和金银管理等措施外,*有关西藏民主改革时期所实行的币制改革和金银管理措施,可参见戴超武:《中国和印度关于西藏币制改革的交涉及影响(1959—1962)》,《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5期。有关税收的改革,1959年西藏原地方政府被解散后,中方开始管理市场,并按旧制向印度商人收税。从1960年起,旧税全部废除,征收商业税3%,这样一单买卖实际上要征收6%的税。但对进口粮食,则一律免税。有关情况,参见阿里外事分处:《中印边境贸易情况》。工委还以处理印商在西藏地区寄放牲畜以及藏民所欠印商债务作为突破口,彻底清除印度在西藏的经济影响,特别是印商对藏民的经济控制和盘剥。
印商在西藏地区寄放牲畜由来已久,大多以“计美其美”形式寄放;这种形式规定,寄放户不管天灾,或发生意外或遭抢劫,每年均要收取一定数量的酥油、毛、绒等物。根据阿里外事分处的调查统计,到1961年10月,印商在普兰县的巴噶区、噶尔县门士区以及日土县乌江、热角两乡寄放有牲畜;在上述区乡的418户中,49户存有印商的牲畜748头只,包括61头牛和687只山绵羊。承放年限最长的达80年,最短的一年多。1959年以后,大部分承放户意识到承放牲畜已无利可图,吃亏太大,有些承放户拒绝再向印商交畜产品。阿里外事分处报告说,承放户提出要求,希望承放的牲畜今后或归自己所有,或以原价买下,或退还给印商;多数承放户希望采取第一种方法。*西藏外事处阿里办事处:《关于印商在我区寄放牲畜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年10月,档案号105-01122-01。“计美其美”规定:牦牛,每只最多的每年交酥油20尼阿噶,合5市斤6两,最少也要交10尼阿噶;绵羊,要上交全部羊毛,每只每年9尼阿噶或5尼阿噶不等;山羊,规定不一,每只每年交4-5尼阿噶酥油,或每只每年交5尼阿噶酥油外,再交全部羊绒或1尼阿噶羊绒。每尼阿噶酥油的价格为1个卢比。有关“计美其美”,还可参见扎呷、卢梅:《西藏牧民:藏北安多县腰恰五村的调查报告》,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1998年。
对于如何处理印商寄放的牲畜,印度驻拉萨总领馆曾向中方提出:应准许牛羊出口,或作价购买。对此,阿里外事分处建议,印商寄放牛羊情况较复杂,解决尚有困难,不主张同印方进行交涉,需要先进行内部准备,对外以调查登记办法拖一下,以便交涉时处于主动。西藏外事处在1961年6月致外交部的电报中同意阿里分处的意见,认为“禁止牛羊出口系我保护牲畜的基本措施,仍须继续贯彻”;因此可告诉印方:“由于印商所有牛羊,其来源复杂,牵涉到债务、存放牛羊的工资待遇以及折算等一系列问题,不得不加以调查。……为了尽早的解决此问题,请印政府转告有关印度商人遵守当地政府的规定,履行登记手续。”外交部6月4日复电西藏工委财贸部和西藏外事处,同意采取上述措施。*《有关印商在阿里寄放牛羊的问题》,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的电报,1961年6月27日,档案号118-00959-07。
此后,阿里外事分处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阿里分处指出,“凡是印商所寄放的牲畜都是从我藏民处购买或讨债得来的,没有一(头)只是从印度赶来的”;因此,不管以后以何种形式寄放,则按下列规定处理:(1)凡从西藏甲地赶到乙地所寄放的牲畜(包括那些年代久记不清来源的牲畜),其购买价格应与印商当时收购这些牲畜的价格基本相同。建议牛每头50盾卢比,合人民币25元;绵羊每只8盾卢比,合人民币4元;山羊每只5盾卢比,合人民币2.5元。(2)凡是以牲畜抵债后又寄放原处的牲畜,其购买价格均以抵债价计。(3)凡在寄放期间因遭天灾或叛匪抢劫,牲畜遭到损失者(包括那些因年代久老死的牲畜),应按特殊情况处理,不能仍以“计美其美”办理。(4)凡在寄放期间,由于牲畜死亡,承放户无力偿还原规定上交畜产品的全部或一部分所形成的积欠,可不再补交。对那些“因自己劳力缺乏、草场少或与我藏民沾亲带故等原因将其牲畜寄放我境内群众处者”,有过牧性质;阿里分处建议,“处理这些牲畜,绝不能与外商所寄放的牲畜一样,应有所不同”。*西藏外事处阿里办事处:《关于印商在我区寄放牲畜情况的调查报告》。
对于藏民所欠的印商债务,西藏外事处在了解有关情况后,于1960年9月向外交部做了汇报。西藏外事处报告说:在阿里地区的普兰、扎达、噶尔等县,部分外商不通过当地政府部门索债,对无力偿还者,也不强求。扎达县部分外商采取先收一半,另一半加上今年的新债款到明年再收一半的办法;亚东也有个别印商通过当地政府部门索债,“大部分是在56年57年所谓西藏大发展期间向印商借债经商谋利的。欠款额较大者为富裕农奴和代理人(其中有的外逃、有的已破产),另一部分为中等农奴,因资金赔尽已弃商归农,无力偿还”。*《报有关藏印贸易情况》,西藏外事处致电外交部,1960年9月29日,档案号105-00433-03(01)。阿里分处根据西藏外事处的指示,进一步调查了阿里地区的情况,于1961年10月提交报告。该报告说,阿里地区80%的债务是在1959年以前形成的,既有欠印商的债务,也有欠尼泊尔商人和不丹商人的;“普兰六个乡两个区共885户,4791人,其中负有外债的424户,共负债49319盾卢比,欠印商43851盾卢比,尼商3293盾卢比,不丹2175盾卢比。噶尔县七个乡一个区共609户,其中负有外债的496户,共负债97737盾卢比,欠印商97423盾卢比,尼商314盾卢比。日土县两个乡共99户,其中负有外债的53户,共负债22036盾卢比,全部系印商的债务”。如何处理这些债务,阿里外事分处建议:“最近二三年内我政府不主动处理外债问题,而是向群众进行如何正确处理外债问题的教育,提高其觉悟,其原则是由各负债户自行解决。这样,那些真正有偿还能力的户已基本上还清了旧债,剩下的将是少数的真正的有困难的户,到时候再处理和考虑国家贷款等问题就容易多了。”*阿里外事分处:《阿里区外债情况典型调查报告》,1961年10月,档案号105-01122-06。有关藏民所欠印商债务的数额,中方有不同的估计;根据外交部的材料,到1961年4月,阿里地区藏民所欠的印商债务为300万盾卢比,印商寄放牛羊的价值(因欠债折合)约300万盾,而印方过去所称是1000万盾。在亚东和帕里,印度声称有债务约400万盾。参见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编:《有关西藏各涉外问题情况汇编》,1961年4月,档案号105-00997-03。印度商代处撤销后,阿里外事分处决定,藏民欠印度商人的债务在1962年也暂时不还。参见《关于定期汇票等问题》,西藏工委致总行的电报,1962年11月11日,档案号118-01048-28。
对中国的上述措施,印度多次发出照会进行指责和抗议。在牲畜寄放问题上,印度外交部在1961年11月16日给中国驻印使馆的照会中指出:“禁止把这些牲口带回印度,等于是没收属印度商人所有的牲口”;“应该允许他们出售,即便是公然没收,也应该给他们以公平的赔偿。”印方称中方的禁令“最后必将影响到贸易”。*印度外交部致我驻印度大使馆照会,1961年11月16日,档案号105-01852-01。对藏民所欠印商债务,印度外交部早在1960年5月给中国驻印使馆的照会中,就曾专门提到印商在阿里地区收回债款的问题;印度声称:印商“按照传统做法同西藏西部进行贸易,他们习惯地在那里赊售货物,甚至将现金借给西藏居民和官员。这样做都很守信用,因为过去在收回债款方面从未发生过困难。但是,目前由于中国当局最近采取的某些措施,印度人无法同大多数的借债人和经商合伙人联系”。印度照会指出,这种情况在西藏中部也同样存在,因为“许多西藏商人已迁往日喀则和拉萨,印度商人没有旅行许可证,无法到那里去”。印度政府要求中方或在特许的基础上提供必要的方便,以便印商去日喀则和拉萨收回债款,或采取措施,使地方当局协助印商收债。*印度外交部致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照会,1960年5月17日,档案号105-00433-03(01)。印度照会英文件,见该卷宗第82-85页。
中方认为,印度在西藏平叛后的一系列做法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在西藏进行“经济上的破坏”。*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编:《我国对印度贸易(包括藏印贸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复藏印贸易情况》。而在这一过程中,中方相信印驻藏商代处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西藏有关部门在1959年西藏叛乱后,即开始对印度驻藏机构进行调查,以便为中央处置中印关系做相应的准备,其中特别关注了印度驻拉萨总领馆及商代处的情况。据西藏工委和西藏外事处的调查,截止到1959年7月,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共有103人,计有职员10人(全部为印人),佣人34人(印籍5人,中国籍29人),家属59人(印籍16人,中国籍43人),全部住在领馆内。驻江孜商代处共112人,计有职员15人(印籍14人,中国籍1人),佣人25人(印籍5人,中国籍20人),家属72人(印籍4人,其余中国人),居住在江孜市内10余处房屋。驻亚东商代处共70人,计有职员12人(印籍11人,中国籍1人),佣人31人(国籍复杂,中国人居多),家属27人(印籍3人,中国籍24人),居住在商代处院内。对于印度这些机构的性质及其人员构成,西藏工委认为:“查印度驻西藏总领事馆和江孜、亚东商务代理处,过去除勾结地方上层培植亲印势力为其服务外,还以高价雇佣藏人和混血儿。在印所雇中国籍(藏族)佣人中,多系印度培养多年政治情况极为复杂的分子,被利用作各种不利于我之活动。自平叛以来,印度在藏之上述机构,除不断增加印籍人员充实内部以外,并继续大量雇佣藏族和外侨,所有被雇人员连同其家属均由印方作为其机关人员向我地方当局呈报登记,企图不加区别地(中国人和外国人,职员和佣人)均作印度人员,纳入印官方机构范围内加以庇护。这样就俨然在我拉萨、江孜、亚东等地形成了类似租界的区域。显然,印度这种作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西藏工委在这封给外交部和公安部的电报中特别强调:“印度在藏官方机构,特别是其商务代理处,如此庞大与复杂,是与印度在该地区的商务情况不相称的,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印在藏官方机构人员情况及处理意见》,西藏工委社会部、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公安部并江孜、亚东外事分处党委社会部的电报,1959年7月22日,档案号105-00661-02。此材料缺印度驻噶大克商代处的情况。
对于西藏工委和外事处的上述建议,外交部和公安部在1959年9月28日的电报中指示说:“关于印度在藏官方机构内扩充人员企图保留特权,进行不利活动问题,我们认为,对这些人应当严加控制,但具体做法上要区别什么是印方企图保留的特权,什么是一般的惯例,同时也要照顾到国内其他地区的情况,因为其他外国领事馆也有普通外侨雇员和华籍职工,领馆雇用华籍职工是应通过我对外服务处,如无对外服务处,可通过外事处代为介绍,如此即可控制人数,对外侨雇员要与社会一般外侨有所区别。”外交部和公安部还特别指示西藏工委对印度这些机构采取合理的措施,要求“对外籍人员,他们如住在印领事馆内,我们就不能随便进入他们住房,没有重大问题,确凿证据不能采取拘留、逮捕措施,拘留逮捕时,绝不能在印机构内进行”。*《印在藏官方机构人员有关问题》,外交部、公安部致西藏外事处、西藏工委社会部的电报,1959年9月28日,档案号105-00661-02。
西藏工委和外事处对印度商代处之性质的判断是极为重要的,它为《1954年协定》期满后中国处理印度商代处提供了关键和重要的思路。首先,工委和西藏外事处判断,印度商代处“勾结地方上层培植亲印势力为其服务”,实际上是“情报据点”,其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搞破坏活动”。比如在西藏平叛后,江孜既无印侨商,其商代处“又不与我接谈商务”。因此工委建议,这些商代处“将来予以取消或改设其他机构,尚待进一步研究”。其次,工委和西藏外事处认为,应对印度商代处的职权范围加以规定,这不仅是因为在商代处驻地“形成了类似租界的区域”,关键还在于印度政府将商代处作为政府在当地的官方机构代表,如噶大克商代处负责代管不丹在藏事务,亚东商代处则负责检点从印度进口到西藏的货物,等等。*西藏外事处:《工作汇报第九期》,1961年7月6日,档案号118-00955-01;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编:《有关西藏各涉外问题情况汇编》。
二、西藏工委和驻印使馆的政策建议与外交部和中央的决策
1961年4月16日,中国外交部指示西藏外事处对《1954年协定》执行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对协定的延长、修订或废除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5月29日,西藏工委向外交部提交《对中印协定期满后的存废修改意见》(以下简称《西藏工委意见》),全面阐述了工委的态度和政策建议。*《关于检查中印协定执行情况事》,外交部致西藏外事处的电报,1961年4月16日,档案号105-01803-01;《对中印协定期满后的存废修改意见》,西藏工委致外交部的电报,1961年5月29日,档案号105-01803-01。
《西藏工委意见》首先分析了平叛后的西藏局势与中印关系的现状,特别是两国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工委认为,“现在西藏的情况比1954年签订中印协定时已起了根本变化。同时印度的态度也比当时坏,已从友好变为反华。1954年的协定,主要是解决藏印间的通商交通问题,而现在藏印之间急待解决的问题为边界问题、印度收留叛匪问题、在印我外逃群众问题、贸易交通问题(土特产出口换取必需品等)、印度在藏的权益(商务代理处、印侨商在藏的债务等)、两国人民的来往问题等,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而其中的某些问题,如边界问题,更需急待解决”。工委强调“边界问题是印度政府制造反华的借口”,是“目前中印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因此,“不管从总的两国关系,还是从局部的藏印关系来看,这个问题,都应该首先求得解决”。工委主张:“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或者提出解决的途径及作法,我西藏同印度关系中的其他问题的解决办法或规定,才有实行的可能。否则,如贸易交通问题,就是按照1954年协定做一些修改,也会因印度闹边界纠纷,随时遭到破坏。”《西藏工委意见》提到中印边界中段的山口道路问题,针对“印方妄称此六个山口即划定了中印在中段的边界”,工委指出:“此问题涉及到边界问题,这是不能同意的。”不过工委也建议,由此“可以先提出解决双方边界问题,然后再谈具体交通道路问题。若因山口牵涉到边界争执不下,可以改变为双方人民按习惯道路来往,不提具体山口,如此我可主动掌握”。工委特别提出,考虑到“印度将提出不丹、锡金在藏的一些土地、寺庙、财产等问题,因过去不丹、锡金均是直接同西藏地方来往、交涉,我不能同意和印方商谈有关不、锡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如何解决藏印贸易以及交通来往等问题,《西藏工委意见》不主张“再像1954年那样签订一个专门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协定”,但可考虑同印度签订一个包括西藏在内的通商交通协定或领事条约,因为“西藏已不复如过去那样存在什么特殊,中印之间也不存在什么特殊的西藏关系问题,这样做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工委估计印方不会同意中方的上述做法,因为“它一贯是企图把‘西藏问题’弄成中印间特殊问题,它企图要在1954年协定基础上,继续保持某些旧有的权益,它更不愿意现在解决边界问题或签订两国间一般性的文件,来缓和、好转中印间的关系。如我坚持,将形成僵局”。鉴于此,工委提出两项建议:其一是“继续谈下去”,但宣布协定到期失效,两国“在西藏方面的来往、贸易将按各自国家的规定处理”;其二是“只签订一个中印两国有关在中国西藏的贸易协定,将香客朝圣等包括在内,或者就原来协定内容,根据目前西藏情况和两国关系加以修改”。西藏工委主张采取后一种做法,主要是因为“根据七年多来的经验和目前西藏的实际情况”,协定应予以修改;如“双方僵持不下,达不成任何协议,对我并无不利,当然我尽量争取不破裂为好”。在处理商代处的问题上,工委认为“无再设置之必要”,主张予以取消,必要时可改设领事馆。不过《西藏工委意见》也提出,“若印方坚持要设立官方机构并坚持要维持商务代理处的名称”,则必须明确规定商代处的职权,并坚持对等的原则。
《西藏工委意见》同时提到了与藏印贸易有关的其他问题,如印度在江孜和噶大克两地商代处建房及租地问题。对此西藏工委主张“争取不与印方达成协议。如印方坚持租地建房,则另行商谈,不订入协定或换文中”。
在接到《西藏工委意见》后,外交部第一亚洲司1961年7月3日电示中国驻印使馆,请其提出意见。7月29日,驻印度使馆给第一亚洲司发回一封长电,*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致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的电报,1961年7月29日,档案号105-01803-01。电报中不仅对《西藏工委意见》提出了分析意见,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从中可以看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驻印使馆与西藏工委的意见分歧是明显的。
在《1954年协定》期满后如何处理的问题上,驻印使馆在长电中强调:西藏问题是中印关系中的重要问题,牵涉面很广,比较复杂,必须综合考虑,“全面衡量利弊”。驻印使馆既不同意延长协定,也不赞同以原协定为基础进行修改,因为同1954年相比,“七年多来西藏地方情况、中印两国关系以及以反美斗争为主的外交全局都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驻印使馆提出,中方的基本原则,应是“坚持废除印在西藏的特权”,同时“为了争取政治上主动,可考虑在适当时机我主动同印方接触,或在印方同我接触时,我主动表态(重订新协定),对印方要求(延长或修改旧协定)给予拒绝,首先把门关死”。为此,驻印使馆还就有关谈判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1)签订新协定首先应争取不突出西藏地方特殊地位,应将其“作为我国一般边境地区对待,这对废除印在藏特权有利。西藏外事处所提签订两国间一般协定将有关西藏部分包括在内,印方如能接受,这对我有利。但估计印方不会接受。因此建议谈判新协定在原则和内容上仍以有关西藏地方政府与印度间通商、朝圣等具体问题为限。在名称、文字和精神上作为中印两国间边境贸易和边民往来来处理”。(2)关于开放贸易市场、商旅、来往通路等问题,采取从严的精神,应“减少印商活动的点和线,将他们的活动逐渐压缩至边境和少数地区”。(3)有关商代处问题,应先争取减少数量,取消江孜和噶大克两处,并明确规定其职权,“以取消其特权和便于我管理。升格为领事馆,则扩大其职权,虽然商代处也相应升格但比较起来对印方更有利”。(4)关于朝圣问题,“考虑到印方歪曲说,原协定所列山口证实了它所谓的传统边界线,新协定对朝圣道路和山口,不宜再做具体规定,只做原则说明(经习惯道路和山口,或两国政府所指定的道路和山口),也可考虑新协定只处理边境贸易及有关问题(商代处、商贩往来、支付问题等),而将朝圣问题作为两国边境上一项特殊问题,通过换文形式处理”。(5)应进一步加强对边境往来的管理,“如入境时一律要持护照,经我签证(包括朝圣),恐也行不通。这需要根据边界具体情况和我主观力量而定,我们感到原则上要加强控制,具体办法建议由西藏外事处研究”。(6)在新协定谈判和规定中应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7)“估计谈判将是一场严重复杂的斗争,旷日废时非短时间内所能结束,因此旧协定期满时新协定恐难签订,甚至印方还可能有意拖延谈判,在此情况下,印方会提出暂时延长协定的要求。对此我从政治上可同意延长,但应采取从严精神,延长期限不宜过长,以半年为较适宜,目的是压印方,减少其拖延”。(8)有关谈判地点,应考虑到谈判时间长、问题多,就人力和各方面条件等因素来看,“在北京对我有利和方便”,虽然印方可能提出在新德里,但应争取在北京谈,因为“所谈问题主要关系我国西藏地方的问题”。
显然,在如何处理期满后的《1954年协定》、如何认识边界问题在中印关系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处置商代处等关键问题上,西藏工委和驻印使馆都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首先,对于如何处理即将到期的《1954年协定》,西藏工委建议予以修订,认为相关谈判即使拖下去对中方也是有利的。驻印使馆则认为,这样做“这会在谈判中便于印方同我进行无礼纠缠,易陷我于被动,增加废除印度特权的困难”。驻印使馆提出,“比较有利的做法是谈判新协定”,即声明旧协定作废,不能作为谈判基础。其次,西藏工委突出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的核心,建议在新的谈判中首先加以解决,驻印使馆则完全不赞同此种意见。驻印使馆提出:“我们感到强调边界问题的重要性是对的,但是由于印度反华已成为既定政策,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边界问题很可能实现不了‘首先求得解决’,我国方面在对印度的斗争中,还是要采取求同存异的作法。在此情况下,即使边界问题悬而未决,并不能排除两国间其他问题(包括印藏关系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求得解决。”最后,在商代处的问题上,西藏工委主张全部撤销,必要时改设领事馆;驻印使馆则主张减少数量,严格管理,并强调,如改设领事馆,则会扩大其职权,反而对印方更为有利。
外交部显然更倾向于驻印使馆的意见,对西藏工委有关首先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并没有采纳。这在外交部报送陈毅和周恩来的报告中体现得极为突出。1961年11月28日,外交部向陈毅和周恩来报送了《关于1954年中印协定期满后如何处理问题的请示》(以下简称《外交部报告》),其中更多吸收了驻印使馆的建议。*《关于1954年中印协定期满后如何处理问题的请示》。
首先,《外交部报告》肯定了签订《1954年协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协定废除了印度过去在西藏的一些特权,把我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贸易关系、香客相互朝圣和边民往来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了正轨,为双方在我西藏地方的关系的正常化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协定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因此“对我来说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总的方面是平等互利的”。但另一方面,“鉴于印度和我西藏地方的特殊历史关系,我们对印方在西藏的权益当时也做了某些照顾,协定的某些条款实际上是不对等的”,“也存在着一些实际上对我不利的地方”,因此协定的执行是“一个尖锐的斗争过程”。究其原因,《外交部报告》指出:其一,“印方对我西藏地方的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怀善意,中印协定签订后,在合法外衣的掩护下,一直不断地进行种种非法活动,干涉我在西藏的内政,妄图使西藏长期保持半独立的状态,作为印度抵制我国影响的缓冲地带”。其二,“西藏平叛后,印方仍不放弃进行干涉,一再违反协定规定,同时却反污我们破坏协定,对于印度这些利用和破坏协定规定来干涉我内政和限制我影响的企图,我们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于印度驻藏机构的作用,外交部强调:“可以预计,随着西藏民主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影响的不断扩大,印方还会加紧对西藏进行时起时伏,时明时暗的非法活动。尼赫鲁所谓目前印在藏机构对印是有利的,其意图实质上就在于此。”
其次,阐述了处理期满后《1954年协定》的基本态度。《外交部报告》指出,由于平叛后“西藏情况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印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保卫我在西藏的革命利益和贯彻我孤立印度的方针”,对《1954年协定》既“不能原封不动地延长协定”,也“不宜坚持根本废除协定”,这主要是由于“从我对外关系全局来讲,我仍须高举协商解决争端的旗帜,以争取印度人民。同时,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双方边民之间的往来是不可能完全中断,某些经济上的联系对我目前西藏的物资供应还有一定需要,而且维持一定的往来对扩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印度的影响也属有利”。因此,可“通过谈判订立一个新的协定”,而新协定“总的精神应该是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进一步减少和限制印在藏机构和片面权利,对有利两国人民的一般通商、朝圣和边民往来仍可保持。在谈判中我仍可高举中印友好、五项原则的旗帜,抱积极态度,但也不怕拖延或谈不成”。
第三,突出了处理《1954年协定》的一些具体做法。《外交部意见》指出,“由于印度目前正在反华”,同时印度在协定问题上“更多地有求于我”,因此,不必先主动表态,而可采取以下办法:其一,印方如在12月3日以前提出要求延长,中国可表示不同意延长,但愿通过谈判订立新协定。其二,如印方在12月3日前不提出延长或修订协定,中国可有两种对策:(1)“我们也不主动提议订立新协定,待协定到期自行失效。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倾向于这一办法”。(2)“为了争取政治上主动,我也可考虑待适当时机(如在印度出现反华间歇期间)向印度提出,按例原协定将于期满时失效,如果印方愿意,我们准备同意谈判新的协定”。
最后,充分估计了有关新协定谈判的艰巨性。外交部认为,如能进行这样的谈判,“将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因此“必须作好充分准备,提高警惕”。关于谈判地点,外交部建议,“考虑到时间长,问题多,就人力和各方面条件来论,以争取在北京举行为宜”。
周恩来看过《外交部报告》后,于12月2日做出重要批示,他写道:“经与小平、陈毅两同志审定,于明(三)日下午给印方这样一个照会,一方肯定中印协定期满失效,使印方压我要求继续延长协定有效期的希望落空,另一方主动提议根据五项原则重新谈判,缔结一个新的协定来代替原有协定,使印度陷于被动。如印度拒绝,它输理;如同意谈,也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拖而不谈,或谈不成,我也无损,俱可剥夺印方说我不愿友好的借口。”*《周恩来在外交部送审的给印度驻华使馆照会上的批示》,1962年12月2日,档案号105-01803-01。周恩来的亲笔批示,见该文件的第22页。这天中午,周恩来还约请外交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总参谋部等单位的负责人到西花厅开会,讨论关于《1954年协定》期满后如何处理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陈毅、廖承志(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姬鹏飞(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耿飚(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时任第一亚洲司司长)、周秋野(时任第一亚洲司副司长)、程之平(时任第一亚洲司副司长)、雷英夫(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等。
会后,外交部在12月3日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希望双方通过谈判,签订新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方在照会中说:“为了巩固和发展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见,中国政府建议:中印两国政府举行谈判,以便根据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缔结一个新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来代替原有的协定。中国政府希望得到印度政府对于这一建议的答复。”*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使馆的照会,1961年12月3日,档案号105-01803-0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1962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18页。同时,根据12月2日会议的精神,外交部在12月8日将《关于建议谈判中印协定的内部考虑》以电报的形式,发至各驻外使馆、代办处、日内瓦代表团、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西藏外事处、上海外事处等机关。外交部在电报中指出:“西藏平叛后,西藏情况和中印关系已有重大变化,我不能再原封不动地延长协定。但从长远看,从外交全局看,也不宜根本废除。就印方来说,它是亟想延长协定的,以保持其在藏地位。但由于目前正大肆反华,国内右派又在大叫废除协定,在此情况下,印度显然不好主动提出延长,而是采取以反诬我违反协定,破坏五项原则的办法来压我首先表态。”有关中国处理《1954年协定》期满后的政策,外交部在电报中重点传达了周恩来的上述批示。*《关于建议谈判中印协定的内部考虑》,外交部致电各驻外使馆、代办处、日内瓦代表团、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西藏外事处、上海外事处,1961年12月8日,档案号105-01803-01。
在此之后,中印两国就处理即将期满的《1954年协定》的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照会战。印度在1961年12月15日复照中方12月3日照会,拒绝中方的提议,同时还用大量篇幅,指责中国“侵占”印度“领土”,将签订新协定的谈判同边界问题挂起钩来。印度在照会中说:“(中方)开始起初暗中而后公开地侵略曾经明白承认为属于印度的领土,而至1958年更开始对数千平方英里的印度土地提出公开要求,并继之以侵略性的军事活动。”印度为签订新协定设立了先决条件,声称:“印度政府在谈判和签订1954年协定时所抱的希望和愿望已经完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中所执行的侵略和扩张政策所破灭。开始这种谈判的首先要条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扭转他过去几年所执行的侵略政策以及恢复足以保证五项原则在文字上和精神上都得到严格遵守的气氛。”*印度外交部致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照会,1961年12月15日,档案号105-01803-01。印度照会英文件,见该卷宗第39-40页。
对印度的照会,中方予以坚决回击。中国外交部在1962年3月1日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全面驳斥其12月15日照会。中国在照会中指出,印方拒绝中方“友好的建议”,不仅缺乏“最起码的礼貌”,而且“对中国恣意进行恶意的指责和污蔑”。中国强调指出:《1954年协定》和边界问题是两回事,边界争议并不妨碍进行有关通商和交通协定的谈判,印方“却硬要把中国政府的建议同中印边界问题扯在一起,这只能使问题复杂化”。印方的指责不仅“完全没有根据”,“颠倒是非,污蔑中国政府执行侵略政策,而且还荒谬地要求中国扭转这种莫须有的政策。如果印度政府坚持这种态度,那么,中国政府只能很遗憾地从这种态度中得出结论,即印度政府存心使两国关于通商和交通协定的谈判成为不可能”。3月3日上午,章文晋将中方照会面交印度驻华使馆代办班纳吉(Purnendu Kumar Banerjee)。*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馆照会,1962年3月1日,档案号105-01803-0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20-22页。
1962年4月11日,印度复照中国政府,在这份冗长的照会中,印方再次将签订新协定同边界问题联系起来。首先,印方辩称《1954年协定》已解决边界问题,因为协定已“明显地是要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毫无疑问地“确认了当时存在的领土状况”,“不能说中国政府在签订1954年协定的时候,对印度认为的两国间正确的传统边界线存有任何怀疑”。如果中方“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他提出的要尊重印度领土完整的保证的目的是什么呢?先是做出这样一个保证,然后又要求对方的部分领土归属自己,这对于一个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了一项庄严的协定的政府来说,当然是不能允许的。”
其次,指责中国“侵占”印度“领土”,将边界争端的责任归咎中方。印度声称,缔结协定时边界是平静的,“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或纠纷”,而最近几年发生的边境冲突和纠纷,是由于“自从1954年以来,中国军队对印度领土的武装侵袭和占领,加剧了局势。这已经使信任受到破坏,并且在印度人民中间引起了深切愤慨”。照会还特别提到中印边界西段,称中国军队从1957年起“在阿克赛钦地区开始了侵犯和占领印度领土的过程”,“除了非法占领以外,还对大片的印度领土提出非法要求”。
第三,再次挑起“地图战”。印方宣称其官方地图有关中印边界的画法是“精确”的,“符合于1954年和更早时候的领土状况”,诬称中国地图的画法存在“令人迷惑的各种错误”,并辩称中国是了解“印度官方地图上所精确地标明的传统边界线”的,印方“一再提请中国政府注意”这些印度地图,中国“总是对印度政府保证说,这些旧的中国地图是国民党政权的不正确的制图法的产物,还没有时间加以修改”,所以印方“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政府对这条边界线的正确性有任何怀疑”。
最后,为谈判新的协定设置前提条件,印方声称中国如“及早采取步骤履行尊重印度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保证,从印度的领土上撤出他的军队,恢复边境上1954年所存在的现状,印度政府将感到高兴。只有这样做才能恢复信任,并为谈判一项新的协定创造必要的友好气氛”。*印度外交部致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照会,1962年4月11日,档案号105-01803-01。印度照会英文件,见该卷宗第67-7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44-48页。
印度4月11日照会导致中国完全改变了处理期满后的《1954年协定》的态度。中国驻印使馆在4月16日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分析了印度的意图,并对拟采取的措施提出建议。驻印度使馆指出:“印度对我一再提出谈判似估计错误而产生一定错觉。对印下一步斗争,我们意见在谈判问题上可冷一下,给以适当压力,并相机揭露,使其更处被动。”驻印使馆还特别分析了印度对其驻藏商代处的态度,指出:“印对商代处存留问题至今还无具体表示,今年印商务代表去阿里地区事也仍未提出。可能协定失效前后印另找借口拖延撤销,但也可能准备撤走。目前仍在摸我底。因此,也可考虑目前暂不作表示,待协定失效以前不久再提出撤,使其既无宣传资本,又减少印转弯余地。”*《对印11日照会的若干看法》,驻印度大使馆致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4月16日,档案号105-01803-01。
周恩来看了印度4月11日照会后,于4月25日指示浦寿昌(时任总理办公室秘书)告诉外交部,要尽快答复。同时,周恩来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印方此次来照,是全面性的,我们答复时也要全面地加以驳斥”;第二,“我复照总的态度要强硬一些,照会中不要再提要求同印方谈判协定问题”;第三,“要指出印方在来照中所持态度和论点的本身,就表明了印方根本不愿意谈判”。*《4月24日工作纪要》,档案号105-01803-01。周恩来的这一指示是中国处理期满后的《1954年协定》之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中方不再向印方提出谈判新的协定,而是等待协定自动失效。同时,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于5月10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对处理期满后的《1954年协定》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对策方案。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审阅了这份报告。
首先,坚持终止《1954年协定》的政策。外交部在报告中指出:“印度两次拒绝谈判新协定,旧协定的失效已成定局。根据目前对印斗争形势和西藏的现实情况,我们对终止协定要态度坚决,但在做法上要留有余地。”其次,建议对藏印贸易采取灵活的措施。报告指出:鉴于目前西藏、特别是阿里地区的物资需要,应充分利用印度政府和印商的矛盾,尽可能维持藏印贸易的现状,同时要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逐步加强管理,“防止捣乱”。这些措施包括:(1)原在亚东、拉萨、帕里的印商不管是否经过批准,仍准其照旧营业,将来可考虑逐步把拉萨、帕里两地印商挤走。新来的印商经批准后,可允许其营业,但只限于亚东。(2)对来阿里地区从事边境小额贸易的印商,应争取和影响。(3)协定规定的阿里各市场以及印商实际上也去的该地区其他市场,由西藏当地政府重新审查;如无必需取消的理由而又为藏民所需要的,仍可按以往习惯开放。(4)在经济上要做最坏的打算,因为目前阿里地区需从印度进口粮食和日用品,出口羊毛和盐巴。外交部强调:“如印度封锁禁运,势将给我造成困难。因此,除设法打破印方可能的禁运外,应请西藏工委及早筹划另辟途径,如扩大内贸和藏尼贸易。”*《外交部有关对1954年中印协定失效后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962年5月10日,档案号105-01804-01。
1962年5月11日,中国外交部在给印度驻华使馆的照会中指出:“尽管无论是在履行1954年协定的问题上,或是维持边界现状的问题上,中国是受害者,中国政府在提出重新缔结一个新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时候,并没有提出任何先决条件。”而印度“坚持粗暴的、要中国屈服的先决条件,这只能表明印度政府根本不愿意谈判缔结一个新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来代替即将于1962年6月3日期满的1954年协定”。5月17日,章文晋司长接见班纳吉时指出,有关《1954年协定》,中方建议谈判,重新签订协定,章文晋说:“这并不是我们有什么自私目的,也不是非要不可。没有协定,你们活得下去,我们也活得下去。我们完全是为了改善气氛。但是你们把它同边界问题联系在一起,说中国不撤出‘侵略’,就不谈。……这使中国人民痛心。印度把每件事同边界问题,同所谓中国撤出‘侵略’联系起来,这种逻辑很危险,只能导致两国断绝一切关系的唯一前途。”*外交部关于印度政府再次拒绝谈判缔结新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1962年5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40-44页;章文晋司长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谈话记录,1962年5月17日,档案号105-01128-02。
1962年5月18日,中国外交部通知驻印使馆:中印协定失效已成定局,“我们对终止协定要态度坚决,在做法上留有余地。我部定在22日口头通知印驻华使馆,说明协定即将期满,由于印方一再拒绝谈判签订新协定,中国驻印商代处的存在已失去效力。中国政府决定撤销驻加、噶商代处,请印方协助。……请加、噶两商代处即准备在6月2日前撤完”。*《有关协定失效和商代处的撤销问题》,外交部致驻印使馆的电报,1962年5月18日,档案号105-01123-03。5月22日,第一亚洲司张彤副司长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一等秘书塔达尼、新闻专员斯瑞尼瓦森,正式通知印方,撤退中国驻印度的商代处;张彤说,印度政府一再拒绝中国政府所提的友好建议,这样,1954年签订的中印协定将在6月3日期满失效,双方根据协定而设立的商代处的继续存在也将失去了根据。为此,中国政府决定取消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和噶伦堡两地的商代处,请印度政府予以协助。*第一亚洲司张彤副司长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一等秘书塔达尼、新闻专员斯瑞尼瓦森谈话记录,1962年5月22日,档案号105-01805-01。5月22日上午,中国驻印使馆以叶成章代办的名义,打电话给印度外交部,要求约见外事秘书德赛,印方多次答称很忙,让中方约见中国司司长沈书美(S. Sinha)。中国使馆告知印方:“有要事且系奉我政府指示能在今日任何对他方便的时间见他。”经过来往电话九次催询,中方最终在当天下午五时同印方约定,叶成章和德赛将在23日中午见面。23日中午,叶成章在同德赛会见时,通知印方中国撤销驻加尔各答和噶伦堡的商代处。德赛表示,谈判新协定是中国方面提出的,印度不能谈判新协定是由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气氛的关系,印方将对中国结束商代处事给予必要的方便;德赛告诉叶成章说,中国撤退其商代处,从对等的情况来说,也关系到印度驻藏商代处的问题。德赛表示,印度政府对此将进行考虑并做出决定。*《通知我撤销驻加噶商代处事》,驻印度使馆致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5月22日,档案号105-01123-03;《按部示已通知印方撤销加噶商代处事》,驻印度使馆致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5月23日,档案号105-01123-03。
与此同时,中国有条不紊地进行撤退驻噶伦堡和加尔各答两地商代处的工作。5月23日,驻印度使馆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汇报说,他们按部示已通知印方撤销加、噶商代处事。5月24日,中国外交部致电各驻外使馆及代办处,通知中印协定的失效,同时强调要利用协定失效的机会,“进一步削弱印度过去在西藏所享有的权利。这是我同印度的又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5月27日,驻噶伦堡商代处的中方人员全部到达加尔各答;随后,两处全体人员分别于5月30日和6月1日离开印度返回中国。由于中方事先对两地商代处的撤离工作做了周到的部署安排,“一切对外账务竭力了结,不能清算的也作了委托,手续务求合乎规定,因而海关等未加刁难,撤离尚称顺利”。*《对中印协定失效后有关问题的处理》,外交部致电各驻外使馆、代办处,老挝代表团,1962年5月24日,档案号105-01804-01;《有关噶、加人员撤离情况》,驻印度使馆致外交部、外贸部的电报,1962年6月4日,档案号105-01123-03。5月29日,章文晋通知班纳吉:中国已撤销驻印度的商代处,询问印方是否也在期满前撤退其在中国的商代处。班纳吉回答说,他未得到政府的指示。5月31日,章文晋再次会见班纳吉,询问印方的态度;班纳吉说,印度决定撤退在西藏的商代处,打算6月10日撤退江孜商代处,6月15日撤退亚东商代处。班纳吉表示,印方将保留在亚东的商代处房子,留人看守(如花匠、厨师),房子和看守人由驻拉萨总领馆控限和管辖,因为中国也保留了在噶伦堡的商代处房子,“这是对等的”。6月1日上午,张彤接见班纳吉,通知印方有关撤退印商代处的问题;张彤告诉班纳吉说,自6月3日起,印度在藏各商代处不得再使用密码、信使,中方也不再提供信使车辆,印度在亚东的电台即停止使用,并尽快送出境,出境时要报请中方登记。*章文晋司长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新闻专员斯瑞尼瓦森谈话纪要,1962年5月31日,档案号105-01805-01;第一亚洲司副司长张彤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二等秘书梅农谈话记录,1962年6月1日,档案号105-01805-01。
三、西藏工委对中央政策的执行与印度的反应
印度自西藏平叛以来就不断向中方提出其驻藏商代处“在房屋建筑、旅行、信使及邮袋、印度商人在西藏中部所遇到的困难”。*印度外交部关于亚东商代处等问题给我驻印度使馆的照会,1959年10月26日,档案号118-00821-01;印度照会英文原件,见该卷宗第10-16页。关于印度总理已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提及的边界问题以外的一些问题的非正式照会,外交部文件,文总286号,1960年12月12日,档案号105-00725-01。同时,印度商代处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举动也显示,其早已获知1962年6月2日以后将不再行使职权。亚东商务代表姜潘基(Laxman Singh Jangpangi)*姜潘基出生于1905年7月24日,从1930年开始就在英国驻噶大克商代处担任会计师,地位仅次于商务代表,1946年升任驻噶大克的商务代表,1959年12月转任印度驻亚东的商务代表,并于同年获得印度政府颁发的“莲花士奖”(Padma Shri)。在4月5日和6日连续召集印商开会,称商代处将在一个半月以后回国;西藏外事处也在这段时间内,向外交部报告亚东居民、印商以及各方面对印度将撤走商代处的反应。根据中方的判断,“印方似乎在协定失效后不想与我断绝”,想继续保持其在亚东、阿里和江孜三地的据点和权益,为此印方还对亚东市场放宽了对出口许可证的签发,允许部分物资出口到西藏。1962年第一季度“亚东印商进货较去年同期还多,不少印商要求与我国营公司做生意”。*《关于印度官方机构的动态》,西藏外事处致各外事分处并报工委、外交部、西南局的电报,1962年5月5日;《关于我亚东群众和印商对印方撤走问题的反映》,西藏外事处致工委、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5月29日;《亚东印商对印商代处撤退的反映》,西藏外事处致工委、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5月30日;《各方对印商代处撤走的反映》,西藏外事处致工委、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6月2日。以上档案的档案号为105-01123-04。外交部领事司:《关于近来印方在西藏的一些做法》,1961年7月4日,档案号118-00955-17。
1962年5月19日,外交部就印度商代处撤退时所涉及的诸如信使、发电报、印商开业及歇业等问题,做出了相应的部署。外交部在电报中指示西藏外事处,从6月3日起,终止印度商代处的职权,停止使用密码、信使和亚东电台。外交部强调:“我内部掌握上,对其撤退工作可给以适当照顾,如可允许其派人送信,我不承认其信使身份,但也不检查其携带的邮袋。在处理电台问题时,切忌方式生硬。如发现其继续使用,可加以封闭。印商代去阿里事,要切实掌握协定失效前后的区别。失效后我不再提供流动电台,也不同意他以商代名义转市场。噶大克租地租金,应照常向他收。租地允其雇人照看或由总领馆代管,但不同意印商代处留人看管。”*《复对协定失效后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外交部致电西藏外事处,1962年5月19日,档案号105-01124-01。
根据外交部的上述指示,西藏外事处做出较为具体的行动构想。首先,在信使问题上,西藏外事处认为:“协定失效后,印商代处不得继续享受外交信使的权利。……在未得到指示前,分处不能允许印方继续使用信使,更不得承担义务。如印方要求派人送信也得将详情上报批准后才能答应。但由于印商代处和总领事馆使用的信使是共同的分不开的,商代处信使停后总领馆仍有信使往来,而且必须经过亚东、江孜,……虽然拉亚间一时停止了信使往来,但印亚间印方仍可借口总领馆信使继续派出。这样,亚东商代处即可以‘总领馆信使’之名,实际上继续享受信使的权利。我们的意见:不承认过去派出的四名信使为总领馆信使,总领馆欲派出信使应另行商谈。在未达成协议前,拒绝印信使入境。同时,现在拉萨的两名信使的护照有效期将分别在6月3日和6月6日期满,我不再发给其多次出入境签证。把总领馆派信使的问题拖一下,对从岗渡派来亚东的信使暂不过问。我们倾向于第一种办法。”其次,在印驻藏机构发电报的问题上,西藏外事处建议:“从6月3日起,印方不得以任何方式拍发密码电报,如印方提出要求,未经上级批准不得同意。但是,印方可以私人名义拍发明码电报。”再次,在印商开业以及兑换货币的问题上,西藏外事处建议,对亚东未经批准开业的印商,允许经营,如提出要求可发营业执照。“若印商返印,要求将银行存款兑换外币,应根据实际情况和我们的力量合理解决。此问题请当地外贸、银行部门掌握。商代处存款可以汇回印驻华使馆”。西藏外事处还建议:“协定失效后,我颁发各种证明书问题,可维持现状,不忙于改变。目前应集中精力,抓实质问题。”外交部基本同意西藏外事处的上述建议,对信使问题则表示“研究后另复”。*《协定失效后对印商代处若干问题的请示》,西藏外事处致亚东、江孜、阿里外事分处并报外交部,1962年6月1日,105-01124-01;《协定失效后对印商代处问题的处理》,外交部致西藏外事处并转亚东、江孜、阿里分处的电报,档案号105-01124-01。
针对印方以各种借口拖延商代处撤销的举措,外交部在1962年5月25日曾指示西藏外事处:“印正以各种借口企图刁难和迫害我驻噶商代处,以达到扣留我人员,霸占我财产等目的。请你们密切掌握印在藏机构动向,找几条辫子,设想一些报复的方案报来。对印方的非法活动也要提高警惕。但对外切勿显露痕迹。”*《请注意印在藏机构活动》,外交部致西藏外事处并转亚东、江孜、阿里外事分处的电报,1962年5月25日,档案号105-01124-01。西藏外事处在6月1日的复电中,具体设计了几个“抓印方辫子”的方案,主要是印方在江孜年楚河修筑的钉坝和江洛林卡租地及地租问题。西藏外事处汇报说,关于钉坝,自1958年以来,印方修建10多条,严重威胁公路、桥梁和居民的安全。1959年中方修建了防护工程,主动拆除钉坝4条,尚有8条。有关江洛林卡的租约,自1959年以来,印方在江洛林卡修建了五栋房子(三栋打了地基,两栋未盖屋顶)并且派人住守,同时未经同意便将江洛林卡的部分土地(约十克,相当于10市亩)分给其佣人种植。对此,可通知印方拆除在江洛林卡的未完工程,停止其佣人在江洛林卡种地(内部掌握对佣人种地可暂不收回)。与此同时,要印方支付1959年6月以来约三年的占用地皮费,每年约7000元。其他还有亚东商代处雇员遗弃藏族妇女、私卖枪支以及藏匿手枪等等。*《关于抓印方辫子的几点意见》,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工委的电报,1962年6月1日,档案号105-01124-01。因此,从1962年6月2日到6月22日,江孜外事分处贯彻西藏外事处的指示,主要围绕着钉坝、江洛林卡地皮租金以及商代处租房租金等问题,同印度商代处进行交涉和斗争。
印度驻江孜商代处在年楚河修筑钉坝,缘于1954年7月16日的水灾。在这次水灾中,时任商务代表克里希纳·德里(Krishna Delhi)被淹死,印度兵营47人,除14人外全部死亡。*《为江孜印商代处被水淹事表示慰问》,外交部致西藏外事处的电报,1954年7月28日,档案号105-00149-02。江孜商代处为防止类似事件,自1958年以来在年楚河上修筑了12条钉坝。1958年9月,尼赫鲁访问不丹经过亚东时,了解印商反映的情况,其中就包括年楚河的钉坝问题。他在9月22日给印度外交部的指示中,特别提到了年楚河的钉坝,并且指出:“就钉坝问题来说,一定要按中国人的建议行事。我们首先要请求他们建造这个钉坝。如果这样做不成功,那么我们就应该听从他们的建议,我方工程师也应同中方工程师密切合作。”*Note, written at Paro, Bhutan, for N.R. Pillai, Secretary General, Subimal Dutt, Foreign Secretary, M.J. Desai, Commonwealth Secretary; and B.N. Chakravarty, Special Secretary, 22 September 1958,in Madhavan K. Palat,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ume Forty Four (1 September-31 October 1958),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12, pp. 622-625.然而,这些钉坝建成后,曾导致河水南流冲坏大桥,特别是其中一条长钉坝危害最大。1959年中方修建防护工程,江孜外事分处于5月18日向印方正式提出,要其拆除长钉坝的一段,否则中方将自行拆除,但印方多方寻找借口加以阻挠。中方把拆坝日期告印方,并派人于规定日期拆除4条。印方当时派工程师出面直接阻挠拆坝,并致函江孜外事分处称:“在代理处区域以内做任何改变,需事先征得印度政府同意。所谓代理区域,我指的是1946年界线以内的区域。”在中方看来,这些钉坝“严重威胁我公路、桥梁和居民的安全,……我们认为在其撤走之前,应要其拆除。若不拆即采取相应措施”。*《印度在西藏的活动和中印双方的交涉情况》,外事动态编辑委员会编印:《外事动态》,第78期(总第158期),1959年7月23日,第7-8页。据西藏外事处调查,“所谓1946年线是英帝与平康订立的,从未同意过,过去并曾向印方明确交代过,英帝同平康所订旧租约不能继续有效”。
有关江洛林卡地皮租金问题,中方有关部门1958年同意印方在签租约前可在商代处原址上重建;到1959年,印方修建的五幢房屋中,两幢已接近完成,另三幢也打了地基。江孜商代处地皮租约的条款,包括租地总面积85%的地皮(含商代处已进行修建的和计划修建的房屋在内),已于1960年12月商定,对于其余约15%将从哪个方向的邻近地皮补足一事,中方建议印方放弃洪水线以下的河岸地带,而在租地范围的其他方向予以补足。印方对这块补地一再改变主意,不断提出新的方案。*中印之间的有关交涉,参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8-01047-13。围绕着印方租用江洛林卡地皮的租约问题,1961年中印双方共谈判10次,其中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同西藏外事处谈过两次,江孜商代处同江孜外事分处谈过8次。在这些谈判中,中方的基本立场是“不主动促成,在有适当的理由下,采取拖而不办的办法”,“应尽量在租约问题上予以纠缠,拖而不签”,以便“为创造我在下次谈判中取消江孜商代处的有利条件”。因此,西藏外事部门根据外交部“拖而不办”和“拖而不签”的指示精神,在同印度商代处交涉过程中“不与之达成任何口头的或文字的协议,并在具体做法上,预作计划,将达不成协议的责任放在印方身上”。*《对江洛林卡租地租约的意见》,西藏外事处致电外交部并抄江孜外事分处,1961年5月22日,档案号118-00950-11;《复关于对江洛林卡租地租约的意见事》,外交部致电西藏外事处,1961年6月6日,档案号118-00950-11;西藏外事处:《工作汇报第九期》,1961年7月6日,档案号118-00955-01。
1961年8月4日,杨公素接见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高尔(Prakash Narain Kaul)时指出:租约谈好后,由江孜方面具体执行。杨公素告诉高尔说,江孜商代处当初对租地范围是同意的,但看过实地后提出换地要求。中方认为这是“新的要求”,因此“为了承租人的利益,有关方面就要根据新要求与群众商议出最好的办法。假如不提出新的要求,那就很容易解决了。……我希望能及早地照顾到承租人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解决”。*杨公素同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高尔的谈话,1961年8月4日,档案号118-01040-26。高尔于1959年7月代替蔡伯尔(Shri Chibber),出任印度驻拉萨总领事。有关情况参见外交部致西藏外事处的电报,1959年7月22日,档案号105-00661-01。8月16日,江孜外事分处席潮海副处长同印度驻江孜商务代表潘迪特(K. L. S. Pandit)会谈时表示:有关租地问题,“我们要与群众和有关方面商量,……因这涉及到群众和有关部门,我们要与他们很好地商量,以便达到双方均感到满意的调整方案”。在印度所要求的租地上,席潮海说,“本来当时很好解决,当时群众未种庄稼,也不是雨季,因为你们拖延将近四个月,现在情况与当时有些不同,群众种了地,雨季又来了。我们要搞雨季工作,一时不好安排”。*江孜外事处席潮海副处长同印度驻江孜商代代表潘迪特的谈话,1961年8月16日,档案号118-01040-26。潘迪特接替卡堡尔(R.S. Kapoor)任印度驻江孜商务代表,卡堡尔于1961年4月21日离开江孜返回印度。西藏外事处当时希望外交部通过驻阿富汗、缅甸使馆了解潘迪特的一些情况,但并未获得详细的资料。参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8-00950-11。对这一时期与印度商代处的交涉情况,西藏外事处在1961年8月的一份工作汇报中认为,“印方似已摸到我的对策,目前的做法是企图将拖延的责任加诸于我”,“最近印商代处又几次来函询问,并有将拖延解决租地问题的责任加于我方之意。……我们的对策是坚持贯彻‘拖而不签’的方针,抓住印方要求调整租地范围,表示须与当地有关部门和群众商量,拖下去。江孜分处提出可先确定印现住房的租约和必要时提出要印方拆除钉坝两问题,我已同意”。*西藏外事处:《工作汇报第十期》,1961年8月17日,档案号118-00955-06。
江孜商代处当时的住房租约,是同江孜城关区人民政府在1961年11月28日订立的;租约规定,商代处租借甲错白地房9间、玉妥房18间以及通普切房18间,每月租金人民币495.84元,租期从1961年11月28日到1962年4月29日。*《江孜商代处住房租约》,1961年11月28日,档案号118-01041-05。住房租约英文原件,见该卷宗第8-9页。对于江孜商代处现住房租约期满后如何处理,江孜外事分处提出届时以互换信函方式,延长有效期一至二个月。西藏外事处在1962年4月6日向外交部汇报说:“我们考虑,为了不过早地暴露我们的意图,如印方不提续租,我亦不提;待中印协定期满,处理印度在藏遗留问题的方针,确定后再定。这样作我较主动,如印度主动提出续租,我可听而不谈,拖过中印协定期满后再说。”外交部4月16日回电,同意西藏外事处的意见。*《关于印驻江孜商代处现住房租约事》,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4月6日,档案号118-01041-02;外交部致西藏外事处的电报,1962年4月16日,档案号118-01041-02。
1962年6月2日下午,亚东外事分处通知姜潘基,终止商代处的职权,姜潘基表示,他尚未接到政府关于撤退的指示;中方提出希望看到能在一个月内撤走,姜潘基表示尽可能在此期间撤完。有关信使问题,姜潘基提出今后不能使用信使就无法与政府联系,要求继续使用,中方予以拒绝;姜潘基又提出原定在6月4日从拉萨返印的信使如果来亚东,他们返印的交通方式是否仍为由商代处派牲口送,由外事处开路条。中方答应可派牲口送他们返印,但必须明确这些牲口不是印度商代处的。至于是否再开路条,则需报告政府。关于使用密码问题,印方一再提出要求保留使用密码,中方予拒绝,印方表示没有通讯电台他们撤离期间就要瘫痪。中方提出过去商代处有电报挂号,今后可改用私人名义。有关电台问题,印方默认有,并询问运出境时在哪里登记,中方只答复到中方有关部门进行登记。此次会谈后,亚东分处在给西藏外事处的汇报中承认:“上述我方答复,在有些问题上显有错误,这是与上级历次指示精神不符,界线特别不清,分处领导除应进一步做检讨外,请处给予批评和处分。”*《关于通知印商代处终止职权等三点指示》,亚东外事分处致西藏外事处、江孜分工委的电报,1962年6月3日,档案号105-01124-01。亚东分处做出上述检查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其在信使以及电台问题上,在未接到外交部的具体指示时便对印方做了表态。
1962年6月2日下午,江孜外事分处席潮海副处长会见潘迪特,通知他关于终止商代处的决定。席潮海告诉潘迪特,由于印方两次拒绝谈判签订新协定,《1954年协定》期满后双方商代处的存在已失效力,中国在加尔各答、噶伦堡的商代处业已撤退,印度在亚东、江孜及噶大克商代处的职权亦应从6月3日起终止,中方希望知道印方具体的撤退日期。同时从6月3日起,印度在西藏的各商代处不得再使用密码、信使,中方也不再为印方提供信使车,但撤退事宜仍可与中方接触。潘迪特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抱歉,表示将报告政府,一俟得到消息,将告诉撤退的确切日期,同时要求仍可使用信使车。席潮海坚持说:“协定失效,商代处职权即行停止,从6月3日起印商代处不得再使用密码、信使,我也不再为你们提供信使车。”*席潮海副处长同潘迪特的谈话记录,1962年6月2日,档案号105-01125-01。6月4日,席潮海再次在会谈中告诉潘迪特,从协定终止的6月3日算起,希望能看到最迟在一个月内撤退,同时承诺中方可协助解决合理的运输工具,请印方告知将有多少吨东西,约需多少车次以及需车的日期。至于潘迪特提出要将江孜商代处的大桌子、江洛林卡的木材等运往拉萨,席潮海表示,现在不能决定,待研究后再说。潘迪特抱怨说,商代处的当地雇工不再来工作,可能是当地政府发出的停工命令,对此席潮海表示:中方并没有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只是告诉那些人从6月3日起不再保有前商代处人员的身份,他们不能再进行前商代处业务范围的工作。潘迪特希望中方命令当地雇工再去工作,因为“没有你们的命令,他们是害怕,不敢去干捆行李的零活”。席潮海对此表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是否愿去捆行李和干些院内的零活,那是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中方不清楚这些关系,也没有对他们发过什么命令,因此不能命令他们。这问题只能由雇主与雇工之间去协商解决。*《催印方告知撤退的日期等》,席潮海副处长同潘迪特的谈话记录,1962年6月4日,档案号105-01125-01。
1962年6月6日,印度外交部中国司司长沈书美同中国驻印使馆代办叶成章会谈时表示:中国说印度商代处撤退如有拖延印方政府应负责一点,按情况来说,这样说“是有些粗鲁,是不必要的”。对此叶成章指出:首先,中国两次建议谈判新的协定,印度两次拒绝,印方说是看是否有共同基础。印方说的共同基础是不合理的,中方不能接受。印方照会虽未用“拒绝”的字样,但整个照会是拒绝谈判新的协定,因为印方所提的条件是不可能的条件。其次,既然不谈判新的协定,印方半年前又未提出延长协定,协定期满当然失效。第三,协定到期商代处的存在就没有基础了,双方的商代处即应撤走,这完全是协定精神本身就有的。所以为执行协定,中国撤走在印度的商代处。中国希望印度方面能在一个月内撤完,“这是完全合理的”。撤退的事情当由印度政府负责。对于此次谈话,中国驻印使馆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汇报分析说:“从我撤退后印方一系列措施及沈书美谈话看出印方章法很乱。印方在这场斗争中事先对我估计错误,沈说印方为准备撤退其商代处,说出了印度的实际情况。印方总想保留在藏利益,赖不下去时又出小点子,生枝节。但其所谈问题被我据理驳斥后,又难以自圆其说。估计今后印方还会纠缠。”*《印中国司长与叶代办谈话情况》,驻印度使馆致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6月6日,档案号105-01805-01。
1962年6月8日,席潮海约见潘迪特。潘迪特说,商代处虽然接到印度政府通知最迟在10日撤退,但由于有些问题要解决,所以10日还不可能走,并称不可能全部在同一天走,将分批走。席潮海坚持要印商代处在中国指定的期限内撤退,最好一次办完手续,并拒绝潘迪特提出的再占房间、留人看管物品的请求;至于印方要求将东西运往拉萨,席潮海表示需再请示。中方在此次会谈中还首次提出了钉坝以及房租问题;席潮海指出,印方撤退还有未了事,应在限期内结清。“第一就是59年你们擅自在年楚河一带修的钉坝,须由你们自行处理。表示印方如在限期内不加处理,则我地方当局有权处理。第二,现住房租约已过期,在你们撤退前应交齐租金,现住房租期前的房金应补交,对你们私分江洛林卡土地,我们无法理解”。对中方提出的问题,潘迪特表示,修筑钉坝系经与拉萨外事处商议过的;印方也不反对拆除钉坝,但“此事交上一级处理”。有关江洛林卡的租地租约,潘迪特说:“租金一定交齐,租期前的房金也一定补交齐。江洛林卡的土地给人是在6月2日前,是为了利用荒地多生产。6月2日后该地是你们的财产。”席潮海指出,钉坝系印方私自修筑,“未经我任何部门同意是非法的”,坚持由印方拆除;江洛林卡的土地一直属于中方,“无法理解”印方在租约未签订、又未经中方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把地分给其他人的做法。6月12日,席潮海再次约见潘迪特,双方就钉坝、江洛林卡地皮以及租金等问题继续展开争论,潘迪特将所有问题都推交高一级当局讨论,称“所有悬案将与拉萨外事处和中国在新德里及北京的当局谈”,要求中方为商代处的撤退“给予一切必要的方便”。有关钉坝,潘迪特表示,不能同意中方关于钉坝以及建筑材料等的立场,并说有证据表明此事与拉萨、江孜当局商议过。席潮海指出:“我们有记录,现在就可以核对,请你指出是哪一天商议的,怎样商议的。”席潮海还强调说,“如拿不出那就是说你们没有证据,仍是你们私自搞的”;“若你们在限期内撤退后仍未自行处理,雨季快到,我地方当局将有权自行处理”。潘迪特对此只是说将报告政府。关于房租、地租欠款问题,席潮海说,房租共应补交人民币8929.02元,江洛林卡地皮的租金,从1961年1月16日到1962年6月3日,按每月人民币560元计算,应补交9276元,这些款项必须在撤走前结清,交付时间可商议。潘迪特对欠款表示认可,称补交款可能是7000多元,江洛林卡地皮补交租金和租约签订前所欠住房租金问题应由高一级部门去商谈。潘迪特强调说,印方住过房子虽是事实,但“在它解决之前,我不能在我走以前清理欠款”。席潮海坚持必须在江孜把手续清理了,反对“把这问题推到其他方面解决”。双方重复上述意见达六次之多。对于中方提出的办理一个清账手续的要求,潘迪特不同意,声称“不产生要我写东西的问题”。席潮海坚持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现在是两个办法,一个是把钱交了,或一个是你要出手续。因你们使用了我土地,住了我房,一定要结清。”双方重复上述意见达十几次。对席潮海称印方态度是“故意玩弄、拖延时间”,潘迪特表示遗憾,说“现在不能付欠款,由于强力的条件,我十七日不能离开江孜了”。席潮海坚决反对潘迪特关于“强力的条件”的说法,指出:“你任何时候要走,我们都愿给撤退的方便,你知道我们已给你提供了许多方便,包括运输工具在内,但有些具体经济手续必须结清。”*有关江孜外事处席潮海副处长同印度驻江孜商务代表潘迪特的上述谈话记录,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05-01125-01,第2-4、5-7、8-12、13-17页。
上述会谈后,西藏外事处于1962年6月12日向工委和外交部做了汇报。关于江洛林卡地皮租金和现住房租约签订前的房租,西藏外事处指示江孜分处不能让印方以报告政府、交上一级解决为借口而脱掉,要印方在江孜交涉,解决方式可为:(1)要前印商代处在江孜付清租金;(2)如前商代处目前无款,可由潘迪特开具欠条申明以后由总领馆还清;(3)如印方有不同意见,则要其将其异议写成书面文件,并注明此问题交总领馆与中方交涉,由已去江孜的副领事认可后交中方。关于印方的建筑器材和其他物品,西藏外事处指示江孜外事分处,要印方自行处理,坚决不同意留人看管;但如印方要求其人员先走,将问题交总领馆处理,在总领馆保证按期处理完毕的情况下可予同意。*《关于江孜商代处有关撤退的交涉问题》,西藏外事处致电工委、外交部,1962年6月12日,档案号105-01124-01。6月15日下午,江孜外事分处约见潘迪特,要他付清地皮租金和补交住房租金。潘迪特承认印方实际上占用了江洛林卡的地皮,应交租金,也应补交现住房前欠租金,但拒绝立即结清该项欠款,也不写欠条,重复将报告政府,交上一级解决。6月16日,印商代处人员多吉次仁同陆经武谈话时表示:他们今天已接到指示付房租欠款,但钱不够,将请驻拉萨总领事馆将钱交给中方在拉萨的外事处。关于江洛林卡所欠地租款,多吉次仁说已将此事上报政府,他将再次报告,请迅速决定。*《关于前亚东、江孜商代处撤退情况通报》,西藏外事处致工委、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6月16日;《印商代处人员多吉次仁同我方陆经武谈话》,1962年6月16日,档案号105-01125-01。
对于中国在上述问题上的措施,1962年6月20日,沈书美约见叶成章,向中方递交备忘录,指责中方提出欠款问题是“专断的”,对钉坝的态度“极端无理和专横”。印方声称,“鉴于江孜和亚东的中国当局所造成的局势的严重性,印度政府必须提出明确警告,任何进一步阻止和刁难印度驻西藏商务代理的做法都可能引起严重的反应”。沈书美表示,印商代处所受待遇是一种侮辱,这将引起严重反响。他还说许多人逃走商代处不能负责,商代处也无此权,并称许多人逃到香港谁应负责?叶成章对沈书美的这一说法提出强烈抗议。*叶成章代办与印度外交部中国司司长沈书美谈话纪要,1962年6月20日,档案号105-01805-01;印度政府给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备忘录,1962年6月20日,档案号105-01805-01。
江孜外事分处在1962年6月21日再次向印度商代处催缴房租和地皮租金。潘迪特于6月22日致函分处,写明所欠房租,欠条内容如下:“‘玉妥房’‘通普切’‘甲错白地房’等三处房屋,从1959年12月至1961年11月28日,按每月人民币495.84元,所欠上述房屋的租金为人民币8928.04元;兹申述我们在江孜未付租金欠款。印度驻拉萨总领馆将把这些欠款付给西藏外事处。”同一天,潘迪特还向席潮海递交了地皮欠款的正式信函,并在欠条上签了字。地皮欠条如下:“关于前印度驻江孜商务代理处自1961年1月16日起到1962年6月3日止曾使用江洛林卡的地皮。使用此地皮之每月地皮金曾定为人民币560元,共将付给人民币9276元。因我们现在款项不足,将由印度驻拉萨总领馆付给拉萨外事处。”西藏外事处在致西藏工委和外交部的电报中汇报说:“潘在交房租欠款的信稿时,此信措辞欠当,大有被我所逼,不得不写之意。”*潘迪特向席潮海付处长交送江洛林卡地皮金欠款的正式信函,1962年6月22日,档案号105-01125-01。地皮欠条英文原件,见该卷宗第42页。
亚东商代处在6月18日基本撤完,潘迪特等人于6月23日离开江孜返回印度,印方在江孜的物资,除在江洛林卡之未建成之房屋、土坯十万块、石头十万块和钉坝外,已全部运走。*《潘迪特等人已于6月23日离江孜返印度》,西藏外事处致西藏工委、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6月23日,档案号105-01124-01。中国在印度商代处撤退过程中按印方要求提供了相应帮助。在交通运输方面,截止到1962年7月3日,亚东共向印方提供民工81人次,牲畜291头次;江孜外事分处从6月12日至23日,向印方提供卡车23车次。在物品检查方面,“除藏币、淫画等被扣留和烧毁外,其他未申报的物品、禁止出口的外币及文物等,作为对印方人员的照顾,均予以放行”。*《关于印商代处撤退在交通运输、海关检查签署出境签证等情况报告》,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7月10日,档案号105-01124-01。
江孜商代处撤退后,西藏外事处在1962年6月24日致电外交部,建议照会印度驻拉萨总领馆,指出由于《1954年协定》期满失效以及印度驻江孜商务代理处业已撤退完毕,中方决定收回江洛林卡的全部地皮。西藏外事处希望驻拉萨总领事馆在接到照会后两个月内处理完在该地皮上的印方财产,如土坯、石头和未建成的房屋等。西藏外事处还特别建议,关于年楚河的钉坝,“江孜方面认为钉坝对我将来治理河道有利,并一再提出不必让印方拆除。据此,我们在照会中没有提让印方拆除此钉坝问题。另,还可考虑照会中仍提要印方拆钉坝(主要是政治斗争)。印方不拆我更主动,印方如拆,我将来再修”。外交部27日复电指示,同意暂时不提钉坝问题。*《关于我收回江洛林卡全部地皮问题》,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6月24日,档案号118-01041-01;《复关于收回江洛林卡地皮事》,外交部致西藏外事处的电报,1962年6月27日,档案号118-01041-01。
西藏外事处6月30日通知印度驻拉萨总领馆后,印方未作任何回应。8月22日,西藏外事处蒋树民副处长同拉萨总领事迪欧进行会谈。迪欧表示:关于江洛林卡租金没有争议,明天可付;关于房屋租金双方计算有些不同,大约差58元,此事已经由印度政府和中方大使馆谈。迪欧表示他知道双方对租金数额有分歧,“但我不能给予评论。不管怎样,很快就付”。蒋树民指出,总领事馆有责任谈,因潘迪特写的字据是由总领事馆付款;如迪欧提出异议,应说明理由。对迪欧有关计算存在问题的说法,蒋树民指出,在江孜已计算好,有异议应在江孜由潘迪特提出,而不是印度政府或总领事馆提。对此迪欧回答说,潘迪特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商代处处理此事;他再次强调由两国政府决定此事,希望下周可以解决。*蒋副处长会见迪欧总领事的谈话记录,1962年8月22日,档案号118-01040-05。此次会谈之后,西藏外事处在8月24日请示外交部:鉴于已事实上收回江洛林卡地皮,下一步“同印方的交涉只限于处理印方的遗留财产”,因为印方“想把这个遗留问题作为尾巴,以便今后与我长期纠缠”;为此西藏外事处建议“可抓住这条尾巴向印方进行斗争”,如果印方在期限内不处理,“再致函延期一个月,以争取主动,到时印方不理,我再延期一个月,再不理再延期,做到仁至义尽,准备在较长时间内解决”。外交部虽同意上述意见,但强调“延期不能太多,最多不要超过三次,以免印方产生错觉”。*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8月24日,档案号118-01041-01;外交部致西藏外事处的电报,1962年9月14日,档案号118-01041-01。
印度外交部于1962年8月14日、9月5日、12月12日连续向中国驻印使馆递交照会,指责中方对印度撤退商代处时在江孜所欠租款、钉坝、运走建筑材料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称这些问题“被作为向印度商务代理进行不必要的刁难的题目”。印方在照会中否认江孜商代处同中方订立过租约,称中方所提江孜商代处拖欠租金,“既没有文件证明,也没有法律根据”,称中方“胁迫”印度商务代表在文件上签字。印方照会还将延期拆除钉坝的责任推给中方,指责中方处理印度商代处财产的态度是“无理和顽固的”。*印度外交部致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照会,1962年8月14日,档案号105-01805-01;印度外交部致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照会,1962年9月5日,档案号105-01805-01;印度外交部致我驻印度大使馆的照会,1962年12月12日,档案号105-01805-01。对印方的指责,中国外交部9月22日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做了全面的回应,并在12月26日的照会中进一步指出:要求印方在商代处撤走之前付清欠款“是完全正当的”,数额“也是完全合理的和有根有据的”;印方的指责“有些是歪曲事实,有些是蓄意污蔑。中国政府认为不值得耗费笔墨予以反驳”。*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1962年9月22日,档案号105-01805-01;对印方1962年8月14日,9月5日,12月12日关于撤销商代处问题的照会的答复,档案号105-01805-01。
中国在撤销商代处问题上同印度的交涉和斗争,还体现在处理噶大克商代处租地建房以及印方驻藏机构的电台等问题上。*有关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以及各商代处的电台及其处理问题,将另文论述。《1954年协定》签订后,印度噶大克商代处在1955年9月同阿里地方当局商谈租地问题;印方要求租40英亩土地,每年支付50卢比租金。中方认为,40英亩的土地等于在只有少数固定居民的噶大克建立一个租界,而且年租金只付50卢比是不合理的。印度坚持不让步。1956年5月,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同意减少租地面积至10英亩,但提出要以亚东商代处租地模式订立租约,即租期期满后仍按同样条件续租。在中方看来,亚东商代处租地是在原有租地并建房的情况下订立租约的,而印方在噶大克既无租地又未建房。1957年7月,中方主动提议,印方租地10英亩,租期8年,租金200银元,租约期满后另行商定。1958年1月31日,印度驻拉萨总领事将租约的最后文稿交给西藏外事处,除坚持要按亚东租约模式续约外,提出租期为99年。西藏外事处于1958年10月接受该租约,到1959年10月签字。*《报印外交部8月26日照会所提问题的情况》,西藏外事处致电外交部领事司并阿里外事分处,1961年10月28日,档案号118-01047-02。
考虑到阿里当地严重缺少人力和建筑物资,西藏外事处曾建议,噶大克商代处建房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修建土木结构的临时房屋,第二步,待当地条件具备时再修建永久房屋。印度总领事馆表示同意,但后来要求修建永久房屋,并要求中方提供1800石方、8吨水泥、100名非技术工人等。1960年驻噶大克商务代理并未提出建房问题,其1961年7月到达噶大克后声称,他在德里的印象是,商代处建房问题应由中国政府负责,因此他未作建房的任何准备,而只带来一名工程师。7月21日印方交出修建计划蓝图后,阿里地方当局8月9日表示同意。但印方事先没有对建房做任何准备,建房才继续拖延。*中国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1961年8月26日和11月10日照会的复照,1962年6月7日,档案号118-01047-13。
由于西藏平叛后中印政治关系的变化,中方显然不准备让噶大克商代处完成建房。外交部在1961年7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对印方提出今年要建筑噶大克商务代理处的房屋事,我们除坚持去年与印方确定的先盖土木结构的临时性房屋的原则外,对其建房用车、技工等要求则拖而不签,使他今年建不成。”*外交部领事司:《关于近来印方在西藏的一些做法》。8月26日,印度政府照会中国,指责中国对噶大克商代处的建房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建筑索价过高等。照会中说,对于自1956年以来堆放在工地的旧存碎石子和11685块泥砖,外事处还要索价7112卢比,印方认为“很不合理,特别是鉴于地方当局自己买去26115块砖,仅出价3917卢比。但是,尽管索价过昂,商务代理仍愿照付,希望立即开工。现在商务代理得到通知说,正在向上级请示中”。印方指责说,阿里地区地方当局采取拖延手段,使得商代处房屋的修建工程无法进行,从而阻挠商代处在噶大克终年执行职务。*《印来照内容要点》,驻印度大使馆致电外交部,1961年8月29日,档案号118-01047-01;印度外交部1961年8月26日关于印驻噶大克商代处建房问题的来照,档案号118-01047-03。印度照会英文原件,见该卷宗第16-19页。
对印度8月26日照会,西藏外事处在1961年10月28日提交给外交部领事司的情况汇报中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西藏外事处认为,印度外交部递交8月26日照会的举措,“是我执行拖而不办的方针、使印方计划失败后和我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法,企图歪曲事实,将建房不成的责任加诸于我”。印方有关“竟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最后确定”租地条款的说法虽是事实,“但这完全是由于印方的要求不合理,和其做法上的出尔反尔所造成的”。*《报印外交部8月26日照会所提问题的情况》,西藏外事处致电外交部领事司并阿里外事分处,1961年10月28日,档案号118-01047-02。对印度外交部1961年8月26日和11月10日照会所提出的噶大克建房问题,中国外交部1962年6月7日予以答复。*中国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1961年8月26日和11月10日照会的复照,1962年6月7日,档案号118-01047-13。对于印度商务代理被要求偿付土坯等欠款事抱怨中国地方当局,中国在照会中强调,指责地方当局“索价过昂”,这是有意混淆事实。印度外交部1962年7月23日照会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指责中国在噶大克建房以及印商代处执行职务等问题上的做法,说中国“自称恪守1954年协定,这既不能为印度驻西藏商代处的经历所证明,也不能为中国对中印边界发动的有步骤的侵略所证明。中国政府已用行动来充分表明了它完全不顾协定的文字和精神,以及协定序言中所宣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外交部1962年7月23日给我驻印度大使馆的照会,档案号118-01047-12。印度外交部照会英文原件,见该卷宗第153-155页。
四、印度商代处的撤销及其对印藏贸易的影响
《1954年协定》失效后,印度立即对西藏实施全面的封锁禁运。一方面,禁止向西藏出口货物。从1962年6月2日起,印度停止向西藏出口任何货物。6月2日至7日抵达亚东的货物均系印商在2日前就已运出喜绕塘检查站的货物。7日以后,在亚东的印商均未进货。6月12日,印度宣布西藏为外国领土,对西藏进出口商品实施1934年颁布的关税法,改变一直把对藏贸易与对锡金、不丹贸易一样列为印度国内贸易的惯例。当时有骡夫驮带日喀则尼商的羊毛、牛尾去印度,在经过喜绕塘检查站时被挡回。“据印度警察通知骡帮:他们接到印度政府的通知,自7月3日起,禁止目前在锡金的中国骡帮出境”。7月2日前有骡夫去岗渡,7月3日返至喜绕塘时,印度警察以不准进出为由,将骡夫暂留该地。*《印对藏贸易事》,驻印度使馆致外交部、外贸部的电报,1962年6月13日,档案号105-01123-04;《边境小额贸易》,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7月14日,档案号105-01123-04。另一方面,亚东、帕里和阿里地区的印商陆续关店离境。据西藏外事处1962年6月18日的报告,当时在亚东、帕里共有17户印商,其中7户已关店,人员全部出境返印,6户已关门准备最近出境返印,是否关店出境尚未确定的有4户。在亚东,截至6月27日,共出境31人,仅有一人留下。这些印商出境前基本将店中货物处理完毕,“个别人原在市场上自行采购的羊毛约500包左右,还未运出,存在我银行的24万元人民币也未提取”。但“出境印商都未申请歇业,有三户还向我领了进出口商营业执照。一般都预付了5~7个月的房租”。在阿里地区,普兰塘卡市场原有印商约20余户,70多人,到1962年5月底6月初,印商纷纷回国,至6月10日,全部印商及其佣人都返回印度。6月份以后从事西藏边贸的主要是来自锡金、不丹和尼泊尔的商人,“来亚东进行小额贸易的锡金边民有71人次,不丹边民8人次,下旬来的较多。带进来的物品主要有大米、煤油、糖精、面粉、红茶、白糖、手表、小五金等。出境大部携带卢比并一些砖茶和我国工业品等”。*《印商动态》,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6月18日,档案号105-01123-04;《边境小额贸易》,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的电报;《关于中印协定失效后我区边境贸易情况的报告》,阿里外事分处致西藏外事处并报工委、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7月2日,档案号118-01048-08。此份文件有多处未解密。
印度的全面禁运造成西藏地区货物短缺,物价上涨,特别是粮食,这种情况在阿里地区极为突出。1962年阿里地区缺粮194万斤,印度商品的价格在1963年普遍增长20%。这种情况还可能对西藏地区的稳定产生重要影响。阿里外事分处在1962年7月的汇报中强调:“广大牧区群众,已对今年盐粮交换的停顿状况感到忧虑。对今后盐粮交换失去信心。……部分群众则因此对我不满,埋怨政府。可以估计到,粮食问题如不加以妥善解决,牧区群众将会出现大的动荡,可能在秋冬之交出现大批外逃的事件,也可能产生大量宰杀牲畜,使牧业生产遭受很大破坏的情况。”*《关于中印协定失效后我区边境贸易情况的报告》;《关于阿里地区1964年边境贸易情况》,1965年3月15日,档案号118-01692-11。
由于《1954年协定》的失效,特别是印度商代处的撤销和印商回国所带来的印藏边贸的停顿,对长期依靠印藏传统贸易的一些西藏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此,中央驻藏部门有着清醒的认识。西藏外事处在1962年2月给西藏工委和外交部的报告中对此做过分析和预测;西藏外事处认为:“今后印度对我西藏的作法将更加蛮横强硬,但也没有什么可怕。从西藏形势来看,目前已不似1954年、更不似1958年前的情况,过去那种在某些方面必须依靠印度,必须维持藏印间的通商往来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了。同印度有关系的大商、上层已没有了或者已改变了这种关系。”至于《1954年协定》期满后的藏印贸易,西藏外事处建议,“总的来说应当根据我需要和可能、完全自主的条件下,继续维持”。在具体做法上,西藏外事处建议:“在前后藏方面应该严点,以反击印度的封锁;在阿里方面应该宽些,以适应该地区的具体需要。”*《对中印协定失效后处理印藏间有关问题的意见》,西藏外事处致西藏工委、外交部的报告,1962年2月3日,档案号105-01804-02。
中央首先着重解决西藏的缺粮问题。西藏工委在1962年2月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就曾建议,为应付中印贸易断绝后可能产生的问题,应“在六月份前运送我区粮食600吨,工业品600吨,以备在六月份畜产品上市印商不来,我们可以收购。……建议粮食从新疆调拨,畜产品由新疆外贸局收购”。*西藏工委:《对中印贸易协定失效后边境小额贸易形势的估计和意见》,1962年2月26日,档案号105-01122-07。与此同时,中国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同尼泊尔的贸易关系,特别是进口粮食。尼泊尔当时在日喀则、吉隆、聂木拉设有商代处。1959年西藏平叛后,在西藏的尼泊尔人有360多人,以经商为主,多居住在拉萨、日喀则;每年去阿里从事季节性贸易的尼商约1900人。1961年1月,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世杰同尼泊尔工商部长商谈,尼方有意将南部粮食通过政府交易,以预付款形式购买,转售给西藏,从而“获得高价,增加政府收入”。为此张世杰向外交部和外贸部建议:“在不影响边境传统贸易基础上,由两国政府达成一定数额的购粮协议,使我西藏得到正常的粮食供应,对我是有利的。”*《关于尼向西藏出口粮食事》,张世杰致外交部、外贸部的电报,1962年1月16日,档案号118-01048-01。尼泊尔商人向西藏出口粮食获利很大。尼南部粮食出口印度,在尼境内交货每芒特(37公斤)23卢比,而出口西藏,在聂拉木交货每芒特55卢比,吉隆交货为56卢比。西藏工委在1962年2月也发出指示,要求“不论边境小额贸易的发展情况怎样,我们应积极开展同尼泊尔的贸易,争取物资进口”。*《尼泊尔驻藏各机构、尼侨、尼商情况及其有关问题》,1960年,档案号105-00997-03;西藏工委:《对中印贸易协定失效后边境小额贸易形势的估计和意见》。但1962年3月以来,尼泊尔曲古税卡突然宣布禁止一切粮食出口,称这是尼政府规定的,“即使是习惯搞盐粮交换的边民也不准背出粮食”。西藏外事处向工委和外交部汇报说:“由于尼禁止粮食出口,近来我群众绕道背粮偷越尼边境的日益增多。3月4日尼军三人越境至我工巴莎巴噶尔扎村截回我群众背的粮食。我们认为尼方上述作法可能是暂时性的措施,或是税卡个别人的行动,也可能是尼政府垄断对外贸易。”*《目前藏尼贸易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工委、各外事分处的电报,1962年4月3日,档案号118-01048-02;《关于尼泊尔禁止粮食出口事》,西藏外事处致电外交部、工委并报西南局,1962年4月16日,档案号118-01048-03。为防止藏民到尼泊尔进行粮食交易引发涉外事件,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在1962年5月专门指示西藏军区和工委:“鉴于印度正加紧制造中印边界紧张局势和破坏中尼友好,我尤应大力确保同尼泊尔边界安宁。”因此,“我边民去尼背粮企图同尼税卡闹事的情况是严重的,极易引起涉外事件”。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指示:“目前尼既禁止粮食出口,请你们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工作,劝群众不要去强背。务必要防止闹事。”*《严防我边民与尼泊尔税卡闹事》,总参谋部、外交部致电西藏军区、外事处并告西藏工委,1962年5月9日,档案号118-01048-04。
中国在西藏平叛后实施贸易管理和外币管制,主要是针对印度的,对尼泊尔采取宽松的政策。1962年5月10日,中国宣布在西藏地区实行外贸、海关及金银外币管理。在正式公布管理办法之前,西藏外事处特别指示各地外事分处和海关,要求做好尼泊尔商人的工作;西藏外事处在5月5日的电报中指出:“对尼官方机构可表示,我区建立海关是为了贯彻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有计划地安排进出口。……希望尼侨商对此不要担心。如果有少数尼商感到不方便,甚至不够满意,请商代处(总领馆)帮助解释。”*《关于公布对外贸易及金银外币的管理办法》,西藏外事处、西藏外贸局致工委、外交部、外贸部及亚东、聂拉木、基隆、阿里、江孜、日喀则外事分处、海关的电报,1962年5月5日,档案号118-01048-11。《1954年协定》失效后,西藏工委采取措施,促进西藏同尼泊尔的贸易。其一,对尼泊尔的出口不征收关税,取消沿用原地方政府征税办法,按最惠国待遇;其二,保留尼商自营和门市业务,供给尼商人出口货物和外汇;其三,对尼泊尔口岸的管理松于对印口岸,尽量给尼商手续上的方便。其四,尼商代处持有的外币不进行登记,对边境小额贸易中互相支付尼币和商人用尼币支付国外的背夫、骡夫工资以及运费等等,可照顾过去习惯,不加过问。*《报外贸管理后外商情况》,西藏工委致外交部、外贸部、并报中央、西南局的电报,1962年6月29日,档案号118-01048-22;《关于金、银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西藏外事处、西藏外贸局、西藏人民银行分行致各中心支行,亚东、聂拉木、基隆、普兰、各县银行并报总行、外贸部;江孜、日喀则、阿里、亚东、聂拉木、基隆、普兰、各外事分处、外贸分局的电报,1962年6月22日,档案号118-01048-11。而中国对印度则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商代处撤销后,印商在西藏全区各银行里共有人民币存款320987元,印度在藏机构存款7079元,以及从印度大使馆汇到驻拉萨总领事馆的15000元,收款人尚未支取。对于印方上述款项,工委决定:除一律不批汇,也不给物资之外,如其提取人民币,一则不准在市场上采购金银、羊毛、牛羊皮等物资,同时也不准套购卢比和携带人民币出境。*《关于定期汇票等问题》,西藏工委致总行的电报,1962年11月11日,档案号118-01048-28。
这一时期印度频繁照会中国,指责和抗议中国在印藏贸易和双边关系等问题上的政策措施。印度外交部1962年7月17日照会中国驻印使馆,一方面将1959年以后藏印贸易减少和停顿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当局粗暴地推行它强加于人的专断的新规章的直接后果”,另一方面为其禁运政策辩护,声称印度对柴油、石油制品、汽车零件这些“非传统性的货物”实行的是“有限管制”,“当印度自己也缺乏这种供应的时候,西藏却突然增加这些货物的进口,这显然是为了侵略性的目的”。在1962年9月12日和1963年8月7日的照会中,印度声称,由于“中国当局所强加的新的专断规定”,“使印度商人不能处理他们在1954年协定终止前很久已运入西藏的大批货物,因而他们不得不把这些货物和好几十年才购置起来的不动产丢下,并且留下了大批未了结的贸易债权和贷款”。印方还声称,印度商人全部资产价值达数十万卢比,印度政府掌握这些资产的详情,“希望中国当局公平地赔偿”。*印度外交部致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照会,1962年7月17日,档案号105-01852-01,英文原件见该卷宗第49-51页;印度的照会,1962年9月12日,档案号105-01852-01,英文原件见该卷宗第53页;印度外交部致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照会,1963年8月7日,档案号105-01852-01,英文原件见该卷宗第55页。
对于印方上述指责,中国予以严厉驳斥。1963年10月24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使馆,答复印度外交部1962年7月11日的照会。中方在照会中强调:印度“从既定的反华政策出发”,在《1954年协定》续签问题上“采取了非常僵硬的态度和十分无理的立场。印度政府把中国政府的这一友好建议当作是中国方面软弱的表示,似乎中国有求于印度,因此它妄图借此对中国进行讹诈和勒索。它故意把这个问题同中印边界问题硬扯在一起,荒谬地坚持要以中国无条件地接受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片面主张作为谈判上述问题的先决条件,从而无理地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友好建议”。照会明确表示:“鉴于1954年协定早就失效,印方的一切谰言早已受到应有的驳斥,中国政府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和印度政府长此进行已无实际意义的照会往来。因此,如果印度政府再来照纠缠,中国政府将不予理睬。”11月23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驻华使馆,答复印方在1962年7月17日、9月12日以及1963年8月7日的照会。照会特别指出:“要中国当局‘赔偿在西藏的印度侨民由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而遗留下的一切财产’,这完全是毫无道理的要求,中国政府在以前的照会中早予批驳,现在当然也不能同意。……事实已经很清楚,有关藏印贸易问题的一切困难和障碍,都来自印度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印方企图翻案是完全徒劳的。如果印度政府继续来照无理取闹,中国政府将不予理睬。”12月10日,第一亚洲司建议:“根据总理最近与印代办班纳吉谈话的精神和总理过去对处理这类照会的指示,拟简复印方,并表示对印方今后来照不再置理。”1964年1月3日,印度外交部照会中国驻印使馆,声称中印边界战争已造成两国之间的“信任危机”,不可能就有关“与西藏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进一步交换意见”,因此印度政府“无意再继续交换照会”。*中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1963年10月24日,印度外交部给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照会,1964年1月3日,《中国和印度的来往文件汇编》(1963年3月—1964年2月)第五册,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印,1964年,第307、309页;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1963年11月23日,档案号105-01852-01;第一亚洲司:《关于答复印度外交部1962年8月14日,9月5日,12月12日来照的请示》,1963年12月10日,档案号105-01805-01。
五、结论
《1954年协定》期满后不再谈判新的协定,以及随之所带来的中印撤销各自在对方国家的商代处,这是1959年西藏叛乱后中印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商代处的撤销,标志着中印关系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两国关系格局的根本改变;对中国而言,重大的收获是通过迫使印度撤销商代处,达到清除印度在西藏地区的政治及经济影响的目的,特别是使西藏逐步摆脱印度的经济控制。历史上,英印政府在处理涉及西藏地方的重大问题时,多次利用印藏贸易向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印度独立后,面对解放军进藏、《1954年中印协定》谈判以及中印边界冲突爆发、西藏平叛,同样对西藏实施贸易禁运,以达到其政治和战略目的。而在以往的藏印贸易以及印度实施禁运的过程中,印度驻藏商代处都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西藏工委判断这些商代处都是印方的“情报机构”,迫使印度撤销这些商代处,其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中共中央有关撤销商代处的决策,目标明确,实施步骤果断。中央决定在《1954年协定》失效之前,主动撤出中国驻噶伦堡和加尔各答的商代处,“撤得及时干净,没给印方留下任何借口,这在政治上造成了对我极其有利的局面”,从而使印度“措手不及,陷于混乱、被动”。印度商代处“是被迫撤退的,对撤退准备不足,企图要求留人、留物,其目的在于安插情报点线,与我进行长期斗争”。因此,中央指示西藏工委采取“终止协定要态度坚决,在做法上又留有余地的方针”,同时“适当地施加压力,对原则问题,抓着印方的辫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而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西藏外事处:《中印协定失效后处理印商代处撤退工作总结(草稿)》,1962年10月3日,档案号105-01804-04。
再次,西藏工委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时“坚持原则,寸步不让”。特别是在江孜,在年楚河钉坝、江洛林卡租地租约等“若干重要问题”上,工委按照中央的部署和预定的方案,针对“印方采取事事斗、处处斗、无一不斗的策略”,中方“采取事事顶、无一不顶的方针”,对印度商代处在“新发生的问题和遗留的一些问题”采取的拖延、抵赖的态度,“进行了针锋相对极其严肃的斗争,使印方的图谋陷于破产”。*《工作汇报(关于前印商代处撤退问题)》第29期(西藏外事处致各外事分处、外交部、西南局),1962年7月3日,档案号105-01124-01;西藏外事处:《中印协定失效后处理印商代处撤退工作总结(草稿)》。工委和西藏外事处以及各地部门所设计和采取的“拖而不办”以及“拖而不签”的具体做法,保障了中央决策的顺利实施。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西藏各级部门通过清理印商寄放的牲畜以及藏民所欠印商债务,使一些地区的藏民彻底摆脱了长期以来所遭受的印商的剥削。
第四,西藏工委有关边界问题的建议再次体现了其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的一贯态度。在《1954年协定》谈判的准备时期,工委综合分析了中印关系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力促中央首先同印度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但其政策建议并未被中央采纳。*有关张经武1953年10月21日的电报,参见戴超武:《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1953年10月21日电报探析——兼论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暂维现状”政策及其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在有关《1954年协定》存废问题的政策考虑中,工委同样向中央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工委除着眼边界争端对中印关系的重大影响外,还更多地考虑在处理边贸以及其他越境活动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作为处理涉藏问题的一线机构,工委和西藏外事处所考虑的重点,同中国驻印使馆显然存在着重大差异。
最后,印度的禁运和商代处的撤销而导致的藏印经济关系的全面停顿和断绝,为西藏彻底改变传统的经济模式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有关印度商代处撤销对西藏经济,特别是藏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西藏工委曾做过预案;工委虽然认识到从印度进口粮食及其他日用品等方面将面临困难,特别是在阿里地区,但同时也估计困难只是“暂时的”,主要是交通运输上存在的困难,只要解决了交通运输问题,“即可以粮食、日用必需品满足阿里群众的需要,换回羊毛土特产品”。由于《1954年协定》失效后印度的全面禁运以及印度商代处的撤销,停顿的藏印贸易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上述预判,工委在中央的指示下,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重点解决牧区藏民的口粮问题,开展对尼泊尔的边贸,争取从尼泊尔换回粮食,同时由国营公司出面,收购藏民积压的一些羊毛,稳定市场。*《对中印协定失效后处理印藏间有关问题的意见》;《关于中印协定失效后我区边境贸易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加快推进西藏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以摆脱依赖进口和边贸对西藏发展的束缚,从而使西藏逐步走上了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其战略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责任编辑:史云鹏)
§中外关系研究§
China's Policies towards the Withdrawal of Indian Trade
Agencies in Tibet, 1961-1963
Dai Chaowu
Abstract:The China-India Agreement of 1954 stipulated to open three Trade Agencies in each other's country. In 1961, China began the difficult negotiation with India over the renewal of the 1954 Agreement, especially over the withdrawal of Indian Trade Agencies in Gartok, Yatung, and Gyantse. After Tibetan rebellion and Indian total embargo against Tibet in 1959, China concluded that all Indian trade agencies had served not only as major means of Indian government to control Tibetan economy and border trade, but also as important intelligence strongholds. Tibet Work Committe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ok measures to pressurize Indian withdrawal of all trade agencies in Tibet. The withdrawal of Indian trade agencies in Tibet signals the end of an era in China-India relation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marks the eradication of the Indian economic monopoly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ibet. Furthermor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initiate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ibetan modernization, the strategy to get rid of Tibetan dependence on Indian imports and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traditional pattern to a new model. Tibet Work Committee had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his process.
Key words:The China-India Agreement of 1954, Indian Trade Agencies in Tibet, Tibet Work Committee, China-India relation, trade between India and Tibet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15@ZH009)
作者简介:戴超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241)
中图分类号:K271,D8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6)01-00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