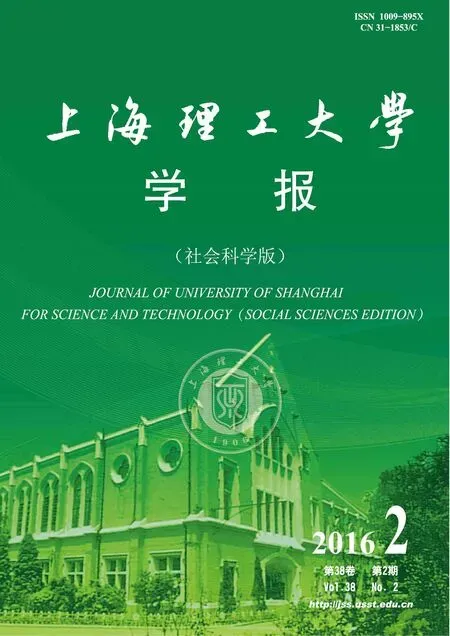从《爵士乐》看莫里森的黑人悲剧美学思想
2016-04-04汪顺来
汪顺来
(常州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常州 213002)
从《爵士乐》看莫里森的黑人悲剧美学思想
汪顺来
(常州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常州 213002)
摘要:《爵士乐》是托妮·莫里森的“历史三部曲”之一,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美国大都会的悲剧故事。爵士乐是黑人音乐中的“宠儿”,吹响了美国新时代的序曲,它将黑人音乐中的浪漫、自由、愤怒、诱惑、死亡等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诱使大都会上演一幕幕新潮、刺激、奢靡、性乱、杀戮的场景。此时,理性已让位于具有酒神精神的非理性,悲剧从音乐中诞生。从西方悲剧美学理论的视角,探讨《爵士乐》中体现的莫里森独特的黑人悲剧美学思想。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爵士乐》;历史背景;西方悲剧美学理论;黑人悲剧美学
《爵士乐》是当代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它取材于《哈莱姆黑人之书》(TheBlackBook)中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位黑人姑娘在派对上被情人射杀,却拒绝指认凶手,并冒着生命危险拖延时间,给情人一个逃跑的机会,最后她死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是一部爱情悲剧,悲剧原因却扑朔迷离。凄婉的情节中弥漫着蓝调音乐的芬芳,又燃烧着爵士乐的激情。莫里森凭自己高超的艺术手法对故事进行了加工,重构了一个发生在纽约大都会的悲剧:在20世纪20年代移民潮的驱使下,一对中年夫妻乔·特雷斯和维奥莱特从美国南方农村移民到北方城市。生活节奏的变化如同爵士乐那样随心所欲,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要么被融入,要么被淘汰。维奥莱特无法接受大都会生活的变奏,仍坚守过去的传统;作为推销员的乔有自己的“美国梦”,他渴望成为一名“新黑人”,很快他就迷恋上大都市。为寻找一个倾诉的对象或“年轻的爱”,他迷上了“时髦少女”多卡丝,而后者终日沉迷于音乐和舞会。由于怀疑女孩的移情别恋,乔在舞会上枪杀了多卡丝,重现了《哈莱姆黑人之书》中悲剧一幕。莫里森不满足情节的单调,她要让另一受害者维奥莱特解开悲剧之谜。维奥莱特大闹葬礼,随后拜访多卡丝的姨妈爱丽丝了解真相,最后是爱丽丝的“爱”让维奥莱特冰释前嫌,挽救了这场婚姻危机。
《爵士乐》是一场黑人女性的悲剧,多卡丝和维奥莱特都是悲剧的受害者。故事情节复杂跌宕,引人深思;人物形象丰满独特,既有叛逆的美少女多卡丝,也有任性的黑妇人维奥莱特,还有温情睿智的姨妈爱丽丝;思想深邃,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精神崇高,将具有酒神精神的爵士乐进行了升华,让爱抚慰受伤的心灵。在《爵士乐》中,莫里森再现了黑人悲剧美学思想的魅力。
一、移民潮的骚动
莫里森将《爵士乐》放置于一个特殊年代一个特殊群体在特定地点发生的特别事件。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经济“飙升的时代”。世纪之交,美国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一战中,美国大发战争财,一举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强国。北方工业发展尤为迅速,发达的工业生产急需劳动力;当时的黑人已是法律上的自由人,因而成为廉价劳动力的首选。移民潮悄然兴起,进军北方是黑人的理想,北方城市中的纽约已经成为国际大都会,有最大的黑人社区哈莱姆。20年代还是黑人音乐的繁盛期,爵士乐风靡大都会,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总之,《爵士乐》里既有爵士乐的喧哗,又有移民潮的骚动。
《爵士乐》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的美国,这一时期是美国移民最活跃的时期,既有欧洲向美国移民的潮流,又有美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转移。在美国,东部向西部,南方向北方的人口迁移见证了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的事实。茫茫人流中有一支黑色移民大军,形成了一股最具特色的洪流。美国黑人离开世代生息的宁静而痛苦的乡村来到嘈杂而陌生的城市,寻求新的生活[1]。
乔和维奥莱特夫妇于1906年就加入了移民大军,他们离开了泰勒尔,登上“南方天空”号的黑人车厢。此时,他们的心情很是复杂,既有“满腔热忱,还有一点害怕,在十四个小时摇篮般平平稳稳的旅途中竟然没有打过一个盹”[2]30。其实,黑人移民有深刻的外因:南方农业机械化使得黑人劳动力大量过剩,因而他们的生活也愈发贫困;同时,北方城市工业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像黑人这样不计较报酬,能吃苦耐劳的优秀劳动力。北方对黑人总是有巨大的吸引力,所以说黑人移民是南方的推力和北方的吸引力合作的结果。另外,种族歧视是黑人移民深刻的内因:奴隶制的废除使黑人变为法律上的自由人,但现实中黑人处处受歧视,上学、就业等各方面都不能享受同等待遇。种族歧视是黑人内心难以去除的阴影。现在,乔夫妇终于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不会再有绿如毒药的帘子把吃饭的黑人和其他用餐者隔开了”[2]31。种族歧视犹如那绿色的帘子,有形或无形中将黑人排除在外,它浸透着毒药,深深地伤害了黑人的心灵。
黑人们怀着美好的憧憬来到了北方城市,心情一下子得到了释放,想尽快忘记南方的一切。乔难以抵抗大都会的诱惑,很快就沉浸在大都会生活的遐想中——奢靡、温暖、吓人,到处都是和蔼可亲的陌生人。对乔来说,南方永远是苦痛,他要努力忘记南方,包括美景。实际上,他“用不了一会儿功夫就忘记布满鹅卵石的小溪,忘记了枝杈垂地的老苹果树,忘记了过去的太阳……”[2]35遗憾的是现实并不如想象那般美好。北方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黑人们挤在大都会的哈莱姆的贫民窟里,生活依旧贫困。
二、爵士乐的喧哗
美国黑人是个有音乐灵感的民族,是美国音乐文化的一支生力军。黑人音乐源于非洲传统,节奏感强,易于表达喜怒哀乐之情。布鲁士是爵士乐的先驱,是一种口头流传而不上乐谱的音乐,曲调忧伤,俗称蓝调乐。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从新奥尔良兴起,随移民潮涌入北方城市。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1901—1971)是当时有名的“爵士之王”。电影和唱片工业的繁荣对爵士乐的风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快爵士乐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性音乐”[3]。
爵士乐的风靡让20世纪20年代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爵士时代”。科技的发展刺激着经济的飙升,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音乐和舞蹈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女性的解放突然间把妇女变成新时尚的宠儿,“摩登女郎”(爵士时代出现的年轻轻佻的少女)应运而生——短裙、烫发、高跟鞋、香烟成了她们不可少的行头[4]。小说《爵士乐》中的多卡丝就是一个典型的“摩登女郎”形象。由于父母死于暴乱,自幼寄养在姨妈家,叛逆的个性使她听不进姨妈爱丽丝的忠告。16岁的她就开始出入各种舞会。大都会的音乐像幽灵一样勾走了她的魂,狂舞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可这个天真的少女就不明白,她“不是大都会的对手,它渗出的音乐每天都在发出恳求和挑战。它说:‘来吧,来作恶吧。’”[2]70爵士乐虽是黑人的东西,但在大都会的土壤下已滋长了罪恶,变得龌龊不堪。爱丽丝觉得美好的音乐已经变味,成了“肮脏下作的音乐。那音乐净教人干不理智、不规矩的事。光是听见那音乐就跟犯法没什么两样”[2]60。然而,大都会的男女老幼陶醉在爵士乐的梦幻世界里,如醉如痴。具有酒神音乐特征的爵士乐,音色优美,它的节奏、力度与和声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受酒神音乐驱使的大都会人暂时忘却了现实的苦痛。尼采说过,悲剧起源于酒神艺术的音乐,即悲剧从音乐中诞生。
三、西方悲剧美学理论
悲剧美学特指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包括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中存在的一切悲剧审美形态。因此说,悲剧美学并不仅指戏剧中特定的悲剧审美形态,小说中的悲剧情节和具有的悲剧精神是悲剧美学表现的特殊的美。
悲剧精神是悲剧审美形态的灵魂。人的悲剧精神的表现形式千姿百态,具有无穷无尽的色彩。作家笔下的悲剧作品正是每个人物个人独特的悲剧精神个体性的物化形态。但个体的悲剧精神又综合成民族的悲剧性,彰显悲剧美学的深刻内涵。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西方传统悲剧美学理论的开创者。他在《诗学》中系统地阐述了悲剧美学理论,包括悲剧的定义,悲剧的六大基本要素: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和歌曲,以及悲剧的接受美学理论:净化说。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制定了“三一律”(时间、地点和情节的统一),奉为圭臬;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剧作家莱辛(Goffhold Ephrain Lessing,1729—1781)指出,悲剧是一首引起怜悯的诗。莱辛的思想丰富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功用的内涵。
传统的悲剧美学理论在20世纪受到极大挑战。以非理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现代悲剧美学理论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受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的意志哲学和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音乐精神的熏陶,发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呐喊,对以理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悲剧美学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悲剧的本质只能被解释为酒神状态的显露和形象化,为音乐的象征表现,为酒神陶醉的梦境[5]。可见,“酒神精神”和“音乐精神”构成了尼采悲剧美学思想的核心。他沿用了叔本华的学说中关于音乐的论述,即音乐是表现形而上的艺术,是意志自身的写照,因而表现着自在之物。由此,尼采得出结论:音乐由于能激发对酒神普遍性的比喻性的直观体验,因而能产生神话,也就是悲剧神话,即用比喻来谈论酒神精神的神话。据此,尼采探讨了悲剧的起源在于狄奥尼索斯(酒神)的崇拜和产生幻觉的歌队音乐精神,也即酒神精神。尼采的现代悲剧美学理论对后世的存在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和荒诞派戏剧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四、莫里森的黑人悲剧美学思想
莫里森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西方悲剧美学理论和尼采的现代悲剧美学理论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巧妙的糅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黑人悲剧美学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性的内容包括情节、性格和思想。情节是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格是人物品质的决定因素;思想是证明论点或陈述真理的话[6]。尼采则声称悲剧精神源自酒神精神和音乐精神的升华。莫里森综合了二者的思想,将悲剧性的内容注入黑人性元素,将悲剧精神上升到民族性的关怀,使得她的悲剧思想更具深度。
(一)独特的人物
莫里森笔下的悲剧人物是清一色的黑人女性,是弱者中的弱者。人物性格各异,有逆来顺受者,有大胆叛逆者,也有孤僻怪异者等,但她们都要承受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力,是强权下的“他者”。正是这些黑人女性见证了黑人悲怆的历史。如《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刻画的可怜可悲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她相貌平平,逆来顺受,却总遭人白眼和母亲的鄙弃,甚至遭生父的强暴,而她将这一切归咎为自己缺少一双蓝眼睛,最后在一连串的打击下走向崩溃。在《所罗门之歌》中“奶人”的母亲露斯是个性格怪异的女性,她饱受丈夫的感情折磨,不得不将爱放在奶孩子上面,“奶人”的绰号由此而来;甚至常到公墓躺在父亲的坟上,来证明自己曾被爱过。这种生不如死的感受反映了黑人女性心灵的凄苦。
与前两者女性性格迥然不同的是《爵士乐》中出现的叛逆少女多卡丝,她幼年曾目睹父母死于暴乱的惨象,此后便寄养在姨妈爱丽丝家。姨妈的关爱怎么也无法弥合她童年的阴影,加上20年代社会大环境的诱惑,多卡丝叛逆的个性迅速膨胀。16岁那年是她第一次抛开姨妈管教的“越轨之举”,她与好友费丽丝轻而易举地加入了寻欢作乐的行列。“费丽丝帮着她散开了耳朵后面的两根发辫,把口红涂在她的指甲上,她的嘴唇上已经涂过了。她把领子掖到下面,衣着就显得更成熟些了……多卡丝的舞跳得很好——不像有些人那么快,但她跳得很优雅,尽管鞋子令人难堪;另外,她跳得非常煽情。”[2]68初涉舞会让她尝到了疯狂欢娱的滋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她成了舞会的常客。乔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她缺失的父爱,所以她与乔的恋情带有更多的游戏成分。这位崇尚性解放的“摩登少女”很快就迷乱在情欲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最后倒在乔的枪口下。
莫里森笔下的悲剧人物专注于黑人女性这个特殊群体,其中有黑人女孩,也有黑人母亲。她们的悲剧成了黑人女性群体的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人性格是内因,社会环境和家庭遭遇是不可忽视的外因,但本质上的是由于缺失爱,包括父爱、母爱和友爱等。正如莫里森说过,她写爱或爱的缺失。她的创作实践证实了自己的承诺。
(二)复杂的情节
莫里森对悲剧情节的构思既有对现实的模仿,又超越了现实的局限,再现了人物在极限生存条件下的心理张力。暴力、杀戮、乱伦等情节在莫里森小说中屡见不鲜,让读者思考情节背后人物的心理张力。如《天堂》中鲁比镇的九名黑人男子血洗女修道院的暴力事件:“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对剩下的人他们可以从容下手。没必要匆忙离开。……他们一共九个人,比他们奉命要蹂躏或杀掉的女人多一倍,何况他们还随身携带可满足任何需求的用具:绳索、一个棕榈叶十字架、手铐、催泪瓦斯和墨镜,当然还有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枪支。”[7]鲁比镇的黑人由于无法接受这个黑人社区的变化,将罪恶的根源归于邻近的女修道院,悍然发动突袭,杀害了修道院所有无辜的女人,而这些女人由于不忍种族和性别的压力才走到一起的。修道院对她们来说就是天堂,可是天堂也不安宁,屠杀随时光临。读者可透过情节思考黑人在种族性别双重歧视下扭曲的心理。此外,乱伦的情节在莫里森的小说中也经常发生。如《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遭生父的强暴;《所罗门之歌》中“奶人”对哈恰尔(彼拉多的外孙女)的始乱终弃;《爱》中比尔·科西娶孙女的同学希德续弦等等。乱伦的背后揭示了黑人男性压力下的扭曲的心灵、缺失的爱和矛盾的赎罪心理等。
《爵士乐》中乔·特雷斯生下就被人收养。母亲是个“疯女人”(森林中的野姑娘),屡次找寻不得踪迹;父亲到处游荡。童年的不幸使得乔渴望得到爱,强烈占有爱。来到大都会后,他经受不住诱惑,逐渐冷漠了夫妻感情,年过半百的他爱上了多卡丝。这段近乎乱伦的恋情是出于荒唐的自由的选择。乔渴求得到年轻的爱,多卡丝希望得到失去的父爱;乔想占有爱,多卡丝要选择爱。爱的动机上的差异潜伏着悲剧的诱因。暴力再次上演,乔将多卡丝射杀在舞会上。
(三)深邃的思想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思想是证明论点或讲述真理的话。思想是悲剧的深层内容。莫里森小说的悲剧思想一方面在于它的民族性,她的小说关注的是美国黑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尤其是对黑人女性的呵护,几乎每部小说都是围绕黑人女性的境遇展开的;另一方面在于悲剧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即爱的救赎。爱的主题是贯穿她十部小说的主线,她的第八部小说还与“爱”同名。爱是抹平伤痕、拯救罪恶的良药。
《爵士乐》中多卡丝被杀后,维奥莱特大闹葬礼,并造访爱丽丝(多卡丝的姨妈),企图揭开多卡丝的身份之谜和寻找乔移情别恋的原因。爱丽丝回答她:“用你所剩的一切去爱,一切,去爱。”[2]119爱丽丝的一句话点醒了维奥莱特的心智,她开始懂得爱才是打开心结的钥匙,是疗伤的药。乔射杀多卡丝后,负罪感折磨着他。当问及杀人的原因时,他说:“害怕。不知道怎样爱一个人。”[2]227由于爱的迷惘,乔自酿悲剧,成了罪人。好友费丽丝转告他多卡丝临死前的话:“只有一个苹果。只有一个。告诉乔。”[2]227多卡丝的遗言解脱了乔的恐惧和迷惘。话中的“苹果”暗指“珍贵的爱”,她和乔都是彼此眼中珍贵的苹果/爱,所以她至死也不会出卖情人。是多卡丝的爱荡涤了乔的罪。爱的救赎是莫里森悲剧思想的灵魂。
(四)崇高的精神
根据尼采的悲剧理论,悲剧精神是酒神精神和音乐精神的升华。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酒神精神使我们相信生存的永恒乐趣。只是我们不应在现象中,而应在现象的背后,寻找这种乐趣我们应该认识到,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如何必然准备好走向死亡,我们不得不看到个体存在的恐惧——然而却不应该吓得发呆,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会短暂地把我们拽离形态万变的喧嚣。”[8]尼采的悲剧理论中,酒神精神使人们得到“醉”的快感,作为形而上的酒神音乐引起了恐惧和惊骇,慰藉是短暂的,死亡是永恒的,因此悲剧是必然的。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喧嚣的“爵士时代”。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在《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Gatsby,1925)中描述了那个时代奢华的场景,因而成为“爵士时代的代言人”。但是繁华的表象背后孕育着危机——精神的萎靡、道德的沦丧和美梦的破灭。盖茨比的个人悲剧印证了那个时代的悲剧。莫里森在《爵士乐》中重书了那个时代的奢华景象,只不过她把场景移向大都会的黑人聚居区哈莱姆,聚焦于黑人移民群体。这些从农村逃难来的黑人也经不起酒神音乐的陶醉,卷入了时代狂欢的漩涡中:“一切终于都欣欣向荣了!在办公室里,在大厅里,无所事事的人们憧憬着未来的计划、桥梁和迅速对接的地铁列车。A&P雇佣了一个黑人职员。长着大粗腿和粉红色猫舌头的女人们把钞票卷成绿色纸筒存起来,然后大笑着搂着一团……”[2]5莫里森用唯美的语言勾勒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人们无所事事,生活在梦幻中,金钱是他们唯一的追求。繁荣的背后潜伏着危机,悲剧的脚步在逼近。
尼采曾断言,悲剧从音乐中诞生。音乐是美国黑人灵魂深处的声音。他们通过音乐来诉说内心的苦与悲、爱与恨、希望与绝望。将音乐与文学联姻是美国黑人小说家的天赋。拉尔夫·埃里森、佐拉·尼尔·赫斯顿和兰斯顿·休斯都善于将布鲁斯的节奏和伤感的曲调切入到作品中,使其更具独特的黑人性,以颠覆白人文学传统的权威。莫里森继承了前辈的传统,作品中的音乐色彩更浓。在访谈中,她这样评述爵士乐的魅力:“当你听到黑人音乐——爵士乐的前奏时——你意识到黑人们在谈论别的事情,他们在谈论爱,谈论失落。但在那些抒情曲里却有着崇高和满足。黑人们从来没有幸福过——总是面临离别、失去爱情、感情和性爱的危机,最终还是失去了一切。但这所有的一切并不重要,因为是他们的选择。选择你爱的人才是大事。爵士乐强化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爱的空间是用自由置换的。”[9]
莫里森十分推崇爵士乐,不仅在于爵士乐具有即兴、应答、互动的特点,而且在于爵士乐表达了崇高的主题:爱的空间和自由的选择。古罗马批评家朗吉弩斯认为,崇高是高尚灵魂的回音。只有高尚的作者才能写出崇高主题的作品。莫里森的小说超越了单纯的善与恶的探讨,广泛触及黑人灵魂深处的东西,即爱的空间。这个空间到底有多大,如何守护它是莫里森小说中永恒的主题。
五、结束语
《爵士乐》弹奏出20世纪20年代移居哈莱姆的美国黑人内心深处涌动的声音,让人仿佛听到了浪漫、愤怒、诱惑和死亡等音符在跳跃。时而低沉,时而高亢,把美国黑人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宣泄得淋漓尽致。《爵士乐》以爵士乐命名,既点明了作品的音乐性,又突出了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性,从而主人公的悲剧也就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莫里森的黑人悲剧美学关注的是黑人女性的悲剧,情节上复杂多变,暴力、乱伦、情爱等交织在一起,但是爱的救赎是莫里森小说悲剧思想的灵魂。莫里森将爵士乐、历史和美国黑人的情与欲融合在一起,表达自由后的黑人迁移大都会后遭遇的窘境:为了逃避贫困而大迁移,却卷入难以自拔的情感漩涡。为了解开纠缠美国黑人的心结,莫里森开出了一剂良方——爱的救赎。爱是灵魂深处最宝贵的东西,是荡涤罪恶的良药。
参考文献:
[1]余志森.美国通史(第四卷):美国崛起和扩张的时代,1898—192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18.
[2][美]托妮·莫里森.爵士乐[M].潘岳,雷格,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
[3][美]卡罗尔·卡尔金斯.美国文学艺术史话[M].张金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4.
[4]王毅.美国简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155.
[5][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11-12.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美]托妮·莫里森.天堂[M].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2.
[8][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杨恒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00.
[9]Schappell E.Interview with toni morrison[M]∥Plimpton G.Women Writers at Work: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2nd reved.New York:Modern Library,1998:365.
(编辑: 巩红晓)
Morrison’s Black Tragic Aesth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azz
Wang Shunla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zhou 213002,China)
Abstract:Jazz,as one of Toni Morrison’s “Historical Trilogy”,tells a tragic story happening in New York,Harlem in particular,in 1920s.As a “beloved baby” of the black music,Jazz initiates the overture of American new era.Jazz finds its full expression in all elements of black music:romance,freedom,fury,temptation,death etc.Modern,stimulating,sexual,and violent scenes are displaying on the stage of New York.Rationality has then given way to irrationality with Dionysus Spirit,which marks the birth of tragedy,however,Jazz has awaken Afro-Americans’ repressed impulsiveness,thereby finding their ego in Harlem.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explore Morrison’s unique black tragic aesthetics in Jazz in the view of Western tragic aesthetic theory.
Keywords:Toni Morrison;Jazz;historical background;western tragic aesthetic theory;black tragic aesthetics
收稿日期:2015-09-01
作者简介:汪顺来(1970-),男,副教授。研究方向: 美国少数族裔文学。E-mail:john0159@126.com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16)02-0149-05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16.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