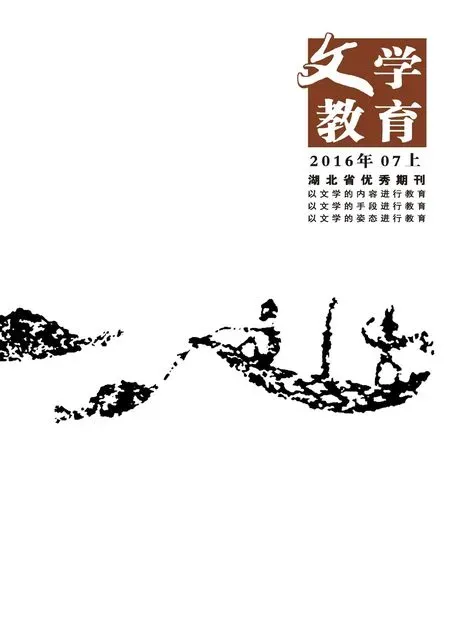浅论《耶路撒冷》的乡愁书写
2016-04-04吴在晶
吴在晶
浅论《耶路撒冷》的乡愁书写
吴在晶
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描写了一群出生于二十世纪70年代、介于青年与中年之间的故乡出走者,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或经济能力,但却始终怀着无法开解的乡愁,这乡愁的意义超越了“70后”的生活经验,是中国社会转型之后新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甚至“90后”们普遍面临的困惑。
《耶路撒冷》“70后” 乡愁
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以初平阳卖房留学及其为《京华晚报》写的专栏为两条主要线索,围绕“景天赐”一章展开所有冠以人物名字的章节,前后对称,彼此之间又各有联系,构成一个层层连缀的放射式蛛网结构;主人公们的际遇也以故乡为一个原点:出于对不光彩往事的规避心理、对未来梦想与人生的摸索追寻,这群“70后”选择出走,逃离了故乡;如愿在北京这个大城市的代表安顿下来以后,他们处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呼吸困难,于是开始怀念故乡、追忆往事,渴望得到心灵的救赎;当故乡的回忆开始遭到毁坏和改造时,他们又被集中到故乡这个原点,可惜此故乡非彼故乡,以初平阳为代表的一批人,其精神困惑与伤痛并未完全得到解决,去往遥远的“耶路撒冷”可视作寻找新的心灵故乡。从故乡到异乡再到故乡的“离去-归来”模式中,“70后”们的当代乡愁愈发突出,无处安放的乡愁最终成为城市中的游子们共同的精神伤痛。
一.到世界去——追寻与逃离
《耶路撒冷》中的“70后”们在长大后都离开了花街,在外面广阔的世界寻找自己的安身之处,“‘到世界去’已然成为年轻人生活的常态”[1],这十分贴切地反映了当下青年的现实情况:一方面,故乡在某种程度上隔绝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瞬息万变,充满无限可能,而故乡的进化速度相对缓慢,新成长起来的一代“70后”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领略到外面世界的精彩——“北京不宜人居,但它宽阔、丰富、包容,可以放得下你所有的怪念头”[2],为了拓宽自身生命的可能性,他们选择“走出去”、走出花街,例如杨杰,他最终到北京当起了水晶生意的老板;再如初平阳,他大学毕业后回到淮海教书,却因为忍受不了枯燥琐碎的生活,考研去了北京。
另一方面,故乡的“滞后”,以及儿时犯下的错误,使长大成人的游子们产生了规避心理,最亲密、最纯净的“故乡”同时又是“原罪”的起点,在《耶路撒冷》中即表现为各位主人公对景天赐的讳莫如深:景天赐是秦福小的弟弟,小时候在运河里游泳时被闪电击中而精神失常,在受到一次刺激后自残致死。景天赐的死主人公们都负有责任:是易长安鼓动天赐在闪电袭击的运河上继续比赛游泳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杨杰明知不该,还是送了已经精神失常的天赐一把手术刀;秦福小眼睁睁看着弟弟自残,错过了抢救时机;初平阳是目睹天赐自杀而逃走的胆小鬼、秦福小的“帮凶”。儿时的单纯已经演变为最不可饶恕的恶,嫉妒、懦弱、虚荣……原本微弱的恶意促使了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死亡,他们不得不逃离“犯罪现场”,在繁华的城市文明中寻找心灵的慰藉以求忘却,这时对于故乡的逃离已经成为了对自身的“恶”的逃离、对“善”的追寻。
因为追寻理想、逃避故乡所代表的“原罪”而逃离故乡,这是《耶路撒冷》中的“70后”主人公们经历的第一个阶段,相较现代城市中的游子们出走的现实原因,作者放大了一个“原罪”的因素,凸显了现实出走者们对于故乡的落后与束缚的恐惧,加上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共同导致了从故乡出走的行为。远离了生养自己的双亲与故乡,现代游子们心中的负罪感与追忆、思念交织在一起,这也是乡愁无法开释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向故乡的靠拢以至回归
成功“逃出”故乡、初到城市的兴奋和喜悦慢慢消失后,年轻人们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像理想中那么完美。空气的污染、物质的严苛、人际的疏离等等,多少都打击了年轻人们的热情。
尽管存在着心理落差,但《耶路撒冷》中的“70后”主人公们大多都仍抱持着理想主义,与冷漠的现实交战:初平阳辞掉了枯燥的工作,毅然两次跨考北大;易长安从当乡村教师到办假证都随遇而安,在被警察追逐时仍要住最好的酒店、与陌生女人做爱,无时不贯彻他的生活美学;杨杰变成了一个不事应酬的商人,修身养性祈求内心的平静;秦福小只因男朋友吕冬对于“私奔”的爽约,在外漂泊了十几年,未婚单身却领养了一个孩子,只因为他长得像自己死去的弟弟。他们的理想主义代表了被现实挤压的年轻人们美化生存的愿望,有这样一群并不随波追流的年轻人,在尽可能地坚守着自己的精神阵地。
在强大的社会洪流中坚守原则是异常困难的,年轻人们进行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仍是在
《到世界去》这个专栏中,作者写道:“我们在北京的天桥上打着被污染的喷嚏,然后集体怀念运河上无以数计的负氧离子……但是怀念完了就完了,我们继续呆在星星稀少的北京。”[3]他们的乡愁是理想主义式的,在严酷冷漠的现实中,故乡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质朴、真率、包容性的存在,故乡有最亲密的亲友和故人,有最难以忘怀的回忆和往事……虽然怀念故乡,但是受到现有的地位、成就、家庭关系等种种限制而无法回归。但如果现实对人的挤压达到了一定程度,不仅会产生向故乡靠拢的情感依恋,甚至会出现回归故乡的行为。作品中的例子是初平阳的前女友舒袖,她不顾父母的反对随初平阳北上,在清苦与寂寞中支持着恋人,最终却还是不堪现实的压力回到故乡,与他人结婚生子。《耶路撒冷》中其他主人公们的回归则与景天赐息息相关,得知初平阳家的大和堂要卖掉,秦福小终于决定返乡,打算为天送买下这所天赐曾经最喜欢的“一推开窗户就会看到运河”的房子;易长安在逃亡路上仍决定回乡,是因为要为“兄弟·花街斜教堂修缮基金”捐款签字。花街是他们的原点,天赐是他们的“原罪”,还是出于无法舍弃的乡愁与旧情,他们向故乡靠拢,甚至彻底回归。
尽管《耶路撒冷》中的人物纷纷先后回归故乡,但这只是一个小说中的偶然事件,现实中许多从故乡出走的“70后”、“80后”、“90后”仍然留在城市,但他们的乡愁和初平阳等人的乡愁一样,都包含了了现代社会现实对人的挤压,在这个过程中,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市游子们体会到了理想与乡愁的双重失落,对自身的价值与定位也产生了摇摆和困惑。
三.再次逃离——故乡的边界与外延
在回归魂牵梦萦的故乡的过程中,新的问题又开始出现:一是此故乡非彼故乡,故乡的异化导致“游子”们回归后,产生心理上的困惑与落差,变成了有家难回、故乡难归的状态;二是此时非彼时,自身的进化超越了故乡的包容范围,自身与故乡格格不入。这两种问题是相伴出现的,都让新归故乡的年轻人们感到无“家”可归、无“乡”可归。《耶路撒冷》中有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专栏故事《夜归》:主人公在城市成家立业之后,久违地带妻儿回家过年,面包车却在大雪中抛锚了,年迈的父亲从村里赶着牛车回来救援,拉动着后面的面包车回家,构成了一副奇异的景象。在这个故事中,故乡的变化让归家者产生了陌生感,但是这种变化还是止步于较低水平,土路让车抛锚,故乡承载不了已经完全蜕变、面目全非的归家者,摆出拒绝的姿态。虽然血肉联系还在,重重波折之后还是回了家,但是这里已经不是最终归宿,回到城市是必然的,甚至他们要走得更远,就像初平阳要去往耶路撒冷一样。
城市本非精神的原乡,故乡也今非昔比,那么出走者们该何去何从呢?《耶路撒冷》中的初平阳新寻了一个理想乡——“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只是初平阳要去留学的地方,自从小时候听到目不识丁的秦奶奶对着圣经念出“耶路撒冷”奇妙的发音,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就深埋在心底。“耶路撒冷”对初平阳来说,是心灵上一直向往的第二故乡,它承载了初平阳儿时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承载了遭受“文革”摧残的妓女秦环(秦奶奶)的自赎与慰藉,耶路撒冷作为宗教圣地所具有的神秘性与包容性,以及它所承载的难忘回忆,使其成为了初平阳心灵的自赎之所。
徐则臣谈到《耶路撒冷》中的乡愁时曾说:“乡愁更像是一个前现代的概念,现代、后现代了好像不讲乡愁了。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度来说,大家还是要谈乡愁,还是要谈一种归宿,还要谈精神安妥。”[4]在当今社会,随着现代文明的扩张,不同于父辈出走者们普遍的深厚的乡愁情结,越是年轻的故乡出走者,其乡愁就越是隐性化和泛化,而“70后”处在夹缝中,既怀着浓浓的乡愁,又充满了对未来可能性的开掘欲望,他们的乡愁即使回到了故乡仍未得到开解,自身价值和精神安定上的问题尚待解决,这促使他们继续追寻新的心灵故乡。这时,乡愁促使人追寻的对象已经不只是生养自己的地方了,而是更广阔的天地,“故乡”这个词也由此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内涵和意义,成为一个模糊的能指,乡愁的对象和内容发生了变化,变为对最后精神之所的追求。
《耶路撒冷》呈现了一批抱持理想与情怀的年轻人,他们在繁华而冷漠的大城市中,保留着一种似乎不合时宜的乡愁情怀,保留着关于故乡的回忆与良知。抛弃故乡带来的负罪感,以及在城市文明中理想碰壁的失落,是当代乡愁存在的主要原因,在“离乡-归乡-再离乡”的摇摆与反复背后,“70后”出走者们对自身的价值有一个终极追问,物质安妥并不是他们的终极追求,追求精神安妥才能暂时缓解他们的价值焦虑,这是当代的思乡病,是物质挤压下精神流浪者们对现实的反抗与逃离、坚持与追寻,在这点上,不只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代的理想主义者”的“70后”们如此,在现代文明高速运转的新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们同样也是如此。尽管回归与否都会有伤痛与困惑存在,但对生命广度和自我价值的追求一直都存在,泛化的乡愁情结促使着人们寻找最终的精神家园。
[1]徐则臣.《耶路撒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3,见第28-29页、30页、148页。
[2]《徐则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耶路撒冷》,见中华网,http://culture.china. com/reading/literature/11170682/201510 12/20543565_1.htm l。
[3]梁鸿.《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花街的“耶路撒冷”》.见中国作家网,http://w w w.chinaw riter.com.cn/bk/2014-04 -30/75696.htm l。
[4]李燕君:《隐喻的故乡与泛化的乡愁——评徐则臣的<耶路撒冷>》[J].名作欣赏.2015(35)。
(作者介绍:吴在晶,湖北大学2013级汉语言文学国家基地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