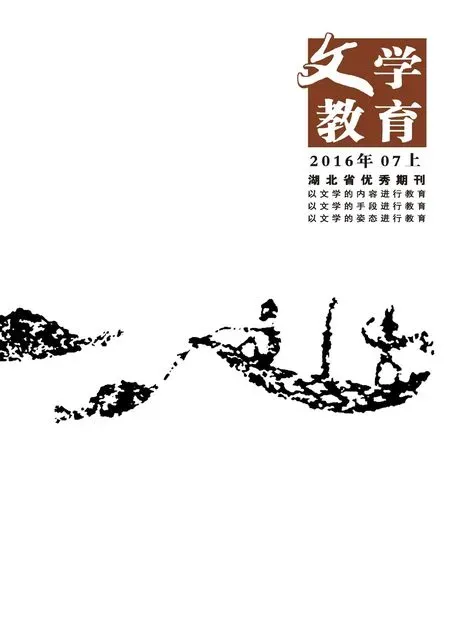《蝴蝶飞》中的姐妹情谊及与《紫色》的比较
2016-04-04郭海平
谷 邱 郭海平
《蝴蝶飞》中的姐妹情谊及与《紫色》的比较
谷 邱 郭海平
赵玫的《蝴蝶飞》以一对底层姐妹花为主线,娓娓道来了远离故乡的两只“蝴蝶”如何在城市中相依为命,最终步入了香消玉殒。同样是以一对姐妹花为主线,爱丽丝·沃克《紫色》中的黑人女主人公茜莉却在姐妹们的团结一致与帮助下,幸运地走向了自我实现。对比两篇小说中的“姐妹情谊”,从《紫色》中找寻那条让“蝴蝶”走向自由与新生的路。
赵玫 《蝴蝶飞》 艾丽斯·沃克 《紫色》 姐妹情谊
《蝴蝶飞》是作家赵玫的中篇小说,原载于《上海文学》2014年第6期,随后被《小说月报》2014年第8期转载。作品描写了物欲横飞的时代背景下底层人民的艰难生活,主人公巾帼同好姐妹青娥被迫远离故乡,在城市里浮萍般飘泊,最终被吞没的故事。爱丽丝·沃克的《紫色》借助书信体的形式,通过茜丽姐妹的信诉说了她们从苦难阴影中摆脱出来的成长历程,同时也讲述了生活在多重压迫下的黑人妇女,以“姐妹情谊”为基础,合成一股力量,勇敢地踏上了女性解放的道路。“姐妹情谊(sisterhood)这一术语源于西方传统女性主义运动,它最初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出现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它指的是,在父权社会体制的压迫及其在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压制下,广大妇女在潜意识中形成的一种情同姐妹,互助互爱的情谊,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团结起来反抗共同的压迫。”[1]“姐妹情谊”将黑人女性团结起来,给她们战斗的力量,给她们建立了一个逃离种族主义与父权制压迫的避风港,正如嵇敏指出:“‘姐妹情谊’是广大黑人女性谋生存、求发展的精神、物质的双重保证。它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集体力量形成巨大的推动力。”[2]在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姐妹情谊也是她们孜孜不倦建构的主题之一,其中赫斯顿在《她们眼望上苍》中讲述了珍妮与费奥比之间通过语言与心灵的沟通来唤醒姐妹意识;爱丽丝.沃克的《紫色》表达了女性之间通过姐妹联盟来反抗父权制及种族压迫,齐心互助走向自我实现;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里森在《天堂》中体现出姐妹情谊超出了血亲、肤色、种族、阶级以及个体差异性,女主人公们通过姐妹之间的爱建构起一个属于她们的天堂。国内,“姐妹情谊”同样是女性作家炙手可热的主题,“五四”时期,丁玲的《在暑假中》描写了一群年轻女教师之间的“同性之爱”;80年代,张洁的《方舟》讲述了三位女性在男性的压迫下互帮互助,给予彼此真诚与关怀;90年代林白的《瓶中之水》诉说了女主公二帕与意萍之间的依恋之情,她们之间的情谊已经成为彼此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姐妹情谊”在文学作品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女性团结起来抵抗压迫、共同走向自我实现、走向女性解放永远是“姐妹情谊”不变的初衷与坚持。
一.同生与共灭
《紫色》中茜莉与莎格的姐妹之情带领两人走向了新生,然而《蝴蝶飞》中的巾帼、青娥虽然情谊深厚,这对姐妹花却没能走向光明的未来而是落得玉碎香残的结局。茜莉与莎格在彼此困难的时刻陪伴左右,不离不弃,反观巾帼、青娥二人,青娥倾力帮助巾帼,巾帼虽心系青娥,然而在青娥危难时却没有陪伴其左右助她走出困境,两姐妹先后走向灭亡,“姐妹情谊”对于被压迫在底层的女性而言,像是生命的源泉,不可或缺。《紫色》中,茜莉是黑人女性,在家受继父欺凌,出嫁受丈夫与继子欺辱,挑起生活的重担,承受肉体与精神的摧残,浑浑噩噩,像“骡子”[3]一样艰难度日。直到莎格的出现,茜莉在她的帮助下开始一步步弃绝“骡子”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莎格来到茜莉家养病时,奄奄一息,茜莉无私照顾,最初,莎格怀疑茜莉的虚情假意,但在茜莉的持之以恒下,莎格重新站立起来并深受感动,决心全力帮助这个无助的人,本应是情敌的两人却心心相惜,结起了深厚的姐妹情谊。莎格带领茜莉慢慢找寻自我,并助她拿到了茜莉亲妹妹聂蒂写来的信,读完信后,茜莉开始了反抗之路,出于愤怒,她怀有杀死丈夫X先生的冲动,在莎格的劝说与陪伴下,走出了这个将会毁灭自己的念头。随后,莎格将茜莉带回自己家中,给予茜莉物质与精神上支持,最终在莎格的帮助下,茜莉将自己的创造力发挥出来,开启了制作裤子之路,实现了自我独立与自我实现。莎格与茜莉姐妹俩陪伴彼此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携手走向了新生。
《蝴蝶飞》中,青娥每每拯救巾帼于危难之中,然而当她同莎格一样生病奄奄一息时,巾帼却未能倾力照顾她,任由她拒绝治疗走向灭亡,随后,巾帼沉浸在悔恨中无助时,已没有了青娥的帮助,最后遭遇车祸而亡。巾帼、青娥为了支撑家里的经济负担,开启了进城之旅。青娥的父亲吃喝嫖赌欠下的债落到了她的身上,
进城后,青娥进入了青楼,随后巾帼的父亲重男轻女,将弟弟上学的重担压在了巾帼的肩上,她不得不投靠青娥,并在青娥的帮助下找到了流水线上的工作。巾帼再一次投奔青娥是因她开启了追梦旅程而无法保障生活走投无路时。巾帼在一次联欢会上的演唱得到了老板的表扬,并鼓励她带头组建合唱团,然而,“合唱团”被女上司歼灭在摇篮里,巾帼被迫离职。失业的巾帼反而带着豁出去的决心,开启了圆梦的旅程,她去酒吧及酒店应聘歌手,然而现实总比想象中艰难,就在她走投无路之时,青娥的电话又将她带离绝境,此时的青娥换到了海滨的“红楼”,成了那里的招牌,青娥将巾帼安顿在自己身边,同时带着巾帼到海滨酒楼一家家应聘,缴纳一笔笔试唱费,在青娥的帮助下,巾帼开始在“五层楼”上班,她模仿周旋并一夜走红,然而,追梦路途是残酷的,周边餐馆群起攻之,在一阵恐吓与威胁下,女老板妥协了,解雇了巾帼,但在女老板的推荐下,巾帼进入了“武町之恋风”,抚三弦,唱《樱花》,如鱼得水。然而就在巾帼红火之时,青娥却病入膏肓,在巾帼搬离青娥住处时,青娥已经病了,她拒绝告知医生自己得了艾滋以致病情逐渐恶化,虽然巾帼知道青娥孤独无依,除了在她转院之前去看望她并拒绝收下青娥的存单,巾帼一直没有前去探望。两人最后一次对话是青娥打给巾帼的一个电话,当巾帼去郊外的隔离医院探望青娥时,只探到了遗物与骨灰,医生说青娥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她将青娥的骨灰撒在故乡的麦田之后,回到城里,却发现自己已慢慢地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在雨水的淋漓下,她反思自己“我曾经变得自私与冷漠,并不是这个世界所致,而是我的内心,已慢慢地,没有了爱……慢慢地,唱歌变成了一场噩梦……无论她怎样装扮成艺术家,都会被认为是赚钱的工具”(56-57),巾帼无神的漫游在街上,死于车祸。巾帼、青娥同茜莉姐妹一样受到生活的压迫,然而由于巾帼的自私,两人未能像茜莉与莎格一样携手走向新生。
二.同盟与散沙
纵观《紫色》,小说中黑人女性最终团结一致,形成联盟,互帮互助,共同面对困难,然而,《蝴蝶飞》中的女性,在面对压迫时,软弱与自私,弃同伴与不顾,像一盘散沙一样永远无法筑起一座避风港。《紫色》中,女性之间是团结一致,互帮互助的,这种姐妹情谊除了两姐妹或小范围以外,还包括书中所有黑人女性的同盟。书中,茜莉与莎格的患难与共,茜莉与儿媳索菲亚之间的真诚以对,茜莉与妹妹聂蒂、索菲亚与姐姐们之间的同脉姐妹之情等,这些双边与多边姐妹情谊帮助她们度过了所有困难。同时,书中黑人女性不仅仅是小范围的互帮互助,而是团结起来筑起一座避风港,为姐妹们遮风挡雨,当白人种族压迫同胞姐妹时,所有黑人女性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团结一致对抗压迫。索菲亚因同白人冲突而陷入困境时,茜莉、斯贵克等黑人姐妹们没有置她于不顾,而是想方设法营救,她在牢里期间,茜莉、斯贵克两人无私照料她的孩子,当她回来后,大家亦给予她家的温暖,让她感受到姐妹情谊的强大与关怀。反观《蝴蝶飞》中的女性,巾帼、青娥仅有彼此一个姐妹,书中其他女性缺乏团结精神与反抗意识,她们除了软弱,也许还有正如孙桂荣所指出的“女性之间总是因为社会角色、包括身份、地位、名声的悬殊而彼此疏离,还会因为女性才智、气度、品貌之间的或明或暗的比视而彼此轻视仇视”。[4]巾帼流水线上的女上司刁难她,然而“周围的姐妹心知肚明,却谁也不敢得罪那个骄横的女领班”(42),巾帼不得不离职另求它路,当巾帼演唱周旋而为“五层楼”招来慕名而来的客人后,海滨其他酒楼群起而攻之,最终女老板未能同巾帼共同面对,为保平安辞退了巾帼,她在辞退信中说道“我们从来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根本就无从控制自己的人生……”(50)。青娥所在的青楼,老板娘刻薄,其他姐妹人情冷淡,未能建立惺惺相惜的姐妹情谊,虽然她因为豪爽受到客人与老板的青睐,在“红楼”颐指气使,然而一旦她不能失去头牌后,她难逃被遗弃的命运,就像巾帼所想的“她知道像青娥这样的女人在这种地方病倒后,是不会有什么人来照顾她的”(48),青娥一个人在隔离医院度过了余生,死后在巾帼来之前无人前来询问,像被遗弃的荒草。《蝴蝶飞》里没有《紫色》中的姐妹同盟,她们或自私或懦弱,巾帼、青娥没有茜莉与索菲亚一样幸运拥有背后的避风港。
《紫色》中的黑人女性受到种族与男性的双重压迫,《蝴蝶飞》中来自底层的女性受到社会与重男轻女思想的双重压迫,同样是无助的,然而,她们却未能像《紫色》中的黑人女性团结一致,形成联盟,为自己及姐妹们建立一座避风港,所以她们的结局未能像茜莉一样幸运地走向自我实现的道路,“姐妹情谊”于压迫在底层女性而言,是生命的源泉,无比珍贵与重要,《紫色》中黑人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值得她们借鉴,团结一致,共筑一个底层女性避风港,携手走向自我实现。
[1]寇艳.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姐妹情谊探析[D].江西:南昌大学,2013:9.
[2]嵇敏.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概观[J].外国文学研究,2000(4):62.
[3]佐拉·尼尔·赫斯顿·他们眼望上苍[M].王家湘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29.
[4]孙桂荣.“姐妹情谊”及其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展开方式[J].女性文学研究(5):55.
[5]赵玫.蝴蝶飞[J].小说月报,2014.
[6]艾丽斯·沃克.紫色[M].杨仁敬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
[作者介绍:谷邱,武汉轻工大学研究生;郭海平(通讯作者),武汉轻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