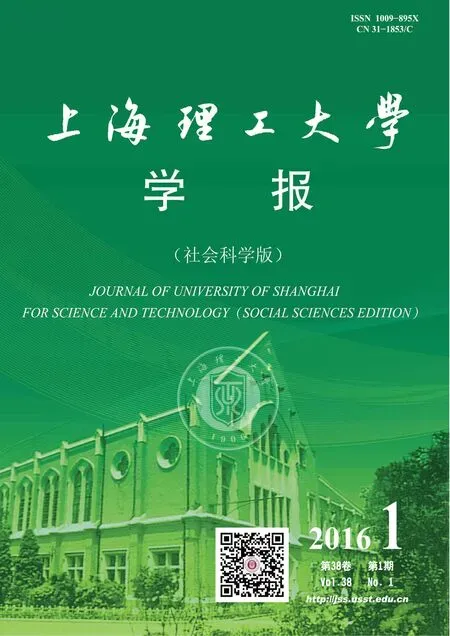论辛西娅·欧芝克《大披肩》的女性大屠杀叙事
2016-04-04赵娜
赵 娜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芜湖 241002)
论辛西娅·欧芝克《大披肩》的女性大屠杀叙事
赵娜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芜湖 241002)
摘要:在大屠杀言说和不可言说的争论中,欧芝克创作了影响广泛的大屠杀作品《大披肩》,受到各类读者认可。运用叙事学方法和大屠杀相关研究成果探讨欧芝克的女性大屠杀叙事特征,分析欧芝克选取的历史原素材,阐释运用的叙事模式实现的完整叙事,解析母亲视角的特殊意义,提出女性人物的大屠杀经历将从性别视角突出女性历史性话语,映射犹太女性遭受的多重迫害,从母亲视角深刻体悟大屠杀对个体以及犹太民族造成的创伤。
关键词:女性;大屠杀;叙事;母亲视角;辛西娅·欧芝克
大屠杀文学是美国当代犹太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反映二战时期欧洲犹太人遭遇的种族屠杀,面临的生存危机,以及战后的创伤生活,它是对人类历史灾难的记忆、认知与反思。研究者坚信“大屠杀含有对今天所有人有益的教义”[1],尤其关注欧洲和以色列男性作家的作品。S·莉莲·克雷默指出批评家对美国作家及女性作家的大屠杀作品研究不足[2]1。与国外相比,国内更聚焦于美国犹太作家的研究,包括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萨克·罗森菲尔德、伯纳德·马拉默德等。在女性大屠杀文学受到较少研究的情况下,辛西娅·欧芝克(Cynthia Ozick,1928—)异军突起,被誉为是“美国最杰出的大屠杀小说家之一”[2]149,近年来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在跨越50年的创作中,欧芝克获得美国文学各项大奖,包括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四次)、华伦特犹太小说奖、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奖、古根海姆学者奖、斯特劳斯奖等,见证了美国犹太女性文学的发展与兴起。大屠杀成为欧芝克作品直接或间接的创作题材与欧芝克的族裔身份背景息息相关。她少年求学中遭遇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因大屠杀的历史加剧了她对犹太人遭受迫害的敏感性。尽管学界对大屠杀的不可言说性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如西奥多·阿多诺(Adorno)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再写诗就太野蛮了”[3],然而这种警戒并没有阻碍文艺界采用各种方法再现这段非人性历史,其中《辛德勒的名单》、《苏菲的选择》、《夜》、《金陵十三钗》等都是影响广泛的大屠杀作品。欧芝克也坦承:“我非常担忧这个主题被小说败坏,小说通常都会腐蚀历史。”[4]这种苦难主题工具化的担忧显示了作者对大屠杀言说的风险意识,然而内心的驱动使她以大屠杀为题材,创作了20世纪最受好评的大屠杀叙事作品。事后她说:“我不欣赏我所做的。我做是因为情不自禁。它需要去做。我自己并不想做,之后我用某种方式惩罚了自己,谴责自己所做的。……但是我不在那里,故事并不是记录,而是一种想象。”[5]391欧芝克的内疚情结不仅源自她创作了应当保持沉默的大屠杀故事,更在于为自己没有与同胞同生死而愧疚,为自己无力拯救而汗颜。
欧芝克以作家的想象叙述了个体的遭际,释放了内心的压力,表达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她的创作是对极端恶的揭露,建构了女性话语的大屠杀历史,进一步开拓了大屠杀研究的领域。
《大披肩》由短篇小说“大披肩”(1980)和中篇小说“罗莎”(1983)两部分组成。作品自出版以来受到评论界好评,“大披肩”一词已成为大屠杀寓言式的索引词,可见其艺术影响力。自1988年以来直接论述《大披肩》的就有(但不限于)约瑟夫·洛恩(1988),弗朗辛·普洛斯(1989),伊莱恩·M·卡瓦(1993),艾米·戈特弗里德(1994),约瑟夫·奥柯楠(1997),莎拉·布利彻·科恩(1997),简·斯德特兰德(2002),米丽亚姆·希文(2009)。其中,洛恩认为《大披肩》是欧芝克的顶尖作品[6];卡瓦提出《大披肩》在大屠杀文学中具有重大的意义[5]179。目前国内外对《大披肩》的研究主要围绕大屠杀创伤、叙事艺术、精神分析、母女关系等视角进行了讨论,本文运用叙事学方法和大屠杀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叙事题材、叙事声音、叙事结构以及母性视角的分析,探讨小说中的女性大屠杀叙事特征,以性别视角阐释大屠杀对个体以及犹太民族造成的创伤。
一、虚构的文学再现
由于大屠杀题材的特殊性,选取何种素材对于创作非常重要。作者选取的素材、介入的方式以及引发读者互动的形式都是成功叙事的因素。在众多大屠杀历史文本中既有各种触目惊心、难以想象的灭绝屠杀描述,也有纳粹政府记录的屠杀文本,对于没有亲身经历的作家来说,素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能否创作出优秀的叙事作品。欧芝克谈及“大披肩”的创作灵感来自威廉·夏伊勒编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的一句话:“谈及婴儿被扔到电网上,那个景象停留在我脑海中。”[4]这一惨烈景象为欧芝克创作提供了灵感。如果说大屠杀的残暴性无法想象,那么纳粹迫害妇女与孩子的方式同样是前所未有的残虐。“犹太人区和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极其悲惨,惨绝人寰,任何口头、书面的记述和描绘都不足以道其万一。”[7]即使如此文学界以其特有的方式,记录、再现了人类的历史,纵然任何文学作品不能还原当时发生的场景,它仍然反映了历史的真相。科恩指出“那些写作大屠杀的作家被警告要遵守两项没有言说的命令:要尊重大屠杀事件的唯一特性,忠实再现这一野蛮事件,不要为了艺术效果而操纵事实;决不要异想天开或以嘲笑的方式对待这一严肃主题,否则会降低或削弱它的重要性”[8]。欧芝克是如何再现这一野蛮历史事件,又是如何加工弑婴题材的。首先,欧芝克选取的素材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选取了历史学家发现的“原始素材”,没有操纵事实。另外,作者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赋予被害婴儿女性的身份,聚焦弑婴母亲的行为,从母女亲情的视角再现了残酷的大屠杀历史。小说这样搭建的素材强调母亲身份遭受的更多戕害,这对于全面深入了解大屠杀有重要的意义,毕竟以男性书写者为代表的大屠杀叙述忽略了女性的特殊体会。虽然纳粹企图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然而对待男女进行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女性叙事的独特性在于“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揭示都是与她们生物特性相关的主题,比如无月经或停经以及心理影响,怀孕、分娩和与她们身体相关的性侮辱、强奸以及折磨”[9]。《大披肩》以大屠杀中的弑婴为题材,从性别视角揭示了大屠杀对女性身体造成的伤害,对亲情的毁灭,以及导致的永久的心理创伤。幸存者罗莎的遭遇不是遍及每个犹太人的经历,是独特的女性叙事、母亲遭际,凸显了性别视角下的大屠杀再现。
历史素材确定后,采取何种叙事声音无疑会影响叙事的效果。作品形式与表达的主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欧芝克通过现实主义叙述声音使得描述的事件打上了真实的色彩。全知叙述者在话语层次上既高于目击者和其他小说人物,又具有读者所未有的亲临现场的视角,因而具有超脱凡人所具有的权威,无所不知。苏珊·兰瑟(Susan Lancer)认为“个人型叙述声音的权威中叙述的‘我’也是结构上‘优越的’声音,它统筹着其他人物的声音,然而却不具备作者型叙述声音那种超越具体人的优先地位”[10]。在各种叙事中目击者无疑是叙事的权威知情者,从其视角观察较易获得读者的认可。然而作为大屠杀亲历者这种悲痛的经历反而使其无法言说,就如林斌所言:“一方面,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所特有的个体内在创伤性一度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公众妄加言说的资格,同时也令那些享有言说特权的亲历者(受害者或施暴者)因为身份的耻辱而三缄其口。”[11]这就是为何欧芝克采取了全知作者型叙述声音,以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为焦点人物叙述了惨绝人寰的弑婴,具有有效观察事实真相的叙事功效。
弑婴是《大披肩》讲述的核心事件,欧芝克通过弑婴身份的建构充分展示了文学虚构的魅力。历史文本中空白的弑婴形象在小说中具化为被铁栏网电死的婴儿。全知叙述者说“她跟罗莎那好似得了霍乱病一样憔悴乌黑的面色不同,这全然是另一类脸,眼睛如天空般湛蓝,光滑柔软的毛发与罗莎外衣缝着的星星一样黄。你可以认为她是他们的后代”[12]。玛格达蓝色眼睛、金色头发的外貌特征向读者暗示她是纳粹的后代。“可以”一词揭露了一种可能性,这一话语的模糊性引发读者思考事实的真相。作者型权威叙述即使改变不了事实,但却可以控制读者对事实的理解。斯特拉看着玛格达蓝色的眼睛断然说她是“雅利安人”(Aryan),判定了玛格达的德国身份。叙述者通过斯特拉这个人物视角引导读者认定玛格达是德国后裔,但是又让母亲罗莎否认了斯特拉的判断。罗莎说:“你父亲不是德国人。我是被德国人强迫过,是的,不止一次,但那时身体太弱不能受孕。斯特拉是个淫秽的人,禁不住凭空想象你父亲是一个肮脏的人,一个党卫队的人。……你是纯洁的。”[12]身为玛格达的母亲,罗莎谈论弑婴的身份当然具有合理性、可信性、权威性,然而她的话语不一定会得到读者认可。被德国人强迫过的事实已然成为战后人们解读集中营妇女遭受的普遍经历。否定玛格达德裔的身份既揭示了纳粹对犹太女性造成的身体伤害,更展示了罗莎对被剥夺合法母亲身份的抵制。玛格达的身份成为叙事有意造成的难题,令读者质疑叙述的可靠性,不过问题在于全知人物的叙述为何制造玛格达身份的模糊性?这些材料建构的情节和意义需要读者来判定。谈论弑婴身份的目的不是为了非同一身份的行为找到借口,而是思索同一性原则建构的伦理遭到了纳粹恶行的践踏。问题在于孩子的身份根本不应是人类社会确立屠杀的原则,如果是德国人的孩子,纳粹毁灭的就是自我,反之亦然,在没有他者的关照下纳粹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叙事的矛盾性一方面展示了罗莎作为母亲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作者欧芝克的立场,即族裔非同一身份不应成为屠杀的借口,而读者在叙事的张力中进一步认识到大屠杀营造的同一性意识形态应当受到我们的坚决抵制。
欧芝克在历史素材的基础上,赋予主要人物女性的身份,采用作者型叙述声音,使历史文本的简写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厚描,引发读者从女性视角再度思索大屠杀造成的创伤。欧芝克的文学叙述在矛盾的叙事张力中获得对事件本质的看法,在历史事实与小说虚构的缝隙中建构了作者的声音,给读者留下生存的叩问。
二、完整感再现
早期小说经常采用完整的叙事艺术模式,现代小说则多使用意识流、非线性叙事模式,造成了叙事的不完整性,留下许多空白。《大披肩》没有采用线性的时间顺序进行叙事,而是描写了几个典型的场景,再结合人物的回忆、幻想,勾勒出一副全景的画面,构成了完整的叙事。随时代变迁,大屠杀亲历者已渐渐走出历史现实空间,所以对大屠杀需要建构真切的历史描述以对后世起到警示作用。读者期待叙事完整是自然的,而完整的叙事也有助于对历史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叙事如果过于零散,会造成读者不安与烦躁,合集后的《大披肩》两个故事互为补充、相契合,读起来比较顺畅,填补了许多空白。《大披肩》从故事结构、主题和人物三个方面营造了完整的叙事系统。
《大披肩》在故事结构层面完整地讲述了罗莎在集中营、战前波兰以及战后美国的生活。短篇“大披肩”仅有七页,主要叙述了集中营的弑婴事件,揭示了大屠杀对身为母亲的犹太女性的残酷迫害;中篇“罗莎”有五十多页,主要描述了大屠杀阴影下、在女儿还活着的幻想中罗莎在美国的艰难生活,间断回忆了罗莎在波兰的优越日子。从大屠杀到大屠杀后叙事,欧芝克以“极简主义”风格向读者呈现了亲历大屠杀的幸存者罗莎的一生。洛恩讨论了这两个故事的关系,他认为“‘罗莎’在许多方面表现为‘大披肩’的继续,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前者的连续。两个故事都可以独立成书而不需要彼此。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一旦读者阅读了两个故事,就不得不参照彼此来阅读,这是欧芝克设计的米德拉什模式”[6];斯德特兰德也指出“这两个故事在多方面都是相联系的”[13]。集中营叙事以弑婴为高潮再现了纳粹灭绝人性的行为;战后在美国罗莎通过回忆、幻想、斗争展现了幸存者不能遗忘的历史记忆。“罗莎”的故事结局可看作《大披肩》开放式的结局,然而从“意义完整”的角度看,它已经达到高潮。前部在弑婴中抵达,后部在沙滩寻找内衣时对大屠杀的控诉达到高潮,从故事结构层面建构了完整的叙事。
另外,无论是短篇“大披肩”还是中篇“罗莎”都紧紧围绕大屠杀主题展开。“大披肩”是欧芝克唯一直接描写大屠杀的作品,以现在时叙述的弑婴事件令读者感到发生的现实性。短短几页素描了罗莎作为受害者在集中营的生活,小说没有描写“焚尸炉”、“毒气室”等众所周知的屠杀手段,而是集中描写罗莎试图保存一岁多的婴儿但最终未免于难的事件。罗莎亲眼目睹女儿被扔向带电的铁丝网,眼睁睁看着女儿在眼前死去却不敢发出丝毫的声音,做任何企图认尸的动作。这一场景展现了大屠杀文学中人性扭曲的重要主题:在大屠杀面前,作恶者和受害者都失去人性,难逃大屠杀的罪恶。“罗莎”这一部分可称为“大屠杀后”叙事,聚焦战后罗莎挣扎在大屠杀阴影下的生活。从给店中的顾客讲述集中营的故事直至亲手毁了那个二手店,罗莎自发、自觉的言说和控诉行动构成了战后生活的意义。抵制对大屠杀的遗忘、传播集中营的故事是欧芝克书写女性大屠杀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她强调女性应当承担的叙述者的责任,从而建构了女性大屠杀叙事的意义。
人物的中心化也是确保叙事集中及完整性的重要因素。每个人物都以不同的行事方式对主题发生作用,而太多人物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大披肩》两个故事都以罗莎为中心人物。根据E·M·福斯特(Forster)划分人物的标准,罗莎应属于“圆形人物”,即复杂变化的人物。罗莎战前是波兰上层社会人家的孩子,父亲是银行家,母亲是诗人,衣食无忧,瞧不起下层的犹太人民。希特勒纳粹的侵略剥夺了她富饶的生活,不得不经历地狱般的集中营生活。从否定犹太身份,被迫与犹太人一起经历磨难,到最终讲述犹太人的故事,她实现了一定的身份意识转变。战前罗莎受父母的影响不认同意第绪语和讲意第绪语的犹太人,激烈地反驳纳粹对她犹太身份的定义。战后来到美国她依旧愤怒的撕去树博士的信,因为他将她定义为“幸存者”。在矛盾中,对大屠杀故事的讲述最终在他人及自我眼中确认了的犹太身份。两个故事均聚焦在罗莎一个人物身上,使读者对中心人物在大屠杀影响下的生活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体悟到大屠杀对女性个体生命的摧残以及对人物命运的改变,从而建立起连续的个人生活史,凸显了叙事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三、母亲视角
欧芝克强调自我作为见证者的历史性角色在大屠杀叙事作品中得以实现。她与家庭中女性成员的密切交流渗入了她的写作,影响了她对罗莎和玛格达的刻画。作为母亲欧芝克对母女关系有深刻的体会,也正如此她充分发挥想象力,勾勒出一幅母亲与女儿被纳粹隔绝在人世的悲惨画面。《大披肩》从母亲视角书写大屠杀是女性书写女性见证者的作品,母亲视角的大屠杀叙事揭露了人性最卑劣的一面,因为母亲本能遭遇了大屠杀的焚毁。
当罗莎看到玛格达的身体抛向空中落到地上时,虽然有个声音让她冲过去,然而“她只是站在那里,因为如果她跑的话,他们会开枪,如果她试图去拣玛格达火柴棍似的尸体,他们也会开枪,如果她让她狼嚎般的尖叫声爆发出来的话,他们还会开枪的。所以,她只是握住玛格达的披肩,堵住自己的嘴,往嘴里塞进去,使劲地塞进去,直到她咽下了狼嚎的尖叫声”[12]。欧芝克从母亲视角向读者展示大屠杀面前母性的扭曲。正常环境中母亲会毫不犹豫地去拯救濒临危险的孩子,罗莎却犹豫是先找大披肩还是玛格达,最后还是决定先找大披肩,可是等她拿到大披肩看到玛格达时,纳粹已将孩子抛向电网。读者看到罗莎的生存本能超过了与她牺牲的孩子在一起的欲望,然而这更突出了纳粹对人性的彻底摧毁,母性在纳粹面前的扭曲恰恰是大屠杀对人性毁灭的证据。
战后罗莎在女儿还活着的假想中生活,因为母性本能是她生存下去的强大动力,她未来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由集中营中所经历的决定。母亲身份的罗莎对大屠杀的讲述构成了女性大屠杀叙事文本的意义。罗莎对大屠杀的反思在对时间的感悟中表现出来,她将生活分为三部分:以前的生活、中间的生活、之后的生活。她解释说之后的生活就是现在的生活。之前的生活是我们出生的家园生活,中间的生活就是希特勒。更糟的是她说之前是一个梦,之后是一场玩笑。只有中间停留着[12]。集中营将时间划分为“之前”和“之后”,而中间永远与前者不同并深刻影响之后的生活。对时间的思索反映了罗莎的生活态度,她之后的生活都停留在希特勒那个时期,这与她曾经是母亲的身份息息相关。斯特拉和罗莎都经历了集中营残暴的生活,然而她们表现出不同的生活态度。罗莎执着于大屠杀的记忆,同为幸存者的斯特拉劝罗莎放手,认为是时候该有自己的生活了。博斯基也说有时忘记是必须的。博斯基的生活态度是忘记痛苦的生活,将精神不正常的妻子安置在医院,试图追求罗莎,向往未来美好的生活。戈特弗里德评论到:“斯特拉和博斯基都忘记了玛格达,这个人物不仅代表了大屠杀中死难的人物,更是有关的记忆。”[14]战后在意念中玛格达的生存就是罗莎的生活。尽管“从欧芝克视角来看罗莎摒弃她同时代的犹太人和她异常不合时宜的同化态度有问题,然而罗莎拒绝忘记过去预示了她的重要性”[15]。罗莎母亲视角叙事的意义在她坚持传播大屠杀故事中突显出来。罗莎的母性受到强调,这是女性特有的经历,当然不是所有女性。就像斯特拉没有母亲的经历,无法理解罗莎不放手的做法。而博斯基作为一名男性,也秉承快乐本能的价值观。斯特拉和博斯基代表了那类对大屠杀遗忘和漠视的犹太人,受到作者欧芝克的批评。小说强调了罗莎作为一名母亲所特有的经历,具有一定特殊性,在大屠杀叙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弑婴,罗莎可能和斯特拉一样能够融入美国的生活中,然而母亲身份决定了她看世界的不同方式。大屠杀给母亲幸存者造成的心灵创伤和痛苦阻碍她像斯特拉一样忘记那些惨痛的经历,母亲身份的罗莎对大屠杀的记忆和传播使得她的形象高大起来。母亲身份受害者的经历,无疑具有一定的性别意识形态,这与作者的性别身份、族裔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读者的我们是如何对罗莎产生同情的,虽然她不认可自己的犹太裔身份,让我们看到她道德的缺失,然而“我们作为读者,发现自己被叙述者所控;我们的距离——不管是视觉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被层层的转述声音和思维之间视角的微妙变化、被所给的或故意未给的信息所控制了”[16]。我们受欧芝克母性话语的控制不禁对罗莎这个人物产生深切的同情之感。欧芝克创造罗莎这个角色,虽然她身上有种种缺点,然而女儿被纳粹士兵屠杀、对女儿的幻想,以及坚持讲述大屠杀历史的行为,让读者改变了对罗莎的看法,情不自禁深深地同情她,从而实现了欧芝克书写大屠杀的目的,擢升了民族意识。从同情到理解并认同罗莎战后生活的转换,读者建构了自己的主体性,而这个主体既有同性认同,也有男性认同,所有读者都能进入对罗莎的同情契约,因而欧芝克的叙事是成功的。作为耻辱历史的见证者,罗莎生存的意义就在于继续对死难者的神圣记忆,将大屠杀保存为集体的民族记忆。欧芝克一方面描述罗莎在大屠杀语境中母性的缺失,从而与其保持距离,又透过罗莎的眼光去看弑婴事件,拉近了读者和罗莎的距离,共同聚焦在母亲亲历的大屠杀事件,深切了解了大屠杀中作为母亲的犹太人的特殊遭遇。
四、结束语
面对纳粹的种族迫害、驱赶、追捕、监禁、流放、折磨、屠杀,如何再现历史成为作家们思索的问题。虽然大屠杀的真实永远无法再现,但欧芝克的书写是见证创伤、体悟伤痛、接近历史真相的过程,女性大屠杀书写也是欧芝克对自我历史角色的思索。罗莎身上留下的伤口成为每位阅读者内心的伤疤,她遭受的多重迫害,包括族裔身份带来的监禁,性别身份遭受的性虐待,母亲身份的被剥夺,非常人的生活,都使读者对大屠杀的残酷有了刻骨心扉的认识。欧芝克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同时赋予女性特殊的文化建构责任,号召犹太女性肩负起传播民族历史、文化的责任,增强了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为深层次研究大屠杀提供了另一个女性空间,建构了女性大屠杀文学的意义。大屠杀不仅在犹太人灵魂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也让每一个走进的人都嗅到了人类的残暴,因为大屠杀不仅是犹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防止野蛮大屠杀行为的再次发生,需要我们不断审视文明进程中人类的处境。
参考文献:[1]Langer L L.Preempting the Holocaus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1.
[2]Kremer S L.Women’s Holocaust Writing:Memory and Imagination[M].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9.
[3]Adorno T W.Notes to literature,volume 2[M]∥Nicholsen S W.Tra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87.
[4]Prose F.Idolatry in miami[N].New York Times,1989-09-10(A1).
[5]Kauvar E M.Cynthia Ozick’s Fiction:Tradition and Invention[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
[6]Lowin J.Cynthia Ozick[M].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8:106.
[7]塞姆·德累斯顿.迫害、灭绝与文学[M].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53.
[8]Cohen S B.Cynthia Ozick’s Comic Art:From Levity to Liturgy[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7:146.
[9]Goldenberg M.Double jeopardy:being jewish and female in the holocaust[M]∥Friedman J C.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London:Routledge,2011:391-411.
[10]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
[11]林斌.“大屠杀后叙事”与美国后现代身份政治:论犹太大屠杀的美国化现象[J].外国文学,2009(1):96-103.
[12]Ozick C.The Shawl[M].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90.
[13]Statlander J.Cultural Dialectic:Ludwig Lewisohn and Cynthia Ozick[M].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2002.
[14]Gottfried A.Fragmented art and the liturgical community of the dead in cynthia ozick’s the shawl[J].Studies in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1994,13:39-51.
[15]Alkana J.‘Do we not know the meaning of aesthetic gratification?’:cynthia ozick’s ‘the shawl’,the akedah,and the ethics of holocaust literary aesthetics[J].Modern Fiction Studies,1997,43(4):963-990.
[16]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6.
(编辑: 巩红晓)
A Study of Woman’s Narration of the Holocaust in Cynthia Ozick’sTheShawl
Zhao N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2,China)
Abstract:With the speakable and unspeakable debates of the Holocaust,Cynthia Ozick creates the widespread Holocaust literature The Shawl which is widely accepted by the readers.By means of narratology and the research findings on Holocaust studies,the paper discusses how Cynthia Ozick has created female narration in The Shawl,explores the historical subject of the fiction,analyzes the narrative mode,and explic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mother’s perspective.It proposes that female’s narration of the Holocaust will consolidate women’s historical discourse,reflect women’s suffering of multiple persecutions,and reconsider the trauma for the individual and the Jews caused by the Holocaust from the mother’s perspective.
Keywords:women;the Holocaust;narration;mother’s perspective;Cynthia Ozick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16.01.008
中图分类号:I 7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16)01-0042-06
作者简介:赵娜(1976-),女,讲师。研究方向: 美国文学、女性主义论。E-mail:hazelzhao@126.com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5YJC752048)
收稿日期:2014-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