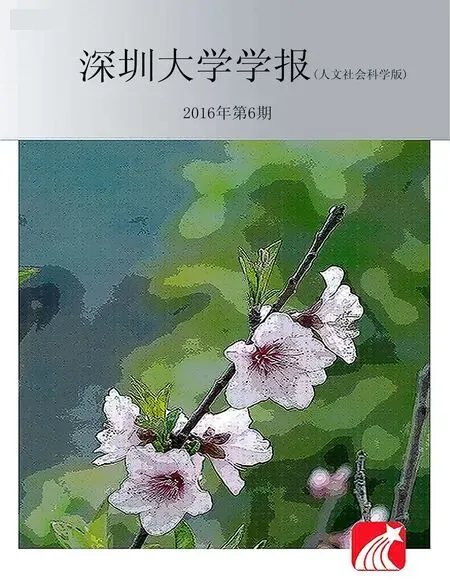从教学过程说开来
——关于中外教学过程的省思
2016-04-04张楚廷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从教学过程说开来
——关于中外教学过程的省思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教学理论产生于德国。与教学目的、内容、方法一道,教学过程也被研究者关注。有不少学者认为,教学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认识活动。这种看法具有片面性,并且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人是一个知情意的融合体,教学不只是为了发展认知,亦应关注情感的陶冶、意志的锤炼。教学过程是知情意的全面演绎。任何关于全面发展的论说,离开了知情意的综合发展,可以说是核心内容上的缺失。
教学;过程;知情意;人的发展
教学起源于最早的教育活动之中,教学理论似起源于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但夸氏的《大教学论》不如说是教育理论。比较系统的教学理论产生于德国。课程理论产生于美国。课程哲学可能是以《课程与教学哲学》①的出现为标志的。盛产哲学的德国和美国不知为何没有走到课程哲学和教学哲学,或许是还没能来得及吧?但中国人做到了。
教育的理论很宽,然而教学的理论是其最重要的部分。大凡教育家们都要研究教学的。
一、关于教学的诸问题
为什么德国人侧重于教学理论?为什么美国人侧重于课程理论?为什么中国学者就混称课程与教学理论呢?对此需要有一个探源的问题,然而我的另一个看法是:这样两种理论之间可以互译。例如,把教学的内容理解为课程,又把课程的实施称为教学。这或许是中国学者将它们统称为课程与教学论的原因吧。
教学理论在19世纪前就出现了,但课程理论20世纪才产生于美国。课程哲学则出现在21世纪的东方。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用世界的多元化来解释。
人为什么可以教?人为什么需要教?人应当怎样教?应当而且可以教些什么?把人教成个什么样?人需要教多久?教些什么、教了多久才算足够了?不同的人需要教的内容不同、方法也不同吗?教学的目的是一个、两个还是更多?教学的过程是怎样的?教学的内容应如何选择?由谁来选择?学习的人自己也可选吗?怎样的选择是合理的?合理与否的标准是什么?这种标准又由谁来制订?他制订的原则又是什么?有一个公共的原则和尺度吗?这种尺度会随时代变化吗?教学的过程会随着教与学的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吗?不同学科教学的过程会是一样的吗?一个一个单元的教学过程都一样吗?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是好的?有没有更好的?有没有最好的?教学有没有生病的时候?生病了没有,由谁来诊断?谁来治疗?如何治疗?可不可以预防、保健?有没有一门教学病理学?
二、关于教学过程的研究
回答以上的问题,写一本书可能还不够。仅就教学过程讨论一下,内容也不少。
中国学者中受前苏联学者的影响,不少人认为:教学过程即一个认识过程。几乎所有研究教学理论的学人都会述及教学过程,但看法不一。将其视为一个认识过程的很多;有的称之为特殊的认识过程,但还是认识过程。似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日本学者佐藤正夫在他的著作《教学理论》中大篇幅地论述了教学过程[1]。论及教学的认识过程,知识掌握过程中的归纳途程与演绎途程,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的掌握,教学过程的结构、阶段,知识的巩固。基本上是围绕认知来展开的。
夸美纽斯认为“教学过程是从观察到理解、记忆的过程”;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大致也持这种看法;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则认为教学过程是“一个新旧观念联系和系统化的过程”;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认为“是学生直接经验不断改造和增大意义的过程”[2]。大体上都是围绕认知来看待教学过程的。
对于这些说法,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提出许多问题。神学知识是“从观察到理解、记忆的过程”中形成的吗?古典大学就开设这门课程,拿什么去观察?牛顿弄出了一个无限小、一个微分,你怎么观察得到?怎么“从直接经验不断改造”中得来?古希腊人就提出了形而上学知识,这种知识又怎么观察得到?又怎么可能从直接经验中来?数学中的第5个完美数,人们寻找了近两千年,怎么那样难?如果可以观察,可以从直接经验中提升,怎么要那么久才知晓?
认识是人思维的结果,无论是否经过观察、经过直接经验,都少不了思维这个环节。然而,即使思维也有许多不同类型。有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归纳思维和演绎思维、发散性思维和收敛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还有抽象之后的再抽象。如此之多的思维种类,那么,思维展开的过程也就十分多样和复杂。这也意味着,虽然是思维过程、认识过程,但也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尽管认识活动是教学活动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但也不是全部。只视为认识活动就有简单化倾向;这种倾向也表现为对人的认识的简单化,极为神奇、复杂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单化了。人不只是一个认识体,不只是一个知识容器。
人有想象,人可幻想,人能仰望天空,人会做梦,美梦和恶梦都有,人能异想天开……所有这些都只简单地归结为认识吗?许多论著中所言的教学过程包含了这些吗?如果没有,那岂不是把教学过程仅仅视为认识过程的看法大大简约了神秘且神奇的人吗?我们的教学理论、教育理论竞然可以做这样的事吗?
我们学校里,中小学乃至大学里,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灌输式教学。不知是否受到了把教学过程只视为一个认识过程的观念的影响。由此,才有不断地认识、认识、再认识,观察、观察、再观察,记忆、记忆、再记忆,思考、思考、再思考。此外,别无其他。连一个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教学都很难展开啊。
三、教学过程是知情意的全面演绎
我既写过教学理论的著作,又出过课程理论的著作,而我的这些著作都基于我对人的理解、感悟,在这些感悟中,人就是我心中的神,一切由此展开。
仅就认识而言,也绝非只有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它实际可分为八个阶段:感性、悟性、灵性、知性、理性、哲性、诗性、神性。人的认识是如此美妙。
上天把所有的秘密放在了人身上,而已有的教学过程认识论则不知这种秘密,从而不知人有多么神秘。有人问我:你怎么知道上天如此恩惠于人了?我即答:我跟上天已通过话。上天告诉了我:它为什么把秘密都放在人身上?为什么如此慷慨?事实上,在所有的生命体中人是最年轻者之一。小鸟一亿年历史了,小草历史更长,而人则不到一千万年,目前所知为382万年。这至少表明,上天、大自然要把人孕育出来十分不易。要把那么多秘密放在人身上,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今,谁也不敢说能把所有的秘密揭开,能揭开很小一部分的人也需很大胆量和智慧。
对教学过程认识的简单化,反映了对人的认识的简单化。针对这一点,我特地说了以上一番话。我们轻看了教学和人,就是轻看了上天的伟大和神奇。
最低限度上,我们对人是知情意这三方面的美妙融合要有所了解。尽管认知十分重要,但也不能讲过头。常有一说:只要认识问题一解决,一切便迎刃而解。如果是这样,我们只要让所有的干部认识到国库里的钱不能装进了自己的荷包就够了,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如果由此一切迎刃而解,那么,贪污犯在一个小时里可以绝迹。可是,贪污犯几乎仍然是前赴后继,砍头他都不怕。
通常说道德,它也不只是一个认识问题。分解一下,便有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由此而修养、而践行。还是知情意三个方面的融合。道德情感的支撑不可或缺,做了坏事脸不变色、心不跳,就无可救药了;还有,在一千次没有贪赃枉法之后,第一千零一次亦必须照旧。这就是三者统一,缺一不可。为什么在现实的道德教育中多偏于说教?原因之一便是夸大了认知的作用。
现在我们可以说,教学过程是知情意的全面演绎。弄得好,即是全面演进;弄不好,便是残缺不全。对于教师而言,除了传递知识而外,还有自己的情感投入,还有教学中必然会有的坚持、耐心等。对于学生,除了认知其所学外,还有情感陶冶、意志锤炼。由此而得到发展。教师和学生都有各自的知情意活动。
知情意这三方面是彼此关联的。当你对一个事物或对象认识较多、较深时,就可能更有兴趣;又由兴趣的加深而喜爱它;再由喜爱而知晓得更多、更深。因为认识到必须去做的事,遇到困难和挫折就需要坚持,此时就需要意志帮忙。还可能因为坚持了,成功了,而对所认识之对象认识得更好,感情也加深了。
优秀的教师都明白,除了自己认真备课、讲课外,还要在教学方法上很讲究,让学生喜爱自己之所教和他们之所学;并引导学生在遇到困难时坚持一下,不轻言放弃。在课堂上,他会关注学生的表情,同时有办法去调节。一旦学生不喜欢自己之所学,教师之所教,效果难以想象。也就是说,优秀教师会充分融合自己的知情意,并由此而带动学生在知情意上的融合,这样,他们就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四、关于全面发展
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我曾从九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过阐述。比如,我认为全面发展乃是每个人自己的全面,即个性发展。姚明的全面发展与举重运动员的全面发展不一样;华罗庚的全面发展与钳工、电焊工的全面发展不一样。
全面发展是发展全面,而不是面面俱到,是由片面走向相对的全面。在念书的时候,中学、大学里的同学都认为我是全面发展的。可是,仅就认知而言,我的历史科曾只考了57分;论体育,我的百米跑不进14秒;我会唱歌,但绘画水平几乎等于零;我的语言文字能力得到了提高,但我的古典文学学得很差。很可能,恰是从整体上看我的知情意发展较为协调。认知方面还可以,此外,我能哭能笑,很容易被感动,有时悲伤而泣,有时喜极而泣;想做的事也能坚持,长期的伏案写作,得了颈椎病,仍不停笔。上天赐给的书,我尽量地读;上天给我的泪,也尽情地流;上天给我的意,我也尽力去发展。于是知情意在我身上融合。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之说。首先可注意的是,从古希腊人到康德,都把体放在第一位。在他们看来,体乃体魄,体与魂是在一起的。这就是对“体”的一种较为全面的理解。在“体”的活动中,知情意都存在,都发挥作用。
对于“德”,我们已指出,其基本内涵便是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构成。
至于智力活动,它总是与非智力因素同时存在的。这种非智力因素主要就是情与意,它们的作用极大。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千虑一得、千锤百炼、千方百计,有志者事竞成,千回万转去奋斗,走向成功的可能性就大。
说一千,道一万,全面的心理上的核心内容是知情意。教学过程关注知情意,教学目的为着知情意的发展,人由此而走向和谐发展、个性发展、自由发展、美学发展。离开了和谐、自由、个性、美学,还谈什么全面发展?还怎么发展全面?
五、自由与必然
自由唯独属于人,故人即自由,自由即人。然而,人天生的自由在后天还需去发展、去创造。
古希腊圣哲就指出了“自由学术”与实用学术之别,“高级学术”与“次级学术”之别[3]。这就把不同的知识与自由联系起来了。其实,知识都能给人一定的自由,然而,不同的知识给人的自由还是有差别的。亚里士多德正给予了区分。
从斯宾诺莎到黑格尔,都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似是在认识必然之后的事。但恩格斯前进了一步,他说“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4]。这就是说,自由也可以存在于对必然的认识之前、之中。
我本人觉得还可以进一步,自由还可以存在于情意之中,可以有自由意志,自由地爱和恨等等。简言之,自由不仅与认知相关,也与情感和意志相关。
卢梭关于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观念传遍了全世界;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是脍炙人口的诗句。
虽然人生而自由,但后天还需自己把握自由、发现自由、享有自由、发展自由、创造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尊重他人自由、剥夺他人自由的人,是不自由的。
教育是干什么的呢?可以说就是帮助学生在知情意方面都得到发展,也可以是帮助学生维护自由、扩大自由、创造自由。此乃杰出人才所必需。教师首先是理解和尊重学生的自由,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否则,杰出人才辈出不是也很容易吗?古希腊人就特别珍贵的自由教育,今日的我们能不珍惜吗?
其实,自由不只存在于认识之前、之中、之后,还可以存在情感和意志领域。今日,人们都知道,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是学术繁荣的生命线。在我做教师、做校长的工作中,我都明白这一点,对自己、对他人,我都特别珍惜自由,并践行。由此,我的大学有了良好的发展,我本人也得到了发展,知情意诸方面都有所发展。在我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也这样体现着、贯穿着知情意协调发展的理念。
注: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1][日]佐藤正夫.教学理论[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236-276.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715.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4-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5-456.
【责任编辑:向博】
Speaking from Teaching Process
ZHANG Chu-t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08)
Teaching theory originated from Germany.Apart from teaching objectives,content and approaches, teaching process is also a subject of study.Many academics believe teaching process is a creative cognitive activity. This view is one-sided and has produced some negative impacts.Man has cognitive abilities,emotions and will power.More than developing cognitive abilities,teaching should also focus on edifying emotions and strengthening will power.The teaching process should cover all the three aspects.We can say that any theory on all-around development withou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bilities,emotions and will power actually does not have core content.
teaching;process;cognitive abilities,emotions and will power;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G 421
A
1000-260X(2016)06-0151-04
2016-10-21
张楚廷,湖南师范大学原校长,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等,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数学理论与实践等多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