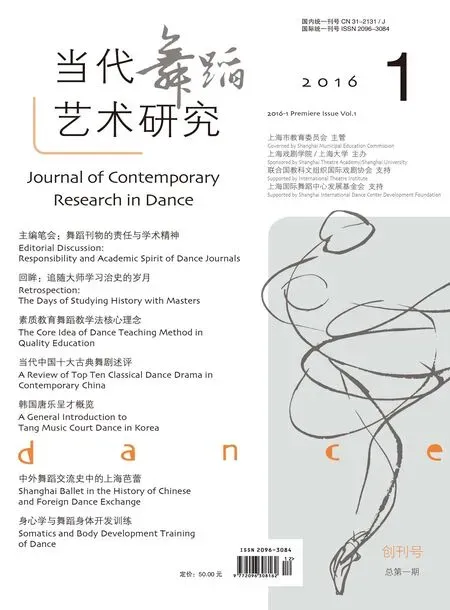抱残守缺 志求信史
2016-04-03刘青弋
刘青弋
显然,在中国舞蹈史学走过60个春秋的今天,以“抱残守缺,志求信史”为题讨论中国舞蹈史学研究和基础建设,既是彰显中国舞蹈史学工作者的理想和责任,亦为说明中国舞蹈史学建设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处境。梁启超先生曾在谈及中国史学面临的现实处境及其出发点时如是说:“故吾侪今日之于史料,只能以抱残守缺自甘。惟既矢志忠实于史,则在此残缺范围内,当竭吾力所能逮,以求备求确,斯今日史学之出发点也。”[1]52年轻的中国舞蹈史学身处抱残守缺之境,如何求得信史?
一
在网络时代与自媒体话语自由、大众追逐“成名成家”梦想的当下,学界往往忘记了史学是一个专业——一个为了追求说出“过去的真相”,需要进行扎实、艰苦的学术训练,为获得第一手的史料和证据,长年累月地“甘坐冷板凳”,或者“一盏孤灯到天明”埋头于书山文海中工作的专业;或者有如奥运会的运动员需要经年累月的艰苦训练,拼尽“洪荒之力”才能获得成绩的专业。然而,当下浮躁的学风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则有时将学界变成了自由市场和娱乐场所。有人不做,或不愿做,或不懂得做为“学”之工,却顶着“学者”“专家”的光环趋利而上。当他们将一些东拼西凑地抄袭、剽窃,甚至是抢劫他人的成果,或者借助“枪手”“抟”成的所谓“著作”,将一些“连抄都抄错”的“学问”投入市场和教育领域,对于中国舞蹈教育和学术建设的伤害可想而知;加之,学术领域的“官本位”“行政化”,资源分配和评价体系中的“权力和利益交换”,以及高校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将学术资源变为自产自销的自留地,都是导致中国舞蹈学术水平滑向低谷的推手。
作为一门严肃而辛苦的专业,中国舞蹈史学比其他史学研究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尽管在历史上有西汉司马迁《史记·乐书》传世,让我们得以领略先祖关于(包括舞在内的)乐的深刻思想;有宋人陈 《乐书》传世,让我们能够对宋时及其此前的雅乐舞、胡舞、俗舞的发展历史能够有一个概括的印象;有清末民初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戏曲考原》等传世,使得我们认识“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及其由古代歌舞演变的轨迹,也让我们拥有可作参考的断代乐舞专题史;也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有陈文波的《中国古代跳舞史》(神州国光社,1925)问世;在30年代有钱君《中国古代跳舞史》(神州国光社,1934)、齐如山的《国剧身段谱》(北平国剧学会,1935)发表;在40年代有常任侠《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说文社,1945)付印……也尽管有当代学者的诸多的努力及其优秀的成果的出版……对于我们传承中华民族灿烂的乐舞文化遗产,对于我们重拾文化自信,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然而,中国舞蹈几千年的历史整体面貌在今人的眼里仍然像是“水中月”“雾中花”。
另一方面,中国舞蹈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任务即是为了“考古以证今”“以史明鉴”。通过记述中国舞蹈历史赓续活动之体相,探究其活动的成败得失及其因果关系,揭示舞蹈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及法则,为当代舞蹈家的舞蹈创造与研究提供借镜——它将舞蹈视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发现“其本身是如何、可以如何”的问题,进而探求“指导其应该如何”的问题。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将前者称为“学”,后者称为“术”。指出“术”是从“学”中生出来的。因此,如果我们对“学”不能搞明白,“术”便从来也是不得法的……[2]111因为“历史”即意味着重建消失或残缺的过去,而探究中国舞蹈历史活动的成败得失及其因果关系,首当其冲要回答的问题便是“什么是历史上的社会文化事实”——探索“历史上什么事情真正地发生了”,这是史学的责任,是志求信史的前提,也是抱残守缺尤盛的中国舞蹈史学建设的难点。
“志求信史”首要的条件是史料的真实,也即证据的真实。而且,一部信史,材料不仅是要真实的,还应是典型的、重要的;同时,对历史所做判断和阐释是正确的,符合历史的真相。因此,史学工作者首先必须具备搜集和考订史料的基本功。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舞蹈史学的第一批成果不是由舞蹈工作者完成的,而是由具有深厚功力的中国史学或文化艺术史学的专家们完成的——例如阿英发表的《中国古代的民间舞蹈》、阴法鲁发表的《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舞蹈》、向达发表的《拓枝舞小考》、常任侠发表的《中国古代的舞蹈艺术》,李拓之发表的《中国的舞蹈》、欧阳予倩发表的《试谈唐代舞蹈》、石田干之助著、欧阳予倩译的《胡旋舞小考》、魏尧西编校的《宋代队舞》……他们为中国舞蹈史学研究做出了学术示范,赋予了中国舞蹈史学建设起步的高度。
为了追求“信史”,吴晓邦、欧阳予倩及上述专家指导并带领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开展的第一步工作即是史料的搜集与考订。例如《苏州道教艺术集》(1956)、《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1958)、“中国古代舞蹈资料陈列室”(1958)等成果可作明证;而经几年积累之后的成书不是《中国舞蹈史》,而是欧阳予倩带领下完成的断代史《唐代舞蹈》(1960),以及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成员完成的《中国舞蹈史长编》(1962)——意在先行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按史料编年次序排列形成的“长编”,以便在其基础之上,进一步撰写“中国舞蹈史教材”——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舞蹈史》(史称小5卷)才得以付梓面世——第一代中国舞蹈史学工作者从导师们那里继承了对史学专业的敬畏和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引领他们60年来勤奋治学,年到古稀不敢怠惰。因而,孙景琛、彭松、王克芬、董锡玖、刘恩伯等前辈学者在史料的挖掘、积累方面所具备的专业基本功是令后辈望洋兴叹的。他们在荒漠中开垦建设,在史料方面做了“在大海里捞针”“在沙漠中淘金”般的艰辛劳动。因此,他们给予我们中国舞蹈史学的是具有开创性成果,为后来人的研究打下的坚实基础是有目共睹的——这亦是笔者作为《中国舞蹈通史》项目的主持人邀请他们担纲古代舞蹈部分的著者,并以他们的代表作为学术基础的根本原因。①并且,为了保证这套史书在体例上统一和成果的原创性,笔者删去了自己执笔的清代舞蹈断代史的成果;而是以自身在对中国现当代舞蹈研究、对战争和革命文艺研究、对西方现代舞蹈之于中国舞蹈影响研究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大规模地开展20世纪中国舞蹈口述史研究中获得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舞蹈通史》在民国时期舞蹈历史研究方面的补佚和创新。因而《中国舞蹈通史》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国家级教材”。该教材是建立在对中国舞蹈史学半个世纪优秀成果的集大成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对经过实践检验的学术成果进一步确认、补佚、修订、改作、完善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既非是旧作的重版,亦非是“一穷二白”般的初撰,从而,既在史料挖掘和学术观点方面具有原创性的价值,亦在学风方面彰显了追求信史的努力和品质。
二
什么是舞蹈历史上的社会文化事实?什么是真实的、可以作为舞蹈信史的史料?在重做历史中,我们往往参照已有的“历史”,而书籍上的“历史”不过是时人关于“历史”的记载,或是后人对“历史”的认识,未必是历史本身。而大凡由人所做的记载都会或多或少受主观因素影响其真实性。当代人常常使用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历史来证史,然而,当事人的记忆容易有误,当事人对事物的判断也会有误,当事人的私心亦会影响证词的可靠性。因而,虽然“人人可做口述史”,但是,还是应强调贝斯·罗伯森所说的“口述历史跟文字回忆录以及传统历史研究一样,需要努力、专业与毅力”[3]3。否则,以“口述史”的名义的工作不仅不能为信史提供可靠的材料和证据,还将制造出诸多的历史谎言和伪证——可怕的是,由于疏于考证,让有误的“历史”,通过亲历者之口,形成所谓“铁证”,从而让日本学者栗山茂久所说的,由于不同叙事中的“真相”之间的差异之大,有时让我们对“真相”这个概念本身感到的怀疑进一步加剧;并为中国舞蹈史学制造出更多的、永远悬疑的“罗生门”和“历史乌龙”!
一切追求“信史”的舞蹈史研究者都像利奥波德·冯·兰克等史学家所希冀的一样,将探索“历史上什么事情真正地发生了”作为史学的责任和理想;因而,为取得史学研究新的进展,舞蹈史学工作者均为获得第一手的史料证据而呕心沥血。
孙景琛先生认为,资料是科研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历史的研究,首要的条件就是掌握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如此才有可能通过对史料的深入研究,写出符合历史实际的信史,并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他以十余年之功作为第一副主编完成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编辑工程,之后启动了《中国乐舞史料大典》汇编的重要工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史学建设进行开拓的多方面思路。并且,他在《中国舞蹈通史》(先秦卷)的修订过程中运用新的史料对舞蹈的历史现象进行了新的阐释。例如,笔者曾针对晋葛洪在《抱朴子》中所记录“禹步”为“三步九迹”“二丈一尺”的步态、现存羌族“释比”所跳“禹步”的多变步态与前人所释“禹步”“步不相过”的步态之间的矛盾等,对这位前辈提出疑问。而孙先生则以亲身考察的道教乐舞中的“步罡”为例,重新诠释了道家“步罡”和晋《抱朴子》里所记录的“禹步”之间的关系;同时,以传统民间舞的历史遗存现象解释了“巫舞”和“禹步”之间的联系和异同,从而正确地诠释了历史。
王克芬先生念念不忘导师们的教导。欧阳予倩先生关于研究舞蹈史要掌握大量的资料,写舞蹈史要用资料说话的要求影响了她一生。因此,她的史作,处处注重出示证据。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舞蹈学界借鉴甲骨文领域研究的成果,认为“巫”和“舞”字同形、同音、同义,进而认为“巫”“舞”同字,并错误地认为“巫”即为最早的专业舞蹈家。王克芬先生则根据甲骨文领域和考古研究的最新发现,指出“巫”和“舞”为不同的字,亦不同型。从而指出,作为传达“神”的意志的“巫”和作为乐舞奴隶的舞者之间的天壤之别,从而及时纠正了中国舞蹈“历史”上的误识。
董锡玖先生亦追随先师的教导和治学精神。欧阳予倩所说的要“下笨功夫”,张庚所说的要“坐冷板凳”,默默地做史料……成为她从事史学工作的座佑铭;而沈从文先生在给她的信中所强调的:研究乐舞史要注意参考近年大量的出土“文物”和传世的活态“演出图像”,与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获得对历史的新见解……促使她走遍了中国大地,踏遍了祖国的石窟寺庙。关于宋代舞蹈的面貌以及独有的“一边顺”的动作特点,均来自于其对中国传统舞蹈在当代活态遗存的考察,以及对敦煌壁画的图像分析。而在《中国舞蹈通史》(宋辽 西夏 金 元卷)的编撰过程中,罹患癌症,为了考证一张宋代舞蹈的历史图像的年代,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坚持向在欧美博物馆工作的友人求助,直到确认……
彭松先生则希望舞蹈史学界不要老是炒陈旧的东西,因为舞蹈史学有好多空白,应该先把空白填起来。他希望舞蹈学界熟读四书五经,不仅因为“五经皆史”,也因为中国舞蹈史学注重加强对传统文化层面的研究才有深度。因而,他在《中国舞蹈通史》[(秦汉卷)和(魏 晋 南北朝卷)]的修订过程中,挖掘和补佚了大量新的史料,增补篇幅过半;同时注重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对舞蹈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另外,关于对中国戏曲舞蹈的基本功常说的“有法儿”的解释,也在他读了《老子》的“反其道之动”之后获得了新的观点。他认为这个词既非“有饭儿”——即动作对了,就保住了饭碗;亦不是“有范儿”——动作正确的意思;也不是“有法儿”——有方法的意思;而是“有反儿”,也即“起反儿”——从反到正,这是动作的规律——“反者道之动”是老子“相对论”的观点。
有人误解《中国舞蹈通史》的古代图录卷是刘恩伯先生旧作的重版,实则是一种浅尝辄止的妄断。他遵照《中国舞蹈通史》的编撰要求,按时代以历史编年的方法对文物图像进行考证和呈现,要求时间、地点和内容考证的准确性,他将大量的文物图像进行修缮增删,所用之功是显而易见的——与按照文物类型编撰的图典大相径庭,从而,文物和图像不再是孤立的史料,而是成为“以图证史”“以物证史”的有力证据,成为中国舞蹈史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舞蹈史学的研究中,中华民国时期舞蹈的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环节。笔者担纲此卷撰写时亦将真实的史料视为史学的血肉,因此,在遍访了创造和携带这段舞蹈历史的亲历者,对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的挖掘和考证之后,才获得了察看民国时期舞蹈的新视角,建立起民国时期舞蹈发展相对完整的历史框架,让一些“历史”的误识得到纠正,并一改一般将民国时期视为舞蹈文化沙漠的观点,提出并证明:民国时期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都市流行舞蹈风行与兴盛,学校教育舞蹈萌芽与兴起,现代演艺舞蹈创建与奠基,传统戏曲舞蹈继承与发展,革命和抗战宣传舞蹈普及与高涨,民间历史生活舞蹈传播与繁衍,成为民国时期舞蹈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填补了空白,改写了“历史”。
再如,乐舞学界一般均持“雅乐亡矣”的观点,舞蹈界亦认为,中国古典舞在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从而将在当代重建的、甚至是创作的舞蹈当作中国古典舞本身。笔者遍查中国历史古籍善本,发掘了38套100例舞谱史料;同时多方实地考察了雅乐在当代的遗存,因而,得出在某种意义上说“雅乐未亡”的结论,为探寻复建缺席的中国古典舞历史代表作提供了可能性;在“史料”的挖掘方面获得新的成果的同时,在研究方法方面强调了舞谱研究、图像研究,以及在实践层面的操作研究在舞蹈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
三
中国舞蹈史学研究方法建设一直是业界关注的话题。笔者认为,舞蹈史学只有建立自己本体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才有自身的独立性;同时认为,舞蹈作为人文学科的属性,决定了其从文化到本体研究具有不同层次和不同方向。如果我们仅仅以所谓纯粹的舞蹈观来研究历史,自然会将作为“文化”的舞蹈变为仅仅是狭义的“艺术”的舞蹈——只是利用相关审美研究的方法,必然使得中国舞蹈的历史研究既无深度,亦无广度。由于舞蹈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因而,任何单一的方法都无法完成对舞蹈历史的研究,致使舞蹈史不同研究方向虽然采用不同的方法,却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趋向综合。然而,值得强调的是:方法的运用只有与研究目标相匹配,才会有效。
就年轻的舞蹈史学建设的当下而论,主要是对既有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的创新运用——史料搜集、分析、考订是其基本步骤。中国史书编撰所采用的以人为主的纪传体,以时间为主的编年体,以政事与政制为主的政书体,以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都为舞蹈史研究提供了参照。自然,舞蹈作为非文字性质的文化活动,除了由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还有“遗存之古物”“口传之口碑”“遗存之实迹”“现实之演出”……都纳入我们史料采撷的视野。因此,文物考古法、活态遗存考证法、图像研究法、动态分析法……都成为我们可以选择的途径。而现代兴起的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文化研究的方法,语言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亦无一例外地进入舞蹈史研究方法之列。而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和国家间频繁的文化交流,则使我们的史料搜集和研究的视野不只停留在本民族或本土,同时投向异族和海外,尤其是“丝绸之路”民族间、国家间的相互影响,因而文化比较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忽视。
“法无定法”——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往往和史学追求的目标匹配,亦和史学工作者对中国舞蹈历史的认知密切相联,因此,史学研究的方法难以统一万全。如果我们将舞蹈视为人类纯粹的艺术活动,我们自然偏重运用艺术学和美学的研究方法,将其从人类生活中析离出来,其目的在于强调舞蹈的审美属性,并从这一角度回答历史提出的问题。而如果我们将舞蹈视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必然强调舞蹈的社会和文化属性,自然偏重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方法,关注其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联系,其目的是解决舞蹈文化史建设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舞蹈视为乐舞艺术的组成部分,也自然将其置于综合艺术之中进行考察,必然强调其与歌舞诗乐戏文等相关艺术因素之间的关联,而不同艺术门类的研究方法将会被选择运用,其目的在于强调舞蹈作为综合艺术的属性,并从这一角度回答历史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强调作为独立学科的舞蹈史学,其目标是解决舞蹈史学的特殊性和纯粹性的问题,自然将舞蹈从综合性的文化艺术背景中分离出来;身体动态研究、舞蹈图像研究、文本的语言研究、身体体现研究等接近舞蹈本体研究的方法,成为这类舞蹈史研究注重的方法。总之,研究方法本身,没有高低对错之分,只有运用是否得当或是否有效之别,因而,非此即彼或者厚此薄彼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另外,治史者的舞蹈观、史学观亦大大地影响我们对史料的选择、方法的应用以及结论的得出。如果我们以西方剧场舞蹈或现代演艺舞蹈的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舞蹈,那么便会对除此之外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对中国舞蹈特殊的历史持否认态度。如果我们以中国古代宫廷舞蹈或专业舞人舞蹈作为中国古代舞蹈历史的正宗,那么,自然将所谓“正史”中的文献作为“信史”的主要依据,也自然不经意地排斥中国民间舞蹈生机勃勃的历史事实,并在大量的历史活态遗存面前闭上眼睛。就中国舞蹈史学研究的总体来说,虽然比较偏重文献研究,但对文献研究却远不够深入;并且较忽视实证研究和操作性层面的研究,因而需要注意改变。
舞蹈史学作为艰苦的专业,还由于舞蹈史学要求让那些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稍瞬即逝的舞蹈动态能够再现作为历史的证明,也由于史学的要求所有的证据必须全真才真,一假则伪!孤立的史料是不能构成史学的,因而,辨别误识和伪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注重找出反证[1]100——“证伪”的方法和“证真”一样在史学研究中占有同等的地位。
史学与史考和史纂亦不同。如何才能够让历史成为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余英时先生在《史学、史家与时代》中认为,“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4]90。因此,我们应重视他在《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中所推介的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一个欲成专门之业的史家必须具有批评精神,不为权威所慑,而后始能根据他自己治史之心得重建历史的面貌。这种重建的能力就是柯林伍德所说的“历史的想象”。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历史家所构成的历史景象必须获得证据的支持。在历史的推理之中,根本的关键便在于证据之有与无及对于证据的了解。[4]134-136因此,在中国舞蹈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让真实的史料和史实本身成为有力的语言,作为一种原在,言说历史的本真存在。
显然,中国舞蹈史学的建设远远没有完成,而且又面临一个价值重估时代的挑战,因而,我们更加认同余英时先生所说,最后的历史是不可能的;认同英国学者克拉卡先生所说,史学中因有主观因素,永远无法写出最后的定本;认同吕思勉先生的观点,为了接近历史的真实,史事的搜集、考证、订正、编纂便是永无止境的……因而我们期待“中国舞蹈历史”不断出现新的订正、改作、补佚与创新。
然而,能否求得信史,最终取决于治史之人能否拥有“史家四长”,即刘知几所说史才、史学、史识和章实齐所说史德。按照梁启超的解释也即:有了史“德”,心术端正了,才能忠实地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才不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才能极其敏锐;有了史“才”,才会有作史的特别技术,架构好历史和文章的构造。[1]187、202因此,德、才、学、识兼备,以德为先,是史学专业的基本素质和素养,亦是在抱残守缺之境中,矢志不移地求得信史的先决条件。
【注释】
① 2005年,笔者任职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系主任、舞蹈研究所所长期间,荣获北京市首届“人才强教计划-拔尖创新人才”的专项资助,将《中国舞蹈通史》列入其中的子项目,笔者作为项目的策划者和主持人,顶住巨大的压力,坚持跨单位地组织团队,邀请当时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而学术成果被任意抄袭的上述前辈学者担纲古代部分著者,并以他们的代表作为学术基础,从而保证了《中国舞蹈通史》编撰的质量。2006年,《中国舞蹈通史》被立项为教育部“十一五”规划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教材;2013年荣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工程奖”;2014年荣获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一等奖。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
[2] 吕思勉.为学十六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 贝斯·罗伯森.如何做好口述史[M].黄煜文,译.台北市:五观艺术管理,2004.
[4] 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1卷:史学、史家与时代)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