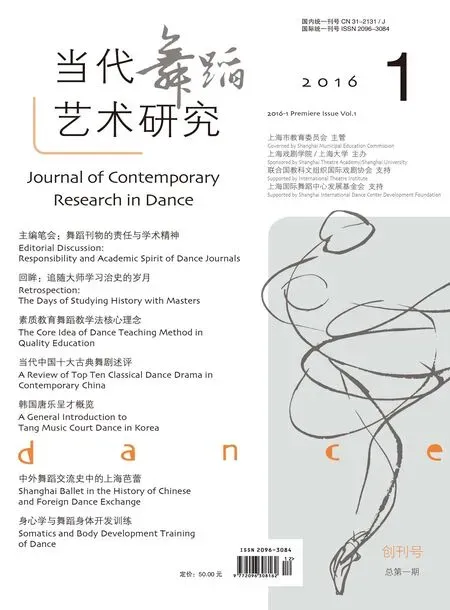回眸:追随大师学习治史的岁月
2016-04-03王克芬
王克芬
一
1956年春,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具体组织领导开始了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工作。同年,在吴晓邦的领导下,召开了舞蹈艺术科学研究工作的多次会议,由戴爱莲、陈锦清、盛婕、胡果刚等专家参加讨论,最终修改制定了“1956—1967年艺术学规划草案(初稿)舞蹈部分十二年远景规划”。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就是其中的项目之一。同年10月,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成立了“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吴晓邦任组长,欧阳予倩任艺术指导,组(学)员有孙景琛、彭松、董锡玖和我。
研究工作必须资料先行。为了搜集活的舞蹈史料,l956年始,吴晓邦老师作为学科带头人和盛婕同志带领研究会到江西、广西等地,搜集历史悠久、至今还保存在民间的古老的“傩”面具舞的资料;到山东搜集“祭孔”雅乐舞,并按照一些老舞生的回忆恢复了祭孔乐舞,录制了一部祭孔乐舞电影记录片,成为后来当地恢复祭孔活动的珍贵依据;还到苏州搜集了道教祭祀活动中的传统舞蹈等。通过以上工作,一方面为中国舞蹈史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锻炼了研究队伍。在这些工作的全过程中,驻会秘书长盛婕同志起到了组织保障作用,无论人力、经费如何困难,她都全力以赴,想方设法去解决;在舞蹈史学的建立与发展中她功不可没。
1957 年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不少人被错划为右派,生活、工作都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而我们舞蹈艺术研究会在吴老师和盛婕同志的保护下,没有一个人被错划为右派,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使我们得到一片安稳的净土,可以专心搞研究。因而,1957年和1958年上半年,成为我们工作最紧张、最有成效的时期。
研究的基础也是资料。在吴老师和盛婕同志领导下,我们多方搜集舞蹈史料,得到了各文物考古单位及有关专家的支持。我们跑遍了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所、音乐研究所、戏曲研究院等单位,从他们的展览室、资料馆中搜集到不少有关舞蹈文物和图书。1958年,国家拨出专款,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古代舞蹈史资料陈列室”。接着,又在沙滩红楼建立的艺术博物馆中,开辟了规模更大的“舞蹈陈列室”。除古代舞蹈陈列室外,又增加了近现代及当代舞蹈陈列室,展示了1840至1949年及1949至1958年间的舞蹈图片、书刊及实物等。土地革命时期、延安秧歌运动以及国统区进步舞蹈活动的有关资料,引起了各方的极大重视。各民族民间舞和1949年后在国际获奖的舞蹈节目等则开辟了专室予以陈列。这些资料的搜集与陈列,凝聚了吴老师、盛婕同志及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全体人员的心血与智慧。十年浩劫,这些珍贵资料大部散失。每提及此事,无不深感痛惜。
与此同时,另一项辑录、分类整理《全唐诗》中乐舞资料的工作亦开展起来。除了我们四个组员外,加上编辑部的隆荫培共五人,查阅了《全唐诗》900卷48,000多首唐诗,将其中有关音乐舞蹈的资料抄录出来,分成音乐、舞蹈两大类。这一浩大的梳理史籍工程,我们五个人只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后来这本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编辑出版的《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不但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欢迎,还受到世界各国汉学家的重视。英美等国的著名大学和图书馆均收藏了这本书。从1956年至1966年十年间,我们的工作成效显著,中国舞蹈史学的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让正在朝气蓬勃发展中的中国舞蹈史研究嘎然止步……“文革”结束后,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再次迎来了春天。吴晓邦先生作为学术带头人,再次带领了中国舞蹈学科的全面建设,他像以前一样鼓励、支持和培养我们建立起学术自信。1978年,受人民音乐出版社约稿,我夜以继日地完成了《中国古代舞蹈史话》初稿,送给吴晓邦老师审阅。记得去取稿那天,我战战兢兢地走到吴老师身边,内心忐忑,不知吴老师将如何评价此书。不料他说:“你的书写得很有意思,除了审稿,你还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我惊呆了,怔了一下,脱口而出:“吴老师!您帮我写个序或前言好吗?”吴老师爽快地回答:“好!好!你把咱们在一起作‘规划’,建立舞蹈史研究小组的时间回忆一下,写给我。”在吴老师的鼓励下,我的书顺利出版。后来被译成英、法、日、韩及繁体字版在海外发行。
二
对于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当初我们毫无经验和学术积累。作为艺术指导的欧阳予倩请来了与舞蹈艺术关系密切的老专家,如音乐史专家杨荫浏,古典文史专家沈从文、阴法鲁、吴晓玲,戏曲史专家周贻白、傅惜华、任二北,美术史专家王逊等来指导我们,为我们作学术报告或专访。于是,我便作为老师们“永不毕业的”“编外学生”,在他们的关怀和培养下得以成长……
记得我第一次见欧阳老师,是秘书长盛婕带我去他家拜师。他招呼我们坐下后,轻声问我:“你知道吗?研究舞蹈史,要掌握大量的资料,要下大工夫,坐冷板凳。不掌握资料就没有发言权,写舞蹈史,要用资料说话。可是现在许多年轻人,看不起资料工作,不愿意做资料工作,这样是搞不了研究的。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你会努力的,是吗?”一向都很要强的我,壮着胆说:“我一定会努力的!”这短短的几句话决定了我一生从事研究工作的基本态度。总结起来,给予我深刻影响的有以下方面:
第一,从事研究工作的态度与方法。
虚心学习,甘当小学生,对历史问题,甚至一切问题,都应抱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不要不懂装懂。历史问题是复杂的,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能定则定,暂不能定的应求证待定,千万不要妄加评论。充分认识资料是基础,资料要先行的道理。由于欧阳老师当时指示我们要尽快广泛搜集舞蹈史料,特别是各时代文物中的舞蹈形象资料,要努力求得考古、文物界专家学者和有关工作人员的支持,建立舞蹈史陈列室。因而,有了1958年2月在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王府大街原文联大楼五楼)建立的中国第一个(由欧阳老师亲自为陈列室题字的)“舞蹈史资料陈列室”等最初的成果。
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在欧阳予倩老师亲自参加和指导下撰写的《唐代舞蹈》(初稿)于1960年打印成册,在第三次文代会上征求意见。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之后,由原舞史研究组的成员组成中国舞蹈史教材编写组,于1962年秋完成《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初稿)。原计划将在这部“长编”的基础上,撰写“中国舞蹈史教材”,也由于“文化大革命”,未能完成。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部“长编”,由北京舞蹈学院铅印发表,改名《中国古代舞蹈史》。因此,是欧阳老师带领我们完成了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的奠基。
在欧阳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当时研究中国舞蹈历史具有了三个方面的重要依据:一是古文献的整理;二是各代舞蹈文物的搜集与研究;三是抢救的古代舞蹈的当代遗存(即活的舞蹈资料)。这三个方面亦是我们一直未停止的工作。
第二,广取博采,实行开放式教学。
欧阳老师非常重视取得各方专家对初创的舞蹈史学的支持与帮助。由于他德高望重,受到许多人的尊重与爱戴,因而能请到上述专家来教导我们。有时,还请专家到自己家的客厅作专题讲座,甚至写信嘱托或亲自带我们到其他老师家去求教。记得欧阳老师为了让我理解戏曲舞蹈的发展脉络,亲自带我去拜见周贻白先生;为了让我能更多地了解明清时期民间舞蹈在社会生活中的状况及有关著作,亲自带我去拜见对明清著述收藏丰富、研究极深的专家阿英老师。另外,音乐史专家杨荫浏、美术史专家王逊、文史专家沈从文、戏曲学专家及藏书家傅惜华等,对我们搜集舞蹈文物、文献,都给予了许多帮助。我们的舞蹈史资料陈列室中,就有他们提供的展品,其中包括不少珍贵典籍。为了帮助我们研究唐代名舞——《兰陵王》,欧阳老师特请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到欧阳老师的客厅,为我们表演从日本学回来的唐传日本雅乐《兰陵王》。
第三,传播中国舞蹈史知识的方法和态度。
欧阳老师告诫我们:古代舞蹈文献史料大都是古汉语,要使人听得懂,听得有兴趣,首先自己要把史料吃深吃透;要用现代汉语,特别注意要用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不要自己还没弄懂,就搬一堆古文、一堆原文去吓唬人,以此来表示自己学问高深,这种态度要不得。要诚心为听众(包括学生)服务、为读者服务,要设法让他们听懂、读懂,这样才能传播舞史知识,宣扬我中华民族灿烂的舞蹈文化。在数十年的研究与撰写舞史专著及论文中,我牢记老师的教导,要求自己狠下工夫,一点一点、一段一段地啃,啃不动就查书或请教老师。近60年来,我不断地努力着,不敢懈怠,希望自己的讲课和著作能让人爱听爱读。甚至在“文革”中家庭受到很大冲击的艰苦的日子里,也魂牵梦绕地惦念着自己的专业,与爱人一起节衣缩食,搜集资料,因而当“文革”结束后,我即能够很快地投入舞蹈史的研究工作。
三
如前所说,是欧阳老师特请北京大学的阴法鲁老师来指导我们完成了《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的编辑工作。这是1956年“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小组”建组后的第一项中心任务。《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中的音乐史料按歌曲、器乐(含弹拨乐、吹奏乐、打击乐)分类,舞蹈按唐人原分类(含健舞、软舞、大曲、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等),还有服饰类等,汇集分编。这一浩繁的资料整理工作和成果的发表为中外研究唐史的学者们提供了很大方便,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和欢迎。据阴法鲁先生讲,他到美国讲学时,看到美国的大学及大图书馆里都藏有此书。
此后,数十年间,我不断向阴老师求教,而老师对我这个底子薄、基础差的学生,从来都是那么亲切、耐心,教我查核资料,追根溯源,找出正确答案。每次“丰收”后告别时,阴老师总会说:“有问题就来问!”可我这个不懂事的学生,却从来没有交过一分钱的学费。
1983年,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编委之一朱维铮教授邀请我为《中国文化史丛书》撰写中国舞蹈史部分,即后来的《中国舞蹈发展史》。当我写到第二章“夏商奴隶制时代舞蹈的发展”时,内容涉及甲骨文中有关舞蹈的记载。对甲骨文,我毫无研究,从来都只能参考甲骨文专家的研究成果来解释有关舞蹈的记载。关于舞和巫的解释,我仍然引用陈梦家先生的说法:“无、舞、巫三字同形、同音又同义。”这一论点在学术界广泛引用,有的人还进一步认为:舞、巫即是同一字,巫就是最早的专业舞蹈家,等等。对此,我心中实在没有底,于是跑去向阴先生求教。阴法鲁先生看了我的初稿后说:“关于甲骨文中‘’(舞)和‘’(巫),目前甲骨文专家有了新的看法。‘’是舞字,但不是巫字。巫字是另外一个字,字形是‘’。直到战国时代的青铜器上还是将巫字写成‘’。你等几天,我再去找一下我们北大的裘锡圭先生,他是著名的甲骨文专家。问后,我再告诉你。”过了两三天,阴先生告诉我:裘先生和其他甲骨文专家,找出了更多证据说明舞‘’与巫‘’是两个不同的字,叫我赶快改正。接着,我又在友人柴剑虹的帮助下,找到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高明编的《古文字类编》和1981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徐中舒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编写组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仔细查阅、学习。这两本书都肯定:甲骨文中的“”与“”是两个不同的字。这就更不能肯定巫是最早的职业舞者。在神权统治的商代,巫的地位至高无上,一切事的决策,都是靠巫传达“神”的意志。巫是靠巫术活动(包含以舞祭的手段)来维持生活,取得所需要的一切生活资料。而舞者,是处于奴隶地位的人,他们以歌舞娱人(奴隶主)的方式取得赖以生存的一切,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在河南安阳武官村殷商大墓中发现的为奴隶主殉葬的24具年轻女子骨架,身边放置了乐器和舞器,她们正是乐舞奴隶。巫人和舞者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有天壤之别。甲骨文中舞与巫字的误识,引起对历史的误解,实在应该纠正。我庆幸自己有这么好的老师,帮助我改正了这一大错。
四
1961年,乘文科教材会议的东风,舞史研究工作全面铺开。当时我们四个学习舞蹈史的学生按断代分工。我负责隋、唐、五代和明、清两大部分。欧阳老师让我学习周贻白老师著的《中国戏曲史长编》,不然写不好“戏曲舞蹈”一章。因为自从戏曲兴起以后,完全取代了隋唐时代歌舞艺术在表演领域独领风骚的地位,无论宫廷、民间、城市、乡村,戏曲都是最受人欢迎的表演艺术。舞蹈作为独立的表演艺术在清代是相对衰落了。写明清舞蹈史,不弄清融入戏曲中的舞蹈,简直就没法写。
戏曲中的舞蹈,寻其源,一是继承前代传统,二是汲取当地民间乐舞的丰富滋养。戏曲继承前代舞蹈传统的例证很多,南宋官本杂剧段数中保存了许多唐宋大曲、健舞、软舞的名目。战国、汉、唐出土文物中,保存了各代舞蹈形象,如“弓箭步”“骑马蹲裆势”“顺风旗”“托掌”“按掌”以及各种舞袖姿态,都与今天戏曲中舞姿身段十分相似。又如古文献中描写舞蹈技巧的“翘袖折腰”,腰肢柔软可入怀袖,其轻盈之态如“萦尘”,似“集羽”,“身轻若燕能作掌上舞”,“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的审美情趣,在戏曲舞蹈中随处可见。
戏曲广泛吸收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从清代直至近、现、当代形成的地方戏,有不少是直接从各地民间歌舞发展演变而成的。戏曲中蕴含丰富的传统因素和民间舞蹈成分,是有目共睹的。在探索研究明清舞蹈史的过程中,周贻白老师给予了我耐心的教导与热情的帮助。在我探索明清戏曲舞蹈的训练方法、艺术和技术特色,以及舞蹈如何巧妙地组合在戏曲表演中表现思想感情等方面,周贻白老师的著作是指引我去研究的明灯。不仅如此,他还将珍藏多年的宝贵资料给我参用。
那天,我走进老师的“书房”,在那间堆满书籍的平房里正伏案写作的老师就放下手中的笔,从抽屉里拿出一沓发黄的毛边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毛笔字,标题是《夜奔身段谱》。他说:“这是一份清代传下来的‘身段谱’,这是原件。另外,我给你抄一份,你拿去好好研究研究!”我如获至宝,心中感激不已,连声地说:“谢谢您!谢谢您!您这么忙,还帮我抄资料。”我看着他疲倦又有些苍老的脸,眼泪差点流了出来。
这份“身段谱”是将唱词、曲牌、身段舞姿、地位调度等连在一起杂写的。其中有不少戏曲动作术语,文字简练、清晰。为了考证戏曲舞蹈的传承与变异关系,我拿着这份“身段谱”去找北方昆曲院的白士林同志(他曾与我同在民族歌舞团工作过)。他是梨园世家出身,伯父白云生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祖父白建桥是前代名昆;曾祖父是清代著名演员,曾当过醇亲王府的戏班班头。白士林演的《林冲夜奔》是他祖父白建桥亲授的。白士林一面看着“身段谱”一面做动作,走地位。最后,他说:“这份‘身段谱’所写,与我曾祖父所传《林冲夜奔》身段差异很小,基本动作与主要地位调度都一样。所不同的是过去的表演拘谨些。现在更开朗明快,更注意舞蹈的美感。”这一事实证明:经过千锤百炼创造的保留剧目,在上百年漫长岁月中,代代传承,较完整地保存了它们的原貌,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与研究。
我把周贻白老师给我的珍藏多年的《夜奔身段谱》经过整理,刊载在我写的《中国舞蹈史·明清部分》中。该书发行后,我多次听到同行说:“这份‘身段谱’太珍贵了,对我们研究戏曲帮助很大。真该谢谢老专家周贻白先生的无私奉献。”
五
在我学习研究中国舞蹈史的数十年中,还得到了杨荫浏老师许多的指教、帮助和鼓励。1978年,杨先生是音乐舞蹈研究所的所长。我独立完成第一本舞史著作《中国古代舞蹈史话》,在请杨先生审稿后,他应邀为我写了序言。他写道:“本书接触的书本资料相当全面,涉及的形象资料相当丰富,而且以舞蹈的实践经验为背景,对于这些资料往往能有比较细致的了解。”还写道:“‘四人帮’的干扰,十分可恨。他们非但阻碍了各种文艺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更恶劣的是用错误思想来毒害研究人员的头脑,致使许多研究人员放弃踏踏实实的作风,去跟着他们说大话,讲空话,甚至养成习惯,一时不易清除。本书写得比较实事求是,完全摆脱了‘四人帮’的影响,也是十分可贵的。”20多年来,我铭记杨先生的教导,坚持发扬好学风,清除坏学风。杨先生的告诫,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我深知自己做学问的底子薄,基础差,只有加倍努力,才能适应新的工作。只要知道杨先生讲课的消息,无论多远,也要赶去听。当时音乐研究所在离城很远的西北郊十间房,我们经常是一大早就赶头班车去听课。杨先生讲课总是娓娓道来,像和学生谈天一样。有时他斟字酌句,一面沉思,一面将他思想深处的东西诉说出来,让人必须全神贯注地听,不然就不能完整地领会他组织得十分严谨的语言所表达的深刻思想。
杨先生治学十分投入,一天当作两天用,总是睡一会儿后半夜起床,写累了,再睡一会,起来再写。杨先生超人的勤奋,使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提纲及部分章节的油印本,都在公开发表前送给我们参考,成为我们写《中国舞蹈史》的范本。中国古代“乐”,原本包含音乐、舞蹈、诗歌。杨先生写的音乐史中,经常会提到舞蹈史,从远古到唐代,许多史料是共同的。特别是唐与宋的宫廷燕乐及其他表演性乐舞,都是乐舞并重,史料共存的。我们从杨先生的音乐史中,不但学到古代舞蹈发展的大致脉络,更得到许多有关舞蹈史的史料线索。杨先生为研究舞蹈史的年轻学者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们研究中国舞蹈史铺平了道路,我们是站在前辈学者的肩上攀登的。
杨先生常在家中给研究生上课,黄翔鹏先生常帮他写黑板,我也常常跑去旁听。有一次我向他请教甲骨文的“舞”字时,他拿出数十年前抄的一份笔记,发黄的毛边纸上,工整的竖行毛笔字,清晰地抄录了《殷墟书契后编》关于“伐祭”的甲骨文及其解释,《周礼》关于“舞雩”(求雨舞)的资料,陈梦家关于无、舞、巫三字的解释,《殷墟书契考释小笺》等书中有关商人乐舞活动的记载。这份笔记凝聚了老师多少心血啊!我一边翻,一边这样想。杨先生说:“你拿回去抄吧!这些书不大好找。”我心中激动不已,这是老师给我的一份重重的馈赠和无限的信任。如今,杨先生已经远去了,我还完整地保存了这份抄录的笔记。十年浩劫,数次抄家,它都幸免于毁。
有一次,我去音乐研究所资料室查资料,杨先生拄着拐杖进来,当时他行动已不方便了,还念念不忘藏了许多珍贵音乐资料的资料室。这里倾注了杨老师及许多同志的多少心血与劳动啊。杨先生好像不是来查资料的,他慢慢地环视周围,那份深情的眷恋,从他的眼里流出。看着他,不觉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当我送他回家后告辞时,他和夫人曹先生都说:“就在这儿吃了中餐再走!”是邀请,也是命令。我顺从地坐下。饭菜十分简单,两老生活一向如此。每月的收入,大概都拿去买书了。
大约是在1983年冬,杨先生的病重些了。探视的人,也有所控制。我有幸得许进房去看杨先生。大概是因为讲到专业,杨先生的精神似乎又好了起来,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清商乐”与“南音”及江南民歌的共同特点,还说音乐界不应去批评某位歌唱家比较重抒情,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软绵绵的调子,即常用“气声”的处理方法唱歌,等等。他说:“这些曲调的特点和歌唱的处理方法,本来就是我们民族固有的传统,不必横加指责。”虽然在病中,他仍在关心、思考当时音乐界的事,也表现出杨先生研究史学却十分关注当前音乐界的动向。
如今光阴和青春都远远逝于身后,但先生们的言谈话语,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年近九旬的我写下的是向大师学习过程中的点点滴滴的故事,这些故事数十年来一直铭刻在我心中。他们留给我们的,不止是史学知识、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用其一生的行动教导后人,教我们如何去做一个道德、学德都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