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前,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
2016-03-31李迪
2016年春节前,老邻居李丹忽然来电,说他搬迁新居了,收拾东西时意外发现了我的一封信。
你猜谁来的?
谁呀?
谢曼诺夫!
哎哟!久违的名字如闪电,往事瞬间重现——
1984年,春寒。我结束了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的采访生活,开始一部小说的写作。
七处位于城南偏僻之地,地名吓人,叫半步桥。这里是预审处,也是看守所,被枪毙的人从这儿直接拉到刑场。是死是活,只差半步。在笼罩着恐惧与神秘的小院,在低矮昏暗散发着故纸霉气的档案室,一份死囚卷宗让我的心收紧!一个女人凄楚哀怨的声音自卷中传出,呜咽地向我讲述了一个爱恨交加的故事。爱她的人以死向欺辱她的人复仇,她为爱她的人拒不吐实,宁愿赴死!
我还原了预审室里的惊心动魄,完成了这部作品,发表在1984年的《啄木鸟》第4期。篇名:《傍晚敲门的女人》。
第二年,年初。《啄木鸟》编辑部转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文化处的信函,说谢曼诺夫要翻译这部作品,请我提供一份自传。
谢曼诺夫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东方文学系主任,1933年出身于书香门第,母亲是圣彼得堡师范学院教授、契诃夫研究专家。受母亲熏陶,他从小喜爱文学,中学就获得了可以选择国内任何大学深造的金质奖章。最终他选择了圣彼得堡大学中国语文系,并留学北京大学,毕生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研究和中苏文化交流,德高望重。有这样著名的教授主动来联系翻译,我很激动,马上准备好自传,并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谢曼诺夫教授:
您好!《啄木鸟》编辑部转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文化处的来函。阅后,得知我发表在《啄木鸟》的中篇小说《傍晚敲门的女人》将由您和您的学生卡雷莫夫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我十分高兴!同时,我要感谢您和您的学生卡雷莫夫,由于你们的辛勤劳动,使得我的这部作品能奉献给苏联的广大读者。您提出要我的自传,以便附在卷首,我已经请《啄木鸟》编辑部转给您。
我知道您是苏联著名的汉学家,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已有三十多年了。早在五六十年代,您就翻译出版了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老舍的《猫城记》等多部著作。近年来,您又翻译了古华的《芙蓉镇》和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这部中篇小说,能由您和您的学生翻译出版,我为此感到荣幸!现在,这部小说的单行本已经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我将通过驻苏使馆文化处转送你们留做纪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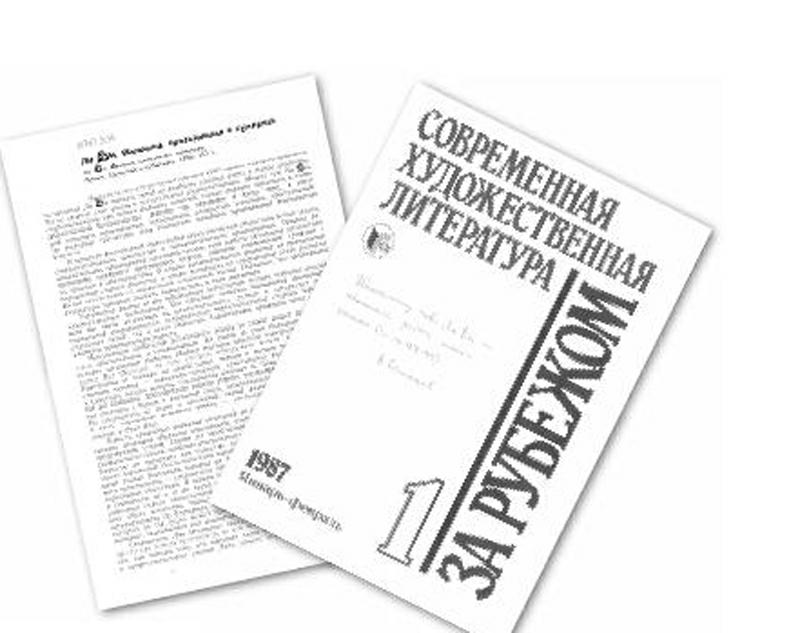
如果来得及,请将原书最后一节中张处长讲丁字街凶杀案是“一个法盲的悲剧”,改成“一幕不该发生的悲剧”。因为丁力不是法盲。“法盲”是目前我国流行的词汇,指不懂得法律的人。而书中的丁力是懂得法律的,在作案时还企图以时间差来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称他是“法盲”不准确。这是我原稿中没有的。
此致
敬礼!
李 迪
1985年2月1日
信及自传由《啄木鸟》编辑部交外交部代转,不久,我就收到了谢曼诺夫的回信:
尊敬的李迪同志:
昨天,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文化处转来了您的信和《啄木鸟》编辑部提供的您的自传。十分感谢您的来信和这些自传材料,这对我们的翻译工作将起到有益的作用。特·卡雷莫夫准备着手翻译您的作品。他是我的一位即将毕业的学生,专门研究中国现代中篇小说。我想译后帮他修改一下,尔后送给“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您的这部反映法律与道德题材的优秀作品由该出版社出版是再适合不过了。鉴于出版社工作繁重,您的这部作品的俄译本问世还需要一段过程。
在您的这部小说俄译本出版之前,我们还想将它在杂志上发表。这比出书要简单得多。如有消息,我将及时通知您,并寄去样本。请您耐心等待。您看如何?至于您信中谈的法律知识问题,一定查核。
今年底,我可能去北京,届时将很高兴见到您。请原谅,此信我是用俄文写的,因为我的中文书写不如会话。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莫斯科大学教授 弗·伊·谢曼诺夫
1985年5月15日
正如信中所说,当年冬天,谢曼诺夫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北京,住在北大。中国作家协会安排我前去见面。我是跟作协副主席冯牧一同前往的。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邀我坐他的车。会见亲切难忘。身材高大而儒雅的谢曼诺夫流利地说着中文,甚至有点儿京腔。听说我高中学的是俄文,他笑着让我讲几句。我背了一小段儿歌颂苏联女英雄卓娅的课文,结巴得不成句,相信他根本没听懂。之后,他说,你的作品正在翻译中,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卡雷莫夫写了一篇评论,将发表在《国外现代文学艺术》。他写得很好,我只改了几个字。
讲到这儿,他忽然盯住我,李迪同志,我看出这不完全是小说,你能告诉我,女主人公真是自杀的吗?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我不想说出事情的真相,因为那太残酷。
谢曼诺夫还是盯着我。眼睛蓝蓝的。
他不相信。但也没再追问。
一年后,《傍晚敲门的女人》分别有法国、日本、韩国的翻译家前来联系翻译出版。同时,我又获得去日本留学的机会。虽然年纪不小了,又有妻儿,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能有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机会也实在太有诱惑。我毅然决定前往。甚至丢掉了国内大出版社的正式工作,从此后成了漂泊世间以写作谋生的自由撰稿人。现在回头想想,也真够壮士断腕的了。说老实话,当年如我者寥寥。我去日本留学了。临走前,我收到了谢曼诺夫委托大使馆转来的信和杂志。我敲开邻居李丹的门,请他帮助翻译。
李丹时任《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自学俄文多年。他正要出差,说回来就翻译。结果,他前脚刚走,我的签证就下来了。于是,忙忙乱乱,东渡扶桑。
时光荏苒,红尘滚滚。这件事,我忘了。李丹也忘了。还好,老天没忘!
2016年春节前当我接到电话,疯跑去见李丹,再次打开来自莫斯科的信和杂志,时间已过去整整二十九年!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这样的问候语也已成为历史。
尊敬的李迪同志:
正如您所见,预定计划的第一部分书评已经完成,但第二部分小说翻译,看来如我预想的那样,要困难得多,卡雷莫夫还在翻译。如果有新消息,我会通知您。如果您能再提供几部新颖有趣的中文推理小说,我将会很感激。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谢曼诺夫
1987年5月11日
随信转来的苏联《国外现代文学艺术》杂志,是1987年第1期。
谢曼诺夫精心地在封面上注明:
“尊敬的李迪同志,我的学生的短作,见48-49页。弗·谢曼诺夫”。
同时,他还对内文中的一处印刷错误用笔做了修正。字里行间,渗透着老人的爱!
卡雷莫夫的评论全文如下——
中国
李迪 傍晚敲门的女人
北京 群众出版社,1985年,175页
中国文学评论界认为,北京青年作家李迪的这部小说是最成功的侦探题材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已经拍成了电视剧并上演。与此同时,已经发表了多部中长篇小说的李迪,开始关注“公安”这一主题。在中国,旨在揭露刑事犯罪的作品,主题被称为“公安”。近三四年,类似作品的数量在成倍地增长。
在全面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社会面临着完善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除立法措施外,人民法制教育的五年规划也在实施,使公民广泛了解其权利和义务是该项规划的组成部分。全国大规模开展了打击违法犯罪,以及在中国发展现阶段出现的背离正常社会生活行为的活动。显然,侦探文学在该活动中能够起到重要的使命作用。
当然,远不是所有已发表的侦探题材作品都符合很高的艺术要求。供消遣的侦探读物已经开始转向尖锐的社会问题。这类文学揭示了个人与整个社会相互危害的一面。尽管只是一部分侦探读物在转向,但这一转向也是值得高兴的。《傍晚敲门的女人》就是该进程中的典型范例。
对于许多喜欢侦探题材的小说迷来说,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那么独特和惊险。在北京的一处住宅里发生了一宗神秘的谋杀案,侦察员发现死去的电器公司总经理王少怀身中八刀。犯罪分子没有留下任何罪证,犯罪动机不明。目击者提供的唯一线索是,有一个女人在傍晚时敲了这处住宅的门。侦察员找到了这个女人,她叫欧阳云,是电器公司医务室的医生。她应该是最后一个见到受害者的人。欧阳云很快承认了与王少怀的隐秘关系,同时承认因为王少怀的背叛,她恨之入骨所以杀了王。但是,预审员梁子不相信她供认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通过预审和再侦察,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凶手——送煤工丁力。丁力疯狂地爱着欧阳云。
小说与其说是由于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读者,不如说是由于人物的完整形象、心理描写、清晰结构和缜密风格。现代推理小说的不足之一就是人物的脸谱化,尤其是中心人物——密探或侦察员。很多作品常常表现他们不吃、不喝、不怕累、受伤仍坚持。读完这样的作品,读者脑子里只剩下大檐帽上熠熠生辉的帽徽。但是,这部小说中的梁预审,则有着多面的、甚至有时是矛盾的性格。首先,作家赋予他天性温柔和仁慈的品质,但同时也能在他身上感受到公安部门专业人员的严谨作风。作家不加虚饰地勾勒出梁预审思考、习惯、行为的生动细节。中国公安文学评论家杜元明认为,作为本书的主人公,梁预审关爱被审问对象的孩子,以及对这个不幸的女人的同情,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在小说中,欧阳云的不幸,以及她对自己孩子的疼爱的确令人动容。
梁预审忘我地忠于职守,他不仅仅将自己的职责理解为逮捕犯罪分子,而且把探寻社会不公正的原因和帮助那些由于不懂法而犯法的人视为己任。这宗刑事案件的最终侦破,取决于梁预审的生活经验和职业能力。他没有直接的犯罪证据,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推理案情:“摆在我面前的只有这些案情报告、照片以及法医认定的管叉类作案凶器等文字资料。仅凭这些,不可能真正认识案件,还需要我的想象力能通过时间和空间,勾画出案件的整个轮廓和几个关键性的具体情节。以便在审讯中能胸有成竹地及时核对罪犯的供述,揭破罪犯的谎言,弥补占有材料少和缺乏感性认识的不足。”
这部小说的语言很精彩,贴近生活的对话与卷宗内的文字材料交替进行。作家巧妙地运用“意识流”手法,描述主人公的思考及对往日生活的回忆。
主人公梁预审对往日生活的回忆,完美地起到了结构小说的作用。每一次,当侦查进入死胡同时,梁预审的脑海中都会再现十年前的往事。十年“文革”(1966-1976)期间,他被发配到边疆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劳动。在饥寒交迫的冬日,一只聪明的狐狸时常来拜访村子,偷走农民的鸡鸭。屡次徒劳的围剿后,梁预审成功地将它围捕。就在这时,他发现伤痕累累的狐狸快要临产了,不忍心再伤害它。他把狐狸带回家,打算养好伤后将它放走。可是,过了一些天,狐狸咬断了自己的伤腿,失血过多而死去。因为它看到爱它的公狐狸企图救它而可能被围捕。悲情唤起主人公和猎人们强烈的怜悯与自责。这个情节,表现了作品从现实生活转换到传说般的故事里,如中世纪小说(下转59页)(上接30页)中经常出现的狐狸变成美女。注重对传统形象的运用,使用民间熟知的象征和格言以丰富内容,首尾衔接的严谨逻辑与丝丝入扣的动人细节,都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关键。
中国文学作品中有一个常见的主题:女性的悲惨命运。欧阳云的丈夫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病得很厉害,她七个月都寸步不离丈夫的病榻,而她的工资只发过一次。家里很快就穷得交不起孩子上学的钱。丈夫去世后,欧阳云所在公司的总经理王少怀发誓会爱她,承诺帮助她并以后娶她,但是却欺骗了她。欧阳云识破后想要嫁给丁力,她去找王少怀批准结婚(中国有结婚需要单位批准的规定),却被王少怀拒绝了。
作家在小说中发问,为什么高层领导长期明目张胆地滥用职权却可以逍遥法外,尽管有足够的证据将他绳之以法。在对欧阳云的一次审讯中,她说:“我起先想告他,但一想我们的事说不出口,我到哪儿去告呢?我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再说,就是告下来了,他顶多挨个处分,照样当他的官,可我却完了。名声完了,人完了,工作也完了……”
正是这样的不公正,促使送煤工丁力产生了残忍的报复心理。
小说的结局,为欧洲人展示了出其不意和与众不同的悲惨。似乎,送煤工应该得到一些宽恕,但根据中国的刑法,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而欧阳云在知道判决后自杀了。
苏联目前既没有出版过中国任何现代侦探作品的译著,也没有出版过关于这个主题的任何研究著作。希望苏联读者通过这部作品能日渐了解中国现代侦探推理小说。
特·卡雷莫夫
抚摸二十九年前的来信和杂志,细读其中的每句话,我泪眼模糊。
李丹说,过了这么久,请原谅。
我说,不,不存在。但我不能原谅自己!
谢曼诺夫教授已于2010年逝世于德国黑森。
高大而儒雅。眼睛,蓝蓝的。
责任编辑/张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