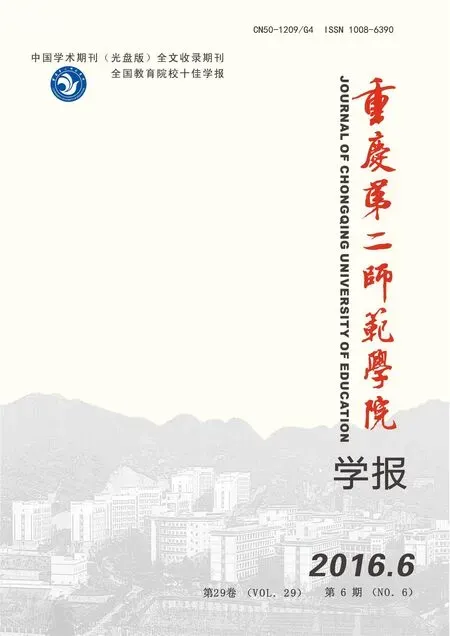论《搜神记》的生死形态转化
2016-03-30莫芸
莫 芸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论《搜神记》的生死形态转化
莫 芸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搜神记》披着“志怪”的外衣,对现实人生的生死问题给予关注,描述了人死后的三种主要情形,即人死成神、人死复生、人死为鬼,并通过描述人、神、鬼三种形态的转化,突破生死之间的界限,凸显“人”的勾连作用,体现了作为史官的作者干宝对现实人生的“人性”关怀。
《搜神记》;生死形态;转化;人性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人们的生死观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而人的生死伴随形态的变化,对生死形态变化的关注是生死观形成的重要依据。生死问题是人类从古至今永恒不变的讨论主题,尤其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人们的生命意识更为强烈。“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流露的生命宛若浮尘的飘忽不定之感,是处于战乱时代人们心理的真实写照。干宝所撰《搜神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志怪小说之一,记载了各种光怪陆离的神异鬼怪故事,而在其“志怪”的外衣下,饱含对现实人生关注的热情,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其中许多关于人的生死的故事,试图通过生死形态的转化来面对和解决生与死的问题。
一、生死形态转化之表现
生死问题是哲学上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人死后将去哪里,成为何物,是古往今来人们都关注和渴望解决的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对“死亡”做一个界定。本文中的“死亡”是指人作为一种生命形体的存在,其生命体征消失的自然过程。《搜神记》在对各种神奇怪异之事的记载中,涉及对人死后的种种描述。它对人的生死描述主要表现为生命形态的转化,即人(形体)、神(神灵)、鬼(鬼魅)三种形态的转化。
(一)人死成神
人死成神,即由人到神的转化形式。需要说明的是,一般认为古时候鬼、神不分,但本文根据《搜神记》的实际情况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这里的“神”主要是指具有神力的神灵,他们通常能够通过神力对人间降下巫祝,对人间的生活进行干预,人们通过祭祀神灵以示顺从并寄托希望,这种人神交流方式具有原始巫术意味。而后文的“鬼”则并不具备如此神力,是人死后灵魂无处安息的鬼魅。《搜神记》记载了多个人死成神的故事。如“冯夷”条记载冯夷渡河溺死,天帝署他为河伯。冯夷溺死而被封为河伯,由人经死变成神,进入神灵世界。这是第一种,人死由他人署为神。第二种,自我预知成神,主要有“刘玘”条与“蒋山祠”条。“刘玘”条记载刘玘自我预知自己死后会成神,一夕饮醉后无病而卒,其棺自行成冢,民为其立祠。“蒋山祠”条写蒋子文预知自己当为神,对故吏说:“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值得注意的是,蒋子文不仅预知自己死后当为神,并且要求人们为他立祠,不然则要下巫祝惩罚下民。百姓未为其立祠,于是降下巫祝引发虫灾、火灾。由故事前文叙述可知,蒋子文“嗜酒好色,挑达无度”,而死后成神仍然不改这种性格,说明神灵世界也存在品行不端的神,或者说,神灵世界乃是现世人生的投影。与蒋子文死后仍成品行不端的神相对,“丁姑祠”条则显示了丁姑善良的品德。丁姑生前被严酷的姑婆折磨,苦不堪言自经而死后有灵响闻于民间,发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丁姑深感人间妇女劳作的辛苦,于是降下巫祝令自己死去之日为休息日,使妇女休息。丁姑推己及人,并且懂得报恩,她的善良品德一直贯穿于生死前后人与神两种形态,体现出人神的一致性。
由此观之,人死成神只是生命形态发生了转化,精神内质不因形态转化而改变;由人到神,本质上并无变化,而死亡只是一种生存状态和形式的改变。
(二)人死复生
《搜神记》生死形态转化的另一种方式是人死复生,即由人仍到人的转化形式。
《搜神记》卷十五集中记载了人死复生的故事,写的都是人死后由于各种原因、各种方式得以复生。其中,“王道平”“河间郡男女”“贾文合”三条记载的故事与婚恋有关。前两条皆写男女因情愿结为夫妇,而后男子从军征伐,还家后女子已死,而男女双方的情感之精诚感于天地,使得女子复生还阳与男子结为夫妇。“贾文合”条则记载男主人公贾文合得病而死,实为司命神所差小吏召错人,于是遣送贾文合还阳。此后,贾文合到郭外树下宿,梦见一少女独行,想与之结成夫妇,女子以贞德为由拒绝。而后贾文合梦见停丧之女子苏醒,便至女子所在之地拜谒其父,问其女是否死而复生,结果应验,于是女子的父母将其女许配给贾文合。在其他人死复生的故事中,有自我预知复生的,如“史姁”条记载史姁死时言“我死当复生”,“颜畿”条记载颜畿死后托梦于其妻云“吾当复生,可急开棺”等;还有因误死而还阳的,如“贾文合”条与“李娥”条都记载贾文合、李娥因司命神错召而死,经核实后被遣送还阳。在这一卷中,值得注意的是“杜锡婢”这则故事:
晋世杜锡,字世嘏,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余年,开冢袝葬,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目,有倾渐觉。”问之,自谓当一再宿耳。初婢埋时,年十五六。及开冢后,资质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1]186
这则故事与《晋书》记载干宝的父亲死后,其母亲将父亲的宠婢推入墓中殉葬,后十余年开墓其婢尚生之事相似。关于此事的真假我们暂不作评论,当时人们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因此史书中出现此类记载符合当时的社会观念。由此便可推测,干宝记载这样的故事或与其人生经历有关,亦可看出干宝对于人之“生”的关注。
除卷十五外,卷六中也载有三则人死复生的故事,分别是“人死复生”“桓氏复生”和“陈焦复生”。这三则故事里人死复生的现象都与灾异祥瑞相关,涉及国家政权的建立。“人死复生”与“桓氏复生”条记载的都是汉代发生的事,前者为汉平帝时期,后者为汉献帝时期,且两者记叙人死复生的现象,都是不祥之兆。“人死复生”条叙女子死而复生,预示不祥,其后有王莽篡位。而“桓氏复生”条叙桓氏死而复生,其后有曹公由庶士起。“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厥妖人死复生。”两汉时期谶纬盛行,灾异说兴起,人们普遍认为万事万物都依照既定的规律运转,若出现违背常理之象,则有灾异之事发生。《搜神记》卷十二有相关的论述,如“五气变化”条曰:“天有五气,万物化成……五气尽纯,圣德备也……五气尽浊,民之下也。”又说,“应变而动,是为顺常;苟错其方,则为妖眚。故下体生于上,上体生于下,气之反者也;人生兽,兽生人,气之乱者也;男化为女,女化为男,气之贸者也。”便是这种思想和风气的体现。而“陈焦复生”记载的是吴孙休永安四年,陈焦死而复生,预示的是祥瑞之兆:“乌程侯孙皓承废故之家,得位之祥也。”此时为三国鼎立时期,汉王朝已然灭亡,国家处于分裂局面,曹魏、东吴都是臣子以下至上而称帝,这时便要主观回避汉代时人死复生“至阴为阳,下人为上”的不祥之兆,进而改不祥为祥瑞,即“陈焦复生”条所记载的孙皓得位之祥,实际上,这也许是他们为其政权得以立足而敷衍的正当理由。
综上所述,人死之后的另一种形态转化即复生,从人仍到人的转化,生命只是经由短暂的离开而重新复还,两者本质上没有区别。
(三)人死为鬼
《搜神记》对于人死后的另一种描述是人死为鬼。卷十六第一则故事“疫鬼”明确指出人死为鬼:“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从《搜神记》的记载来看,人们对于鬼魅之事通常抱以怀疑的态度,往往欲通过试验以验其真。而以鬼托梦于人来反证其真是《搜神记》多次提及的一种方式,比较典型的有“蒋济亡儿”与“文颖”两则故事。“蒋济亡儿”记载的是楚国人蒋济的儿子夭亡,其妻梦见亡儿向她托梦诉苦,说自己在地下做事憔悴困苦,请求父母帮助其重转差事。蒋济听闻认为此为梦,不足为怪。其母云:“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适!”于是验之为真,遂帮助其亡儿转为录事。另一则故事“文颖”记载的是文颖过界止宿,梦一鬼因为其棺木溺水朽坏而请求文颖为其改葬他地。文颖醒后对同行之人叙说了梦境,同行皆以“梦为虚耳,亦何足怪”之辞回复。文颖再眠又出现相同梦境,醒后云:“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于是发掘其鬼之棺木,果然朽坏,为其移棺,使之安息。
不仅如此,在这些故事中,人死后不仅变成鬼,还能与活着的人相通,这类故事较为典型的有“紫玉”“驸马都尉”“汉谈生”“崔少府墓”等。以“崔少府墓”为例,讲述的是范阳人卢充进入离家三十里的崔少府墓中与少府小女幽婚结为夫妇,三日之后,崔对卢充说:“君可归矣。女又娠相,若生男,当以相还,无相疑;生女,当留自养。”卢充出墓。四年后崔氏女抱儿还充,赠金碗与诗后乃去。人们初闻怪恶,传省其诗后,皆“慨然叹死生之玄通也”。这类故事与人死复生不同,女子死后化鬼未还阳,仍能与人通婚生子,说明时人相信人死只是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人与鬼在精神本质上并无区别。
《搜神记》关于人死为鬼以及人鬼相通的故事还有很多,此不一一赘述。这些故事从侧面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性,是战乱使得人鬼相殊,骨肉分离,夫妇离散,体现了人们对生的渴望以及对战争的憎恶。
二、生死形态转化之成因
由前文可知,在《搜神记》中人的生死形态表现为三种,即人、神、鬼,与此对应,生死形态的转化也有三种,分别是人死成神、人死复生、人死为鬼。这三种生死形态转化的成因包含历史、现实的因素。
(一)历史依据
首先,从前文可知,《搜神记》生死形态转化形式之一是人死成神,而神主要是具有神力的能对人间降下巫祝的神灵。关于人神之间的关系,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有相关论述。《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论绝地天通时曾说:“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2]623本来民神不杂,各司其职,秩序井然。但到了少皞衰落的时候,南方九黎破坏已有的秩序,地民与天神混杂相扰,不可辨别名物。一方面,可以看出古人认为先民们曾经历过民神杂糅的局面,即民神不分,互相混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死成神之由人转化为神可能与早期民神杂糅思想有关。此外,《尚书·盘庚》的有关记载更能说明问题:
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予丕克羞尔,用怀尔然。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
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3]353-356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盘庚托祖宗神灵来劝服百姓同意迁都,从中可看出,先王虽然已逝,但却作为神圣的神灵存在着,并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神力,仍然统治着万民的祖先与在世的君民。这说明神灵具有对现实世界的裁决权,是商代天命观中人神同构思想的体现。由此可见,《搜神记》关于人死成神的记载并非凭空而来,实有其历史的依据。早期的人神同构思想,经过后世的发展,演变为除君王外,其他人也有可能在死后飞升成神,并具备干预现实的神力。
其次,人死复生现象在古书中也有零星记载。《山海经·海外北经》云:“无臂之国,在长股东,为人无臂。”[4]229郭璞注:“其人穴居,食土,无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百廿岁乃复更生。”[4]230另外,《山海经·大荒西经》亦云:“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4]416可见早在《山海经》时代就有人死复生的观念。此外,《左传》也有关于人死复生的记载:“晋人获秦谋,杀诸绛市,六日而苏。”[5]696由此可见,在《搜神记》之前人死复生的观念就存在了,《搜神记》关于人死复生的记载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观念。
第三,人死后变成鬼,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由来已久,也更为常见。《礼记·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6]796明确指出人死为鬼。又云:“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6]797即无宗庙的庶民死后其魂魄无处安息便成为鬼,“孤魂野鬼”之“鬼”或由此而来。《礼记·祭义》云:“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6]811说明鬼是众生死后所归。《说文解字》卷九“鬼部”对鬼的解释是:“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凡鬼之属皆从鬼。”[7]731鬼是至阴之物,是人阳寿殆尽,死后转化成的一种形态。由前文可知,《搜神记》对人死成鬼的描述不仅继承了古人的观念,还继化了其过程与人鬼之间的交流。
综上所述,《搜神记》人死成神、人死复生、人死为鬼三种生死形态转化的观念古已有之,其与古代的思维观念有渊源传承的关系。
(二)社会心理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很多自然现象不能通过人力解释,人们对这些现象通常抱以敬畏的心态,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控制、指导着世界,万事万物都依照既定的规律在运转。而对于人自身的生死问题,人们普遍相信人死后会变成鬼神,死亡只是作为肉体生命的终结,但生命的灵魂和精神没有终结,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九歌·国殇》云:“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8]82意思是说身体虽然死亡,但精神不灭,其魂魄也是鬼中英雄。无论是作为生之肉体,还是死之鬼魂,其精神都一以贯之。即使是以回避态度来对待生死的儒家,也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一方面,“未知生,焉知死”[9]113“子不语怪、力、乱、神”[9]72;另一方面,又“敬鬼神而远之”[9]61。这说明孔子虽然对鬼神和生死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他也承认鬼神的存在。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受玄学与佛教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如前文提到的在《搜神记》中人们对鬼神之事抱以怀疑态度,但通过试验验证了鬼神的存在。而与《搜神记》同时期的志怪小说《博物志》《拾遗记》《幽明录》等都有关于鬼神的描述,说明《搜神记》鬼神故事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因此,《搜神记》的生死形态转化的形成与古代生产力水平和人的心理思维有很大的联系,正因为有滋养鬼怪故事的社会土壤,才有《搜神记》这样的志怪小说产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纷飞,政权更迭频繁。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人们朝不保夕,生死变得无常,普遍产生忧生虑死的心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曹植《野田黄雀行》);“终日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阮籍《咏怀诗》)等诗歌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社会现实以及生死不由己的人生幻灭之感。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对生的眷恋和渴望更为强烈。如果说死后成神成鬼是人们对待死亡的普遍心理,那么死而复生则是特殊的战乱时代人们更为希冀的愿景,因为神、鬼始终是比较虚幻的概念,而只有在现实人生中才能把握生命的律动。
生命肉体有始有终,但精神与灵魂可以不灭,甚至能够冲破既有的生命规律。死而复生,只不过体现了人们眷恋生命的普遍心理。
(三)思想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和佛学的盛行,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并行的局面,它们就形神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关于“形”与“神”的论述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管子·内业》云:“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10]945大致认为人是由精和形两部分组成的,“精”是一种精细的气,可以理解为灵魂;“形”则指人的身体。西汉司马谈云:“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11]740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形神问题成为哲学论争的中心,主要体现在神灭与否的论争。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为有巨大影响的宗教。佛教坚持神不灭论,东晋名僧慧远著《明报应论》《三报论》《形尽神不灭》等,在阐述因果报应时对“形神”关系有所阐释。“夫神形虽殊,相与而化;内外诚异,浑为一体。”[12]781他认为“神”与“形”虽然各异,但仍是浑然一体的。“情有会初之道,神有冥移之功”[12]777,说明形尽而神可冥移,于是而不灭。宗炳认为:“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精粗,感而得,形随之,精神极,则超形独存。无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谓也。”[13]190而反对佛教者则持神灭论,以范缜为代表。他在《神灭论》里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14]462认为形与神并存,是统一的,形存神存,形谢神灭。他进一步说明形神并存统一,认为“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14]462。用利刃的关系解释形神之关系,形与神同存同亡。
其实,在形神问题的争论中,无论是神灭论还是神不灭论,形与神都是紧密联系的一对范畴。从形神关系的角度,能很好地解释《搜神记》的生死形态转化。南朝梁代的陶弘景说:“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15]461生死问题实际上是形神合离问题,形神合离表现为不同的生命形态。“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形神若离即形体与精神分离,表现为人死的现象,精神脱离人的形体而去,可成神灵或鬼魅。人死成神和人死为鬼的生死形态转化都可以纳入“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这个范畴。而人死复生,从人仍到人的转化过程,实际上是形神经由短暂分离而重新聚合的结果。
三、生死形态转化之意义
《搜神记》关于生死形态转化的记载以及对生死问题的探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特殊的人文意义。
(一)突破生死界限
《搜神记》围绕人的生死描述了三种形态的转化方式,分别是人死成神、人死复生、人死为鬼。在人死成神的故事中,“蒋山祠”、“丁姑祠”最为典型。蒋子山、丁姑成神后的性格品行与生前作为人的性格特征无多大区别;在精神内质方面,人神之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尤其是“丁姑祠”中的丁姑,无论是生前作为人,还是死后化为神,善良美好的品德始终贯穿其中,成为丁姑的精神标识,在其生死形态转化过程中,体现了形神的一致性。在这个问题上,人死复生从人仍回归到人的转化过程中,生命本质并无区别。在这三种生死形态转化中,人死为鬼是唯一一个两种形态之间可以进行自由相通的方式。人死后变成鬼,可以通过托梦于在世的人来表达他的诉求,使自己在阴间过得更好。而在人鬼幽婚的故事中,男女双方即便阴阳相隔,在特定的条件下,也能相恋成婚,令人“慨然叹死生之玄通也”。
在通常情况下,人死,就代表生命的结束。而在《搜神记》中人死后可以转化成三种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生死;死亡仅仅是生命的一个过程,并不是生命的终点,人还能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生与死本来有界限,而《搜神记》三种生死形态的转化突破了明显的生死界限,人与神、人与鬼之间都可互相沟通。既然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那么人们便能泰然对待死亡,对死亡也不再感到恐惧,对生命也不再患得患失。《搜神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给战乱中的人们带来了心灵的抚慰。
(二)体现人性关怀
如前文所述,《搜神记》关于人死后形态的变化主要有人成神、人复生、人变鬼三种。在这三种形式中,我们可以发现,“人”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和环节。在人、神、鬼三界中,人可以转化为其中任何一种形态,而神不能变为人和鬼,鬼能转化成人,却不能转化成神。换言之,在人、神、鬼三种形态的转化过程中,突出了“人”的重要性,“人”起着沟通联结人、神、鬼三界的作用。“两汉时期所强调的礼法名教,以及奉为典范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处世理想转而为一种推崇个人主义、自然主义的道家人生态度所取代,后人因此称之为‘人性觉醒’或曰‘个性解放’的时代。”[16]在这一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人作为“人”的一面开始被发掘,生命的意义也在乱世中更多地被关注。
此外,《搜神记》的作者干宝是一位史官,纵然此书是描写神异奇闻的志怪小说,其间也必定会融入史官对现实人生的关怀。《搜神记》之“杜锡婢”复生的故事与《晋书》中记载干宝父亲宠婢复生的事迹相似,说明干宝相信人死可以复生,这是他对人“生”之意义关注的体现。通过生死形态的转化,尤其是人死复生与人鬼相通两种转化方式,《搜神记》表现了战乱征伐时代人们对生命的渴望和眷恋。
四、结语
《搜神记》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志怪小说之一,在神灵鬼怪故事的外衣下对生命的意义进行了关注。它通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神、鬼之间的生死形态转化直面死亡,使生命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体现了生命不灭的美好愿景。概而言之,《搜神记》以浪漫的想象直面和解决了千百年来困扰人们的生死问题。干宝用他作为史官对现实人生的人性关怀,让《搜神记》在特殊的历史土壤的滋养下绽放了生命的光彩。
[1]干宝.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国语[M].陈桐生,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3]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许慎.说文解字(大字本)[M].徐铉,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13.
[8]马茂元.楚辞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0.
[12]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六十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严可均.全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4]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5]严可均.全梁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6]陈群.魏晋南北朝的生死观[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5(4):503-508.
[责任编辑 于 湘]
2016-06-25
莫芸(1992— ),女,四川广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I206.2
A
1008-6390(2016)06-008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