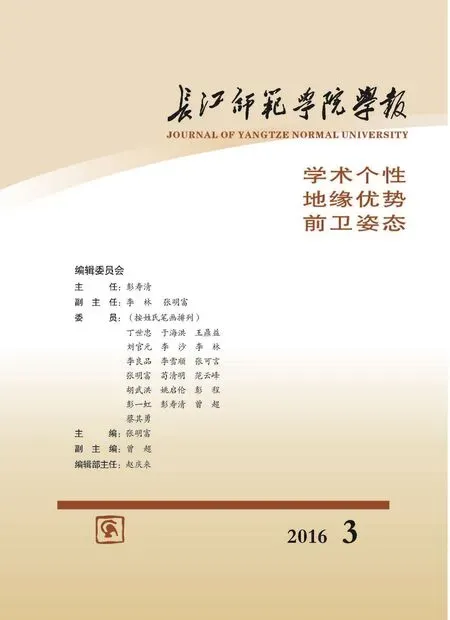人工营林业对北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2016-03-29罗康智
罗康智
(凯里学院 苗族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贵州 凯里 556011)
人工营林业对北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罗康智
(凯里学院苗族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贵州凯里556011)
明代以前,侗族内部虽有方言土语的差异,但文化的同一性程度很高。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并结合实地调查发现,随着侗族聚集地的北部地区人工营林业的发展,不仅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侗族南部地区表现出一系列的差异,而且对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人工营林;文化变迁;林粮兼营
明朝建立后,随着长江流域的区位优势在明王朝的提升,使江河沿岸大城市随之迅速地崛起,这就直接地导致了建材用的原木市场需求量与日俱增,其结果之一就是在无形中拉动了侗族地区人工营林业的发展,并进而推动了侗族内部文化的演化。在这一背景下,侗族聚集地的北部地区 (简称 “北侗”)①的稻田经营仅用于满足自己的食用,而将大量的劳动力和技术力量都投向了林业生产,最终在北侗地区形成了“林粮兼营”的生产格局。随着这一格局的形成,其社会经济文化也开始走上与侗族聚集地南部地区 (简称 “南侗”)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人工营林业的发展,促使北侗社会经济文化开始转型
首先,进入明代以后,随着从湖广经贵州进入云南驿路主干线的开通,使距离这条主干线最近的北侗居民获得了一次很好的发展机遇,即驿路的开通对北侗村寨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社会拖动力。因为朝廷的战略物资和人员的运送需要提供大量的劳役服务,这无异于给驿路周边的北侗居民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明代的阳河在当时可称得上是全国性的黄金水道,国家的战略物资和人员要进入贵州和云南都要从这条河上通过,而阳河在贵州段的河水不深,而且是逆向行舟。这样一来,内地的战略物资和人员要进入贵州和云南都必须人工拉纤,因此沿途的侗族居民只要参与这样的劳役服务就可以获得丰厚的报偿。除获得财富外,同时也会影响到这一区域侗族家族村社的建制,因为相应的侗族家族村社的寨老们甚至还有那些土司家族都可以在这一活动中占据主要地位,从而提升他们的权势和财富,并由此而造成了侗族社会组织内部的平等关系的弱化,逐步地形成了一大批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家族村社的自由从业的居民,而这样的侗族居民又与外来的汉族、土家族居民相互融合,成为整个阳河沿岸的一个特殊群体,使沿河两岸的侗族家族村社的解体速度加快。
其次,随着北侗与内地贸易的扩大,驿路沿线的居民也陆续地被吸引到商业贸易中来。明代为强化对贵州、云南的控制,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除卫所移民外,朝廷还有意识地吸引民间移民迁往驿路沿线定居,并因此而在阳河和清水江沿岸兴起了一系列具有贸易性质的居民点,这就为沿岸的居民提供了从商的好机会。与此同时,朝廷还实施 “盐引①“盐引”又称“盐钞”,自宋代以来朝廷颁发给商人的取盐凭证。“引”是指有价证券,还可以作为“代币”流通。开中”政策[2]。其具体做法是,让商人通过阳河将军事装备和人员运到贵州和云南,交给贵州和云南的卫所使用,然后从这些卫所当中领取 “盐引”作为凭证,在他们返回内地后可以凭借 “盐引”低价买进官盐然后到各地发售赚钱。这是一种有官府保护的商业贸易活动,从事这一贸易活动的官商们只赚不亏,因而能够迅速地致富。这些官商当然不能够独立地运行,在进入阳河时都得借助侗族居民提供劳役和安全保障,因而会很自然地把很多侗族居民吸引到这样的商业活动中来。应当看到,这也对侗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形成了极大的拖动力。原先处于家族村社管理之下的普通侗族乡民,正是通过这样的活动,接触到外界的人员,扩大了眼界,并与中原地区的汉族民众发生密切的联系。
复次,上述两项政策仅对北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拖动作用,尚不构成巨大的冲击,真正对北侗家族村社和侗款构成冲击的则是木材贸易的兴旺和发达,并由此引发了北侗社区内部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转型。明朝建立后,长江下游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其后首都虽然迁到北京,但经济中心一直在长江下游。随着长江下游稻田种植的日趋扩大和手工业的繁荣,新兴的集镇在长江下游和湖广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当时兴建这些大中城市需要动用大量的建筑用材,而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平原的天然林木本身不多,根本无法满足大量因城市兴起的建材需求。为此,整个大明王朝的建筑用材会很自然地需要获取大量的原木供应,偏巧北侗地区恰好是我国南方地区最好、最集中的杉木产地之一,这就为北侗地区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只要采伐木材,贩运到内地就可以获得巨额的利润。其发展结果就是使北侗地区与汉族内地的市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既支持了内地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转型。明朝时,都城先建在南京,永乐十一年 (1413年)后迁到北京。首都的两次大规模兴建,都需要大量的优质木材,而木材的来源有相当一部分就出自北侗地区。起初,明廷收购优质木材,是由朝廷委派官吏直接经办,因而这样的木材被称为 “皇木”,而采办 “皇木”则对北侗地区的社会经济转型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其原因在于,朝廷委派的官吏并不了解情况,也不能简单地出钱购买到优质原木,这些官吏都得假手于北侗地区的各级土司,靠这些土司寻找优质原木的产地,组织人员砍伐和扎排漂运。这样一来,不仅各级土司因此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声望,同时还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当然其中的受益者还包括这一地区的侗族寨老们和侗族居民。他们只要与朝廷配合就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利润,并且获得朝廷的嘉奖。随着 “皇木”采办规模的扩大,这些中下级的土司和家族村社寨老的社会地位也会稳步地得到提升,从而持续地拖动北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最后,“皇木”采办仅是北侗地区社会转型的一个有限方面,更重要的力量是来自民间的木材贸易。与 “皇木”的采办不同,民间的木材贸易规格和质量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数量却大得惊人。一般而言,“皇木”采办的对象是那些数百年以上的巨型原木,而民间购买的木材则规格小得多,特别是耐腐蚀的杉木。优质木材价格虽高,但产量有限,市场的需求量也不大,只有皇家才用得起,但是普通的杉木则不然,一般的贫民百姓只要建房都得购买,而且这样的杉木在整个北侗地区年年供应,其产出周期只需十几年到二十几年,因而民间的原木采伐业能够很快地形成规模化的产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北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转型。
二、北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转型后的特点
在木材贸易未兴盛以前,北侗地区最富有的地带是那些稻田密集的宽谷坝区,但在原木贸易兴盛后,北侗地区的富裕地带开始向山区转移,并且最终造就出山区比坝区更为富裕的格局,这与土地资源的占有情况直接关联。不管是名贵的 “皇木”,还是普通民众用的建筑用材,都需要占用大量的宜林地。位于坝区的侗族村社稻田多,坡地少,粮食有余而宜林地欠缺。处在山区的村社则不同,稻田不多,但坡地宽广。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并结合对这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实地调查,其社会经济文化转型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 “自种自食”转型为 “以粮为食,以林为用”①侗族“以粮为食,以林为用”是一种双轨制的经济生活方式,即以水田稻作及养鱼为食,以山地林材产品为用。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当木材贸易规模不大时,北侗地区的居民只需要砍伐天然林,顺河漂运就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但随着木材贸易的扩大,特别是普通建材需求的扩大,采伐天然林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人工种植杉木就必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当然,完成这样的经济转型需要一系列的知识、技术和技能的创新,北侗地区的侗族居民在吸取汉族、土家族、苗族的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之上,创新了一整套人工营林技术。其具体内容包括:用刀耕火种耕地,用林粮间作的办法实现营林和护林;用逐年间伐的办法逐步地实现林地的更新等[3]。随着这些技术的完善和健全,北侗地区人工营林的面积得到飞速的发展。在明代中后期,人工营林面积已经超过天然林的面积。杉树成为人工营林的主要树种,也成为北侗居民发财致富的主渠道,最终使北侗地区稻田的种植面积被稳定下来,不再增加,因为生产的稻米仅供当地的居民使用,而人工营林地的面积却得到扩大,于是 “以粮为食,以林为用”的社会经济文化格局就此定型下来,并最终取代单纯的 “自种自食”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
其次,木材贸易同样也刺激了北侗地区侗族家族村社内部社会结构的转型。北侗地区早年的家族村社是将大量的宜林地作为家族的坟山利用,整个天然林虽说是家族的公产,但使用的频率很低,大量的木材都是让其自然地枯死,既未考虑更新,也不考虑采伐。村寨的寨老竭力控制的只是稻田而已,而稻田的耕作又得由具体的家庭去承担,寨老们要做的仅是调节各家庭之间的用地和用水的纠纷。随着人工营林业的发展,家族村社的管理重心也随之向坟山转移。于是坟山上的木材得到了及时的采伐,采伐后还得进行及时的更新,因而,如何管护人工林成为家族村社最重要也是最能够发财致富的管理事务。但管理重心无论怎么转移,家族内部人人平等的原则仍然延续,于是家族村社的寨老就只能按照家族内部人人平等的原则,建立款规和款约制度,并按照股份分红的办法合理地使每个家庭分享到从人工营林业的经营当中获得的财富。阳河和清水江沿岸,侗族村寨内堆积如山的林业契约文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转型基础上得到发展并积累到了今天。北侗地区的社会转型过程,表面上看仅是从坟山转换为家族的人工林地,但实际上的社会转型内容比这要丰富得多。家族村社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纠纷调解机构,而是成为了一个财富分红的机构。
再次,男女性别的分工发生逆转。早年的男劳动力主要投身于稻田种植,妇女则主要承担家务劳动,但在人工营林业兴起之后,男劳动力转身投向营林劳作,妇女转而接管了稻田耕作。在人工营林业得到发展后,财富多寡的标志则转向为银两和铜钱的积累。更重要的还在于,社会风尚也在发生了转变,能够进入汉族地区从事木材贸易成为北侗地区居民的时尚,仿效汉族的生活方式也蔚然成风,甚至原先的姑舅表婚和不落夫家的习俗也受到冲击[4]。具体表现在木材贸易的财富积累,直接地改变了稳定的姑舅表婚,劳动力的缺乏又必然缩短不落夫家的时间。总之,人工营林业的发展导致了侗族社会经济文化的一系列转型,而不是简单的经济重心转型。
复次,随着人工营林业的发展,北侗地区家族村社之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此之前,家族村社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家族村社之间的互惠、谅解和协调。这一切,北侗地区主要靠一系列的家族村社的集体活动就能实现。但在人工营林业兴起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家族之间地界的划分与直接的经济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贩运木材的航道成为发财致富的依托,每个家族村社都会为此而争夺,这样一来各家族村社之间原先那种充满温情的和谐就不得不靠严密的侗款和习惯法来维系,各家族村社之间必须定期地、频繁地举行 “合款”,商定各种习惯法条规。其具体内容涉及到地界的划分,土地山林的租赁、抵押,木材的过境报偿,木材航运、航道的权责义务等。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侗规和侗款,其发端期都是在明代中叶,这足以看出家族村社之间按习惯法办事,其实也是人工营林业高度发展与繁荣的产物。
最后,家族村社与外族居民的关系也在人工营林业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人工营林业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前,北侗地区的各家族村社原则上不允许外族居民进入和定居,而且侗族居民和其他民族也很少通婚。家族村社寨老们的管理原则就是坚持内外有别,只对本家族的成员负责任,不理会外族成员。但人工营林业发展后情况就不同了,规模性的林业生产亟需劳动力,长线的沿途贸易又需要获取内地的市场信息,还需要引进中转商,更由于林业生产需要多工种的配合,引进不同的人才势在必然,因而在人工营林业得到初步发展后,外族居民进入家族村社定居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事实。据田汝成《炎徼纪闻》记载,早年接纳汉族居民到家族村社内部定居,是启用 “打老庚”“认同年”的方式实现的[5],也就是每个家族村社把他们需要引进的汉族人才,与本家族的某一个人结拜为兄弟,然后以理想化的血缘兄弟的身份住进该家族村社内部。当然,这样的结果会诱发众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这些汉族居民的社会待遇问题就可能引发争议。如果引进这样的人太多,他们的通婚也会成为社会问题,与其他村社之间的债务也会引发新的问题。应当看到,在传统的家族村社框架内是很难解决的,传统的 “合款”方式也很难解决这样的难题,因而在人工营林业充分发展后,也就是到明代后期派生了众多的社会经济新现象,并在如下3个方面最具代表性:其一,随着进入北侗地区的汉族居民越来越多,导致在木材贩卖的河流航道上形成了侗族村寨与汉族村寨交替布局的格局。原因在于,大量的汉族居民定居,突破了家族村社的管理权限,因而不得不分寨而居。其二,不管是侗族村寨还是汉族村寨对官府的依赖越来越强,一旦侗族和汉族之间发生纠纷,就不得不到官府去提起诉讼,恳求官府做出仲裁。于是相应的仲裁过程和结果又会以碑刻、文书等方式保存下来,这成为北侗地区一种重要的人文标识。这样的碑刻、文书,有的涉及到侗族和汉族的婚姻问题,有的涉及到地界的划分问题,有的涉及到资源的利用分享问题,内容极为丰富,成为侗族地区社会历史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各级地方行政部门辖地范围犬牙交错,致使有些村寨被迫实行多头管理。当然这是一种各方都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但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是汉族和侗族居民的流动而造成的,汉族居民原先所属的行政机构,在汉族居民迁入侗族地区后,由于没有脱离领属关系,因而其原属的行政机构还有权管辖这样的汉族居民。一旦这样的汉族居民在侗族地区购置土地定居后,又得接受定居地区的地方行政管理,而且地方行政部门往往会以管理侗族的方式去管理他们。这样一来,同一个村寨就会很自然地出现一个村寨同时接受两个行政单位管辖的状况,而且各个行政单位的辖地也会变得互相插花和犬牙交错。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侗族居民进入汉族地区因经营木材贸易而定居下来,一旦购置土地,落了籍也会导致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多头管理。这种现象在明清之交的北侗地区极为普遍,其实质正好是人工营林业飞速发展的一种社会性标志。应当看到,汉族居民大量地移居侗族地区不是一种简单的事情,在整个明代这一行动也曾诱发过众多的冲突。早在明朝建国初期,明廷建立铜鼓卫和五开卫时,就引发过侗族的反抗,为此,明廷不得不派遣两位亲王远征黎平[6]。事平后,又派遣汤和统兵和侗族居民一道耕种,以便消除侗族居民的疑惧。经过长期的磨合,这两个卫的设置才最终被确定下来。与此同时,为吸引侗族居民与明廷合作,明廷在所建的各个卫所中也实施了很多的优惠政策。比如,镇远卫下属的邛水土司,在镇远府建立后虽说拨归镇远府统辖,但朝廷对这个土司的照顾依然未改。该土司所辖的居民在名义上尽管也要交税、服役,但由于该土司的辖境内有驿路的主干线穿过,当地的侗族和苗族居民随时应卫所的招募,参加货物和信件的传递,还临时充当武装力量维护地方治安,而按照明廷管理的定制都可以获得金钱和实物的回报,结果该土司所辖的居民交给国家的税赋还不到他们可以从驿路上所获报偿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只要为卫所提供劳役,就可以生活得十分优裕。如果加上他们经营木材贸易和林副产品所获得的收入,其收入更为可观。应当看到,明廷的卫所建制虽然需要征用侗族的土地,但实质上各侗族家族村社从中获得的实惠反而更大;同时,还应当看到,这种经济上的诱惑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北侗地区的侗族居民乐于接受汉文化要素,积极地与明廷配合,显然与经济上的这种实惠相关联。也正因为如此,贵州自建省后,整个北侗地区进入了平稳发展、社会安定的大好时期。侗族居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北侗地区开始稳步地向汉文化靠拢。但与此同时,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侗族也进而创新性地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这就是在北侗地区具有标志性的 “林粮兼营”生计模式和与此相关的严密的 “侗款”组织。
三、讨论与结论
此前的史学研究习惯于认定与汉族关系越密切就表明相关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就越高,如果按照这个习惯性的分析模式,得出的结论不言而喻要认定北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而南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但这是一种与事实相左的分析模式,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综合性的发展,并不是某一项社会经济指标的发展,光看市场经济发育的程度不能完整地表明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体到南侗地区而言,他们与汉族地区的商贸活动水平虽然低于北侗地区,但经济的发展水平、社会的安定程度、人们的生活幸福感指数等却不一定比北部侗族地区低。事实上,南侗地区的社会经济组织虽然沿袭的是千百年来的侗族传统,但社会经济组织的有效程度却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举例说,在整个明代,整个南侗地区,社会动荡的频率和烈度都很低,社会极为安定和舒适。南侗地区侗族居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并不逊色于北侗地区,以至于明朝靠行政力量迁往南侗地区的汉族居民,在明代时,往往是很快地就融入到当地侗族社会之中,成为当地侗族的成员,或者说他们是被 “侗化”,而不是侗族居民被 “汉化”[7]。查阅南侗地区的现存家谱后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不少家谱都有内谱和外谱之别,内谱是用汉字当中的同音字记录侗语,记录的内容是各个家族自己内部的血缘传承,而外谱则是用汉字记汉名,而且对祖先血缘的追溯都要追溯到内地汉族中的名门望族。其实这两种家谱反映的是同一个家族村社的血缘传承系统,其间的差异是表面的,因为即令侗族乡民确实存在着汉族的血缘,确实与内地的汉族有血缘联系,但事实上经过若干代的生活后,他们其实已经成为真正的侗族乡民,对汉族血缘谱系仅是一种模糊的记忆而已,在实际的生活中几乎不会发挥明显的作用。
[1]杨庭硕.相际经营理论:跨民族经济活动的理论与实践[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5:204-205.
[2]罗康智.明史·贵州地理志考释[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5.
[3]吕永锋.清水江地区人工林经营中的水土保持手段述评[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4(1):123.
[4]罗康智.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与侗族传统婚姻习俗的变迁[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1):42-43.
[5]刘锋.百苗图疏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91.
[6]翟玉前,孙俊.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考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272-273.
[7]杜薇.百苗图汇考[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261.
[8]罗康智.侗族节日设置的层次类型及特点分析——以黎平黄岗侗族为例[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5).
[责任编辑:丹涪]
F316.23
A
1674-3652(2016)03-0029-05
2015-11-28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清代清水江中下游苗侗社会变迁研究”(11XZS032);贵州省教育厅社科研究基地项目“低碳经济视野下对侗族农业遗产的发掘与创新研究——以黔东南社区为个案”(2015JD130)。
罗康智,男(苗族),贵州天柱人。博士生,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民族学研究。
①文中所用的“北侗”和“南侗”不是指侗族分为南北两大支系,而是就其聚集地的分布范围而言。按照前人的研究,“北侗”地区大致包括贵州天柱、三穗、剑河、锦屏,湖南新晃、靖州等地;“南侗”地区大致包括贵州黎平、从江、榕江,广西三江、龙胜、融水,湖南通道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