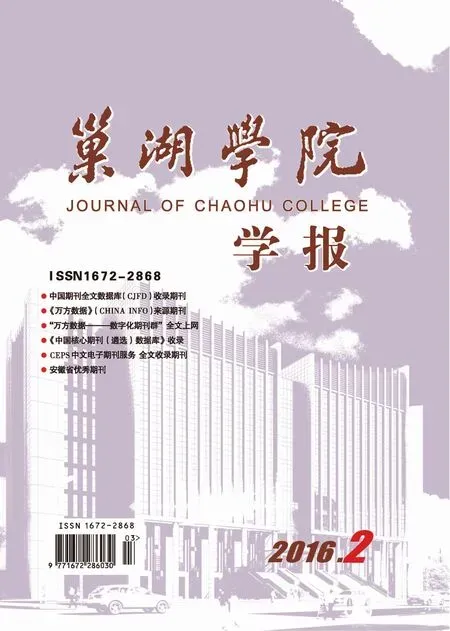试论明传奇中“集唐诗”的发展及其功能转换
2016-03-29安琦
安 琦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235000)
试论明传奇中“集唐诗”的发展及其功能转换
安琦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淮北235000)
摘要:唐诗在明代曾经出现过接受的高潮,整个文坛莫不以唐诗为宗,形成了浓厚的学习唐诗的氛围,“集唐诗”就是这个氛围滋润下的产物。它在早期的传奇中承担了下场诗的功能,在晚明时却转换了功能,担负起传奇作家表达哲学思想的需要。
关键词:唐诗接受;下场“集唐诗”;功能转换
有明一朝,文人对唐诗的推崇应该是空前的,从“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开始,整个文坛皆以唐诗为宗,社会上形成了浓厚的学习唐诗的氛围。传奇的下场“集唐诗”就是在这个氛围下产生的。下场诗,又叫“落场诗”,是传奇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每一出戏之末尾,起着总结剧情、制造悬念的作用。在早期的传奇中它是不规范的二句或四句韵语,到了中晚明逐渐出现了规则的四句绝句诗体,并采用唐诗,形成了“集唐诗”。早期的“集唐诗”依然承担的是下场诗的作用,而到了晚明时,其功能发生了转变,开始变成了戏曲家表达哲学思想的工具。
1 明代唐诗接受
明初建国,为巩固基业,朱元璋在思想上实行钳制政策,令天下之文人“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其子朱棣更是命“儒臣辑《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颁布天下。”[1]在严酷的文化专制下,思想界得到了统一,天下文人莫不以八股举业为专,文学之创作风潮甚微。当时诗坛流行的是“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和陈献章、庄昶为代表的性理诗派。台阁体以点缀升平,歌咏帝德,宣教皇恩为中心;性理诗派承袭宋儒之习气,以理趣、教化为诗歌之要义。两派创作均谐和于承平之世风,缺少性情。所以虽主政诗坛,在文学审美上却是平庸和低俗的。到了弘治、正德年间,为了扭转空洞浮华的诗风,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2]①徐朔方先生认为此观点并非李梦阳之观点的全部,以此来指代李之诗学思想,有失公正的“复古运动”。“复古运动”在明代共形成三次大高潮[3]。三次高潮开启和拓展了明代的唐诗接受的一个盛世。明代的唐诗接受是宋、金、元三朝所无法比拟的,从明代唐诗的整理和出版上,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弘治以前,刊刻的唐人诗集并不是特别的多,在选刻的范围上也看不出明确的倾向。进入正德以后,唐诗的出版热潮逐步形成。不但个人选集大量的发行,汇刻唐诗诸家的总集、丛书也大量出现[4]。据统计,明代编辑的唐诗选本至少有323部,其中大部分是弘治以后编定的[5]①孙琴安先生在《唐诗选本提要》中统计明人所辑唐诗选本为216种。本文采用的是金生奎先生在《明代唐诗选本研究》中的统计结果。唐诗的流行,使得明代中后期的诗坛蒙上了浓郁的唐人风韵,营造出了空前的唐诗氛围。文人作诗皆以唐诗为范本,探讨唐诗,品评唐诗成为当时最时髦的话题。尽管后期的公安派、竟陵派都力图摆脱唐诗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摆脱唐诗以前,他们或多或少的都受过唐诗的影响。
2 传奇戏曲中“集唐诗”的发展
“集唐诗”的发展轨迹是与唐诗接受的轨迹相一致的,它兴起于明代正德年间,繁盛于万历年间。二者通过戏曲家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关系。“集唐诗”的艺术源头是“集句诗”。“集句诗”是在西晋时形成的。元人陈绎曾在《诗谱》中云:“晋傅咸作《七经诗》,其《毛诗》一篇,略曰:‘聿修厥德,令终有俶。勉尔遁思,我言维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觌面目。’从乃集句诗之始。”[6]到了宋代,这种诗歌体式始有“集句”之名[7]。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云:“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谓无人能对,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荆公始为集句诗。”[8]集句诗发展史上明代开始出现专集唐诗的“集唐诗”。传奇戏曲最早的“集唐诗”出现于陆采于正德十年(1515)创作的《明珠记》中[9-10]②郭英德先生在《明清传奇文体研究》中认为最早出现“集唐诗”的作品是梁辰鱼的《浣纱记》。笔者不同意此观点,笔者在早于《浣纱记》创作的《明珠记》中发现了下场“集唐诗”。根据程华平先生的《明清传奇编年史稿》中考证,《明珠记》创作于正德十年(1515)。全本都使用“集唐诗”是从汤显祖的《牡丹亭》开始的。后来的戏曲家如阮大铖、洪昇都承袭了这股风潮,在剧作中皆采用了全本集唐的形式。
与自己创作诗歌相比,“集唐诗”的难度更大。它不但要考虑平仄的对应问题,还要考虑声律的协调。所以如果没有受过良好诗学教育,不熟悉唐诗,是无法完成集唐的。相比于元代戏曲家拙于诗词的创作,明代戏曲家多数受过良好的诗学教育。他们自幼熟读唐诗,谙熟格律,精于作诗。在前后七子的推动下,“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创作理念成为一时之风尚。浓郁的唐诗品读和仿作氛围使得戏曲家自幼便深受唐诗风格的影响。而且《唐诗品汇》等大型的唐诗丛书以及《广韵》《集韵》《中原音韵》等韵书的出版,也为诗学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正是这多种因素的组合造就一批有思想、有诗才的戏曲家。从明代戏曲家的个人著述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戏曲家在创作传奇戏曲的同时也纷纷创作有个人的诗集。如汤显祖,他十二岁就开始作诗,十三岁受教于徐良傅[11],二十五岁就刊印了诗集《红泉逸草》,二十七岁编纂了第二部诗集《雍躁》,三十一岁编纂了第三部诗集《问棘邮草》[12]。综其一生,共创作了2260余首诗。正因为有如此良好的诗学基础,所以他在《牡丹亭》中可以选用128位诗人的280句诗组成70首诗[12],而且这些“集唐诗”均完美的和剧本结合在了一起。又如阮大铖,他出生书香门第,科举世家,很早就显露出诗歌创作的才华。他爱习唐诗,自称“以陶王为宗祖,以沈宋为法门”[14]。在《春灯谜》《牟尼合》中,他也使用了全本“集唐诗”,充分显示了他的诗学修养。
3 “集唐诗”功能的转换
“集唐诗”的出现给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同时也间接的提升了传奇的文体地位。它给传奇吹入了一股传统的雅文化之风,也带来了新的审美效果。但是随着传奇创作的繁盛,这种下场“集唐诗”也受到了许多戏曲家的批评和诟病。王骥德就认为:“还有集唐句以逞新奇者,不知喃喃作何语矣。”[15]黄振认为:“上下场诗,前人多集唐句,文气本不贯穿,不过拈一两句与本出稍有沾染者入之,余皆闲文,且烂套可厌。”[16]王骥德等人是从场上之曲的角度,反对对下场诗过度的雅化,更反对生硬地采用唐诗。应该说这些批评都有一定的道理。的确,“集唐诗”发展到晚明时确实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许多戏曲家为了迎合宗唐诗的风气,不顾自己的才力,硬是在传奇中塞入“集唐诗”作陪衬。这样的创作态度自然引发了批评家的不满。所以出现对“集唐诗”的严厉批评也是不足为怪的。
其实如果我们将王骥德等人的批评与公安派对前后七子的批评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传奇集唐诗的发展与明代唐诗的发展方式高度吻合。传奇戏曲中的“集唐诗”是在唐诗运动的推动下出现的。但是随着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理论的泛滥,对唐诗经典的吸收变成了机械地模仿,于是诗歌创作出现了一股逆流。“集唐诗”在戏曲中的发展也在一个高峰之后开始走入死胡同。在王骥德、臧懋循等人的推动下,元曲开始被重新尊为经典,质朴、粗犷的语言成为戏曲界认可的语言风格。在这种情况下,集唐诗也开始走向衰落。在衰落的同时,“集唐诗”也开始酝酿着浴火重生。到了晚明,下场“集唐诗”已经不再单纯的承担下场诗的功能了,在戏曲家的笔下它已经变成了他们表达自己哲学思想的一个工具了。所以并非所有的与剧情不和谐的下场“集唐诗”都应该批评,应当区别的对待。有些剧作家为了用“集唐诗”表达自己创作的思想和观点,在与剧情联系程度上就不做过多的考虑。这方面之代表莫若汤显祖的《牡丹亭》。
《牡丹亭》的下场“集唐诗”历来是被人认为是与剧情完美结合的,与洪昇的《长生殿》中的“集唐诗”并称双璧。但是如果细细的去品味,也多有偏离剧情之词。如第八出《劝农》时描写杜宝下乡劝农,勤于政事,下场诗是“闾阎缭绕接山头,(杜甫)春草青青万顷田。(张继)日暮不辞停五马,(羊士谔)桃花红近竹林边。(薛能)”这首诗虽然也是写乡间的风景,但是却与劝农的主题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所以徐朔方先生虽对其“集唐诗”颇多赞美之词,但是同时也认为“可能这是多余的奢侈之笔,多半无助于作品的提高。”[17]而实际上,汤显祖的本意也不是在于利用“集唐诗”来加强剧情,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表达他的“至情”的哲学主张。
“至情”是汤显祖在晚明反理学的大潮下提出的哲学主张。理学发展到晚明时,已经是漏洞百出,穷途末路。冲破理学的禁锢已经不可避免,从王阳明的“心学”到李贽的“童心”说,反理学的大潮一浪接一浪,各种思想主张纷纷涌现。汤显祖的“至情”在众多的哲学主张中独树一帜,它上承唐人风韵,下接晚明的思想解放需求,强调以情反理,而表达情之方式就是下场的“集唐诗”。在汤显祖看来,唐人是有情之人,唐代也是有情之时代,“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时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娭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18]所以“集唐诗”表达的就是一种自由无羁的精神和畅所言情的唐人风韵。据赵山林先生统计《牡丹亭》中的“集唐诗”多数用的是晚唐的诗。晚唐的诗风清丽,极善于表达情感,用它作为下场诗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与《牡丹亭》的“情可以使人生死”的主题吻合。从这个意义上说,“集唐诗”虽然无法完成下场诗的功能,但是却在更高的层面上提升了作品的哲学内涵。因此,“集唐诗”的功能的转换,在一定程度是对下场诗的一种发展。
可惜这样的发展仅仅局限于一部分有思想的文人圈子里,并没有持续太久。当传奇发展进入清代后,清廷的文字狱和思想的钳制使得文人对戏曲、哲学的思考大大减弱。当花部戏强硬的占领戏剧界时,文人之戏剧基本走到了尽头。“集唐诗”是文人思想的火花。当文人戏剧走向了末路,“集唐诗”也不免走向寿终正寝,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标本。只是这个标本依然美丽,值得玩味。
参考文献:
[1](清)陈鼎.东林列传:卷二[C]∥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三.台北:明文书局,1991:135.
[2]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00.
[3]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
[4]陈伯海.唐诗学史稿[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504-505.
[5]金生奎.明代唐诗选本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7.
[6](元)陈绎曾.诗谱[C]//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623.
[7]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137.
[8](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艺文[M].长沙:岳麓书社,1998:118.
[9]郭英德.明清传奇文体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1;
[10]程华平.明清传奇编年史稿[M].济南:齐鲁书社,2008:19.
[11]徐朔方,编著.汤显祖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58:12-13.
[12]徐朔方.汤显祖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5.
[13]王育红,吕斌.《牡丹亭》“集唐诗”探析[J].中国韵文学刊,2005,(6):71-76.
[14]胡金望.人生喜剧与喜剧人生——阮大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7.
[15](明)王骥德.曲律[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142.
[16](清)黄振.石榴记:凡例[C]∥清嘉靖己未拥书楼重刻本.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33.
[17]徐朔方.汤显祖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1.
[18](明)汤显祖.青莲阁记[M]∥汤显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113.
责任编辑:李晓
作者简介:安琦(1979-),女,安徽萧县人。淮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音乐学及文艺美学。
基金项目:淮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3zdjy095);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SK201639);淮北师范大学校级项目(项目编号:2014xp042)
收稿日期:2016-02-08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68(2016)02-007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