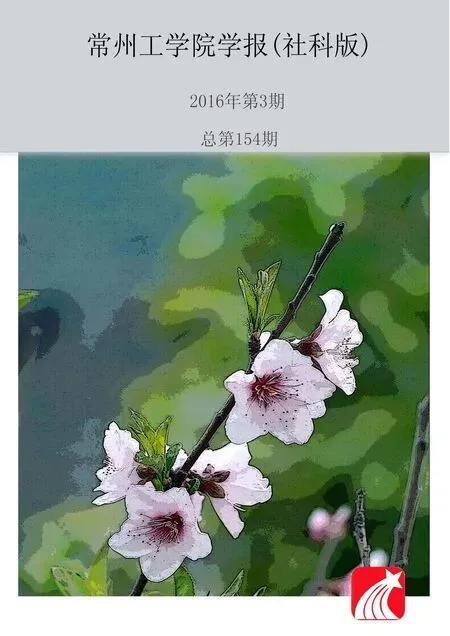论《博古叶子》插图版式的文人特质与图式的高古格调
2016-03-29温巍山
温巍山
(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苏常州213002)
论《博古叶子》插图版式的文人特质与图式的高古格调
温巍山
(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苏常州213002)
摘要:文章对明代画家陈洪绶晚期插图作品《博古叶子》的基本背景、版式与图式表现作了客观分析与研究,认为该作品的创作与其当时的生存状态紧密关联,插图既注重了故事情节和场面刻画,又凸显了文人特质与高古格调,线性表现散逸、随性,《博古叶子》是陈洪绶晚期插图创作的代表作品。
关键词:《博古叶子》;版式;图式;文人;高古中图分类号:J205
甲申之变使陈洪绶(号老莲)对仕途的最后一丝幻想也彻底破灭,这种打击使他悲痛欲绝,但趋于平静之后反而能全心全意地投入绘事,老莲的传世精品也大多完成于这个最后的时期(1645年至1652年),《博古叶子》便是其中的一件。就老莲的插图创作而言,这件作品属于晚期插图的“绝唱”作品,人物造型古意盎然、淡雅天真,中期插图的严谨造型与装饰气息已演变为信手拈来、浑然天成,晚年的老莲虽然为生活所累,但绘画状态已进入巅峰阶段。本文将从《博古叶子》的版式、图式两个方面切入,分析、探讨其幽静、冷寂的图像中所蕴含的文人特质与高古格调。
一、基本背景
《博古叶子》(翁万戈藏)[1]194,五十开,纸本,雕版木刻插图,画面尺寸为16 cm×8.7 cm,创作时间为清顺治八年(1651年),这是陈洪绶去世的前一年,作画地点为杭州吴山火德庙的西爽阁。这套叶子历来有“三绝”之称,题赞、酒约来自明代著名戏曲家、抗倭名将汪南溟撰写的《数钱叶谱》,镌刻出自徽派雕版名手黄建中之手,图画、书法出自“南陈北崔”的陈洪绶之手。明朝灭亡以后,老莲弃绝仕途,基本靠卖画维持生计。世事难料,十几年以前,为了友人周孔嘉一家八口的生计而创作了著名的《水浒叶子》,十几年以后,他又为自己一家二十口的生计创作了《博古叶子》,老莲的自题这样写道:
廿口一家,不能力作。乞食累人,身为沟壑。刻此聊生,免人络索。唐老借居,有田东郭。税而学耕,必有少获。集我酒徒,各付康爵。嗟嗟遗民,不知愧怍。辛卯暮秋,铭之佛阁。[1]195
可以看出,作为明朝的遗民、现实生活中的职业画师,老莲的家境已今不如昔,特别是1646年以后,仅存的一点家业也悉数毁于硝烟动乱,日子过得相当清贫,身体也不如从前,但老莲人穷志不穷,他宁愿向市井的酒徒讨生活,也绝不迎合权贵。从《春风蛱蝶图》(长卷,1651年,上海博物馆藏)的题跋中可以得知,《博古叶子》是老莲回赠“二十年兄事洪绶”[2]18的友人戴茂齐。戴茂齐为安徽新安人,与老莲相交甚厚,经常接济老莲,而老莲也“往往以笔墨周友之急”[1]258,可谓志同道合。《博古叶子》画了48个人物故事,这些故事人物多出于《史记》《汉书》,既有陶渊明、杜甫这样的文人雅士,也有董卓、石崇那样的奸恶豪奢之徒。画面以“钱”为主线,以人物刻画为中心,运用插图的叙事性、角色的丰富性与当时的市场需求接轨,真实传达晚明时期文人士大夫“求奇”“求异”的审美情趣。从“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的“一文钱”杜甫,到“其卧徐徐,其视于于”的“空汤瓶”陶渊明,画面折射出陈洪绶当时的穷愁和“独善其身”的状态,唯有在酒与笔墨淋漓之中才能得到解脱。酒牌上的题赞多为一些古僻、难懂的句子,如“谓尔不群,尔伉大君;谓尔不驯,尔多令人”[1]198等,再加上行草的书写,非一般市民能够阅读,所以,《博古叶子》镌刻成册后发行对象也和《水浒叶子》一样,主要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用于礼品与收藏,但也不排除它酒赌两用的实用功能。
二、版面设计的特色与文人特质
《博古叶子》的版面设计基本沿袭了传统“上文下图”的线框结构,俗称“门框式”构成,简洁、明了,这个套路与《水浒叶子》基本相同,“门楣”为赌约,“门扇”为主体画面,而将题铭、题赞和酒令分置在“门扇”线框之外的左右,这一点与《水浒叶子》不同。将大量文字放在线框之外,可以使画面的视觉效果更加完整,这是《博古叶子》在版式设计上的一个重要特色,纵观明代雕版插图的版式,用行草书写在线框之外进行布局的架构几乎没有,只有一些题目、页码以工整的字体出现在线框之外,即使是“牌记插图”,文字也是以行楷书写在线框之内,如正德六年(1511年)建阳杨氏清江书堂刊本《新增补相剪灯新话大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闽建书林余绍崖刊本《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等,大量文字以“楹联”式的布局,对主体画面进行了分割,导致了主体画面空间的狭小和拥挤。老莲在创作《水浒叶子》的时候就对这种传统的插图模式进行了改良,去除了画面内多余的线条分割,在人物图形周围的空白之处随机书写。在《博古叶子》中,干脆将文字放在线框之外,这个富有创意的手法,应该来自文人画题跋的启示,我们从老莲的长卷创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字与画的组合表现,如《南生鲁四乐图》(长卷,1649年,苏黎世利特伯格博物馆藏)、《陶渊明归去来图》(长卷,1650年,美国檀香山美术学院藏)的画面文字的排列、字数与位置对画面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里不是简单的“意犹未尽”,而是一种“隔断”作用,即用文字分割画面、说明画面,使画面的每一小段相对独立,方便观众阅读,这种表现形式可以追溯到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明代插图的题款非常普及,一般多用行楷、行书,这样可以方便受众阅读,但无论是长款还是短款,一般都在线框之内。而叶子插图属于实用性很强的插图,画面上文字元素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题铭、题赞和酒令的位置经营,多采用中国书画的题款方式,如万历末年的《酣酣斋酒牌》、咸丰三年(1853年)任渭长的《列仙酒牌》,题铭、题赞和酒令的书写都采用典型的立轴题款方式。老莲晚年作画多用行草落款,字体清瘦,笔法劲挺,这种行草书写的文字,无论在“门楣”之内,还是“门扇”之外,都与刻板的线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营造了版面的文人特质,高居翰评价这些纸牌“代表了高艺术品质与实用功能的完美中和”[3]331。《博古叶子》的版式设计实际上划分了三个区域,既突出了画面“高艺术品质”的视觉中心地位,也将赌约、酒令等清晰地传达给受众,虽然是行草书写,但因为版面区域的“职责分明”,让受众在观看主体画面与阅读文字时互不干扰、一目了然,这也是老莲别具匠心之处。
三、图式的叙事特征与高古格调
清代戏曲作家汪光被在《跋章侯博古叶子》里用“《水浒》之传也以人,《博古》之传也以事”[2]498来概括陈洪绶两套叶子图式的不同特征。在早、中期的插图创作中,老莲的兴趣点主要在人物绣像性情姿态的刻画,到了《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时期,画面开始出现背景,但重点还是在人物表现上,人物体量依然较大,主体地位明显。而到了《博古叶子》时期,图式开始注重以故事情节、场面人物组合,虽然叶子的画面很小,但老莲营造的叙事场面却很气派,如《孟尝君》《卓王孙》等。小林光宏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同《九歌图》、张深之本插图相比,熟练的、即兴式的描写一概简略,这有小画面受限制的原因,事实上每一图都作了精心的构图。同是酒牌,《水浒叶子》一律无背景,各图描绘了大小基本相同的一个人物,《博古叶子》则能看出更加富于变化的插图创作痕迹。[4]84
这种“更加富于变化”的亮点首先来自老莲“精心的构图”,构图紧密地围绕着故事进行变化,更加符合插图创作的基本规律。《孟尝君》画的是名“倾七国”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田文宴请宾客的场面,老莲非常智慧地将前景布置了树木,特别是左面松树茂密的松针团块,与右边的饮酒人群形成了“藏与露”的反差,以田文为首的人物动势与目光和松针后面隐隐约约的人物进行互动,同时,加入了上酒的家丁、小厮,使画面进一步产生“流动”“穿梭”的气氛,营造了“客三千”的强大阵容。《卓王孙》的主角是汉武帝时蜀郡临邛的大富豪——卓王孙,但实际表现的却是《凤求凰》,即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卓王孙附庸风雅,却赔上了自己的掌上明珠。老莲通过一个巨大的屏风将画面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前景是大才子司马相如正专注地弹奏,后景是正在偷听的绝代佳人卓文君,画面中,悠扬的旋律正在演绎着一个爱情故事。老莲用屏风的布白衬托了司马相如,用清奇古怪的松树将卓文君隐藏在幕后,形成前亮后虚、一阳一阴的画面效果。同样,在《石季伦》《董贤》等画面中都可以发现这种运用场面动态人物的组合与故事情节巧妙结合的图式手法,但这种叙事图式也由于老莲人物造型的怪诞、线性的古拙以及简洁的背景和古色古香的器物,使画面散发出浓重的文人画气息和高古意味。
高古是人们对陈洪绶绘画的最高评价,认为他的画面有太古之风、晋唐意味,但老莲的高古不是复古,更不是摹古。《二十四诗品》有高古品云: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踪。
月出东斗,如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
虚伫相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玄宗。[5]26
这里的高古,指的是诗境风格,但老莲的高古同样具有高洁脱俗、古朴质实的深邃内涵,对于晚年的老莲来说,高古不仅是其绘画风格成熟的一个重要标杆,而且是其内心清逸世界的写照。甲申之后,老莲从极度痛苦的阴影中走出,对于个人生与死已经看得很淡,他亲近佛门,研究画理,将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融入了水墨丹青之中,他在诗中写道:“千山投佛国,一画活吾身。”[2]119这里的“活”字直接关联了“画”与“身”,他为“画”而活着。这种清寂、素朴的精神状态,将老莲送入了一个古怪、幻象与永恒的表现空间,《蕉林酌酒图》(立轴,约1649年,天津博物馆藏)、《吟梅图》(立轴,1649年,南京博物馆藏)就是他此时最好的写照。《博古叶子》的创作同样也体现了这种生命状态,人物造型、线性表现与中期插图相比,更加“高古奇骇”,《水浒叶子》透出的高古气息,在这里更加古怪、冷寂和自然。首先,在人物造型方面,各种大中小型的人物表现都很夸张,不太注重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比例关系,画得非常随意,似乎一切都是一种感觉。如《梁孝王》,画面前景手持名片的邹阳、枚乘两位文学家明显体量较小,而后面的梁孝王不仅体量大,而且行大礼的弯腰幅度十分夸张,突出了礼贤下士的主题。就人物组合中的比例而言,主角明显较大,其次是男人,女人多娇小玲珑,如《金张许史》《武安侯》。就单个人物而言,头部较大,身体较短。就女人而言,头虽然大,但却是婀娜多姿,躯干苗条而且有强烈的扭动,明显有戏剧表演的身段意识,延续了老莲的一贯作风,如《董偃》《朱买臣》等,与同一时期的《折梅仕女图》(立轴,1650年,辽宁省博物馆藏)、《扑蝶仕女图》(立轴,1650年,上海博物馆藏)基本一致。就整体的人物动态设计而言,老莲紧紧抓住人物的个性并与故事情节巧妙结合,动态夸张并具有表演性,如《杜甫》“留得一钱看”的困窘模样,《陶渊明》“其卧徐徐,其视于于”自得其乐、浑浑噩噩的醉姿,我们似乎看到陈洪绶此时的影子。
在线性表现方面,许多学者都认为老莲晚年的用笔走向圆润,犹如春蚕吐丝、行云流水一般。如小林宏光认为《博古叶子》“增加了柔和的线描”、“衣纹线、轮廓线多用曲线”[4]98。而陈传席的看法就更加全面、客观一些:
线条布置愈趋自然,散逸疏旷,不像壮年时那样凝神聚力、细圆而利索,但更加苍老古拙,勾线也十分随意,意到便成。有些线条又回复了早年的一些特征。但早期是不纯熟,晚期是纯熟后的自然浑朴。[6]164
从《董贤》《虬髯客》等画作,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随意天成的圆笔线条,可以看到顾恺之、阎立本、吴彬等人的影响,但线条的旋转、起伏更加随性、自在。圆笔的弧线为《博古叶子》的主体线性,这种弧线在《宜文君授经图》(1638年,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中就已经出现,只是当时线性较工性,而此时的线性完全是写性,更加苍老、劲健。另外,《博古叶子》的线性也是呈多元状态,并非都是曲线。在《百里奚》《原宪》中,我们可以看到方圆结合的线条,起笔的捺脚、转折都有明显的停顿和力度。在《吴王濞》《吕蒙正》中,可以看到李公麟、丁南羽的线性感觉,铁线描和钉头鼠尾描的成分更多一些。在《卫青》《国氏》等画面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水浒叶子》的“方折直拐”,只是“锋芒”不再,多了几分老辣和散逸。从老莲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中,也可以发现这种线性状态,如陈起德收藏的《史实人物图》(长卷,1647年),就是方折和圆转线性有机结合的典型案例。《摹古双册》(绢本册页,约1651年,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中的《罗汉图》《苦吟题石图》,将这种线性的反差推到了极点。可以看出,崇祯十五年(1642年)以后,老莲入赀国子监生,招为舍人,饱览内府藏画,“艺事益进”,在造型与线性表现上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技艺日益提升。到了《博古叶子》时期,全然一派“古淡天然”“易整以散”的高古气象,并提出了:
然今人作家,学宋者失之匠,何也?不带唐流也。学元者失之野,不溯宋源也。如以唐之韵,运宋之板,宋之理,行元之格,则大成矣。[2]21
这是老莲在顺治八年(1651年)四月为林仲青题画《溪山清夏图》所作的长题,也是老莲晚期绘画的艺术主张和个人总结,对唐宋传统的认识更加精辟、深刻,此时的笔意也越发“渊雅静穆”“稚拙苍浑”,无论是图式、造型与线性,完全是自我心境的流露。
四、结语
作为陈洪绶的最后一件插图作品,《博古叶子》不仅呈现了“对于富贵与世俗名利的冷嘲热讽”[3]331,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文人画家参与插图创作,并将文人画的创作理念与实用图形相融合,提升了实用插图的审美价值和收藏价值。老莲的创作实践,不仅在插图领域里展现了独特的高古格调,也对后来任熊的《列仙酒牌》以及清代插图、近现代插图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我们从各个角度与层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挖掘。
[参考文献]
[1]陈传席.陈洪绶全集:全4册[M].天津:天津美术出版社,2012.
[2]陈洪绶.陈洪绶集[M].吴敢,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3]高居翰.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1644)[M].王嘉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4]上海书画出版社.陈洪绶研究:朵云第六十八集[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
[5]郁沅.二十四诗品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陈传席.陈洪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庄亚华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6.03.013
收稿日期:2016-01-20
作者简介:温巍山(1959—),男,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600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6)03-0049-04